第一节 “艺术”与“文化”二词的观念梳理
一、汉语“文化”一词的观念梳理
“文化”一词虽是日文对英文“culture”、德文“kultur”的转译,但汉语中“文化”一词似可追溯至《易·彖传》之释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处的“人文”可理解为“人道”,“人所理解并创造的秩序系统,人伦道德”。“化”的古文字是“匕”,《说文》解释:“匕,变也”,进一步引申为“教化”、“化成”。因此,汉语里“文化”一词(包括日文里的“文化”一词)可以理解为以“人道”、“人所理解并创造的秩序系统、人伦道德”去“改变”、“教化”人类自我。在中国文学史上,“文”还可理解为与“质”相对的“文采”、“文饰”,也即文学形式。孔子认为“文”与“质”的配合要中庸合度,“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将艺术的形式分为“形文、声文、情文”三类。“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文”是“纹路”、“形式”、“外观”,它的内容、本体是什么呢?如果说上文所说的“人文”也即“人道”,那么“人道”是什么东西呢?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里,指出了这个“文”的本原。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唯人参之,性灵所钟,是为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大自然万物幻化,杂然纷呈,都是“道”之文,可是在天地之间,唯有“性灵所钟”的人类才能“仰观俯察”,将“天道”、“人道”打通天间,因“天道”、“人道”异质而同构,相异而体同。中国“人文”始自《周易》,而孔子集其大成,圣人“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天地(自然)之道与人伦之道相互打通,并通过圣人的“立言”而昭示人类群体。(1)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所谓“文化”,即是以历代圣贤智哲(尤其是儒家精英人物)的思想和理念来不断完善人类社会,它本身也像西方文化理念一样,有其强烈的优越感和使命意识,其逻辑前提是“道”。“道”是宇宙创化的普遍真理,用契合此“道”的“人文”、“人道”、“人所理解并创造的宇宙秩序,异质而同构的人伦道德系统”去教化天下,乃是将人类社会引向理想完善之境的不二选择。这是从狭义上看,从广义上看,所谓“文化”还指向依据“人文”和“天道”而逻辑地展开的典章制度、文学艺术、伦理规范、信仰系统等。刘勰《文心雕龙·情采》里的“文”,虽是“文学”之“文”,但它也是“人文”现象之一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文学”已被泛化为包括美术(五色之形文)、音乐(五音之声文)、辞章(五性之情文)的文艺系统,美术和音乐被提升到文学之前。(2)
中国文化(包括中国艺术)自成系统,且与埃及文化、古巴比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日本文化、朝鲜文化、东南亚文化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东方文化系统,其艺术精神也多有相互沟通互为发明的方方面面。(3)数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以及深受中国文化精神影响的中国艺术并未遭遇到颠覆性的挑战,只是到了近现代才遭遇了异质性的西方文明的挑战,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认为,目前中国已被一种并非中国的哲学和宗教所征服,但他接着又指出,以前中国也一度出现过佛教形式的宗教征服,最终被中国本土的世界观所克服,因此谁也不能确定,中国这种本土的世界观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再次成功地重申自己。中国艺术甚至整个东方艺术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性的挑战,晚近以来,中国绘画、戏曲、文学都曾被激烈地批判和否定过,如五四时期所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言论等,可是时过境迁,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在经过与西方文化和艺术的整整一百多年的磨合和碰撞之后,其可资开掘和发扬光大的价值也渐渐露出本来面目,这倒有些应和了汤因比在论及文明接触时的观察和思考。汤因比指出:“在这种接触中,‘侵略性’文明往往把受害一方污蔑成文化、宗教或种族方面的低劣者。而受害一方所作出的反应,要么是迫使自己向外来文化看齐,要么采取一种过分的防御立场。在我看来,这两种反应都是轻率的。文明接触引发了尖锐的敌意,也造成了相处中的大量问题,唯一积极的解决办法是,双方都努力地调整自己,相互适应……今天,不同的文化不应该展开敌对的竞争,而应该努力分享彼此的经验,因为它们已经具有共同的人性。”(4)
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的观念梳理
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克洛依伯和克莱德·克拉克洪在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一书中,列举一百多条不同的“文化”定义,并认为这些不同的“文化”定义可以归纳为9种基本的概念:它们分别为哲学的、艺术的、教育的、心理学的、历史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生态学的和生物学的“文化”概念。其中,被认为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定义出自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71年出版的《文化的起源》一书,这是一个人类学的“文化”概念。
文化或者文明,从其广泛的民族志意义上言,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
泰勒对“文化”的定义与中国古代时“文化”一词的含义很不相同。汉语传统中的“文化”一词的意思乃是以“文”去“教化”,是一个动词,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重点在“改变”、“变化”、“教化”、“化成”;而泰勒的这个“文化”是一个名词,凡是和人有关联的精神理念的方方面面都包括在内,它是一个内涵划分详细的类名词。
在泰勒定义的这个结构完整的文化架构中,艺术占据第三位,而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架构中,经济基础之上“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中,“文学、艺术”位于政治、法律、哲学、宗教之后,恩格斯的叙述:“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5),文学、艺术被置于政治、法律、哲学、宗教之后,艺术成了高高在上、远离经济基础的一个“飘浮的能指”,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显得无足轻重。然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文学、艺术承载着人类精神文化(上层建筑),具有特殊的抽象性,因而它们又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体现,所以高居在上。无论如何,马克思、恩格斯毕竟没有否认文学艺术在人类文化中所占据的一席之位。
自从泰勒这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名词出现之后,“文化”基本上成了一个带有结构性质和层级性质的类名词。所谓结构性质,是指“文化”一词是一个由分类细密的文化成分(因子)所构成的完整的结构。所谓层级性质,是指在“文化”系统里,艺术、宗教、哲学、习惯、经济、法律、伦理、道德、科学这些文化的构成成分具有等级性,如在泰勒的“文化”构成中,“艺术”位居第三。
除了上述泰勒所提出的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定义,尚有如下一些“文化”的定义较为著名。
(1)历史的“文化”概念。(克洛依伯和克拉克洪:《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
文化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从总体上看是指人类创造的财富积累:图书、绘画、建筑以及诸如此类,调节我们环境的人文和物理知识、语言、习俗、礼仪系统、伦理、宗教和道德,这都是通过一代代人建立起来的。
(2)社会学的“文化”概念。
文化是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语词,这里用作更为广泛的社会学含义,即是说,用来指作为一个民族社会遗产的手工制品、货物、技术过程、观念、习惯和价值。要之,文化包括一切习得的行为、智能和知识、社会组织和语言,以及经济的、道德的和精神的价值系统。一个特定的文化的基本要素是它的法律、经济结构、巫术、宗教、艺术、知识和教育。
可见,社会学的“文化”概念不同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文化”概念,它已不满足于罗列文化的构成因子,而把这些文化构成因子背后的价值、模式作为“文化”概念的重心,这比较接近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精神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的揭示,已从个别上升至一般,从现象走向本质,其中,艺术都据有其不可忽视的一席之位。(https://www.xing528.com)
因此,“文化”概念在汉语传统里和近现代话语环境之下,都是在本义的基础上,不断变化建构起来的。汉语的“文化”的本义是以天人之道所逻辑展开的礼仪、制度、规范去教化天下,而“culture”一词的拉丁语词根的本义是“cultur”,即“耕种”、“培育”。对比一下“文”的本义与“cultur”,就很有意味,“文”乃道体的外在显现,通过圣人,“垂文”而彰显天下、教化天下,“文”的本义的主观超验色彩强烈,而“cultur”作为与土地、作物、耕耘有关的生产劳作行为,其实践性、功利性明显,这或许与两种文化一重感性直悟一重理性分析的文化精神差异不无关系。
“文化”一词从出现、积累、发展、演变,直到当代,更扩展成为一个包括人类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含义更为丰富的类名词,(6)1982年在墨西哥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文化政策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给“文化”下了一个新的定义。
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系统、传统以及信仰。(7)
这个“文化”定义中,显然在精神文化层面上,“艺术”又被提升到显著的位置。在现代和当代中国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或对“文化”内涵的认知上,艺术无疑都在文化系统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位。如童庆炳在《文学理论要略》里对“文化”的界定:文化在这里是人类符号创造活动及其符号产品的总称,这种符号活动和产品总是凝聚着人类的信念、情感、价值、意义或理想追求。(8)
这个“文化”的定义看起来好像专指精神文化,但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科学活动也是一种符号创造活动,因此它实际上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二者,文学艺术作为语言符号和意象符号的创造性活动又最具有符号性,因而文学艺术在这个“文化”定义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徐复观先生在其名著《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更认为人类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即艺术,原文为:“道德、艺术、科学,是人类文化中的三大支柱”。接着他又指出: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中,实有道德、艺术的“两大擎天之柱”,“艺术”在文化价值系统里的位置仅在“道德”之下。(9)
三、“艺术”一词的观念梳理
今查《辞源》,“艺术”词条的解释为:泛指各种技术技能。《后汉书》卷二十六,《伏湛传》附伏无忌: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注: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晋书·艺术传序》:“详观众术,抑惟小道,弃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经。……今录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纪者,以为艺术传”。
可见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艺术”一词的含义与今天的“艺术”一词的含义很不相同。我们大致可以认为,“艺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指与生活实用有关的技能技术,与哲学(诸子百家)、文学(诗歌传统)相比,“艺术”显得并不那么高贵。传统社会中精通绘画、戏曲或某一种工艺的职业人士,常被称为“艺人”,在今天我们称之“艺术家”、“艺术大师”。创作敦煌壁画的古代的某个无名画师在今天就可能是一位艺术家而备受尊崇。孔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在当时都是实用性学科,其中恐怕只有“乐”,属于今天的艺术系统中一门艺术类型,到了汉代“艺”仅指“书、数、射、御”,“礼、乐”则因其超实用性而被排除在“艺”之外。比较一下“艺术”与“学术”、“道术”、“心术”的语义内涵就能从另一方面说明问题,“学术”、“道术”、“心术”乃“学”、“道”、“心”之“术”,它们之间是“体与用”的关系,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而“艺术”一词的两个词素“艺”与“术”是并列关系,“艺”与“术”一样是技能技巧。
 (“艺”的甲骨文)是一个象形文字,表示以手培植或扶持树木。《说文》上对“埶”(或作“兿”)的解释是:种也,即种植的技术。《广韵·集韵》上对“術”的解释:“術,技术也。”可见,“術”与“埶”一样指特殊的技艺、技术。英文“art”的词源拉丁文“ars”也是“技能”、“本领”的意思,其进一步的词源希腊文“techne”也是指一种“技术”、“技艺”,东西方艺术的本义都是具有形而下的品质,(10)不仅如此,西方的“culture”(文化)一词的本义与今天的含义也有极大的区别。
(“艺”的甲骨文)是一个象形文字,表示以手培植或扶持树木。《说文》上对“埶”(或作“兿”)的解释是:种也,即种植的技术。《广韵·集韵》上对“術”的解释:“術,技术也。”可见,“術”与“埶”一样指特殊的技艺、技术。英文“art”的词源拉丁文“ars”也是“技能”、“本领”的意思,其进一步的词源希腊文“techne”也是指一种“技术”、“技艺”,东西方艺术的本义都是具有形而下的品质,(10)不仅如此,西方的“culture”(文化)一词的本义与今天的含义也有极大的区别。
在古希腊,有诗歌、舞蹈、绘画、雕塑、悲剧等概念,但没有将它们统一起来的“艺术”的概念。缪斯掌管文艺号称文艺女神,但其掌管的历史与天文不是今天的艺术,并且,视觉艺术不属于缪斯的掌管范围。
大约自公元4世纪起,西方有所谓“七艺”——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成为欧洲高等教育的标准课程。这个“七艺”系统和孔门“六艺”系统一样,重在实用性的技能技巧。至中世纪又在“七艺”的基础上,增加七种手工艺术——毛纺、军事装备、航海、农艺、狩猎、医术、戏剧。(11)直至17世纪末,佩罗(Charles Perrault)明确将美的艺术与自由艺术区别开来,将艺术与科学区别开来,其美的艺术系统里,包括雄辩术、诗歌、音乐、建筑、绘画、雕塑、光学和机械力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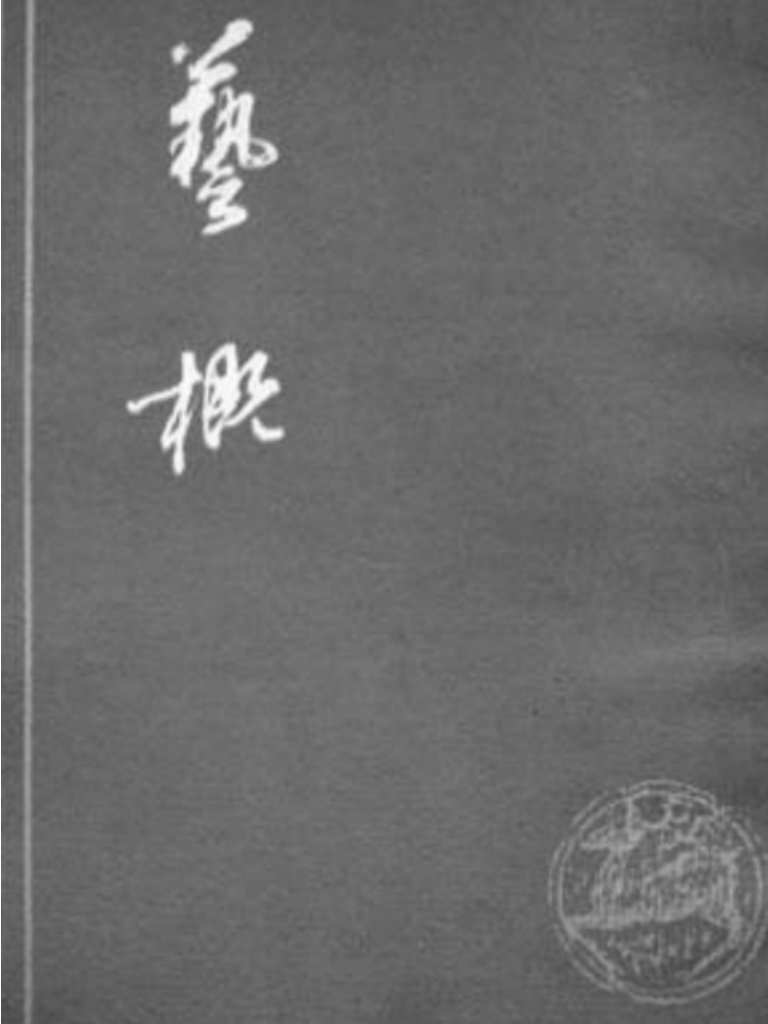
图2-1 刘煕载著《艺概》
在中国的清朝末年,刘熙载著《艺概》(见图2-1),用“艺”将诗、词、曲、赋、散文、书法等集合在一起,比较接近现代审美的艺术系统,但它显然注重文学,不能算作一个完整的艺术系统,但是它也是一种企图以审美性质将诸门艺术进行概念统一的尝试。在此之前,中国古代所谓“艺”之所指虽然包括了今天“艺术”系统中的部分艺术门类(如音乐、诗、书、画等),但主要还是指技能技术,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认为,用传统语意上的“艺”来对应近代的艺术精神,有所乖违,从更深一层去了解,老、庄之所谓“道”,正适合于近代的所谓艺术精神,(12)意即汉语传统里的“艺术”与今天所谓“艺术”趣味迥异。
东西方思想家没能从审美性质上观察诸“艺”,因而形成古代社会内容混杂的艺术系统,当代西方学者对此已有较为清晰的论说,如克里斯特勒(Paul O.Kristeller)在其论文《艺术的现代系统——美学史研究》中指出,古希腊罗马时代没有留下关于审美性质的系统或精心说明的概念,留下来的只不过是许多分散的概念和意见,它们一直影响到现代,它们必须经过仔细遴选、脱离语境、重新整理、重新强调以及重新解释或误解之后,它们才能够被用作美学系统的构建材料。我们必须同意这个结论:古代作家和思想家尽管面对杰出的艺术作品的确受到它们魅力的感染,但他们既不能够也不急于将这些艺术作品的审美性质从它们知识的、道德的、宗教的和实践的功能内容中区别开来,抑或用一种审美性质作为标准将美的艺术集合起来,或将它们作为全面的哲学解释的对象。(13)
学术界普遍认为法国美学家夏尔·巴托于1747年出版的著作《简化成一个单一原则的美的艺术》是现代“艺术”概念诞生的标志。该著将“美的艺术”确立为以模仿自然美为原则,以愉快为目的的艺术,以“音乐、诗歌、绘画、雕塑和舞蹈”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系统,“美的艺术”摆脱了技艺和科学,而净化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概念。(14)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被引进汉字文化圈,是在日本的明治时代(1869—1912),在日本古代典籍中,“艺术”一词与中国古代该词的意义相同,而日本人西周用该词表示包括“美术、文学、音乐、舞蹈、戏剧”在内的现代美的艺术的系统。在中国,由于受日本“美术”与“艺术”二词混用的影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般都是以“美术”指称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当时文化精英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王国维、鲁迅都对“美术”(实即“艺术”)发表过议论,如鲁迅在《儗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中指出:“美术为词,中国古所不道,此之所用,译自英之爱忒”,“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苟合于此,则无间外状若何,咸得谓之美术,如雕塑、绘画、文章、建筑、音乐皆是也。”(15)至五四运动前后,随着国内一批美术院校、美术学刊的出现,以及吕澂、陈独秀关于美术革命(绘画革命)的文章发表于《新青年》杂志,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艺术”与“美术”二词各自独立,这是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在中国确立的标志,也是古典艺术论向现代形态的艺术理论转型的主要标志之一。“艺术”从“技艺”上升到民族文化构成中的精神领域和理念层面,自然促使全民族全社会对它的重新审视、重新判断,建立在新的范畴基础上的全新的艺术学由此揭开了序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