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喃传[1]《潘陈传》对《玉簪记》的因袭与改编
《曲学》第一卷
2013年,361—373页
夏 露
中越戏曲有着悠久而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戏曲很早就传播到越南,影响了越南戏曲的产生与发展,像《汉宫秋》、《琵琶记》、《玉簪记》、《西厢记》等戏曲的典范之作,很早就被越南文人。所接受越南文人将之改编为越南喃传,长久以来通过口头形式代代相传,其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在越南家喻户晓。
无名氏《潘陈传》,约创作于19世纪初期,是越南古典文学的优秀代表作之一,越南古代民间歌谣云“女子不读《翘传》、男子不读《潘陈》”,虽然这似乎是从批评的角度出发,但是将《潘陈传》与越南古典文学的“第一杰作”《金云翘传》并举,可见《潘陈传》的艺术地位和流行盛况。《潘陈传》脱胎于中国戏曲《玉簪记》。从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来看,《潘陈传》与《玉簪记》保持了较为高度的一致。但是,越南作者也根据情况进行了多处改编,使之成为典型的越南士大夫喃传。笔者将以文本考察为依据分析《潘陈传》对《玉簪记》的因袭与改编,并探讨其中的文化成因。
一、《潘陈传》对《玉簪记》的因袭
越南文人素有接受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传统,尤其是以才子佳人故事为主题的喃传佳作,许多都脱胎于中国文学作品,例如《王嫱传》、《花笺传》、《金云翘传》、《二度梅传》、《潘陈传》、《西厢传》、《琵琶传》等,即分别脱胎于中国的《汉宫秋》、《花笺记》、《金云翘传》、《二度梅》、《玉簪记》、《西厢记》、《琵琶记》等小说戏曲。越南改编之作虽然保留原作的主要情节和人物姓名,但是往往在许多细节方面进行修改,使之成为具有越南特色且被越南民众广为接受的新作。
其实,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作品之间的因袭与改编也是十分常见的。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相当一部分是世代积累型的作品,小说和戏曲之间常常相互改编。所谓“戏剧与小说,异流而同源,殊途同归者也”,大约是中国小说戏曲关系的最好概括。例如《玉簪记》,虽然是明代剧作家高濂的作品,但它并非高濂独创,与中国古代其他很多小说戏曲一样,《玉簪记》带有世代积累型性质,经历了从杂剧到小说,又从小说到戏曲的演变。具体而言,这一故事最早起源于《古今女史》中对陈妙常的记载,其后演变为杂剧《女贞观》,尔后又有小说《张于湖误宿女贞观》,最后高濂在前人基础上创作了著名传奇戏《玉簪记》。[2]为观察越南《潘陈传》与《玉簪记》故事情节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对影响《玉簪记》的小说戏曲故事做简单的梳理。
《古今女史》的成书年代和作者今已不可考,但比较而言,可见其对潘陈故事的记载相对较早。书中简略叙述:“宋女贞观陈妙常尼,年二十余,姿色出众,诗文俊雅,工音律。……词载《名媛玑囊》。后与于湖故人潘法成通,潘密告于湖,以计断为夫妇。”[3]可见,陈妙常是确有其人的历史人物。在这个早期的记载中,潘、陈二人并无婚约,而且其中人物除去潘、陈二人之外,于湖的作用也很大。到了杂剧《张于湖误宿女贞观》[4],潘陈故事情节有了发挥。杂剧的叙述角度从张于湖开始,言其赴任长沙太守(《古今女史》中是赴临安),路过金陵,因故入宿女贞观,被陈妙常才色吸引,曾写词挑逗她,被对方以诗拒之。杂剧中还增添了潘生为观主之侄,妙常珠胎暗结之后被观主状告于官府,而断案者为潘生故知张于湖,于湖成人之美,判两人结为夫妻等等情节。后来在杂剧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有关“张于湖误宿女贞观”题材的小说,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注有言:“明余象斗《高锦情林》一,有《张于湖记》。吴敬所《国色天香》十,有《张于湖传》。何大抡《燕居笔记》九,有《张于湖宿女贞观》。余公仁《燕居笔记》七,有《张于湖女贞观记》。文字大同小异,未知即此本否?”[5]可见,相关题材的小说还不少,又或许这些小说是相互传抄所致。但整体上讲,以“张于湖误宿女贞观”为题材的小说都差不多是明代作品,所述的情节显然受到相关杂剧影响,小说中甚至直接引用杂剧里面的一些诗词。不过,小说在人物和情节方面都较杂剧有所不同,例如陈妙常从先前平民的女儿演变为世家女,她的身份也变为观中的知客,这就使得她能与潘必正直接唱和诗词,而不必像杂剧中那样请门公从中转达情意。此外,或许受到明朝中后期色情小说的影响,“张于湖误宿女贞观”题材的小说中有不少挑逗和猥亵的情节。而在断案中,张于湖施巧计成人之美,言妙常与必正有指腹为婚之亲,这后来被《玉簪记》改述为真有其事。而这个情节到了越南的《潘陈传》更为重要,书中一开头就从潘、陈两家为世交,进而指腹为婚谈起,以此交代潘陈身世。
《玉簪记》的版本不少,据《六十种曲》,有文林阁刊本、广庆堂刊本、继志斋刊本、陈眉公评本、一笠庵评宁致堂刊本、凌初成改定本(易名为《乔合衫襟记》)、万历间白绵纸印本(名曰《会真文庵玉簪记》),等等。此外,《西谛书目》还记有《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明黄懋时刊本[6]。全剧共三十四出,情节基本依据小说《张于湖误宿女贞观》,但《玉簪记》新增了一些情节,例如元将南侵、陈氏母女逃难离散、王公追求妙常、潘生得相思病、妙常探病、潘生被姑姑逼着上京赴试且中进士,等等。此外,还将妙常的身份由平民女改为世家女。略去了她与潘生交往后珠胎暗结的事情。而有关张于湖判案一节,由先前小说中的于湖计断二人为夫妇,改为王公子求妙常遭拒后诬告她,进而骗财赖婚,而于湖素知妙常品行,判定王公子说谎并责王其二十大棍。由此看来,在这一纵向的小说戏剧改编的过程中,之前于湖、妙常和潘生之间三方恋爱的故事到了《玉簪记》之后,变得以潘陈情爱故事为主,于湖的角色有了很大的改变。张于湖其实也是历史人物,他即是宋代有名的词曲家张孝祥。据《宋史》之《张孝祥传》,张孝祥曾任职建康留守,与小说和杂剧中的叙述相同,因此有人认为相关的故事很可能就是张于湖本人风流韵事的写照。例如《剧说》认为“高深甫作《玉簪》,假于湖以资谈笑,当亦如《琵琶》之蔡邕、《荆钗》之于王十朋耳。”[7]综上所述,潘陈故事到了《玉簪记》里,虽然出于戏曲演出的需要,还带有不少俚俗打诨的色彩,但是已经基本演变成了才子佳人模式。而到了越南《潘陈传》中,则彻底演变为才子佳人小说。所以,某种程度上讲,潘陈故事在越南的传播与接受是中国小说戏曲世代积累型性质在海外的延生。
《潘陈传》,作者佚名,但根据其文字内容,可以推测为士大夫文人所作。从其所叙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来看,与潘陈故事中的《玉簪记》最为接近。《潘陈传》全文为六字句、八字句相间的长篇叙事诗歌形式,常见的版本为940句(有的版本为950句或954句)。《潘陈传》早在1889年即被转写成现代拉丁字母形式的越南文[8],但在20世纪初依然有几种喃文版行世,其中阮朝维新壬子年(1912)神溪桐峰刊刻的《潘陈传重阅》序言中有这样的文字:“我国古传演音歌,盖古有之,而辞亦古奥……以《潘陈传》昌盛之,而其后《翠翘传》、《宫怨吟》、《征妇吟》诸继作盛焉。虽其艳辞丽藻……而其中有质干焉,有益藻焉,案玉敲金格致完备,令人抚卷而艳慕之者,固自不少也。某以后来著作虽妙,而此传实先之……赞绝之后,检阅刊刻之耳……”这段文字中说《翠翘传》、《宫怨吟曲》、《征妇吟》等越南喃诗文佳作都出于《潘陈传》之后,未必准确,不过,也说明《潘陈传》很早就盛行。而从越南名士范泰(Ph·am Thai,1777—1813)曾批评《潘陈传》借用中国故事而毫无特色,且于1804年创作《初镜新妆》的情况来看,《潘陈传》在此之前就诞生。[9]
越南学者杨广函( )认为其故事情节可以分为四回[10],目前现代字母文字形式的越南文版本的《潘陈传》基本依据此观点将之分为四部分,颇似中国戏曲的四折。具体内容如下:
)认为其故事情节可以分为四回[10],目前现代字母文字形式的越南文版本的《潘陈传》基本依据此观点将之分为四部分,颇似中国戏曲的四折。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潘陈两家定婚约(第1—150句)。具体讲述中国宋靖康年间,原本为同窗好友的潘公和陈公,同年高中科举,又成为同僚同朝共事。二人妻子同年怀孕,潘家与陈家指腹为婚。陈家以玉簪、潘家以象牙扇为订婚信物[11]。后来,潘公得子(即潘生),陈家得女(即娇莲,妙常)。由于年事已高,潘公和陈公都告老还乡,潜心教子。由于分隔两地,山长水远,两家不便通信往来。
第二部分:潘生与娇莲远离(第151—302句)。陈公不幸早逝,留下寡妻孤女,偏偏又逢战事,娇莲与母亲外出逃乱,不幸走散。娇莲遇见张氏女,被送入金陵一个寺庙,取法号为妙常。
第三部分:潘生遇见妙常(第303—668句):潘生在京城会试落榜,无颜回家,在成都某旅馆苦读以待下一期科考。突然想起姑姑在金陵修行,便去探访。姑姑将之留在寺庙中学习。在寺庙中,潘生对妙常一见倾心,恳请女尼香公为媒,展开苦苦追求。起初妙常或装聋作哑或严辞拒绝,直到潘生得相思病生命垂危才看在师太情面去探视。后来某天夜晚,潘生以谢恩为名欲进入妙常房间,妙常不允许,潘生以自刎相逼。妙常打开门,两人在交谈中发现彼此即为当年指腹为婚的儿女姻亲。从此两厢情愿,来往日益密切。
第四部分:潘生与娇莲结为夫妇(第668—940句)。潘生参加会试,高中探花。归来后他向姑姑表明自己与娇莲(妙常)的事情。姑姑劝潘生在张氏家举行婚礼迎娶娇莲,之后夫妇荣归故里。在潘家,妙常与在此寄居的母亲重逢,令喜事锦上添花。后来,潘生被皇帝召回京城任职,还选派他开赴疆场杀敌。后大捷归来,夫妇享受荣华富贵。
从故事主要情节和人物来看,《潘陈传》基本脱胎于《玉簪记》。尽管如此,《潘陈传》在借用中国文学故事的同时,根据情况在情节、人物等方面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编,以至于原作的主题在越南再生的作品中有了巨大改变,不可同日而语了。
二、《潘陈传》对《玉簪记》故事情节的改编
如上所述,《潘陈传》的基本故事内容与《玉簪记》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但仔细考察内容,我们发现越南无名氏在接受中国文学作品的同时进行了许多别具匠心的改编。
(一)集中叙述主线情节
《玉簪记》虽然主要讲述潘陈二人曲折有趣的爱情故事,但除主线之外,还用了相当的篇幅讲述新任太守张于湖、泼皮王公子与妙常之间的情感纠葛。而越南无名氏改编为喃传《潘陈传》,仅从书名的命名来看,就意味着作者要集中着眼于潘陈二人的故事,因此作者大刀阔斧删除支线情节,将整部作品紧紧围绕潘陈二人展开。书中开头部分即与《玉簪记》有很大区别,浓墨重彩描绘潘陈二人由同窗到同僚的友情,为延续两家友好而将儿女指腹为婚。其中前十句诗文如下:
庵中书琴散漫放/闲倚玉案吟金卷/话说宋靖康年间/和郡潭州两书生/金榜题名千秋传/潘陈二氏继书香/年少同窗共读时/潘陈已情深意重/笔砚抒志立誓言/十年寒窗终遂志[12]
在《潘陈传》中,作者几乎用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来描写男女主人公的身世以及见面之前发生的故事。而在《玉簪记》原作中,仅提到潘陈二人是同僚,但并未说明他们是同学,指腹为婚的细节也相对简单。此外,《潘陈传》对潘陈二公如何教子读书、教女女红都有详尽描述。尤其是第三部分写潘生在金陵寺庙遇见陈妙常后一见倾心,坠入情网,进而展开苦苦追求,一步步努力地去接近、说服妙常改变心意的过程,作者不惜笔墨用了472句诗,几乎占据全文的一半篇幅。《玉簪记》的结尾只写到潘生中进士,之后赢取妙常。而《潘陈传》补充了潘生高中科举后受到皇帝重用,让他赴京城任职,又派他开赴疆场杀敌,最后载誉归来享受荣华富贵等情节。总之,《潘陈传》将原著中局限于佛门净地的大胆情爱故事,经过细心修剪,改编为具有越南特色的才子佳人故事。
《潘陈传》全篇不足七千字,这样的情节安排,使得在短小的篇幅里能集中塑造主要人物,故事整体结构也更加严密、丰满,体现了改编者的艺术处理手法。
(二)删改原著中潘陈二人交往的部分关键情节
《玉簪记》对于潘生和陈妙常两位主人公的叙述和描写基本上笔墨各占一半,尤其是对两人情感发展的过程,作者采用的是使主人公双方共同“前进”的方法。其中既有潘生对爱慕妙常才貌的心理描写,也有妙常独自一人夜半在房中的内心挣扎——对于爱情热烈向往却又畏怯害羞的体现。原作中接替描述男女双方情感、态度变化,最后冲破阻力结为连理。在他们情感发展的过程中,茶叙、琴挑、偷诗既是他们情感发展的线索,也是全剧中最有特色的部分,而其中“琴挑”对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发展具有最为关键的作用,这也成为日后戏曲上演中的经典桥段。在“琴挑”中,潘生借琴抒发自己对陈妙常的爱慕之情,陈妙常假装生气,但对潘生也产生了爱慕之情。在中国古代,琴常常成为男女暗吐心意的良媒。传统戏剧中的文君听琴、莺莺听琴,可为最经典的篇章。可以说,在“才子佳人订终身,落难公子配佳人”的永恒主题中,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越南喃传中,也不乏以琴为媒介和线索展开男女恋情的故事,例如《金云翘传》里曾四次写翠翘的琴技来烘托人物形象和交代故事背景,《石生传》里的琴声更成为石生与公主之间的爱情故事的关键线索。然而,在《潘陈传》中,作者却舍弃了《玉簪记》最动人的情节——“琴挑”,把两人之间的互动完全改为潘生一个人单方面苦苦追求。所以,很自然地,像“偷诗”那样以妙常主动表露心迹进而获得潘生积极响应的情节,到了《潘陈传》中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三)增添香公多次牵线情节
如上所述,在《潘陈传》中,由于越南无名氏将《玉簪记》中潘陈二人情感发展中的对手戏演变潘生单方面的苦苦追求,而在传统的封建时代,特别是在佛门净地,潘生是不便直接去找妙常倾诉衷情的。为此,作者势必要为之塑造一个类似《西厢记》的红娘角色。事实上,《潘陈传》中的香公就很好地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在《玉簪记》中,对香公着墨不多,其地位也并不重要;而在《潘陈传》中,作者大大增添了香公牵线搭桥的情节,使之成为潘陈二人情感发展的关键人物。全文中,香公为两人传送消息、牵线搭桥多达六次,贯穿两人相识相知的整个过程。第一次(第360—376句),潘生向香公打听在净心堂所见女尼为何许人,初表爱慕之心,香公简明告之妙常情况后规劝他不必多问。第二次(第388—456句),潘生难耐相思苦,到妙常住处寻望,意外见到妙常,向她倾诉爱慕,遭妙常关帘拒绝后心中愁苦,找香公诉说心事,并恳求香公帮忙,促成他们的姻缘。香公劝他不要在佛门净地谈情说爱,但经不住潘生苦苦哀求,最终同意向妙常转告其情意。第三次(第490—519句),香公找到妙常,对妙常转达了潘生的想法,妙常有所心动和犹豫,但依然拒绝进一步发展,香公转而劝她既然拒绝婚恋就一心向佛,坚定信念,或能修行圆满。第四次(第520—542句),香公劝慰潘生既然情感之事无望,不如埋头读书,考取功名,他日或还有希望迎娶佳人。潘生得知情况后,对妙常愈加倾心,依然恳求香公帮忙。第五次(第544—572句),香公再次去求证妙常是否能答应潘生,妙常以门户不当,自己身世浮萍投靠僧门,不愿惹是非,以长痛不如短痛为由而继续拒绝潘生,香公转而劝她不必多想,潜心修佛。第六次(第577—639句),相公劝潘生努力读书求取功名,忘掉妙常,而潘生依然坚持追求,再次恳求香公传话,并因此害了相思病。香公引妙常前去探望,两人最终得以倾心交谈,了解原来彼此正是先前有婚约之人,从而放心交往起来。
可见,香公虽是《潘陈传》中的次要人物,但是在潘陈二人的感情中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她身处佛门,明白出家人应该潜心修佛的道理,但同时她身上也有浓重的人道主义色彩,对潘生的一片痴情深表同情和理解,因而才能担任“红娘角色”,多次在两人之间担任传话者,为他们的情感发展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不断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四)对疏漏情节的改进
《玉簪记》由于是戏曲,着重于舞台上人物的对话与动作,在叙事方面显然不如小说,因而出现了一些疏漏情节。例如潘生落第后到金陵城投奔姑母,按理说,姑母从年轻时起就离家修行,那时潘生尚年幼,现在已过二八年华,从幼童成长为风姿俊雅的少年郎,姑母不太可能一眼就认出他来,但剧中只写潘生一句:“有人在么?”然后观主便道:“是必正侄儿,乍一见忽惊疑,我儿为何到此?”[13]时隔多年,一眼就认出侄儿,这就让人觉得不太符合逻辑。《潘陈传》的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就改为两人见面的时候,观主对潘生“ (静观良久)”,写出了观主带着疑惑将潘生从上到下细细打量,回想他幼时模样,并与现在对比一番,再最后确认他的确是自己侄儿的过程写出来。语虽简洁,但很清楚地位让读者心中补足了这样的景象,更符合逻辑。
(静观良久)”,写出了观主带着疑惑将潘生从上到下细细打量,回想他幼时模样,并与现在对比一番,再最后确认他的确是自己侄儿的过程写出来。语虽简洁,但很清楚地位让读者心中补足了这样的景象,更符合逻辑。
还有,在《玉簪记》中,潘陈二人暗自往来,已有夫妻之实,度过了许多甜蜜时光,但却不知道彼此早有婚约,这似乎有些不合逻辑。按理说,两家父母在告知儿女定亲之事时,必会将对方的姓名、籍贯以及双方的定亲信物等告知自己的儿女。这些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必定也是铭刻在心的。潘陈两人在情投意合、颠鸾倒凤时,居然没有想到要询问对方的姓名和籍贯,而潘生决意娶妙常为妻时也不曾问闺名。而在江上送别时,两人拿出信物互赠,竟然不知对方的信物与自己的正是一对。这些情节都会读者和观众产生疑惑。《潘陈传》对此做了极大改动。在写到潘生病愈后到妙常禅房致谢,妙常起初不允许他进房间,潘生以死相逼,妙常才答应他。在他们交谈的过程中,当潘生询问妙常的俗名、家乡时,妙常就乘机将婚约之事和盘托出。后来两人出示信物,明白对方正是自小定亲之人,父母之命加上真心相爱,实在是喜从天降,于是萦绕在两人心中的忧愁一扫而光,从此不再顾忌什么,开始了真正的交往。这样的情节处理,令人感觉更加合乎情理,也使得潘陈两人的结合更加符合传统礼教的要求。
三、《潘陈传》对《玉簪记》人物形象的重塑
《潘陈传》对《玉簪记》情节的删改除了带来故事内容的变化之外,更通过叙述语言对其中人物的形象进行了重塑。
(一)妙常(娇莲)形象的改变(https://www.xing528.com)
《潘陈传》中最能体现作者创作意图的是他对女主角妙常(娇莲)形象的重新塑造。这一重塑几乎改变了原作的主题思想。在有关陈妙常事迹的中国小说和戏曲中,她出身卑微,性格大方,但同时也沾染俗气,是男子们可以随意调笑的对象。《古今女史》里就提到于湖和必正都曾调笑妙常。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中国俗文学作品中惯于描写风流女尼。另一方面,唐宋时期的“女尼”、“女冠”中确有相当一部分人虽在空门,却与过着与娼妓一样的生活,甚至时常被召入宫禁。受这些因素的影响,《玉簪记》所塑造的妙常虽然能品诗弹琴,但同时也是多情放纵的人。例如初次与张于湖和潘生见面时,她完全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概念,毫不介意与他们交谈,后来甚至请他们到自己的房间饮茶、弹琴、下棋。当她与潘生互生情愫时,似乎早已忘记自己是有婚约之人。所以,《玉簪记》里的妙常是一个敢于冲破封建伦理和佛门束缚的叛逆者,她和潘生之间的爱情是他们两人共同追求的结果。
到了越南的《潘陈传》中,妙常形象有了巨大变化。首先她的出身是大家闺秀,而非平民。她从小受到严格的儒家伦理教育,行为举止端庄有礼。在与母亲走散不得不寄身禅门时,她虽然也思念家乡、念及婚约,但依然专心修行。当潘生对她一见倾心,向她表白时,她不像《玉簪记》里的妙常主动回应,而是“充耳不闻不言语/念自己身处佛门/岂敢对人轻薄语/装聋作哑忍服输/花阶潜影返禅楼/慌忙摇动云窗闭/轩外余香伴君留”[14]。后来,潘生托转述衷情,她“虽含责备巧妙讲/红颜薄命不堪受/置身蒲柳望松林/疏离尘杂心欢喜/耳畔不再蜂蝶戏/愿请老者告来客/此地不教蜂蝶语/今生愿皈菩提下/一片丹心斩青丝/经书油灯伴身旁/思恋情怀怎可累/何况潘生读书郎/流云不忍笼秋镜/谨愿来客多包容/从此不再轩外扰”[15]。后来必正以佛门既然慈悲宽广,就应该体恤他一片真心等理由求香公再次带话给妙常时,她甚至打算以逃避他方的办法来阻止这种苦苦相求。直到潘生相思成病,她才看在师傅的情面上前去问候。潘生病愈来谢,她依然坚拒,对方以自刎相逼,她才无可奈何地让他进入房间,且立刻告知自己指腹定婚之事以杜绝他的幻想。
在《潘陈传》中,在潘生和妙常并未确定关系时,从未有他们单独相处的场景。这与《玉簪记》中妙常与潘生谈笑晏晏的相处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虽然《潘陈传》和《玉簪记》中对女主角的基本设置是一致的,但是这两个妙常的性格是不同的。《玉簪记》中的妙常敢于不顾一切追求个人幸福,尽管表面上她也拒绝、责备过潘生,但是,当潘必正离开后,她却又后悔,禁不住地喊:“潘郎!潘郎!”态度情感是受心理支配而非伦理影响的。对待婚约,她也采取权变的态度,跟母亲走散时,母亲提及先前婚约,她说道:“一富一贫,乃见交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于今丧父家寒,况经年远,此事不必提起!”这就可以理解她为何能毫无拘束地男子交往,甚至与潘生双双坠入情网。而在《潘陈传》中,作者的意图是要塑造一个品貌双绝的深闺小姐形象,所以,不但大刀阔斧地删除妙常与其他男子的交往情节,甚至与潘生的交往也特别符合礼法,这就将《玉簪记》中妙常完全变成了一个含蓄、矜持、单纯的,符合传统道德的标准闺秀。
(二)潘生(必正)形象的改变
在《玉簪记》中,作者对潘生和陈妙常两位男女主人公的叙述和描写基本上笔墨各占一半,既有潘生惊其艳丽生情的心理描写,又有妙常独自一人夜半在房中的内心挣扎——对于爱情热烈向往却又同时畏怯害羞的体现。且对两人情感发展的过程,作者采用的是使主人公双方共同“前进”的方法,分别接替描述男方女方的情感、态度变化,互相试探进而知晓对方心意,最终结为连理。潘生初次见到妙常,虽然也深感“仙姑修容光彩,艳丽多人”“,此心羁绊,不忍轻去”[16],但他并未急切地表达爱慕之心,而是出于对对方的尊重,把心思深藏。反而是妙常主动请他一起喝茶,潘生才抓住机会进行试探。另外,在《玉簪记》里,虽然也有潘生相思成疾的描写,但是他并未亲自开口求妙常答应他什么,反而是妙常写下了对剧情发展影响巨大的《西江月》:“松舍青灯闪闪,云堂钟鼓晨晨。黄昏独自展孤衾,欲睡先愁不稳。一念静中思动,遍身欲火难奈。强将津唾咽凡心,争奈凡心转盛。”而潘生“细观此词”,立刻知晓“陈姑芳心尽露。敢是天就我姻缘,把此词作个供案”。[17]这令本身也正处于相思中的潘生大喜过望,因而他们一拍即合,终成佳缘。
到了越南《潘陈传》中,潘生初次见到讲经堂中倚靠竹帘的佳人,就急切地去找香公打听妙常身世,表达爱慕之心。对两人的关系,作者花了相当的笔墨描述潘生对妙常积极主动的追求,以及求而不得的苦闷与烦忧,进而多次恳请香公为媒。在他因相思成疾而卧床不起时,巧借医生、道士之口道出他的一场病不是寻常药物可以医治,唯独有童真女才是救命良方。这样引出香公主动为其去劝说妙常探病,妙常出于人道主义很自然地去看望他。总之,可以说,他们两人感情的发展是在潘生积极主动而进行的步步努力、步步前进的情况下取得进展的。如果潘生不那么痴情和执著,他最终是绝无可能与妙常修成正果的。
越南学者杨广涵( )在分析潘生形象时说:“前辈们常叮嘱‘男子不读《潘陈》’,是因为书中把潘生描写成了一位能为恋人自尽的痴情男子形象。前辈们认为男子不应如此懦弱和萎靡。”[18]这正表明潘生在越南民众心中已经成为痴情男子的代言人。
)在分析潘生形象时说:“前辈们常叮嘱‘男子不读《潘陈》’,是因为书中把潘生描写成了一位能为恋人自尽的痴情男子形象。前辈们认为男子不应如此懦弱和萎靡。”[18]这正表明潘生在越南民众心中已经成为痴情男子的代言人。
尽管如此,我们注意到他对妙常的态度始终是尊重的,没有丝毫的轻薄,反而显得十分有风度,也很端正严肃。第一次在寺庙偶遇妙常后,他禁不住追至禅房,但遭妙常无声回避之后,他没有强求,而是“羞愧不堪难启齿/无处有路谈寄语/带愁郎君独自回/但见夕阳笑人痴/怨恨佳人更自责/许是粗鄙招人拒/青山绿水高天在/明月清风亦如故/寄语风月与云彩/谁人能解痴人心”[19]!后来他对妙常“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也主要是去恳请香公出手帮忙,当妙常以潜心修佛为由来拒绝他时,他还心生敬重,毫无猥亵和挑逗。
(三)观主(必正姑姑)角色的转变
在《玉簪记》中,对潘陈二人爱情最直接的阻挠来自观主(即潘必正的姑姑)。第二十一出“姑阻”中,观主察觉到潘陈二人的感情之后,令潘生陪自己在净心堂打坐,以此阻挠潘陈二人的约会;接着又催促潘生上京赴试,目的就是斩断两人的情思。在这里,观主所的耐心的是,佛门净地谈情说爱会毁坏女贞观的名声,而且,身为潘生的姑姑,她希望他能专心学习,考取功名,光耀门楣。
到了越南的《潘陈传》中,观主的形象从一个封建卫道士被改写为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高风亮节的家人。她对两人的爱情没有横加阻挠,得知两人不仅相恋而且有婚约后,认为这是美事一桩,替潘陈两人高兴。她还安排潘陈二人的婚礼,将妙常送到张嫂家中,让她从那里出嫁。这样的处理,使得他们的结合更符合礼教,免遭人非议。
观主角色的转变,也令人感到两部作品的主旨发生了变化。在《玉簪记》中,剧情中的最大冲突就是自由爱情与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观主在那样的情况下必须扮演封建家长来维护正统礼教。然而,在《潘陈传》中,两人在互相表白时就已经知道对方便是从小定亲之人,因此两人的恋爱和结合变得合理,完全符合纲常礼教,他们与观主并不构成冲突。
四、造成两部作品根本差异的文化因素
综上所述,《潘陈传》虽然脱胎于《玉簪记》,在基本情节和人物方面几乎相似。但是,《潘陈传》在许多方面具有原作不同的新面目。尤其是在原作中被人津津乐道的情节——“琴挑”和“偷诗”,到了越南再生作品中完全消失了。这也造成两部作品中男女主角的形象产生了根本变化,尤其是陈妙常身上最吸引人的叛逆色到了越南则完全失去,进而彻底演变为一个矜持守礼的闺秀形象。
在文学的传播中,接受比影响更重要,更引人深思。一个作品传播到他国,由于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接受中自然会出现重大的不同。《潘陈传》之所以在情节、人物形象和创作意图方面与原作相去甚远,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它出自儒家高级知识分子之手。出于对统治阶级既得利益的维护,他必然塑造典型的符合纲常名教思想的女子形象。其次,佛教在越南的传播过程中进行了大量本土化改革,越南人对于宗教的信仰更接近于一种生活习惯,而非严谨的清规戒律。因此,刻意描写寺庙中的男女之情显得不那么重要,也不会引起强烈的反响。还有,女性在越南社会中的地位向来较其他儒家文化圈国家的女性地位要高。由于气候炎热及耕种条件,越南女子极少养在深闺,“男女授受不亲”只是一种传言,她们经常参加各类庙会等社交活动,农村自由恋爱更是大胆,这在越南的建筑、民间雕塑以及民间歌谣中都有具体体现。自古以来,越南女性多开朗大方,在同男性交往中并不似我国女性那般腼腆,因此陈妙常的“越轨”行为在他们看来没有那么新奇,无需刻意塑造这样的形象。
此外,越南虽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但越南人在思想上的禁锢远不及中国,尤其是在性方面不像中国古代那么压抑,或许无需通过文学作品来释放这种压力,反而要依靠文学作品来规范社会行为,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所以,在越南文学发展过程中,没有经历中国明清那样色情文学泛滥的时期。越南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士大夫的喃传,相当多的是通过才子佳人的故事来宣扬忠孝节义等儒家教化思想,娱乐性不强。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潘陈传》的创作过程中,作者为什么会毫不吝惜地将中国《玉簪记》原作中最具光彩的部分做了删改,将一部以反抗封建礼教为主题的戏曲彻底改造成“体制内”的才子佳人小说。
【注释】
[1]所谓喃传,是越南古代用喃文创作的韵文小说,早期采用七言诗歌形式连缀而成,后来在借鉴越南民歌的基础上形成固定的六八体和双七六八体诗歌形式。《潘陈传》即采用六八体诗歌形式创作,全文为六字句、八字句相间的长篇叙事诗歌。由于越南封建时代长期使用汉文为官方文字,喃文并不普及,因此,喃文仅限于部分文学创作。不过,由于喃文是符合越南语口语的文字,加上喃传是韵文体裁,且有故事情节内容,因此特别适合口头传诵。长久以来,越南的一些优秀喃传作品都是口口相传,有些甚至作为儿童的催眠曲,在民间十分普及。
[2]参见《玉井山馆笔记》、《渔樵漫钞》和《六十种曲》等文献。
[3](清)焦循《剧说》卷二,《中国古典戏曲理论集成》第八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21页。
[4]参见《孤本元明杂剧》,涵芬楼藏版。
[5]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83页。
[6]参见孙楷第《日本东京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国立北平图书馆出品,1931年,第234—253页。
[7](清)焦循《剧说》卷二,第121页。
[8]参见〔越〕黄春越、阮明进( )《国语文字史探索》(
)《国语文字史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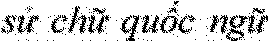 ):“从此他继续翻音,出版了一大批汉喃作品,有:《家训歌》、《女刘》(1882)、《六畜争功》(1887)、《潘陈传》(1889)、《陆云仙传》(1889)……”越南文化通讯出版社,2007年,第401页。
):“从此他继续翻音,出版了一大批汉喃作品,有:《家训歌》、《女刘》(1882)、《六畜争功》(1887)、《潘陈传》(1889)、《陆云仙传》(1889)……”越南文化通讯出版社,2007年,第401页。
[9]据越南学者清朗( )《越南文学略图》(
)《越南文学略图》( )上卷,呈现出版社,书未注明出版年份,第548页。
)上卷,呈现出版社,书未注明出版年份,第548页。
[10]参见〔越〕杨广涵(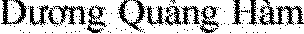 ),《越南文学史略》(
),《越南文学史略》( )之“潘陈”目,学习资料中心出版社,1968年。
)之“潘陈”目,学习资料中心出版社,1968年。
[11]《玉簪记》中的信物是玉簪与玉扇,而《潘陈传》中是象牙扇与玉簪,可能因为象牙是越南珍贵特产之一。
[12]《潘陈传》尚无中译本,此处由笔者暂译。其原文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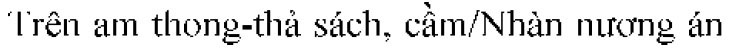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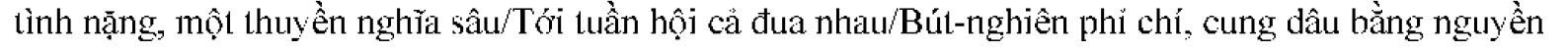
[13]参见《玉簪记》第十二出《必正投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44页。
[14]《潘陈传》第404—410句,此处为笔者暂译,其原文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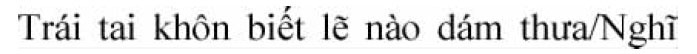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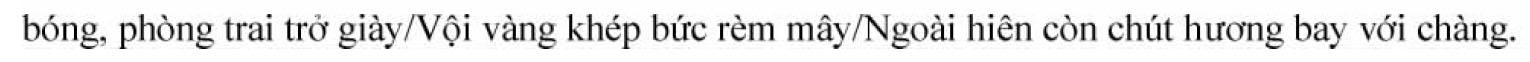
[15]见《潘陈传》504—518句,此处为笔者暂译,其原文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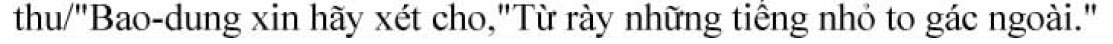
[16]参见《玉簪记》第十四出《茶叙芳心》,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51页。
[17]参见《玉簪记》第十九出《词姤私情》,同上,第69页。
[18]参见〔越〕杨广涵(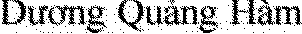 ),《越南文学史略》(
),《越南文学史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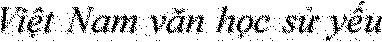 )学习资料中心出版社,1968年,第390页。
)学习资料中心出版社,1968年,第390页。
[19]参见《潘陈传》第409—420句,此处为笔者暂译,其原文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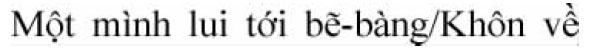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