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周德清“务头”之说本义
《曲学》第一卷
2013年,115—127页
李 晓
务头的本义是什么?是唱曲出彩的地方,同时也是体现该曲牌个性的地方。为了使唱曲有出彩的地方,一要知道务头在曲中的位置(注重于字调),二要知道如何使唱曲出彩(注重于腔格)。于是,与此相关的填词、唱曲的技术问题就很重要了。
一
自元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提出“务头”一说之后,历来辩说纷纭,尤其是当代学人的文章很多,笔者亦仅以本人多年来的学习心得提挈要点阐述之。周德清提出“务头”一词,未详其义,亦无须解说,因为在周德清时代,唱曲、填词者皆熟悉其义。曲中“务头”之处,唱之是佳音,诵之是佳句,能使听者、观者喝彩,跟唱曲、填词关系密切,所以凡研究者亦应知其原义。
“务头”在曲词中为重要、关键、出彩之处。曲中之务头,自然以“宛转动听”为要务。虽然周德清对曲之唱未作解析,但他在《中原音韵》中留存下来的信息,乃是探索“务头”本义的重要依据。他在《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中说:“要知某调某句某字是务头,可施俊语于其上。”在《造语·全句语》说:“短章乐府,务头上不可多用全句,还是自立一家言语为上;全句语者,惟传奇中务头上用此法耳。”[1]并且在《定格四十首》中注明“某调某句某字是务头”。我们细细梳理一下,就可以知道曲中“务头”的一些基本特点:
(一)周氏在《定格四十首》中详注务头的位置,似乎是固定的。
字位如[寄生草]第五句之“虹蜺志”,末句之“陶潜是”;[金盏儿]第三句之“酒”字;[朝天子]第七句之“人”字;[红绣鞋]末句之“口”字;[满庭芳]第六句之“纸”字,第七句之“扇”字。句位如[醉中天]之第四句“美脸风流杀”,末句“洒松烟点破桃腮”;[醉扶归]之第四句“揉痒天生钝”,末句“索把拳头揾”;[普天乐]之第八句“怕离别又早离别”;[十二月尧民歌]之后词起句“怕黄昏忽地又黄昏”;[四边静]之第二句“软弱莺莺可曾惯经”,末句“好杀无干净”。
(二)周氏在解说中认为,务头可以是“字”,可以是“句”。
其句可以是一句或二句,亦可二句对,如[卖花声]之起句对“细研片脑梅花粉,新剥真珠豆蔻仁”;亦可三句对,如[醉太平]之第五、六、七句“文章糊了盛钱囤,门庭改做迷魂阵,清廉贬入睡馄饨”;[拨不断]之第二、三、四句“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上遮,青山正补墙头缺”。
(三)周氏特别强调务头处的字调,须要音律浏亮,宛转其调。
如[塞鸿秋]“腕冰消松却黄金钏,粉脂残淡了芙蓉面。紫霜毫蘸湿端溪砚,断肠词写在桃花扇。风轻柳絮天,月冷梨花院。恨鸳鸯不锁黄金殿。”周氏评曰:此曲“音律浏亮”,是因为其务头处第一句“却”字,第三句“湿”字,皆为上声,“音从上转”。余曰:“却”字转音后落到阳平声“黄”,且“蘸湿”为去、上,皆可婉转其调。如[迎仙客]“雕檐红日低,画栋彩云飞,十二玉阑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国,感慨伤悲,一片乡心碎。”周氏评曰:“妙在‘倚’字上声起音,一篇之中,唱此一字,况务头在其上。”余曰:“天外倚”三字为阴平、去、上,其音先落后揭,抑扬顿挫,得此一字果然全篇皆活。如[梧叶儿]“别离易,相见难,何处锁雕鞍?春将去,人未还,这其间,殃及杀愁眉泪眼。”周氏评曰:“如此方是乐府。音如破竹,语尽意尽,冠绝诸词,妙在‘这其间’三字,承上接下,了无瑕疵。‘殃及杀’三字,俊哉语也……第六句止用三字,歌至此,音促急,欲过声以听末句,不可加也,兼三字是务头,字有显对展才之调。”余曰:“这其间”三字为去、阳平、去,以拗句发调,“殃及杀”三字为阴平、阳平(入作平)、上(入作上),其音自“这其间”发调后过声“殃及”至“杀”字上声,其音调特别宛转。
(四)周氏认为,在务头处可施俊语,以求声文并茂。
《中原音韵·作词十法》“六字三韵语”条,周氏批评通篇二字一韵,不分务头,亦不能唱采,认为只能在“全篇中务头上使”,才能“以别精粗,如众星中显一月之孤明也”。在《定格四十首》中,周氏的评说,亦首重音律,次及俊语,因为在唱曲中只有音调宛转动听,方能显出词采的俊逸。余曰:在有的务头之处,亦不乏用词平平,无所谓“俊语”,首要的乃是字声音调。尤其是务头在“字”上,无论一字,二三字,不见风采,其以音调优美动听取胜。何谓“俊语”,其标准是很模糊的。如上文[梧叶儿]中“殃及杀”三字,周氏曰“俊哉语也”(周氏并未指其为务头),很难理解,但其七字句“殃及杀愁眉泪眼”,却可视为俊语;而务头“这其间”,只在音律上逞其作用,其词一般。历来称颂的[寄生草]之“虹蜺志”、“陶潜是”,亦一般。可以称为俊语者,有二例,如[塞鸿秋]之“松却”之“却”字、“蘸湿”之“湿”字,[庆东原]之“袜冷凌波”之“冷”字。而作为务头(字)所在的句,或以句为务头者,可谓俊语者却多见。作为务头(字)所在的句,如[金盏儿]“酒”字所在句“黄鹤送酒仙人唱”;[迎仙客]“倚”字所在句“十二阑杆天外倚”;[塞鸿秋]“却”字所在句“腕冰消松却黄金钏”,“湿”字所在句“紫霜毫蘸湿端溪砚”;[庆东原]“冷”字所在句“袜冷凌波”。以句为务头者,佳句颇多,如[醉中天]之“美脸风流杀”,“洒松烟点破桃腮”;[普天乐]之“怕离别又早离别”;[十二月尧民歌]之“怕黄昏忽地又黄昏”;[醉高歌]之“几点吴霜鬓影”,“晚节桑榆暮景”;[醉太平]之“文章糊了盛钱囤,门庭改做迷魂阵,清廉贬入睡馄饨”;[山坡羊]之“把团圆梦儿生唤起”;[拨不断]之“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上遮,青山正补墙头缺”。
二
仔细研究周德清的评说,尚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在元末明初的《水浒传》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中,雷横在郓城县到勾栏听东京来的白秀英说唱《豫章城双渐赶苏卿》,白秀英说了又唱,唱了又说,后来“那白秀英唱到务头,这白玉乔按喝道:‘虽无买马博金艺,要动聪明鉴事人。看官喝彩道是去过了,我儿且回一回,下来便是衬交鼓儿的院本。’白秀英拿起篮子,指着道:‘财门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过。手到面前,休教空过。’”白秀英唱到务头处,便停下不唱了,向观众乞赐缠头以后再接着唱。此为小说之描写,不当作为学术之依据,但是也能反映小说创作之时的演艺行把“务头”作为唱曲的一种行话,直接与“唱”有关。说明“务头”处为唱腔上最动听之处,观众爱听,唱者要唱好。它提示了我们理解“务头”的本义,不能不重视“务头”处的曲唱之“腔”。
周德清是在元北曲中提出“务头”的,注重于曲之填词的字调。根据曲唱的原理,曲之唱是“依字声行腔”的唱,因此“务头”与字声密切相关,周氏注重于字调,是对填词者提出的要求,字调处理得好,是曲之腔宛转动听的必要前提。周氏强调字调是有其道理的,我们且顺着周氏之说讨论一些问题。
其一,务头不是曲牌定格的要素,而是“定腔”的要素,字调是曲牌定格的要素,佳者要善于在字调上取务头,便于好唱。
周氏《定格四十首》中,有[雁儿]、[一半儿]、[喜春来]、[天净沙]、[小桃红]、[寨儿令]、[落梅风]、[水仙子]、[殿前欢]、[庆宣和]、[清江引]等十一曲,没有确指务头的所在,然对其字调却详论优劣。所谓“取务头”,则有为填词、度曲者所设置的意思,并且是以字调的优良搭配体现出来的,如此只要不犯字调亦有不取的。填词者取了务头,度曲者才能唱出务头;填词者不取务头,度曲者就唱不出务头来。如周氏在《作词十法》讲六字三韵时,说到[折桂令],便说六字三韵须用在务头上,“皆二字一韵,不分务头,亦不能唱采”。但在《定格》的该曲中首句“长江浩浩西来”没有用六字三韵,亦没说首句是务头,而说第六句“天地”(阴平、去)为务头,却将字调用错了(周氏曰:“若得去上为上,上去次之,余无用矣,盖务头在上。”),那么首句唱不出务头,第六句亦唱不出务头了。若要唱出“务头”,便要“取”,原曲为“天地安排,诗句就云山失色”,周氏曰:“歌者每歌‘天地安排’为‘天巧安排’,‘失色’字为‘用色’,取其便于音而好唱也,改此平仄,极是。”填词重在起调毕曲,是“定腔格”所在,佳者在调平仄中“取务头”,是为了唱出“定腔”,若不取务头,虽不犯律,但不能“唱采”。周氏讲究字调,亦是为了便于好唱,本质上是为了保“定腔”。务头不是曲牌字调定格的要素,但是“定腔”的要素,一般说常用在起调毕曲上,亦可用在曲中的某个位置上,这里有其灵活性;而字调是曲牌定格的要素,在曲牌中的位置是固定的,所以才有曲牌格律的规范。如果字调搭配(平声阴阳与上、去声)得优良,唱曲即能出彩,便是取了务头,出彩处便是所取的务头。所以在曲牌格律谱中,只有字调的定格,而没有标明何处是务头,要看填词者取务头还是不取务头。
其二,周氏所谓的“某调某句某字是务头”,重点在“某字”;所谓“句”之务头,最终落实在“字”上,亦就是某某字的字调上;“腔”出彩的乃在某某字的字调上。
所谓如[醉中天]之第四句“美脸风流杀”,末句“洒松烟点破桃腮”,第四句的字调为上、上、阴平、阳平、去,其“脸风”上声连阴平,“流杀”阳平连去声,揭起而抑下;末句的字调为上、阴平、阴平、上、去、阳平、阴平,其“点破”上、去声相连,周氏亦曰“妙”。如[醉高歌]之第二句“几点吴霜鬓影”,末句“晚节桑榆暮景”,第二句的字调为阴平、上、阳平、阴平、去、上,其“几点”阴平连上声,“鬓影”去、上声相连,先抑后揭发调;末句的字调为上、上、阴平、阳平、去、上,其“节桑”上声连阴平,“暮景”去、上声相连,揭起而抑,抑而再揭,宛转其调,结句相当浏亮。所谓某某句为务头,“腔”出彩的乃在几个字上。周氏所谓务头某字在某句上,更是如此,此句当为可施俊语的句位,所以说俊语不在某字,而在该字所在的句也。如[金盏儿]“酒”字在“黄鹤送酒仙人唱”上,其句字调为阳平、阳平、去、上、阴平、阳平、去,其“送酒仙”去、上、阴平相连,以上声字宛转其音,此句当为佳句。如[塞鸿秋]之“却”所在句“腕冰消松却黄金钏”,其“松却”为阴平、上声相连,“湿”字所在句“紫霜毫蘸湿端溪砚”,其“蘸湿”为去、上声相连,二句皆以上声转音,亦为佳句也。
其三,周氏很讲究字调,即平声阴阳与上、去的搭配;因为曲牌之“定腔”固在,定腔格对字调有一定之要求,讲究字调本质上是为了保“腔”。
即使周氏没有明指为务头处,亦详论字调的优劣。如[醉中天]之“捧砚”“上、去声妙”,[迎仙客]之“感慨”“上、去尤妙”,[普天乐]之“冷雨”“去上为上,平上、上上、上去次之,去去属下者”,等等。而其十一首曲牌未明指务头者,亦详论字调,如[天净沙]“古道西风瘦马”之“瘦马”,“去、上极妙”;如[寨儿令]“回头观兔魄”,评曰:“紧要在‘兔魄’二字,去、上取音。”如[殿前欢]“入门下马笑盈腮”,“十年前一秀才”,评曰:“妙在‘马’字上声,‘笑’字去声,‘一’字上声,‘秀’字去声。”若说周氏未明指务头者的十一曲,则没有务头,那么,我们能所知的某某曲牌务头,相对于曲牌总数来说,太微乎其微了。实际上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曲牌固有定腔,其定腔格或在起调毕曲,或在曲中某个位置上。定腔格对字调的要求很严,歌者以定腔行腔,字调不对,拗口不能唱或唱出字音会变;在非定腔格位置的字调就比较灵活,可以字声行腔,但亦须遵守曲牌平仄格律。“某调某句某字”是不是务头,关键就在于填词者取不取务头,讲不讲究字调的搭配;同样的道理,某曲牌有没有取务头,务头取在哪里,由善度曲者反复清唱,特别优美动听处,同牌名的曲子之腔有相似处,大率即是务头所在。我们不用把“务头”看得太复杂了,它是为了唱曲出彩,本质上它是曲牌定腔的必须要求。
三
继周德清之后,明万历年王骥德的解说最有参考价值,王骥德说:
务头之说,《中原音韵》于北曲胪列甚详,南曲则绝无人语及之者。然南北一法。系是调中最紧要句字,凡曲遇揭起其音,而宛转其调,如俗之所谓“做腔”处,每调或一句、或二三句,每句或一字、或二三字,即是务头。《墨娥小录》载务头调侃曰“喝彩”。又词隐先生尝为余言:吴中有“唱了这高务”语,意可想矣。旧传[黄莺儿]第一七字句是务头,以此类推,余可想见。古人凡遇务头,辄施俊语,或古人成语一句其上,否则诋为不分务头,非曲所贵,周氏所谓“如众星中显一月之孤明也”。涵虚子有《务头集韵》三卷,全摘古人好语辑以成之者。弇州嗤杨用修谓务头为“部头”,盖其时已绝此法。余尝谓词隐南谱中,不斟酌此一项事,故是缺典。今大略令善歌者,取人间合律腔好曲,反复歌唱,谛其曲折,以详定其字句,此取务头一法也。[2]
何谓“务头”,王骥德的解说最切合周氏原意。王氏的解说中有四点对后人理解务头很有帮助:
(1)南曲亦有务头
从王骥德的话中知道,沈璟(别号词隐)曾与王氏说起吴中艺人有“唱了这高务”的说法,即指唱“务头”。王氏说“南北一法”,南曲亦有“务头”,并说“旧传[黄莺儿]第一七字句是务头”,余查《玉簪记·茶叙》[黄莺儿]第一句“芳草掩重门”之“芳草”为阴平、上声相连,第七句“琐窗不管春愁恨”之“琐窗”为上声、阴平相连,“愁恨”为阳平、去声相连,字调搭配良好,音调宛转,富有韵味。因为若从字调讲究,南曲亦重视四声阴阳的搭配,所谓“南北一法”,王氏所言即为字调的搭配。
(2)务头落实到字调
唱曲“做腔”处,“每调或一句、或二三句,每句或一字、或二三字,即是务头”。这是对周氏的“某调某句某字”和“务头在其上”的正确理解,很清楚,务头在曲牌的某句中的某字,或一字、或二三字。在其《曲律·论字法》亦云:“务头须下响字,勿令提挈不起。”[3]
(3)务头上辄施俊语
“或古人成语一句其上”,既然说“一句”,即为务头在其中的一句。“古人成语”即指前人所作的绝妙佳句,如朱权(号涵虚子)《务头集韵》中所辑集的古人好语之类的成句,可惜《务头集韵》不传。
(4)善度曲者定其务头字句
令善歌者,取符合律腔的好曲,反复歌唱,以取其特别动听之处,“详定其字句”,即对特别动听的某句某字,分析其字调。因为“做腔”做得好的所在,亦跟字调搭配得好密切相关。或有人说,昆曲也讲务头吗?昆曲中的南北曲,虽然跟元北曲、明初南曲唱法已有很大不同,但在字调与腔的原理上乃一脉相承,传统是“依字声行腔”,填词作曲者是依定格之字调格律填词,若在务头处,更须凛遵字调的格律,讲究搭配,以出好腔。沈璟所说吴中唱“高务”者,或许即指昆曲。昆曲讲“务头”,很明显是讲唱曲的务头。今传有“昆曲务头廿诀”,是曹心泉在清初旧抄曲谱中发现的,其诀二十个字,曰:“气字滑带断,轻重疾徐连,起收顿抗垫,情卖接擞扳。”后注小字云:“此即务头。”很明显,这是讲唱务头的唱法技巧,如其中将究润腔的方法有滑腔、带腔、顿腔、垫腔、擞腔等,不能说这就是“务头”。可以解释为唱到“务头”处须讲究的唱法技巧,使务头处的“腔”唱得更有曲牌的个性。[4](“此诀”,曹心泉有释文,为曹心泉讲、杜颖陶述,篇名曰《昆曲务头廿诀释》,发表在《剧学月刊》1933年二卷一期上。因该文查阅不便,全文附录于文后,以供参阅。)
本人认为,对于“务头”的理解,只要认真研究周德清、王骥德之说,已可基本领悟其含义和要领,填词作曲者须在字调上下工夫而已。而后的诸家之说,尽可取其合理的解释即可。清初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有“别解务头”一说:
予谓“务头”二字,既然不得其解,只当以不解解之。曲中有“务头”,犹棋中有眼,有此则活,无此则死。进不可战,退不能守者,无眼之棋,死棋也。看不动情,唱不发调者,无“务头”之曲,死曲也。一曲有一曲之“务头”,一句有一句之“务头”。字不聱牙,音不泛调,一曲中得此一句,即使全曲皆灵;一句中得此一二字,即使全句皆健者,“务头”也。[5]
虽然李渔说“务头二字千古难明”,对周德清“葫芦提”的说法很有意见(《啸余谱》中务头一卷,即周德清《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但其“别解”亦甚得要领,以“棋眼”作比,务头即是曲之“眼”,曲不可没有务头。有此务头,看能动情,唱能发调;并重视务头之一二字,有此一二字全句皆健,有此一句全曲皆灵。李渔仅点到此而止,不以谜语欺人,诚君子之言。其说的“一二字”要发调,自然须讲究阴阳平仄。在有清一代,曲家和唱家都很重视“务头”的填词和度曲。曹心泉发现的清初“务头廿诀”是一例,以下二例亦很明确。
清乾隆年间的黄振在传奇《石榴记》的“凡例”中曾很明确地说到务头之字调,曰:“每曲中有上去字,有去上字,断不可移易者。遍查古本,无不吻合。乃发调最妙处,前人每于此加意,取合务头。”[6]
清刘熙载在同治年刊刻的《艺概·词曲概》中亦提到“务头”的重要,曰:“辨小令之当行与否,尤在辨其务头。盖腔之高、低,节之迟、速,此为关锁。故但看其务头深稳浏亮者,必作家也。俗手不问本调务头在何句何字,只管平塌填去,关锁之地既差,全阕为之减色矣。”[7]
四
关于“务头”之说,自古以来,尽管解说纷纭,但都重视了务头处字调的重要性。本人受业于吴白匋教授,亦向钱南扬教授问学,二人以宗师吴梅之学教诲,对我的影响很深。对于“务头”的解说,我认为吴梅之说很有道理。吴梅曰:
余寻绎再三,竭十余年之功,始有豁然之境,乃为之说曰:务头者,曲中平上去三音联串之处也。如七字句,则第三、第四、第五之三字,不可用同一之音。大抵阳去与阴上相连,阴上与阳平相连,或阴去与阳上相连,阳上与阴平相连亦可。每一曲中,必须有三音相连之一二语,或二音(或去上,或去平,或上平,看牌名以定之)相连之一二语,此即为务头处。[8]
且以周德清《定格四十首》之例曲证之,无所不合。本人在上文亦分析过周氏定格之字调的平声阴阳与上、去声之搭配,正与吴梅所言相同。有人于此曾提出异议,认为周德清说的是北曲,北曲上去并不分阴阳。自周氏后,阴阳之说订韵者各有所见,有平声不分阴阳,而去声分阴阳者,有上声合阴阳者,在南北韵合订诸书中,已有四声皆分阴阳者。吴梅之说当可通于南曲矣。有人认为按吴梅之务头字调施俊语,不成词或语,我在上文已说施俊语主要是在务头所在句,故有古人成语云云,吴梅亦说“不可拘牵四声阴阳之故,遂至文理不顺”,其意分明,而且他句亦可施俊语。
吴梅之说亦得王季烈首肯,王氏在《螾庐曲谈》卷二《论作曲》中谈务头,引吴梅的论述后曰:“准此说。”且补充说:“盖务头大都在调之末句,或其中吃紧之处,于此必须用俊语,不可轻率。可施之‘可’字,当作‘宜’字解。”又说:“余谓《北词广正谱》所注上、去不可移易之处与《南曲谱》所注某某二字上、去妙,某某二字去、上妙,凡此皆宜用务头之处。于此施以俊语,则词采音节,兼擅其长,诵之是佳句,唱之亦是妙音。李氏所谓最易动听者,此也。”[9]王氏亦认为南北曲皆有“务头”,且将“可施俊语”修正为“宜施俊语”,说得更为贴切,在语意中亦很明确说务头在句中的字调上,如“调之末句”、“诵之是佳句”,所谓“俊语”应从全句看,如周氏说叹孔子一阕的[红绣鞋]之“口”是务头,王氏说“功名不挂口”是务头,以句论,皆是熟娴填词之法的见解。
“务头”一词亦曾在昆曲传奇《桃花扇·传歌》中出现:(https://www.xing528.com)
[皂罗袍](旦)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净)错了,美字一板,奈字一板,不可连下去。另来另来!(旦)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净)又不是了,丝字是务头,要在嗓子内唱。(旦)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净)妙妙!是的狠了,往下来。
这里的说法是错误的。务头不是在“丝”字上,而在“雨丝”二字上,阳上、阴平相连,阳上转音后落在阴平上,有宛转其音的效果。王季烈批评道:
丝字隶支时韵,唱时宜从齿缝出,不可张口出声。故云“要在嗓子内唱”,实与务头无涉。孔氏不解“务头”二字之义,而将“雨丝”为务头,与“丝”字不可出声唱二事,误并作一事,遂使学者益滋疑惑。[10]
论述至此,需要进一步解说的,就是上文已经提到的曲牌“定腔”的问题。
王季烈在《螾庐曲谈》卷三《论谱曲》中谈到“主腔”问题,曾说:“凡某曲牌之某句某字,有某种一定之腔,是为某曲牌之主腔。”[11]他的“主腔”说是论述同宫调曲牌联套的乐理依据,未说到与“务头”有什么关联。其子王守泰在《昆曲格律》中说:“务头是一个曲牌乐调上的特殊表现。”他认为昆曲中的北曲的腔,大致上继承了元北曲的腔,于是对周德清分析的部分曲牌的字调,以《集成曲谱》中同曲牌的腔之结音进行比对分析。他认为,“务头之处应当已形成一个曲牌的具有特殊风格的主腔和结音”,“由于这一结音的特殊性使得这一主腔的旋律特别俏丽,可能这就是务头”。[12]他直接将探讨的问题从字调进展到腔上来,这对我们理解“务头”的腔的属性是有帮助的。
务头既与曲牌的唱腔相关,而且是非常有关的,填词必须在某字位上讲究四声阴阳的搭配,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持曲牌之“腔”。曲牌的唱腔是有个性的,具有与其他曲牌不同的腔的旋律与色彩,腔的个性是如何达到保持不变的呢?洛地先生在《词乐曲唱》中论述了曲牌的“腔”能保持不变的原因,其奥妙就在必须讲究务头。洛地认为:“自明至今,研究、释说的人可称无数,冒说一句,似乎还没有哪位真说到点子上的。比较起来,还是吴梅先生说得最近实,惜似犹亏一篑而未及成。”[13]所谓“近实”,是指说到了曲牌某字位上的四声阴阳的搭配,所谓“犹亏一篑”,是指未进一步说到曲牌的“定腔乐汇”的要紧问题。洛地说:
每个曲牌都是有定腔的。曲与唱同行,每个曲牌在其仍处于“曲子”状态时,必有其特定的定腔“以乐传辞”。“北曲”的每个曲牌传唱辞式漫漶无定的文辞,它的定腔,就不(能)是全曲性的定腔,而只(能)是在某些地方即某个别字位上有其定腔乐汇。这些定腔乐汇是必定要的,否则便不成其为该曲牌了。“北曲”乐府小令将原先漫漶的辞式简洁化、律化而为律曲小令,又必须保留这些须用定腔乐汇之处。这种在各曲牌必须使用定腔乐汇的地方,有个特称,便是“务头”。[14]
为了保持曲牌的个性(音乐上的特别之处),就必须在曲牌的某个和某几个字位上强调“以乐传辞”,有其“定腔乐汇”,所以务头是跟曲唱有着必须的联系的。填词在某个字位上的四声阴阳搭配的要求,必须符合“定腔乐汇”的字声要求,才能在行腔中保持曲牌的个性。洛地先生检查了周德清“定格”小令的所谓务头处,即是“定腔乐汇”处,所以必须按字位的四声阴阳的要求填词,才能按“定腔”行腔,保持曲牌个性。这是务头的本义所在。
从元周德清提供给后人的信息中探寻其义,从务头处为什么要讲究字调发凡,继后深入到字调与“定腔”的关系。周德清在文中已经提出“不分务头,亦不能唱采”的观点,只是未能强调讲究字调就是讲究“腔”。本文最后归结为“务头”是保持曲牌个性的特定字位的定腔,即“定腔乐汇”处。曲家所以特别讲究“务头”,就是为了保持曲牌的“定腔”,以保持曲牌的个性。
附录:
昆曲务头廿诀释
曹心泉讲 杜颖陶述
或以为只是北曲有“务头”,其实不然,王伯良《曲律》曰:“……旧传[黄莺儿]第一七字句是‘务头’……”则南曲也有“务头”。《水浒传》白秀英说唱《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话本,至“务头”停声乞缠头云云,则唱话本中也有“务头”,其实如诸宫调、赚词等,或许也有“务头”,惟以毫无证据不敢妄断。
昔曾闻人言,昆曲中亦有“务头”,然每以询诸知音,率皆瞠目莫对。前年夏间从心泉师学曲,偶于闲话之际,谈及“务头”,承心泉先生不吝赐教,概然以“务头廿诀”相授。
“廿诀”系心泉先生于清初旧抄曲谱中得知,原文系五言四句:“气字滑带断,轻重疾徐连,起收顿抗垫,情卖接擞扳。”后注小字云“此系务头”。
此篇释文,系受教于心泉先生时之笔记。然“廿诀”中,泰半必须口传心授,非楮墨所可形容者,故此篇殊草草,尚祈识者谅之。
昆曲与昔之南北曲唱法均异,故其“务头”,证以旧说,亦未能尽合,故特于本题之上标明“昆曲”二字,以免误会。
——杜颖陶
气:无论吹唱,皆以气为主,气不足则音不贯。故凡学曲,必以养气为第一步,盖房子为什么必要先打地基?因为基础不稳固,建筑在其上的东西,绝不会坚牢。地基和建筑物的关系是如此,气和吹唱的关系也是如此。一支曲子,绝不是可以以一口气从头到尾唱下来的,所以学曲不可不懂得偷气、换气。凡偷气、换气的地方,行家谓之气口,曲中的气口,在规律上并没有指定的地位;但在适宜上,却有它不可移异的地方。
字:曲文是字组成的,因此唱曲不能不顾到字。字有南北之分,普通皆谓“南从洪武,北问中原”,然洪武韵系为科场而作,绝不适于度曲,而歌南曲者,实际上亦不遵用,大致仍以“中原”为依傍,惟入声不派三声而已。记韵之书,如范昆白《中州全韵》,李书云《音韵须知》,王鵕《音韵辑要》等,皆佳。(近曹心泉先生又将各家之书,详为校订,汇为一卷,名曰《剧韵新编》,本刊已发表其一部分,不久全书单行本即可出世矣。)
滑:惟去声字用之,在字第一工尺之后,在曲谱中的记号是从中下向右上的一扬( )。这样一个符号,是告诉说,其前面的一个工尺的尾音,要向上挑起。至于挑起若干高,要看前后的两个工尺了。如果上
)。这样一个符号,是告诉说,其前面的一个工尺的尾音,要向上挑起。至于挑起若干高,要看前后的两个工尺了。如果上 工,那便上
工,那便上 工,如果上
工,如果上 一四,那便于上
一四,那便于上 一四,但尾音的挑起绝没有挑至乙凡两音的。
一四,但尾音的挑起绝没有挑至乙凡两音的。
带:惟上声用之,和滑正相反,记号是从中上向左下一撇( ),或将所带之音写一
),或将所带之音写一 小工尺记在偏右亦可。
小工尺记在偏右亦可。
断:入声断字,惟南曲有之,宜如刀切。
轻、重、疾、徐、连:以上五种不必再加注释,因为笔墨所可写到的,还不及顾名思义可以晓得的多。
起、收:唱曲要分起头收头,逢起必舒,逢收必扳。
顿:顿住之谓,如《断桥》中唱至“叵耐他”时,“他”字要猛可的顿住,这便是“顿”。
抗:抗起也。凡揭高之处,每易不及,故需用此法。
垫:垫腔也,在有赠板的曲子里,比较多见。例如《长生殿·定情》[念奴娇序]中“谁堪领袖嫔嫱”之“袖”字,工谱原来是工五六工尺,但唱时要在六字后垫一小腔,方显得灵活。凡垫腔以前一工尺为准。例如 ,垫腔之后,则成
,垫腔之后,则成 六工
六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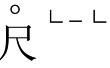 。
。
情:曲有曲情,要唱得出,但以恰到好处者为佳,过与不及,皆所非宜。
卖:所谓“卖头”是也,凡揭高其调,抛开板而唱,单卖一句的地方,谓之“卖头”。例如《送客》[收江南]中“叹从军弟幼”句是,余如《男祭》、《阳告》、《投渊》等皆有之。
接:接接是也,数人递接而唱,衔接之处,要一气浑成,如天衣无缝者方佳。
擞:分三种:(一)灵擞,凡 符号者是。(二)三擞,凡··
符号者是。(二)三擞,凡·· 符号者是。(三)死擞,凡…符号者是,如《山门》[混江龙]“梵王宫殿”句之“梵”字是(按:“梵”字唱法系尺上四四四上尺)。
符号者是。(三)死擞,凡…符号者是,如《山门》[混江龙]“梵王宫殿”句之“梵”字是(按:“梵”字唱法系尺上四四四上尺)。
扳:由快板放慢谓之扳,多在收时,而曲中间也还常见。
【注释】
[1](元)周德清《中原音韵》,《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36、232页。以下所引《中原音韵》,均为此版本,不另注。
[2](明)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14页。
[3]同上,第124页。
[4]曹心泉、杜颖陶《昆曲务头廿诀释》,《剧学月刊》,1993年二卷一期,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研究所。
[5](清)李渔《闲情偶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七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47页。
[6](清)黄振《石榴记》,清乾隆年间刻本。
[7](清)刘熙载《艺概》,《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九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19页。
[8]吴梅《顾曲麈谈·原曲·论北曲作法》,《吴梅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第32页。
[9]王季烈《论作曲》,《螾庐曲谈》卷二,商务印书馆石印本上册,1928年,第四十四、四十五叶。
[10]同上。
[11]王季烈《论谱曲》,《螾庐曲谈》卷三,商务印书馆石印本下册,1928年,第十九叶。
[12]王守泰《昆曲格律》第三章《曲牌》之“务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3—185页。
[13]洛地《词乐曲唱》,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
[14]同上。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