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崖仙使——汉代艺术中的羽人及其象征意义
贺西林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北京,100102)
作者简介:
贺西林,男,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美术考古与美术史。
汉代艺术中常见一种肩背出翼、两腿生羽、大耳出颠的人,此人就是文献中所说的羽人,即飞仙。《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王逸注:“《山海经》言: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洪兴祖补注:“羽人,飞仙也。[1]”仙的概念在汉代文献中屡见不鲜,飞仙图像亦广泛出现在汉代艺术中,其几乎遍及于汉代艺术的全部,贯穿于汉代艺术的始终,构成汉代艺术的一项重要母题,在汉代思想与信仰世界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一
羽人的基本造型是人与鸟的组合。这种造型早在商代就已出现,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晚期墓出土一件羽人玉雕,羽人人身人面,鸟喙鸟冠,腰生翼[2]。战国时代,画像铜器上出现不少羽人形象。如河南辉县琉璃阁59号战国墓出土的一件狩猎纹壶,器表饰有衔蛇践蛇之鸟、操蛇之神、羽人以及狩猎图像,其中羽人鸟首人身,肩生双翼[3]。江苏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的画像铜器残片上也见有羽人形象,羽人皆鸟首人身,或操蛇、或射猎[4]。湖北荆州天星观2号战国楚墓出土的一件羽人驭风鸟彩漆木雕,羽人人首人身,鸟喙鸟爪,身生羽翼[5]。(图1)
那么汉代羽人与先秦羽人是否有关呢?见两种观点,徐中舒说:“羽人、飞兽及操蛇之神,皆为西方最早期,即公元前三四千年来,埃及、米诺、巴比伦、希腊、印度等地盛行之雕刻、造象或传说。”认为其于公元前五世纪传至中亚阿姆河流域,然后进入中国。并断言:“画仙人著翼形,必非中国民族固有之想像作风。”说:“观淮南出土之镜,及汉画中仙人,皆高鼻生羽,高鼻明为伊兰以西之人种,其为外来,尤为显然。[6]”孙作云不同意徐氏看法,认为羽人为中国民族固有之传统。说先秦与两汉羽人图像略异,前者形态原始,后者更富人间情趣,但两者基于同一宗教信仰和艺术传统,皆脱胎于《山海经》,思想根源在于东夷族系的鸟图腾崇拜[7]。
笔者以为,战国羽人源于商代,出在东夷,还是输自海外?迷雾重重,不可明辨。汉代羽人与战国画像铜器上的鸟首羽人有多大关系?亦毫无头绪,难以厘清。然而,2000年湖北荆州天星观2号楚墓的发掘,无疑为寻找汉代羽人的直接渊源提供了新的线索。该墓出土的羽人驭凤鸟雕像似乎拉近了与汉代羽人的距离,两者之间的默契表明汉代羽人可能脱胎于楚文化,与楚羽人一脉相承,其思想根源于战国中晚期楚地渐兴的长生久视之道、神仙不死之术。

图1 羽人驭飞鸟,彩漆木雕,羽人高33.6厘米,战国,湖北荆州天星观2号楚墓出土,荆州博物馆藏
汉代羽人亦多为人鸟组合,偶见人鸟兽组合。与以往不同的是,汉代羽人大都长着两只高出头顶的大耳朵,时代特征极为鲜明。其具体造型大致可见四类,第一类:人首人身,肩背出翼,两腿生羽。第二类:人首,鸟身鸟爪。第三类:鸟(禽)首人身,身生羽翼。第四类:人首兽身,身生羽翼。

图2 羽人,青铜雕塑,高15.3厘米,西汉,陕西西安南玉丰村出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

图3 羽人,青铜雕塑,高15.5厘米,东汉,河南洛阳东郊出土,洛阳文物工作队藏
四类羽人中,第一类出现频率最高。这类羽人身生羽翼,大耳出颠,长相怪异,整体面貌似人,与早期文献中描述的仙人特征基本吻合。汉诗《长歌行》:“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8]”《淮南子·道应训》说仙人若士“深目而玄鬓,涙注而鸢肩,丰上而杀下。[9]”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说仙人“邛疏之双耳,出乎头巅。[10]”王充在《论衡·无形》中更是一语道破了当时图画仙人的特点,说:“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此虚图也。[11]”这类羽人最为多见,如陕西西安南玉丰村汉城遗址出土的西汉羽人小铜像,羽人高鼻大耳,修眉阔嘴,背部和双腿皆生毛羽,造型怪诞,表情诡异[12]。(图2)河南洛阳东郊出土的一件东汉鎏金青铜羽人小雕像,造型与西安汉城遗址出土的羽人非常相似[13]。(图3)
其他三类皆不多见。第二类年代较早的例子见于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帛画,帛画下段画有两个对栖于穿璧羽饰上的羽人,为人首鸽身[14]。类似图像还见于重庆巫山东井坎东汉墓出土的一枚圆形饰棺铜牌上,铜牌下部“天门”两侧均出现有人首鸟身羽人,其中一侧的羽人还是男女双首合体造型[15]。第三类例子在山东嘉祥宋山3号东汉小祠堂西壁上栏可窥见一斑,西王母仙庭中,跪于西王母旁边的一位羽人即为禽首人身形象[16]。第四类例子见于河南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17]和南阳麒麟岗东汉画像石墓[18],其中羽人皆人首兽身,身生羽翼。
二
留存至今的羽人图像大都出自墓葬,汉代墓室与享祠建筑、棺椁葬具以及各类随葬品中,几乎随处可见羽人的踪影。
河南洛阳西汉卜千秋墓主室脊顶壁画前端绘一持节引领的羽人[19]。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主室脊顶壁画绘一驭龙飞升的羽人[20]。陕西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墓室后壁上端见有羽人驭龙图[21](图4)。陕西定边郝滩新莽前后壁画墓墓室西壁绘赴仙图,画面一侧绘西王母仙庭,见有笋状峰峦和三个蘑菇状高台,西王母端坐中间高台上,两位侍女陪伴两旁。一侧高台上立一羽人,为西王母举华盖;另一侧高台上有一玉兔和一九尾狐,台下有一蟾蜍。画面另一侧下部绘灵异乐舞场面;上部绘赴仙,前一羽人踏云引领,后随云舟以及由鱼、兔、龙骖驾的数辆云车,最后是两个乘鹤者[22](图5)。陕西靖边一座新莽前后壁画墓墓室券顶绘天象神灵,其中见有奔走的羽人以及羽人驭云车图像(图6)[23]。辽宁金县营城子2号东汉壁画墓主室北壁绘升仙图,画面上角见一羽人,其手持芝草,脚踏浮云,正在接引升仙者[24](图7)。河南密县打虎亭2号东汉晚期壁画墓墓室券顶绘云天灵异,其中见有或骑天马、或乘白鹿、或捧仙药的羽人[25]。

图4 羽人驭龙,壁画,西汉,西安理工大学汉墓

图5 赴仙,壁画,新莽前后,陕西定边郝滩汉墓
陕西绥德四十里铺永元四年(92)田鲂墓前室后壁横额中间刻乐舞百戏,日、月分列两端,月旁刻仙庭,见有西王母、侍从、九尾狐、三足乌、捣药玉兔;日旁刻赴仙,二羽人骑鹿前导,后随一辆飞鸟骖驾的云车,舆内座二人,驭者为羽人[26](图8)。河南南阳麒麟岗东汉晚期画像石墓室顶刻画羽人戏灵瑞,一灵瑞居中,两侧各一腾云飘舞的羽人,其中一羽人手持芝草和飘带(图9)。墓中还见有羽人骑兽、羽人乘龟等图像[27]。山东安丘董家庄东汉晚期画像石墓前室北壁东端方柱见有羽人;封顶石刻有日、雷公、雨师、风伯、电母、云气、羽人。中室南壁东端方柱和西壁见有羽人;室顶斜坡及封顶石见有或持芝草、或六博、或戏龙的羽人。后室西间西壁刻有大山、龙、虎、鹿、象、鱼、鸟、羽人以及狩猎场面,其中羽人或挥舞嘉禾,或戏灵瑞;北壁横额和室顶南坡见羽人戏凤、羽人戏虎。后室东间北壁和东壁见羽人戏虎、羽人戏鹿;室顶西坡刻云车出行,前有羽人骑虎开道,后有羽人骑兽压队[28]。沂南北寨村东汉晚期画像石墓墓门东立柱刻东王公和两个捣药羽人;中立柱亦刻一羽人。前室西壁北段刻羽人戏灵瑞(图10);过樑和八角擎天柱及上端斗拱出现有多个羽人。中室东壁横额鱼龙曼衍戏中见一驭虎羽人;过樑和八角擎天柱及上端斗拱刻有西王母、东王公以及羽人戏龙、羽人戏凤等图像[29]。苍山城前村东汉元嘉元年(151)画像石墓墓门左立柱刻西王母、羽人、山峦,图像与题记“堂三柱,……左有玉女与  (仙)人”吻合。后室后壁上栏刻朱雀、凤鸟、白虎、羽人,图像与题记“后当朱爵(雀)对游
(仙)人”吻合。后室后壁上栏刻朱雀、凤鸟、白虎、羽人,图像与题记“后当朱爵(雀)对游 
 (仙)人,中行白虎后凤皇(凰)”对应 [30]。
(仙)人,中行白虎后凤皇(凰)”对应 [30]。

图6 羽人驭云车,壁画,新莽前后,陕西靖边汉墓

图7 升仙,壁画,东汉,辽宁金县营城子2号汉墓

图9 羽人戏灵瑞,画像石(拓片),纵120厘米,横260厘米,东汉,河南南阳麒麟岗汉墓出土,南阳汉画馆藏

图8 赴仙,画像石(拓片),横额纵28厘米,横265厘米,东汉永元四年(92),陕西绥德四十
里铺田鲂墓出土,绥德汉画像石展览馆藏

图10 羽人戏灵瑞,画像石(拓片),纵123厘米,横51厘米,东汉,山东沂南北寨村汉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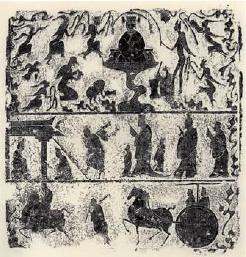
图11 西王母仙庭,画像石(拓片),纵69厘米,横67厘米,东汉,山东嘉祥宋山出土,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藏

图12 骑鹿升仙,画像砖(拓片),纵25厘米,横44厘米,东汉,四川彭州九尺乡征集,四川省博物馆藏
山东嘉祥东汉晚期武氏家族墓地中的武梁祠、前石室、左石室三座享祠两 侧山墙锐顶西王母与东王公仙庭中皆出现有羽人。前石室室顶、后壁小龛内两侧壁上栏及后壁上部见有羽人。左石室室顶、后壁小龛两侧下栏及小龛后壁上部也见有羽人[31]。其中前石室顶石天庭图,分四层,下层刻有坐于斗车中的天帝以及拜谒者和奔赴天庭的车马;上三层刻雷公、风伯、雨师、电母以及驭龙、驾车的羽人。嘉祥宋山三座东汉晚期小祠堂两侧壁上栏皆刻画西王母、东王公仙庭,其中皆见羽人。如3号小祠堂西壁,上栏刻西王母仙庭,西王母端坐于中央蘑菇形基座上,两侧有飞鸟、蟾蜍、捣药玉兔和七个羽人。其中一羽人持杯跪于西王母旁,一羽人为西王母举伞盖,其余五个羽人手持嘉禾,奔走跳跃(图11)。2号、3号小祠堂后壁上部也刻有羽人。与这批画像石同出的一块永寿三年(157)题记石上见有:“上有云气与仙人”[32]。
墓室画像砖上也不乏羽人图像。如河南南阳出土的一块汉画像砖,画面中央刻画二龙穿璧,一侧刻画羽人驭虎,一侧刻画一头奔牛和一只张牙舞爪的熊[33]。四川彭州义和乡征集的一块东汉画像砖,其上浮雕羽人六博图像[34]。彭州九尺乡征集的一块东汉画像砖,刻画一骑鹿升仙者,一羽人随其后,羽人一手托举药盘,一手前伸,似在递仙药,骑鹿者回头伸手,似在接药[35](图12)。
羽人图像还广泛出现在葬具上。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第三重漆棺棺表一侧绘仙山祥瑞图,见有象征昆仑的三峰之山以及龙、虎、麒麟、凤凰、羽人[36]。长沙砂子塘西汉墓漆棺足挡绘羽人驭虎图[37]。四川东汉晚期画像石棺上,羽人图像特别丰富。彭山江口双河崖墓石棺棺表一侧刻画西王母仙庭,见有西王母、三足乌、九尾狐、蟾蜍、丹鼎、捧药钵者以及吹奏和抚琴的二仙人[38]。郫县新胜乡石棺棺表一侧也刻画西王母仙庭,此外还见山巅仙人六博图像[39](图13)。简阳鬼头山崖墓石棺棺表一侧刻日神、月神、树、龙、鱼、鸟、车马、仙人骑、仙人博图像,并题刻有“日月”、“柱铢”、“白雉”、“离利”、“先(仙)人博”、“先(仙)人骑”[40]。
羽人图像也习见于随葬器物上。陕西咸阳新庄村西汉渭陵陵园建筑遗址出土一件羽人骑天马玉雕,羽人手握芝草,执缰策马,腾跃云天[41](图14)。河北定州三盘山122号西汉墓出土一件错金银铜管,表面刻画山峦、云气、羽人、龙、虎、鹿、熊、鹤、兔、鸟、凤凰、天马以及胡人骑象、胡人骑驼、骑射狩猎等图像[42](图15)。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汉“中国大宁”博局镜上见有四神、怪兽、羽人[43]。故宫博物院藏一枚汉代神仙博局镜上见有西王母仙庭、羽人射虎、羽人驭鱼、羽人驭鸟等图像[44](图16)。河北定州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一件透雕玉屏上雕有西王母和羽人[45]。河南南阳出土一件东汉博山铜炉,造型为羽人头顶香炉[46]。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出土一件陶树灯,座上塑虎、鹿、猴、兔、蛙、羽人等,树上塑龙、蝉、羽人,羽人或坐于树枝上,或驾驭飞龙[47]。四川彭山东汉崖墓出土一件陶塑钱树座,上端塑一羽人,羽人手持芝草,驾驭翼羊[48]。

图13 西王母仙庭,画像石棺(拓片),东汉,纵89厘米,横225厘米,四川郫县新胜乡出土,四川省博物馆藏

图14 羽人骑天马,玉雕,长8.9厘米,西汉,陕西咸阳新庄村出土,咸阳市博物馆藏
除墓葬系统外,宫殿遗址中也发现有羽人。陕西西安南玉丰村汉城遗址出土的青铜羽人小雕像,据发掘者称,其出土地点“南距长乐宫北宫墙遗址约5米。出土时夹在距地面约0.5米的红烧土和瓦砾的堆积中。从其造型和出土地点看,可能是西汉宫廷内的供物[49]”。另外,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描述西汉鲁恭王刘余灵光殿壁画中亦绘有神仙,与其共处的还有玉女、胡人、龙、虎、朱鸟、白鹿、玄熊等[50]。再者,铜镜、博山炉等器物,虽出自墓葬,但多非明器,而是随葬的“生器”。种种迹象表明,羽人图像同样存在于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环境中。

图15 神仙祥瑞纹铜管,青铜器,高26.5厘米,径3.6厘米,西汉,河北定州三盘山122号汉墓出土,河北省博物馆藏

图16 神仙博局镜,青铜器,直径16.5厘米,汉,故宫博物院藏
通过上述举证,可归纳出以下几点认识:1. 羽人图像存在于现世环境与死后家园两大时空体系中。2. 在墓葬与享祠建筑中,羽人通常被刻画在墓室与享祠顶部或四壁上部,以及墓门或墓内各室入口的横额与立柱部位,大多分布于建筑的上层空间。3. 羽人常出现在三类图像组合中[51],① 翱翔于云天,与天帝、雷公、雨师、风伯、电母等天庭诸神济济一堂;② 出没于仙庭,与捣药玉兔、蟾蜍、九尾狐、三足乌等灵瑞一同陪侍在西王母或东王公周围;③ 游戏于祥禽瑞兽中,与龙、虎、鹿、朱鸟、凤凰、熊羆等祥瑞戏舞。三类图像时而独立,时而交汇,全然一种超自然境界。4. 羽人的行为状态常见有驭龙、驭虎、骑鹿、骑天马、驭云车(龙、虎、鹿、鱼、鸟等骖驾的车)、戏龙、戏虎、戏凤、戏鹿、侍奉、六博。还见有驾鹤、乘鱼、骑象、驭翼羊、戏天马、戏熊、射猎、抚琴、吹奏、捣药、献药等。
三
羽人,飞仙也。那么何谓仙?《释名·释长幼》:“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故制字人傍山也。[52]”仙也作仚,《说文》:“仚,人在山上貌,从人山。[53]”可见,仙与山密切关联。《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王逸注:“明光,即丹丘也。[54]”《山海经·西山经》:“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郭璞注:“皆光气炎盛相焜燿之貌。[55]”故丹丘,即昆仑丘。另《史记·封禅书》:“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56]”闻一多所说既是:“神仙并不特别好海。反之,他们最终的归宿是山——西方的昆仑山。他们后来与海发生关系,还是为了那海上的三山。[57]”他还说:“西方人相信天就在他们那昆仑山上,升天也就是升山。[58]”《淮南子·地形训》:“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涼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59]”由此可见,即便是太一的天庭,也未脱离云崖之巅。仙与山的结合造就了一个超凡世界,这个远离尘世、超越生死、自由自在的世界就是汉代人心目中的天堂。
仙正是生活在这个超凡世界中的主人,他们不食五谷,吸云气,餐沆瀣,饮玉醴,茹芝草,吃大枣,踏云乘蹻,云游四方。《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60]”《淮南子·原道训》:“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蜺,游微雾,惊怳忽,历远弥高以极往。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景。扶摇抮抱羊角而上,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61]”桓谭《仙赋》:“吸玉液,食华芝,漱玉浆,饮金醪。出宇宙,与云浮,洒轻雾,济倾崖。观仓川而升天门,驰白鹿而从麒麟。周览八极,还崦华坛。氾氾乎滥滥,随天转琁,容容无为,寿极乾坤。[62]”汉镜铭亦见:“尚方作竟(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徘徊名山采芝草,浮游天下敖四海,寿蔽金石为国保。[63]”正如顾颉刚总结之:仙的中心观念,即长生不老和自由自在[64]。羽人作为飞仙,具备仙的一般特性,即不老不死与自由快乐,是永生与自在的典范。
然而汉代艺术中所见羽人,大多似乎并不轻松悠闲,其行踪总是来去匆匆,状态总是忙忙碌碌。这种现象表明,羽人可能是汉代众仙中的一类,其除具备仙的一般特性,即自身长生不老和自由自在外,或许还有更重要的作用与功能。图像与文献两方面显示,汉代羽人肩负三项神圣使命,即:1. 接引升仙,赐仙药;2. 行气导引,助长寿;3. 奉神娱神,辟不祥。
羽人乘蹻、踏云、驭车常见于汉代艺术中,如羽人驭龙、驭虎、骑鹿、骑天马、驭云车,其中不少羽人手握延年益寿的仙草,还有些羽人秉持象征王命的符或节。他们穿梭于云崖之巅,导护于赴仙者之列,状态非常紧迫,感觉不是在独享云游的快乐与惬意,而是在奋力接引奔赴天堂的众生。图像显示,接引升仙,赐予仙药是羽人的重要使命。羽人的这种功能也见于文献,汉诗《长歌行》说:“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65]”稍晚曹植《飞龙篇》云:“晨游泰山,云雾窈窕。忽逢二童,颜色鲜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长跪问道。西登玉台,金楼复道。授我仙药,神皇所造。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寿同金石,永世难老。[66]”
在汉代艺术中,羽人常出现在龙、虎、鹿、鸟、熊等各种祥禽瑞兽间。他们或游走跳跃,或屈伸俯仰,或轻举升腾,与众祥瑞嬉戏共舞。图像显示,羽人与祥瑞明显存在互动关系,两者似有某种交感与呼应,其举止状态很像所谓的行气导引。《庄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67]”《淮南子·精神训》:“若吹呴呼吸,吐故内新,熊经鸟伸,凫浴蝯躩,鸱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68]”《后汉书·华佗传》:“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  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69]”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中提到的导引术有龙导、虎引、熊经、龟咽、燕飞、蛇屈、鸟伸、猿据、兔惊[70]。《抱朴子内篇·微旨》还说:“明吐纳之道者,则曰唯行气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则曰唯导引可以难老矣。[71]”很显然,羽人行气导引,既在巩固自身,同时亦在传达实现长生久视的方法与秘诀,以助众生延年益寿,甚至不老不死。
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69]”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中提到的导引术有龙导、虎引、熊经、龟咽、燕飞、蛇屈、鸟伸、猿据、兔惊[70]。《抱朴子内篇·微旨》还说:“明吐纳之道者,则曰唯行气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则曰唯导引可以难老矣。[71]”很显然,羽人行气导引,既在巩固自身,同时亦在传达实现长生久视的方法与秘诀,以助众生延年益寿,甚至不老不死。
在汉代艺术中,羽人还频见于西王母、东王公仙庭中,尤其是西王母仙庭。羽人侍奉在西王母身边,或撑举华盖,或手持信符,或抚琴,或吹奏,其角色显然是西王母的随从或信使。此外,也常见仙人六博,其出场不同,包括西王母仙庭。关于仙人六博,在时代稍晚的诗文中可略见一二,魏曹植《仙人篇》:“仙人揽六著,对博太山隅。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72]”南陈张正见《神仙篇》:“已见玉女笑投壶,复睹仙童欣六博。[73]”南陈陆瑜《仙人揽六著篇》:“九仙会欢赏,六著且娱神。[74]”从中可见,仙人六博有自娱或娱神的含义。另外,汉代镜铭见有:“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左龙右虎掌四彭,朱爵(雀)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刻娄(镂)博局去不羊(祥),家常大福宜君王。[75]”这表明,作为宇宙式图的博局,具有辟邪功能[76]。由此推知,仙人六博同样具有辟除不祥的象征意义。
生死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永恒主题,延年益寿乃至长生不死是人类的本能诉求,承认大限的存在,但又试图超越之的尝试,则是这一诉求合乎逻辑的发展,仙正是这一诉求在汉代思想与信仰中的特殊表达。作为飞仙,羽人出没于阴阳两界,既关照生者,又慰籍死者,其不仅是长生久视的榜样,更是引导众生与亡魂往生洞天的仙使。
(责任编辑:朱元晦)
注释:
[1]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7页。
[2]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59页,彩版四六。
[3]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66页,图版玖叁。
[4]淮阴市博物馆《淮阴高庄战国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第189—232页。
[5]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81—184页。
[6]徐中舒《古代狩猎图象考》,《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92、284、232页。(原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下册),1933年)
[7]孙作云《说羽人——羽人图羽人神话及其飞仙思想之图腾主义的考察》,《孙作云文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下)。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61—641页。(原载《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汇刊》1947年第1期)
[8]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2页。
[9]《淮南子》,《诸子集成》(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204页。
[10]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页。
[11]王充《论衡》,《诸子集成》(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5页。(https://www.xing528.com)
[12]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市发现一批汉代铜器和铜羽人》。《文物》,1966年第4期,第7—9页。
[13]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2·秦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43页,图版说明第45页。
[14]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39—45页。
[15]重庆巫山县文物管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98年第12期,第77—86页。
[16]嘉祥县武氏祠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发现汉画像石》。《文物》,1979年第9期,第1-6页;蒋英炬《汉代的小祠堂:嘉祥宋山汉画像石的建筑复原》。《考古》,1983年第8期,第741—751页。
[17]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5期,第1—16页。
[18]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6·河南汉画像石》。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02—116页,图版说明第44—45页。
[19]洛阳博物馆《洛阳卜千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第1—12页。
[20]同注17。
[21]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5期,第7—44页。
[2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76页。
[23]此墓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材料尚未公布。
[24]内藤宽、森修《营城子—前牧城驿附近の汉代壁画砖墓》。东京:刀江书社,1934年,第15—36页。
[2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269—312页。
[26]榆林地区文管会、绥德县博物馆《陕西绥德四十里铺画像石墓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3期,第19—26页。
[27]同注18。
[28]安丘县文化局、安丘县博物馆《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济南:济南出版社,1992年,第9—18页。
[29]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北京: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1956年,第12—29页。
[30]山东省博物馆、苍山县文化馆《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考古》,1975年第2期,第124—134页;方鹏钧、张勋燎《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象石题记的时代和有关问题的讨论》。《考古》,1980年第3期,第271—277页。
[31]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52—82页。
[32]嘉祥县武氏祠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发现汉画像石》。《文物》,1979年第9期,第1—6页。济宁地区文物组、嘉祥县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一九八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第60—70页。蒋英炬《汉代的小祠堂:嘉祥宋山汉画像石的建筑复原》。《考古》,1983年第8期,第741— 751页。
[33]中国国家文物局、意大利文化遗产与艺术活动部《秦汉—罗马文明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322—323页。
[34]中国画像砖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砖全集·四川汉画像砖》。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图版说明第77页。
[35]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彭县等地新收集到一批画像砖》。《考古》,1987年第6期,第533—537页。
[36]同注14,第25—27页。
[37]湖南省博物馆《长沙砂子塘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第2期,第13—24页。
[38]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7·四川汉画像石》。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16—117页,图版说明第48页。
[39]四川省博物馆、郫县文化馆《四川郫县东汉砖墓的石棺画象》。《考古》,1979年第6期,第495—503页。
[40]雷建金《简阳县鬼头山发现榜题画像石棺》。《四川文物》,1988第6期,第65页。
[41]咸阳市博物馆《咸阳市近年发现的一批秦汉遗物》。《考古》,1973年第3期,第167—170页。张子波《咸阳市新庄村出土的四件汉代玉雕器》。《文物》,1979年第2期,第60页。
[42]中国历代艺术编辑委员会《中国历代艺术·绘画编》(上)。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50页,第333页图版说明。
[43]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6·铜镜》。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59页,图版说明第20页。
[44]故宫博物院《故宫藏镜》。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48—49页。
[45]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1期,第8—20页。[46]李国灿《东汉青铜天鸡羽人炉》,《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第69—70页。
[47]洛阳博物馆《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2期,第116—134页。
[48]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6—37页。
[49]同注12。
[50]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28—529页。
[51]羽人偶见有极为特殊的出场。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中室室顶北坡乐舞百戏图中见有六博和游走的羽人,场面人神混杂、真幻交织。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中室东壁横额鱼龙曼延戏中也见一羽人驭虎图像。《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认为此羽人是戏者所扮演的角色。对读李尤《平乐观赋》、张衡《西京赋》,此说当是。
[52]徐坚等《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49页。
[5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83页。
[54]同注1。
[55]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53—54页。
[56]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69—1370页。
[57]闻一多《神话与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1—172页。
[58]同注57,第174页。
[59]同注9,第57页。
[60]王先谦《庄子集解》,第4页,《诸子集成》(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
[61]同注9,第2—3页。
[62]同注50,第248页。
[63]同注44,第46—47页。
[64]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中华文史论丛》一九七九年第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79年,第35页。
[65]同注8,第262页。
[66]同注8,第421—422页。
[67]同注60,第96页。
[68]同注9,第105页。
[69]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39—2740页。
[70]同注10,第274页。
[71]同注10,第124页。
[72]同注8,第434页。
[73]同注8(下),第2482页。
[74]同注8(下),第2539页。
[75]孔祥星《中国铜镜图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66页。
[76]周铮《“规矩镜”应改称“博局镜”》。《考古》,1987年第12期,第1116—1118页。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72—174页。附记:原文《汉代艺术中的羽人及其象征意义》载《文物》2010年第7期,第46—55页,本文有所增补。
(上接第10页)《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76、3);《兰州花寨子“半山类型”墓葬》(《考古学报》80、2);《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60、2)。
[10]《元君庙墓地反映的社会组织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一九七五年东海峪遗址的发掘》(《考古》76、6):《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76、3);《兰州花寨子“半山类型”墓葬》(《考古学报》80、2)。
[11]《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12]《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
[13]《随县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14]黄留珠《汉代仕进制度》。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第106—142页。
[15]埃及原有人殉制度,自公元前2300年起,人殉逐渐为Shabti(小人像)所代替。但人殉并没有消失,仍有妇女自杀或被杀陪葬现象,但毕竟越来越少了。(Nigel Davies: Human Sacrifi ce in History and Today pp36—37)
[16]蔡邕《独断》:“随刻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妆)具。”《汉书·韦贤传附韦玄成传》:“日上四食。”
[17]以上有关陵寝、陵庙的观点,采自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8]按马皇后为明帝后而非光武后。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