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学者登堂入室
事实上,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掌握要多于和早于西方人了解中国哲学,所以中国学者也比西方学者更早地感觉到了西文中的“是”同西方哲学的关系。
我们前面已经从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中转引过霍布斯的一段话,他猜测到语言中有无系词“是”可能会影响哲学的形态和面貌。从中国学者的立场上,胡适立即从逻辑的角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比较了《易经》里的辞与西方逻辑的命题,说道:“一个中文的命题或者辞和西方的与之相当的东西的不同在于系词。系词在西方的逻辑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在中文的命题里却被省略,它的位置仅用短暂的停顿来表示。……在西方逻辑中围绕系词发生出来的一切神秘的晕就这样被消除了。”胡适是在1917年写就的博士论文中首先表达了这一观点的。
据我看到的材料,在中国学者中联系语言进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较深入的当数张东荪了。他的成果集中反映在《知识与文化》一书中。该书初版于1946年,然而作者的“自序”落款为“民国二十九年”,即1940年,由此可知此书成于30年代,书后还附有五篇论文,都写于书稿之前。1995年由汤一介任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编委会整理出版了一部张东荪文化论著辑要(张耀南编),收录了《知识与文化》作为其中一篇,并以此作为这部辑要的书名,通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但原书的第三编及五篇附录删去了。
张东荪论述语言与思想方式、哲学形态的范围甚广,其目的是要让人见出中西哲学及思想方式上的差异,其中有许多值得注意和发掘的深意。这里我们且先注意他关于与本体论有关的一些语言问题的论述。
我们先要说明一点,张东荪说过“中国哲学上没有本体论”,(19)但有时他又说成中国没有“本体的哲学”,并标明后者的英文原文为“substance philosophy”,(20)这个术语我们不记得在西方哲学的典籍中读到过。我们知道张东荪所说的“本体”同中国哲学史上所说的“体用”之“体”是有明显区别的。因为他说:“此字(指substance)译为本体亦可,而译为本质亦无不可,但最好兼取二者之意。”(21)并且他又说过:“西方人的哲学无论哪一派,其所要研究的中心对象是所谓‘reality’,这个词在中国哲学上就没有严格的相当者。因为中国哲学所注重的不是求得‘真实’。须知‘求真实’则必是先把‘reality’与‘appearance’分为两截。而后一字在原始中国思想上亦没有恰好的相当的词。”(22)从这些话来看,他是明白西方哲学的总体精神的。但是,我们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用ontology这个原词,却代之以自造的substance philosophy。他甚至还标明“being”就是本体。(23)我以为这些都反映出张东荪对本体论的研究还欠精当。正是因此,影响了他观察西方语言与西方哲学关系的角度,以致未能中的。他从语言特征方面论述中国没有所谓“本体的哲学”的一个主要例证是说,中文的文法并不强调非得有主语才能成为句子,同时,谓语动词的主动态和被动态也无明显区分,这些都导致句子的主语不分明,而西方哲学的“本体”范畴,据他看来是从主语转来的。“因为中国言语上不注重于主语,所以不能发为‘本体’一范畴”。(24)他的这种含糊其词的说法对于国人理解本体论哲学是造成了麻烦的。例如熊十力就不同意说中国哲学中没有“本体”观念的学说,并为此同张东荪展开过辩论。以至于现在有些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便是举出中哲史上有关“本体”、“本”、“根”的观念来论述中国的本体论的。
由于张东荪未能从表达形式上把握本体论原是关于由西文中的系词形成的“是”的学说,他在讨论“是”与哲学的关系时,是与本体论问题分开的,而主要是同逻辑联系在一起。系词是西方传统逻辑中构成命题必不可少的成分,张东荪指出在“文言”中,汉语是没有系词的。他举出古汉语中“为”、“是”,以及在“某者,某也”句式中的“者”、“也”逐一加以讨论,否定了它们是系词的可能(他的这些观点可从汉语学家那里得到印证)。他还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中文的‘为’字等于英文become与is二者。或可以说其意义在此英文两字之间。但须知英文的is有‘存在’(to exist)的意思。所以英文的being一转即为existence。但中文的‘为’却没有‘存在’或‘有’的意思。……因为中国人思想只讲becoming,不讲‘本体’(being),所以中国文字上没有正式与英文is相当的动词。”(25)这里提到了“本体”是指being,且指出being还有“存在”的意思。那么本体论究竟是关于being还是关于substance的学问呢?being与substance是什么关系呢?本体论与逻辑方法是不相干的吗?张东荪的研究似乎显得线条粗了些,用词也存在明显不当之处,故而挡不住深入的追问。但是,当他揭示西方哲学中有一与现象相分离的本质世界,并以此作为与中国哲学相异点提出来时,他毕竟抓住了主要的东西。同时,他明确断言中国哲学中无“本体哲学”,因而引起了争论,这迟早会唤起人们去搞清“本体论”本身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兴趣。(https://www.xing528.com)
我以为,如果人们肯用心去读,便会发现,初版于1944年的陈康先生译注的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即《巴门尼德篇》)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能引导人们步入本体论门庭的著作。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说明过,柏拉图的这部著作是西方哲学史上本体论的开端。它是在理念论的框架内,通过“是”及分有“是”的各种“所是”之间结合或分有的演示,展开一套存在于理念世界中的先天原理体系。这部书很难读懂。陈康以其对西方哲学的精深理解和对西方语言文字的娴熟把握,对此书作了超出原书篇幅几倍的注释,为我们提供了开启本体论门户的钥匙。
陈康也许是我国学者中第一个将汉语的“是”当作哲学概念译希腊文的estin(is)的。指出下面一点也许是有意义的:清末民初的时候,中国有大批学人东渡日本,经过对日文的转译把西方文化介绍到了中国,因此有许多学术名词都是先经过日本学者咀嚼的,包括哲学领域的许多名词也如此。陈康则是较早直接接触西方哲学的中国学者之一,因此他的翻译有理由受到重视。陈康在注释中说明了“是”的意义比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译名“存在”的意义要广。他还把柏拉图这篇对话中的分词on(being)译成“是的”,把分有“是”的理念称为“是者”。这就把英文中因动名词和现在分词的形式没有区别(都写作being)而难以区分的哲学概念都区分出来了。
陈康也用“有”译由“是”分出的部分,他写道:“‘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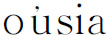 )分为一切的‘有’(onta),‘割裂为最可能小的和最可能大的以及各式各样的有’,那么万有有一共通点,即分有‘是’;”(26)这也是他用“万有论”这个名称取代“本体论”的理由。我们已在第一章中陈述过对这个译名的态度。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不同于“本体论”的名称同样使得寻摘中国哲学史上有关“本体”、“本根”的论述以力图挖掘中国哲学史上的ontology的人失去了攀附。
)分为一切的‘有’(onta),‘割裂为最可能小的和最可能大的以及各式各样的有’,那么万有有一共通点,即分有‘是’;”(26)这也是他用“万有论”这个名称取代“本体论”的理由。我们已在第一章中陈述过对这个译名的态度。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不同于“本体论”的名称同样使得寻摘中国哲学史上有关“本体”、“本根”的论述以力图挖掘中国哲学史上的ontology的人失去了攀附。
陈康在以“是”译estin的同时,也承认“这estin在中文里严格讲起来不能翻译”,他决定采用这一译名是在同其他译名进行比较后的一种选择,对于读者会感到这个译名不习惯、生硬,陈康说明道:“这样也许不但为中国哲学界创造一个新的术语,而且还给读者一个机会,练习一种新的思想方法。”(27)这就从根本上指明了,有关本体论的一系列译名问题,决不仅仅是翻译问题,在术语翻译的深处,将展示出本体论乃是我们还不熟悉的一种新的思想方法。
虽然本体论在现代西方已经衰落,但是它毕竟盛行了二千余年。在我们了解西方哲学史的过程中,本体论作为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思想方法,仍不妨以“新”称之。
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揭示本体论这种“新”的思想方法,为此,我们才不惮其烦地讨论与之相关的语言、翻译问题。陈康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学者早于西方汉学家而注意到了西方哲学同其语言,尤其是本体论同西文“是”的关系,并且,他们的研究也要比汉学家们深刻。可惜的是,他们之后直至现今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在这个方向上专门研究下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