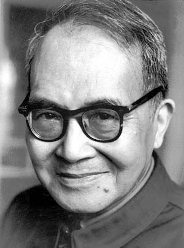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容安馆,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
自文献引证角度而言,钱氏早年的《谈艺录》可算最渊博的诗话,晚年的《管锥编》更是文献积累的登峰造极,为他赢得“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之誉。然而在相当程度上,博学乃钱氏有意示人的公共形象,是外在的学术面相,不过藉此以压倒崇拜材料的文学考证派,非即其庐山面目也。
表面上看,钱氏横贯中西,广涉四部,但论学术趣味,他视野所及,始终以语文修辞现象为中心,大体不出词章之学的范围。[1]《管锥》形式上虽以古籍为单位,其实并非以古籍为真正的研究对象,古今中外经史子集之书,不过供其驱遣,贡献章句的零砖碎瓦,以成就其七宝楼台。[2]至于《七缀集》诸篇,性质亦无所异,实即《管锥》的外编。故他实在是现代的文心雕龙主义者,其长处不在训诂的发明,而在辞例的会通;其取径既非比较语言学,亦非比较文学,勉强名之,可称比较修辞学欤?借用伯林的比喻,他看似无所不知的狐狸,而实为兴趣单一的刺猬。
另一方面,钱氏以博极群书而惊世骇俗,但论学术性格,他绝非文献家、考据家,而是古典意义的评点家,或者说是现代意义的批评家。因此他对胡适派的文学史考证,或陈寅恪式的以诗证史,皆深致不满。[3]《谈艺》旁征博引,可视为适应现代学术规范的随顺世缘之作,钱氏批评的锋芒,只能收敛于文献的深林密叶之中;而他青年时代批注的《石语》(陈衍语录)虽篇幅寥寥,但他与前辈一唱一和,贬抑时流,却更可见其狂狷的真性情。[4]则以《谈艺》为表,以《石语》为里,钱氏其人其学,可以得其近似矣。
故钱氏平生旨趣,可归结为“谈艺”二字:“谈”者,所好在于赏鉴批评;“艺”者,所重在于艺文词藻。
按:钱氏谈艺固然笔挟风霜,论人尤为口无遮拦,一如今日之酷评家。[5]如作文描画其师吴宓,却“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致”;[6]在小说《猫》中,以窝囊的李建侯、风流的爱默两夫妇影射梁思成、林徽音;[7]在西南联大时声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8]以后在私秘的《容安馆日札》中,谈艺之余的评人更见苛刻,于并世名流如冒广生(鹤亭)、邓之诚、谭戒甫、陈寅恪、钱仲联诸公,多肆意讥弹。近时范旭仑作《容安馆品藻录》,一一为之钩沉索隐,并添油加醋,顺风煽火,直可谓《容安馆毁人录》;自好事者观之,是为钱氏功臣,而自钱夫人观之,则为钱氏罪人。
《管锥》之成书,得力于钱氏日积月累的读书心得,其中自《容安馆日札》取材亦甚多;《日札》始作于五十年代思想改造运动时,[9]则《管锥》可视作1949年以后钱氏个人的心力所萃,更可代表1949年以后大陆文史之学的结穴。盖此数十年间,政治气候肃杀,文化界动辄得咎,知识分子惟有从公共思想遁入冷僻学术,亦如文字狱促进清儒由义理之学遁入考据之学。而《管锥编》极材料堆砌之能事,更以简约古雅的文言出之,拒俗众于千里,正隐约可见钱氏“避席畏闻文字狱”的心理。[10]
按:钱氏在完成《围城》后,本拟另撰长篇《百合心》,并已成稿两万字,至1949年后却不了了之;与此类似,沈从文、施蛰存五十年代后亦由文学转向学术,沈攻服饰文物,施治金石碑版。此缘当时文学须直接服务于政治,而文博研究尚能稍远于时事也。施氏更自嘲“一九五八年以后,几乎有二十年,生活也岑寂得很。我就学习鲁迅……抄写古碑。这是一个讽刺。因为鲁迅从古碑走向革命,而我是从革命走向古碑”。[11]则《管锥》亦钱氏之古碑耳。钱氏亦同于沈、施,藉治学为避世,可谓“学遁”矣。
现代学人兼习旧体诗文者,举不胜举,而能兼新文学创作者亦复不少,沈、施以外,如鲁迅、郭沫若、许地山、陈衡哲、袁昌英、苏雪林、郑振铎、闻一多、冯沅君、陈梦家,比比皆是。[12]而钱氏尤个中翘楚,既以《围城》鸣世,复以《槐聚诗存》传世,新旧文学皆臻巅峰。以其学问、文采两手皆硬,故拟为双枪将董平。
钱氏藏书极少,[13]这与他读书之多,恰成“残酷的对照”。[14]又,他在《围城》中曾说“一切图书馆本来像死用功人大考时的头脑,是学问的坟墓”、“图书馆倒像个敬惜字纸的老式慈善机关”,这种图书馆观,与他勤上图书馆的习惯,又成“残酷的对照”。
父钱基博,旧派的国学名家,著作甚富。
诗曰:胸罗万卷似围城,道是逃名已盛名。谈艺论人亦苛刻,本来高士是狂生。
注 释:
[1]《围城》行文的特色,不仅在引证、用典的繁富,尤在修辞的庞杂,此与《管锥编》以修辞为焦点的比勘正相呼应,可见钱氏在创作与学术两方面的贯通。又,钱氏之浩博,既出于天赋(记性)及勤奋(博览),亦因为所关注的问题在于语文修辞层面;故任何语言、任何文本,皆有可供采撷的材料,《管锥》实可无限增补。(https://www.xing528.com)
[2]古史辨派以经、子为史,邓之诚、陈寅恪以诗为史,而钱氏可谓以经、子、史皆作集部看矣。按:龚鹏程指钱氏“固然是在研究经史,但其研究方式和着眼点,仅在经史的文章意味而已。……经学、史学、小学、诸子学、哲学,钱先生均不当行;惟穿穴集部、纵论文学,乃其当行本色,彼亦以此点染四部耳。”(《钱锺书与廿世纪中国学术》,《近代思潮与人物》,中华书局2007年)其意可取。至于夏志清称钱氏为“道地的汉学家,把十部经史子集的代表作逐一加以研究”,“为古代经籍作训诂义理方面的整理,直承郑玄、朱熹诸大儒的传统”(《重会钱锺书纪实》);张文江谓“《管锥编》所依托的十部书,横贯经史子集,气魄宏大,已寓有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批判之意”(《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钟书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页114),则皆甚皮相。
[3]钱氏1978年在意大利所作《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演讲有云:“在解放前的中国,清代‘朴学’的尚未削减的权威,配合了新从欧美进口的这种实证主义的声势,本地传统和外来风气一见如故,相得益彰,使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使考据和‘科学方法’几乎成为同义名词。那时候,只有对作者事迹、作品版本的考订,以及通过考订对作品本事的索隐,才算是严肃的‘科学的’文学研究。一切文学批评只是‘词章之学’,说不上‘研究’的。”(《钱锺书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这最可见他对胡适派学风的不满,同时亦显示,钱氏本人的学问取向正是所谓“词章之学”。又指:“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则显然针对陈寅恪而言。可参李洪岩、范旭仑《钱锺书·吴宓·胡适派》、《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辨疑》(《为钱锺书声辩》,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4]陈衍为前清名宿,以《石遗室诗话》及《续编》指点江山,为民国旧诗坛之龙门,惟鉴赏成分多于学问成分耳。
[5]宗璞小说《东藏记》以尤甲人影射钱氏,指钱氏夫妇以刻薄人为乐,“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参陆灏《东写西读·笺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6]此系吴宓本人对钱的评语(《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册页96)。
[7]参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的生平与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页269-274)。
[8]周榆瑞《也谈费孝通和钱锺书》,据李洪岩、范旭仑《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辨疑》引,《为钱锺书声辩》。
[9]杨绛《〈钱锺书手稿集〉序》。
[10]关于《管锥》何以用文言的问题,钱氏答复余英时云:“可减少毒素之传播。”(刘永翔《钱通》,《蓬山舟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页33)杨绛亦表示:“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锺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版,页155)
[11]《北山集古录·自序》,巴蜀书社1989年版。
[12]欧洲汉学家中,高本汉曾用瑞典语匿名发表三部长篇小说([瑞]马悦然《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页272-278);高罗佩则用英文创作中国题材的《狄公案》系列,尤为知名。
[13]参黄永玉《北向之痛——悼念钱锺书先生》,《火里凤凰》,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吴泰昌《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学者的书房》,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按:任继愈曾谓,熊十力是他所知“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玄圃论学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熊氏系六经注我式的哲学家,故重理解,轻典籍也。
[14]语出钱氏《林纾的翻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