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族音乐学实践者来说,最容易被忽视又不易被认识和察觉的人的因素,是音乐对象主体的音乐意识。音乐意识在音乐对象主体的行为及过程显示中属于心理的、意念的社会属性范畴,它经常处于音乐群体或音乐个体音乐行为中潜伏、隐蔽的更深层次,特别是在传统的或民间的音乐事象中,音乐个体或音乐群体更是如此,因而它常常被民族音乐学实践者所忽略。其结果就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某些民族音乐学实践者的研究常常将音乐对象主体心理的、意念的和审美的、概念的象征性意义抛弃,而成为人类某些群体和个体的一种机械性音乐活动产物,这种考察和研究接触到的音乐事实,只能是音乐事象本体构成的表层形式和内容。
由于音乐对象主体的群体形式包含着个体形式,个体形式又是群体形式的个别体现,因而音乐对象主体的音乐意识也相应包含“群体音乐意识”和“个体音乐意识”两种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不同形态。正确认识和理解二者的特征和关系,是进入对人的音乐行为及过程更深层次认识的基础。
1.群体音乐意识
群体音乐意识是一种复杂、有机的音乐意识组合,它由传统习惯势力左右的若干个体音乐意识综合而成,在音乐上往往包含着有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三种成分。处于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各民族群体,其音乐意识能力和意识成分比重往往表现出较大差异。一般说来,音乐群体所处社会环境生产力越低下、越迟缓,群体成员的社会独立性较弱,群体音乐意识就越浓,潜意识和无意识成分就越大;反之,群体所处社会环境生产力越先进、越发达,群体成员的社会独立性较强,群体音乐意识就越淡薄,潜意识和无意识成分就越小,便可能逐渐被个体的有意识行为取而代之。
【关键词链接】 打歌与踏歌
打歌,以脚步踏跳为主要特色的一类民间歌舞形式,古老踏歌样式的孑遗。踏歌(历史文献所用他称),主要流传于西南地区白、彝、纳西、傈僳、普米、藏等民族中。因民族和支系不同,在不同民族或支系中又有名目繁多自称,如白族称“打歌”;彝族称“打跳”、“跳脚”、“跌(叠)脚”、“左脚”、“跳嘎”、“跳歌”;藏族称“果谐”、“果卓”、“歌装”、“锅庄”等。
踏歌,早在宋代即因“踏跳”、“踏步”特点鲜明而被历史文献记载。宋人陆游《老学庵笔记》写道:“男女聚而踏歌,家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夜疲则野宿至二日,未厌,则五日或七日方散归。”明清时期,西部、西南部各族踏歌习俗,传播更为普遍,文献记载也更明确具体。清人桂馥《扎朴》记:“夷俗:男女相会,一人吹笛、一人吹芦笙,数十人环绕踏地而歌,谓之‘踏歌’。”
白、彝、纳西、傈僳、普米、藏等民歌的打歌与踏歌,主要在民族传统节日、婚嫁活动、乔迁新居、款待宾客时的群体聚会中进行,场所多在野外、街头、广场。表演时,成群结队,挽手围圈或成列,以脚踏地,或徒歌或以竹笛、芦笙,或以弦子(三弦、琵琶)等乐器伴奏,边舞边歌。
鉴于民族音乐学所涉音乐对象主体,主要是与民间音乐相关并在社会民俗中活动的音乐群体,其音乐意识反映即包含着大量潜意识和无意识成分,需要相关音乐研究者深入音乐生活现场去进行融入式的实地考察工作,在群体音乐实践活动中去体察、探寻群体行为中潜意识和无意识成分所包容的群体音乐动机、目的和相关概念,从而达到尽可能客观、准确地理解和认知相关音乐事象本质的目的。例如,中国西南澜沧江流域白、彝、傈僳等民族社区群体,他们在传统的青年婚礼活动中,一般都要夜以继日地进行“打歌”(一种围在火塘边边唱边跳的群舞)活动,原先不同辈分成员不能同聚歌唱爱情歌曲的禁忌(有意识的选择),此时竟荡然无存。老态龙钟的“阿波”和“阿嬷”(对老年男女长辈的尊称)追随在少男少女的歌舞行列,如痴如狂地跳唱着古朴的不同于青年所唱的打歌调,充满着青春的爱意。表面看来,浓烈的气氛、痴狂的歌舞,显现出人们已完全进入受传统习惯势力支配而无个人选择的无意识音乐状态,然而融入此歌舞场景的观察者,却可以从有意识的歌舞禁忌被解除的若干相同事例中,体察到在此种音乐群体无意识状态下潜伏着的群体成员对往昔群歌择配、自由婚爱的追忆和眷恋,从而引导观察者继续迈入“打歌”音乐形态和文化内涵的更深层面的研究。这就像民族学和民俗学学者认识彝族“抢亲”习俗的潜意识那样,最后从中体察和总结出此种习俗隐含着历史上该族曾经历过的“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时男性对女性的首次抗争以及女性对男性在婚姻上的初次让步”这一过渡性婚姻制度环节,为母系社会演进到父系社会的婚姻发展史研究找到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过渡性环节例证。
群体音乐意识对个体音乐意识是一种文化惯力的制约和限定,在各民族社区的民俗性音乐生活中,个体成员绝大多数都处于无意识状态,只有少数为群体公认、受群体尊重的最优秀的歌手和乐手才属例外。这就是为什么民族音乐学实践者一般不能在个别歌手和乐手的接触中,而只能在音乐群体的接触中才可能感受到大多数人牵涉音乐的意识因素、行为动机、文化属性以及稳定的音乐结构形态和原生性音乐特征的根本原因。(https://www.xing528.com)
2.个体音乐意识
个体音乐意识是一种包含在群体音乐意识中,但对群体意识又有所超越的个别成员的音乐意识。在民族、社区、社团等各类音乐群体中,由于个体组合成员音乐素质和音乐实践经验积累的差异,随着群体音乐生活的发展,其个别优秀成员在音乐行为上常常要作出突破群体音乐行为的行动选择,从而表现出个体音乐意识对群体音乐意识的某种程度的超越,这就是群体音乐意识中个体意识有意识成分的觉醒。
个体音乐意识对群体惯性音乐意识的自觉超越,是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事象发展、演变乃至形成新的群体音乐意识的根本动力。因此,民族音乐学实践者在深入民族群体的音乐生活观察某一音乐事象时,又须随时将注意对象和焦点集中投射到某些优秀的音乐代表人物身上,这是探索音乐品种地域、流派风格及音乐作品形式内容个性构成的关键举动。
中国汉族音乐群体中的优秀说唱艺人、戏曲演唱与表演艺术家、乐器演奏家,各少数民族音乐群体中的优秀歌手、乐手和集技、艺、术为一身的宗教性仪式执行者(巫师),在不同社会环境中都不同程度地在歌种、乐种、曲种和戏曲剧种声腔的发展、传播方面有过创造性的积极贡献。中国传统音乐领域中某些代表曲种、剧种表演艺术的演唱“风格流派”的形成(如京剧“四大流派”),某些古琴(图14)、古筝、扬琴、竹笛演奏家的地域化演奏“风格流派”的形成,就是相关表演艺术家、演奏家个体音乐意识自觉超越的结果。这些演员、演奏家的艺术生涯和音乐表演艺术实践,特别是他们个人在音乐实践上表现出的有意识活动及对群体惯性音乐意识的超越,自然应当为民族音乐学考察和研究所注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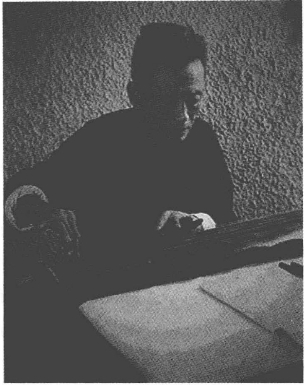
图14 自成一派的古琴家管平湖
目前的一般情况却是,除专业音乐文化发达地区音乐群体中的优秀个体被关注而列为考察和研究对象之外,其余地区音乐群体中的优秀个体(如汉族地区基层的民间艺人、少数民族地区的音乐代表性人物)被列为考察和研究对象的还非常有限,有的民族和地区甚至还处于空白,究其原因,当与目前民族音乐学界仍存在忽视对音乐对象主体进行科学考察和研究的现象有关。
综上所述,树立科学的民族音乐学主体观,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更深入、更准确地对音乐事象进行科学解释,在任何民族的传统音乐生活中,作为创造音乐的主体对象,无论他是群体形式还是个体形式,都正好客观地处于音乐事象与外部环境之间和音乐事象中行为、理念与音乐作品之间的中心环节。把握住了这个至关重要的中心环节,也就把握住了音乐事象与外部环境和音乐事象行为、理念与音乐作品之间的关系,从而也就把握住了音乐事象或音乐作品的本质。人的音乐行为、音乐意识和音乐作品(声音形态),构成了音乐艺术的全部内容。人作为音乐艺术创造过程中最富于生命力和价值意义的积极因素,永远都将成为民族音乐学考察和研究对象的主体和核心。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