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帆(北京大学)
摘 要:本文以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写本为切入点,通过整理与分析写本中粟特字母的词首、词中、词尾三种书写形式,制作出完整的“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字母表”。此外,以此字母表为基础,笔者列表对比了具有相似发音的粟特、回鹘、老蒙古文和满文字母的词首形式,揭示了它们彼此间的承继源流:粟特文促成了回鹘文的出现,回鹘文为老蒙古文之渊薮,满文的创制以老蒙古文为依托。笔者还通过对满文字法中“符号点”之来源和作用的梳理,补足辛姆斯-威廉姆斯对粟特文字母之阿拉米文前世与满文今生的论述。
关键词:粟特文《善恶因果经》;满语;佛教粟特语语法
汉文《善恶因果经》全名为《佛说善恶因果经》,又称《因果经》《佛说因果经》和《菩萨发愿修行经》,作者不详。此经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是在《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中。称其:
右件经古来相传皆云伪谬,观其文言冗杂,理义浇浮。虽偷佛说之名,终露人谟之状。迷坠群品,罔不由斯。故具疏条列之如上。[1]
《大周录》断定这部经为伪经,并且批评其误导信徒。《开元释教录》[2]和《贞元新定释教目录》[3],也都沿袭此说。
《善恶因果经》在今日不少寺庙的法物流通处依然能见其身影,它虽为伪经,在民间却有着持续的影响力。在历史中,此经曾以多种语言在不同地区流行过。敦煌发现的《善恶因果经》拥有汉文、藏文和粟特文等不同语种写本。张小艳博士在《汉文〈善恶因果经〉研究》一文中厘清了该经的汉文本研究状况,提出该经见于佛教目录虽在695年,然而隋仁寿四年(604)的敦煌写本《优婆塞戒》卷末题记中已有该经踪影。[4]604年可以作为《善恶因果经》成立史上的一个坐标。对于藏文本《善恶因果经》的文献学研究与释读,萨仁高娃、陈玉、任小波等藏学研究者在此方面,已经取得不少成果。[5]任小波在其2016年新出版的《吐蕃时期藏译汉传佛典〈善恶因果经〉对勘与研究》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记载在藏文目录中,由法成与释迦光二人依据汉文《善恶因果经》所翻译的两部藏译本[6]在用词与表意上的细节不同。[7]
《善恶因果经》的粟特文本目前只发现一件,是汉文和粟特文双语写本,于1908年由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获得(P. 3516),也即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该写本被伯希和带回法国后,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1920年伯希和与高梯奥(Gauthiot)合作,前者将汉文经文翻译为法语,后者根据伯希和的翻译破译了粟特文写本中的粟特词汇含义并转写和翻译了粟特文。高梯奥的弟子邦维妮斯特(Benveniste)随后又为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做了进一步注释。三人的成果以及粟特文《善恶因果经》的写本图版,在1920年至1928年间一并由法国热内出版社(Geuthner)出版。[8]随着《善恶因果经》“汉、法、粟特”三文集成本的面世,扎克(Zach)[9]等语言学家对书中汉语以及粟特语词汇进行了诸多讨论。[10]1970年,英国学者麦肯齐(Mackenzie)再次转写了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写本,并将其翻译成英语。[11]相继问世的法文本和英文本对粟特文《善恶因果经》的翻译和注释,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哲世维(Gershevitch)、汉贝克(Humbach)、麦斯特尔(Meisterernst)和杜尔肯(Durkin),都以书评的形式,再次探讨了该经的文本翻译与解读。哲世维讨论了经文中的粟特词汇用法[12],麦斯特尔与杜尔肯详察了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对古代汉语中被动句的翻译方式[13]。以恒宁(Henning)与辛姆斯-威廉姆斯(Sims-Williams)为代表的学者,细致区分了粟特文文献中对x与γ的写法异同,并将《善恶因果经》粟特文转写中的rm纠正为‘M。[14]2013年,伊朗学者立足前人的成果,依据全新的转写规则,出版了波斯文的《善恶因果经》。[15]
以上是对流通于国内与国外,对于汉、藏、粟特文三本古老的写本,学者的翻译和研究状况。除了以上几种语言,《善恶因果经》还应当存在蒙古文本与满文本。检验蒙古文《甘珠尔》目录[16],有两条经目似与《佛说善恶因果经》相对应。然而碍于笔者并没有阅读蒙古文《大藏经》的能力,该条目以下之内容是否为《善恶因果经》则尚未可知。笔者仅能依据蒙古文《大藏经》的藏文来源[17],以及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对蒙古文本《善恶因果经》的呼吁[18],推测该经实际有蒙古文本存在。此外,根据满文《大藏经》的汉语来源,笔者推测《善恶因果经》也以满文的形式流传着。[19]满文本《大藏经》 [20]目录下亦有两条与《善恶因果经》相类[21],只因笔者未找到满文《大藏经》原文,不能断言其内容是否全部对应于汉文《善恶因果经》。
本文所研究的粟特文《善恶因果经》(P. 3516),原件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笔者制作“字表”所依据的写本图片来自1920年法国出版的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全部图版。如下图所示:
图1 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图版示例,此为经文50—63[22]
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写本中的每一列均有编号,其首列写有“题为因果经一卷”[23],是为标题列,编号为0,稍有磨损。经文正文有571列,编号为1—571,后文使用的粟特经句前的数字即是此编号。经文中,除去1—3列有所损坏,261—279列书写稍显潦草之外,整部经文书写整洁、用笔连贯。571列中,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分通备。经文1—62列为序分,交代了佛陀说法的时间与地点。在序分中,阿难向佛陀虔诚发问,希望能得到佛陀关于众生之中何以有美丑、强弱等等不同状态的解说。63—550列是正宗分,其主体由佛陀对于善恶因果前缘的解说构成。551—571列为流通分,叙说众人听闻经文后得到的现时果报并将经文“欢喜奉行”。
虽然粟特经文确是对汉文《善恶因果经》的翻译,但其依据的底本与当今通行的汉文《善恶因果经》是否相同还待另说。笔者参照《大正藏》中的汉文经文,逐句对比了汉文与粟特文经文,发现粟特文《善恶因果经》中337—347列中所表达的意思,汉文本里没有与之相对的内容。此外,笔者还发现粟特文对汉文的翻译并非机械地复制。在行文中,粟特文表达的语意与汉文经文在细节处常有不同。笔者推测造成该差异的原因一是翻译《善恶因果经》为粟特文的人,他依据的汉文底本与今日流传的《善恶因果经》不同;二是翻译人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地加入自己的理解和创造以使经文更便于没有汉语储备的人去阅读[24]。
除了版本学和佛经翻译史上的研究意义,书写《善恶因果经》的粟特文本身也值得探索。经文中的粟特文清晰连贯,以此为资源去整理和分析粟特文字母的字体形态,可以制作一份精准的“佛教粟特文字母表”。
笔者即在检阅文中所有字符的基础上,集中在37—74、92—106以及560—571列,按照“词首—词中—词尾”三个不同位置截取了粟特文《善恶因果经》中的字母,制成了“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字母表”。笔者处理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
一、在“竖写”还是“竖读”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善恶因果经》的粟特写本,写手本身便采取垂直书写的方式来誊抄此经(由上而下,由左而右),一如今日之满族书写满文,今日之蒙古族书写蒙古文。粟特文为蒙古文、满文之渊薮,沿波讨源,粟特文之书写方式足见一斑。此外日本学者吉田丰也曾作专文[25]论证粟特文——尤其是被用来书写佛教文献的粟特文——在5世纪后半叶其书写方式大多已由水平横写转变为垂直竖写。按照伯希和对于文本的解读,《善恶因果经》的抄成时间为7—8世纪间,正是在粟特文垂直书写的时段。[26]
二、笔者参照蒙古文和满文的字母学习方式,一一列出写本中所见粟特文字母及其相应的词首、词中、词尾形式,以方便读者观察和了解每个字母在不同位置的用笔和书写方式,有利于现代人学习。
三、此外,笔者还以粟特字母的发音为参考,找出回鹘文、蒙古文和满文中拥有类似发音的字母的词首形式,并将四者的词首形式纳入同一张表格进行对比和分析。这一做法的意义在于能“于比较中见个性”:四种文字的比较让每个粟特字母的个性特征变得突出。比如在区分粟特文里写法相近的t和m时,回鹘文提示笔者t的写法较m更为圆润。其次能“于比较中见共性”。四种文字之间有着亲缘关系,即粟特文为回鹘文之渊薮,回鹘文被蒙古人借用以书写蒙古语,老蒙古文又为满文创制之蓝本。四种文字的共性,是它们之间“血缘关系”的有力证明,说明了粟特文在中国的使用痕迹从未消失。
笔者还将通过分析满文中“符号点”的由来和使用方法,说明粟特系字母如何向着“所写即所读”的精准记音体系发展,即四种本自一脉的文字,通过使用“符号点”来不断明确每个辅音和元音的书写形式:回鹘文开始用字符左边的一点区别辅音n和元音a,蒙古文na/ne同形的现象使得蒙古文“所写非所读”,而这一问题在满文中通过字符右边“符号点”的添加得到解决。辛姆斯-威廉姆斯曾作文论证粟特文的前世今生[27],然而他虽述说了粟特文字之阿拉米文(Aramaic)前世,却并未论及满蒙之粟特文今生。笔者将在第五部分论述“符号点”在满文书写中发挥的作用,并通过探讨对“符号点”使用最为充分的满文字法,展示由回鹘文到满文的文字创用者改进前人文字书写方式的一个办法。
笔者将集中在粟特文《善恶因果经》37—74、92—106以及560—571列中所包含的字母,按照其“词首—词中—词尾”三个不同的位置,截取并罗列出,制成“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字母表”如下。
表1 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字母表
以上是由从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写本中截取的字母所构成的字表。由表中可见,大部分字母之间的差异明显,但仍存在写法近似的字母,比如z与n,t与m,γ与n。
老蒙古文或者满文的字形特征与书写方式,往往可以成为解读粟特字母形态的钥匙。笔者依据经文中的粟特字母,选取了与之具有相同或者类似发音的回鹘文、老蒙古文以及满文字母的词首形式,并在下列表格中简单地比较了四种文字的字母词首形式,以期直观地展示四者之间的相似性。[28]
在列出表格之前,首先要明确的是:
(1)四种文字所承载的语言,并不出于同一语系。粟特语属于印欧语系,后面三种文字所承载的语言虽然都属于阿尔泰语系,但是所属的语族也不一样。所以四种语言在发音上和在字母数量上均不一样。下表的各个字符,仅仅以《善恶因果经》粟特文写本中出现的发音为基准去截取。
(2)回鹘文、老蒙古文和满文,会把全部元音写入字中。
(3)四种文字各有其习用的字母转写体系,在讨论不同文字时笔者将使用相应的转写。
表2 粟特文和回鹘文、老蒙古文、满文的字头对比表
② 回鹘文字母从冯·加班的《古代突厥语语法》一书中截取;A. von Gabain, Alttürkische Grammatik. Lepzig: [s. n. ], 1950, p. 17。
③ 老蒙古文字母从《蒙古文语法》一书中截取;Hambis L., Grammaire de la langue mongole écrite. 1st ed., Paris, Adrien-Maisonneuve, 1945, p. 111。
④ 满文字母从安双成《满汉大辞典》一书中截取;安双成《满汉大辞典》,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⑤ 起始元音,在回鹘文和老满文中表示ā或者ə,满文里只表示ə,满文的ā另有表现形式。
⑥ 表示v的字符,单独有了其他形式,亦即粟特字母之w。β这种写法,也近乎消失。
⑦ 在回鹘文、老蒙古文里,依据各自正字法,γ/x被鲜明区分。
⑧ 在回鹘文、老蒙古文和满文中,写法上没有任何变化。
⑨ 回鹘文中,δ与l的写法就分开了。老蒙古文和满文中l的写法,继承了回鹘文。
⑩ m的变化非常大。在回鹘文中,它从一个圈,变成了向下的一条“尾巴”。为什么回鹘文会把粟特字母里面的圈变成尾巴呢?笔者认为,这个变化不是回鹘文的创造,而是在粟特字母里已经酝酿了胚芽。细细观察经文中粟特文m的写法,笔者发现m右上角确实有提笔的走势。
⑪ 回鹘文里,n边上的一个点,让n容易辨认。
① 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② 写法一致,字母发音产生变化。
③ 满文中有两个t的原因在于,第一个t与阳性元音拼合,第二个t与阴性元音拼合。
粟特人虽然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但是粟特文的影响,在当代社会依旧存在着。从上表的对比中,粟特文、回鹘文、蒙古文和满文,四者的亲缘关系一目了然,事实上,粟特文是回鹘文的前身,回鹘文为老蒙古文之渊薮,而满文的创制又以老蒙古文为依托。接下来笔者将分别论述四种文字的创制和流传过程,以此展现四者在历史发展中的关系。
粟特语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是粟特地区之人所操的语言。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撒马尔罕(Samarkand)是粟特人当年的文化活动中心。[29]撒马尔罕出土的实物考古资料虽多,文献资料却不如中国境内的敦煌吐鲁番等地[30],国内内蒙古以及甘肃,也有粟特文献出土。本文中所讨论的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写本,即出自国内敦煌藏经洞。
粟特人一开始并没有文字,他们使用的文字是阿拉米文(Aramaic)的变体。[31]阿拉米文是通用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an Empire)的文字。[32]阿拉米字是一种辅音文字,在行文书写中不标明元音,从阿拉米文字衍生的粟特文同样也是辅音文字。信仰不同宗教的粟特人会选择不同的字体来书写宗教文献,生活在吐鲁番绿洲说粟特语的基督教徒,使用埃斯坦吉罗文字(Estranghelo)来书写他们大部分的宗教文献。[33]摩尼教徒所使用的摩尼文,则是叙利亚帕米拉(Palmyra)人使用的一种草体文字。[34]不过使用最广泛的还是粟特通用字(National script)[35],通用字被信仰各种宗教的粟特人广泛应用于文学、宗教、医学等各个领域。
如果从时间的角度去梳理粟特通用字,则有三种类型的字体。第一种是敦煌以西出土的粟特文古信札中使用的字体,这种字体属于非草体的一种,字母之间有着清楚的区别且大部分彼此不连写,被认为是最古老的粟特体。辛姆斯-威廉姆斯把信札中的字体称为粟特文古体(Archaic或者early Sogdian)。第二种是佛教经典中所用字体,被称为粟特文正体(formal),出现在5世纪左右。[36]正体中,字母之间开始连写,这导致了部分字母之间的字形区别消失。比如在粟特文《善恶因果经》中的字母z和n,在句中的表现形式几乎没有任何差别(参前字母表)。第三种是粟特文草体(cursive),于7—8世纪间定型。[37]这种字体广泛应用于世俗文书和碑铭文献材料中,还有少部分8—10世纪的摩尼教文献也使用草体粟特文。值得一提的是,回鹘文里继承的粟特字母,正是肇始于斯。
粟特人所长期活跃的河中地区,以及后来的西域、河西走廊一带,一直是中原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等多元文化荟萃之地。回鹘人借助粟特人善于经商的才能以及长期从事丝绸贸易的经历,与中亚各国不断产生联系。回鹘文,或者说生活在中国古代新疆地区的突厥人使用的文字,一开始与粟特文没有区别。根据日本学者吉田丰的观点[38],这是因为给回鹘人带来书写技术的正是突厥化的粟特人,至少是突厥-粟特的双语粟特人。他们生活并融入古代突厥人的世界并且用粟特文来书写宗教与世俗文献。在他们的带动下,回鹘人开始自觉使用粟特文。换言之,回鹘人选用粟特文书写自己的语言,并不是刻意的行动而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无论吉田丰的论断是否正确,粟特人与回鹘人关系极为紧密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我国史书记载中,中原人同回鹘人的第一次成功接触就有赖于一位来自安国的粟特人,粟特人的语言优势让他们在丝路沿线畅通无阻:
太祖遣酒泉胡安诺槃陀使焉。其国皆相庆曰:“今大国使至,我国将兴也。”[39]
粟特人与突厥人通婚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安禄山曾自言:
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40]
在长期的密切交往中,粟特人跟回鹘人开始变得不分彼此。这一过程,类似于粟特人融入在华生活的过程。[41]在二者的密切交往中,佛教粟特文、摩尼教粟特文以及基督教粟特文这三种文字都曾被信仰不同宗教的回鹘人分别接纳和使用。佛教粟特文在回鹘人中只被用来书写佛教文献。[42]而摩尼教粟特文和基督教粟特文,二者合并在回鹘文中,准确地说,应该是活跃在中国西北的古代突厥人所使用的文字中,被称为回鹘体的一种文字书写方式。[43]
西方研究古代突厥语的学者冯·加班(A. von Gabain)的著作《古代突厥语语法》(Alttürkische Grammatik),至今仍然是研究回鹘语的学人绕不开的重要参考。在书中,冯·加班将古代突厥人使用过的字体分为四种,分别是突厥文鲁尼体(die türkische Runenschrift)、突厥文回鹘体(die uigurische Schrift)、突厥文粟特体(die sogdische Schrift)以及突厥文婆罗迷体(die Brāhmī-Schrift)。[44]在生活于中国古代新疆的古代突厥人中,被最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是回鹘体。回鹘体是在粟特体的基础上改进而成,比如通过加点的方式,回鹘体区分了字母q、x、γ,q在左前方加两点表示,x在左前方加一点表示,而γ则不加点。回鹘体在表示n的字符左边加了一点,在表示s的字符右边加了两点以表示š,来区分两个字母。[45]
我国回鹘文研究领域,冯家昇、耿世民先生等先驱们珠玉在前,回鹘文青年学者杨富学等继轨在后[46],在回鹘文领域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然而具体涉及回鹘文字的专著和论文却并不多见。李经纬《回鹘文的字形与字体》一文对回鹘文的字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解读,他将回鹘文字体分为楷书(写经体)、草书、木刻体和模拟体四类。[47]
本文中所说的老蒙古文,相对于今蒙古国使用西里尔(Cyrillic)字母拼写的新蒙古文,指的是回鹘式蒙古文。收录在《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道布的《回鹘式蒙古文》,对回鹘式蒙古文的创制发展,以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作了详细的介绍。[48]
史书中,最早介绍老蒙古文来源的是《元史·塔塔统阿传》。根据列传记载,1204年,蒙古贵族正式用回鹘文为“国书”:
以畏兀字书国言。[49]
“畏兀”文字即回鹘文。回鹘式蒙古文在使用之初,目的是用回鹘文字母来拼写蒙古语,是一种纯粹的“借来”行为或者说“拿来”行为。回鹘式蒙古文拼写法基本上沿用回鹘文的规则。不但字母在不同位置的变体基本一致,就连行款、程式等等也都一样。[50]包力高和道尔基对回鹘文字母表和早期回鹘体蒙古文字母表进行了对比研究[51],发现初期回鹘体蒙古文只是在个别字母读音和书写形式上对回鹘文进行了一些细微的改动。根据现存回鹘式蒙古文文献看来,回鹘式蒙古文最突出的特点是a、n、ng、d、g等字母词尾形式末笔笔画是向下直写的竖笔,因此被称为“立式字尾蒙古文”或“竖式字尾蒙古文”[52],其运笔与书写方式同粟特文《善恶因果经》中的h别无二致。
老蒙古文的产生和使用,承继于回鹘体回鹘文,并在字母连接方面,对回鹘文进行了一些改进。[53]不过老蒙古文依旧是“形不对音”,也就是眼睛看到的文字,不能准确地对应到它的发音。比如说写作humun(人)的蒙古文词,发音却是hūn。而且在元音区分上,对于蒙古文的na/ne、ba/be、wa/we等,只能见一个词就记住一个词的发音,以记忆来区别na/ne等。碍于*nabi与*nebi、*wabi与*webi(如果真的存在这些词)的书写形式完全一致,单纯从写法上,人们并不能将其区分开来。拼写蒙古文的长元音需要记住很多繁复的规则,蒙古语母语者固然可以通过长年累月的积累掌握老蒙古文正字法并且信手拈来地应用,但对于将蒙古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和使用的人来说,蒙古文正字法就成了学习和使用老蒙古文过程中的障碍。无怪乎母语不是蒙古语,却尝试使用蒙古文来书写自己民族语言的满族人要另外对它实行改造。
满语在清代也称清语,它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54]16世纪末,建州女真人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女真社会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统治者认为用蒙古文字已不能适应本族的政治、文化发展需要,于是着手创制满文。努尔哈赤本人精通女真、蒙古、汉三种语言。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敕命额尔德尼、噶盖二人创制满文[55],此时的满文也被叫作老满文。然而,老满文的影响力并没有迅速扩大。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56]在满文创制20年后,蒙古文的影响,仍无减弱。天命四年(1619),朝鲜人李民寏在《建州闻见录》中称:“胡中只知蒙书,凡文簿,皆以蒙字记之,若通书我国时,则先以蒙字起草,后华人译之。”[57]达海在老满文的基础上,对满文书写方式进行了革新。改进后的满文即“加圈点满文”,亦即新满文。[58]本文中所说的满文,并非额尔德尼与噶盖创制的“无圈点”老满文,而是达海改进之后的新满文。从蒙古文到满文,或者说满文对老蒙古文最大的改造,就在于充分使用符号“点”和“圈”来区分老蒙古文里读音相同却写法一致的不同音节,并且改变了长元音的书写方式。
从粟特文到回鹘文再到老蒙古文和满文,满文的创制者给这一谱系的文字赋予了最彻底的变化。他们创新了长元音的表达方式,彻底明确了全部元音和辅音:满文通过符号“圈”“点”的添加与增加,使得每一个字母都能精确记音,实现文字的“所写即所读”。满文之所以能做出如此巨大的改变,有一重要原因就是创制者们看到了这套文字的改进趋势——像回鹘人一样加点并且丰富元音在书写中的形式表现。
辛姆斯-威廉姆斯曾作文解释粟特文从阿拉米文字而来[59],并影响了回鹘文。然而辛姆斯-威廉姆斯却止步于此,没有继续讨论在从蒙古文到满文的革新过程中粟特文和回鹘文所扮演的角色。笔者将为辛姆斯-威廉姆斯一文做补充,详细论述满文中“符号点”所发挥的明辨辅音以及区分元音的作用。充分使用“符号点”去区分每一个辅音和元音的满文,实现了粟特文这一系文字的“所写即所读”。
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元音和谐”是阿尔泰语系最大的特点。满语的元音有六个,分别是a\e\i\o\u\ū,其中阳性元音为a\o\ū,阴性元音[60]e,i\u为中性元音。所谓的元音和谐即指一是同性元音相和谐,比如男人haha、女人hehe;二是阳性、阴性元音分别同中性元音相和谐,比如花朵ilha、尖端dube。但是极少数的情况下,一个词中也会同时出现由阳性元音和阴性元音分别构成的音节,比如小ajige、阿哥age。在达海创制的新满文字法中,“符号点”不仅可以像在蒙古文中一样区别辅音,也可以将阴性元音e与阳性元音a区分开来,中性元音u与阳性元音o区分开来。虽然阴性元音e与阳性元音a,中性元音u与阳性元音o在写法上只有右边“‘一点’之差”,但就是这一个“符号点”的存在,帮助满文成为记音精准的文字,实现了满文的“所写即所读”,解决了老蒙古文中a/e、u/o两对元音在书写中“同形异音”的情况。
从“点”没有被明确和统一使用过的粟特文到固定了“点”的作用的回鹘文与老蒙古文,最后到满文,字母与发音之间对应关系的模糊性被不断削弱,字母表音的能力越来越强。从无到有,从粟特文到满文,“符号点”明辨字母的作用一目了然。从这个角度出发,满文是粟特文这一系字母的最终成熟形式。
图2 点在词汇的左边,用以区分辅音
(从左而右依次读为nananinon、hana、uksin、akdambi)
指示辅音n的词头、词中、词尾(特殊)形式,以及辅音k在词中且下无元音的情况。
左边一个“点”,以“n”开头的单词:
na  ,名词,大地。但是当词中的n下无元音或n落尾时,左边的“点”要消失,比如banjibumbi
,名词,大地。但是当词中的n下无元音或n落尾时,左边的“点”要消失,比如banjibumb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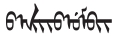 使生长[61]、nahan
使生长[61]、nahan  炕、anagan
炕、anagan  等。
等。
其他元音与n拼读,书写规则同na,见表3:
表3 n的单独书写形式
左边两个“点”:
当辅音k位于词中且下无元音,或在词末其上面元音又恰好是a\e\o\u时,比如:
akdambi  ,动词,信赖;teksin
,动词,信赖;teksin  ,形容词,平整的;okto
,形容词,平整的;okto  ,名词,药。
,名词,药。
图3 点在词汇右边,用以区分送气辅音和不送气辅音
(从左向右依次读为katarambi、gatarambi、tatarambi、datarambi)
当把字母n上的一小“点”,放入“粟特文—满文”的演变历史中,就会发现它的趣味性和创造性所在。邦维妮斯特在《粟特语研究》中曾论述过n/a常难以区分一事,认为n与a之间难以区别不仅给识读造成了巨大困难,还间接影响到了对词源的探索。回鹘文和老蒙古文字法实现了对n\a的准确区别,但二者却用一个形式表示na\ne两个读音。用“点”区分阴性元音和阳性元音,是满族人民的创造。
位于词汇右边的“符号点”既可以明辨辅音也可以明辨元音。明辨辅音,主要体现在它能区分辅音是否送气;明辨元音,主要体现在它能精准区分写法相近的a\e、o\u。
“点”在词汇的右边,可以具体表示所在辅音是否送气。比如小舌音音节ka与ga:
kabangga  ,形容词,成对的;gakarambi
,形容词,成对的;gakarambi  ,动词,张开嘴。(https://www.xing528.com)
,动词,张开嘴。(https://www.xing528.com)
kengse  ,副词,断然地;genembi
,副词,断然地;genembi  ,动词,去、往。
,动词,去、往。
这里的“点”区别送气辅音k与不送气辅音g而不区分元音。由阳性元音a构成的音节ka\ga,与由阴性元音e构成的音节ke\ge的区别体现在写法的不同上。此理同样适用于ko\go与ku\gu。加在右边的“点”只指示辅音是否送气而不区分元音o\u,ko\go写作“方帽子”,ku\gu写作“圆帽子”。这个变化过程对于由舌尖中音t\d构成的音节ta\da、te\de一样适用。
“点”在单词右边,用以区分元音:
比如在a\e、o\u之间。“点”使元音的阴阳中性在词中表现得更为显扬,元音和谐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满文书写中,对于元音阴阳性的区分有两种方式:第一种需要依靠“符号点”的添加,第二种要依靠满文字母的字形变化,比如ka/ke。当词形一致时,通过“符号点”的不同添加方式,元音的阴阳中性能得以区分。这就解决了老蒙古文词汇中“同形异音”的问题。
图4 点在词汇右边,用以区分a/e,o/u
(从左向右依次为nanakan、nenegan、wajibombi、wejibumbi)
综上所述,从粟特文到满文,从“点”的出现到明辨字母作用的最终确立,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从回鹘文到蒙古文,“点”都只是区分辅音而不具备区别元音的功能,满文中,“点”在词汇左边可以标明辅音n、k,在右面可以区分辅音是否送气,以及区分阴性元音和阳性元音。满文解决了存在于粟特文、回鹘文、老蒙古文字母中“同形异音”的表达缺陷,终于实现了粟特文这一系字母的“所写即所读”。
前文通过分析粟特文《善恶因果经》写本中粟特字母书写形式,制作出完整的字母表,可供今后对读之用。这份字母表仅仅是根据《善恶因果经》一个写本制作,此经文中的字母与摩尼教粟特字母、基督教粟特字母有什么区别,甚至与其他佛教粟特写本中的字母之异同,还有待进一步梳理。
在分析字母书写形式的基础上,笔者将具有相似发音的粟特、回鹘、老蒙古文和满文字头列表对比,以直观展示四者之间的承继源流:粟特文直接促成了回鹘文的出现,回鹘文为老蒙古文之渊薮,而满文的创制又以老蒙古文为依托。
通过对满文中“符号点”之来源和作用的梳理可以发现,从粟特文经回鹘文、蒙古文最终到满文,“符号点”从无到有,从区分辅音到兼区分元音,它令粟特文一系的书写符号系统从表音模糊最终演化为“所写即所读”的精确记音体系。
Yang Fan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writing system in the Sūtra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Actions in Sogdian.
The author briefly reviews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this Sūtra at the beginning, and introduces its significance and the approach of this paper.
Then the author mainly deals with the complete set of the alphabet of the Sogdian letters in the Sūtra on the account of their writing forms in the initial, internal and final position. Besides, through the compilation and simple comparison among the initial forms of some specific Sogdian, ancient Uighur, old Mongolian and Manchu letters, the author displays directl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writing system of them. The Sogdian writing system contributes to the appearance of the ancient Uighur, which is the proto-origin of the old Mongolian writing system, which inspires the creation of the Manchu script. In addition, by sorting out the sources and the functions of the “symbolic dot” in the Manchu script, this paper complements the dissertation composed by professor Sims-Williams which discussed the appearance and the effects of the Sogdian script.
Keywords: the Sūtra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Actions in Sogdian, Manchu, Buddhist Sogdian grammar
[1]中华电子佛典协会《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电子佛典集成》,2005年,《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卷,2153号,第472页。
[2]中华电子佛典协会《开元释教录》;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电子佛典集成》,2005年,《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卷,2154号,第677页。
[3]中华电子佛典协会《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电子佛典集成》,2005年,《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卷,2157号,第1022页。
[4]张小艳《汉文〈善恶因果经〉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2016年第16卷,第59—88页。
[5]萨仁高娃、陈玉《藏文〈佛说善恶因果经〉研究》,《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第104—108页。
[6]即Dk354(Pk1023,Tk217)与Dk355(Pk1023)。
[7]任小波《吐蕃时期藏译汉传佛典〈善恶因果经〉对勘与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
[8]Gauthiot R, Pelliot P, “Le Sûtra des causes et des effets du bien et du mal / édité et traduit d'après les textes sogdien, chinois et tibétain par Robert Gauthiot et Paul Pelliot” , Tome I, Fac-similé des textes sogdien et chinois, Paris: Geuthner, 1920.
[9]E. von Zach, “Einige Bemerkungen zu Pelliot's Sûtra des Causes et des Effets” ,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1928,25 (5), pp. 403-413.
[10]Pelliot P, “Encore un mot à propos du Sūtra des causes et des effets et de l'expression siang-kiao” ,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1928, 26 (1), pp. 51-52; Gaspardone E. Robert Gauthiot, “Paul Pelliot et Emile Benveniste: Le Sūtra des causes et des effets du bien et du mal” ,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30,13,pp. 161-162.
[11]Mackenzie D. N. The “Sutra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actions” in Sogdi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2]Gershevitch I. Review of D. N. MacKenzie, “The Sūtra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Actions in Sogdian, Sims-Williams N. Philologia Iranica” , Wiesbaden:Reichert, 1985, pp. 52-54.
[13]Meisterernst B., Durkin-Meisterernst, “Some Remarks on the Chinese and Sogdian Sutra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 Weber D., Languages of Iran, Past and Present. Iranian Studies in Memoriam David Neil Mackenzi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5, pp. 121-127.
[14]Meisterernst B., Durkin-Meisterernst, “Some Remarks on the Chinese and Sogdian Sutra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2005, p. 115.
[15]Hassan Rezaei Gharibidi.  . Teheran:[s. n. ], 2013.
. Teheran:[s. n. ], 2013.
[16]乌林西拉《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目录》(下),北京:远方出版社,2002年,第1826—1877页。
[17]勒·霍尔勒巴托尔、阿拉坦巴根《藏文〈甘珠尔〉、〈丹珠尔〉及其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第92—99页。
[18]任小波《吐蕃时期藏译汉传佛典〈善恶因果经〉对勘与研究》,第3页。
[19]翁连溪《乾隆版满文〈大藏经〉刊刻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6期,第61—65、98—99页。
[20]吴元丰《满文与满文古籍文献综述》,《满族研究》2008年第1期,第99—128页;Marcus Bingenheimer, Catalog of the Manchu Buddhist Canon., 2011[2018-04-10].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anchu/catalog.php。
[21]sain ehe i weilen karulan be foyodome cincilara nomun,直译为:有关善恶业报的经文;fucihi nomulaha sain ehe be deribure be ilgame faksalara nomun,直译为:佛陀说果报出自善恶行为。
[22]Gauthiot R, Pelliot P. Le Sûtra des causes et des effets du bien et du mal / édité et traduit d'après les textes sogdien, chinois et tibétain par Robert Gauthiot et Paul Pelliot.PL.Ⅵ, 1920.
[23]'krtyh 'nβ'nt ptwry 'yw prw'rt.
[24]例如编号23中的rty ms 'sty š'w ptxwrk'-cšm',现代汉语直译为“黑色而充满诱惑的眼睛”对应《大正藏》里“有青黑而婉媚”。翻译人没有机械地将“青黑”翻译成green-black,而是黑š'w;并且对于汉文里省略的“眼睛”,粟特文补充上了。
[25]Yoshida Y. “When did Sogdians Begin to Write Vertically” ,Tokyo University Linguistic Papers (TULIP), 2013, 33, p. 375.
[26]Pelliot , P. Mélanges d'indianisme. Paris:[s. n. ], 1911, pp. 341-343.
[27]Sims-Wlilliams N.,“From Aramaic to Manchu: Prehistory, life and after life of the Sogdian script” ,荣新江、罗丰《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物的新印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14页。
[28]因为哪怕是同一种文字,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根据书写人的不同,也会有不一样的书写模式。就满文而言,达海改进的新满文与额尔德尼创制的老满文之间的区别非常大。表格中“不求甚解”的展现方式,如果能令排列在一起的四种文字,使人产生“原来它们真的相像”的感觉,就达到了它的目的。
[29]Etienne De La Vassiere,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J. WARDER, tr. Brill, Leiden-Boston, 2005, p. 298.
[30]Reck C., “The sogdian Buddhist Fragemnts of the Berlin Collections: A survey on the result of the Catalogue Work” , 荣新江、罗丰《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物的新印证》,第381—388页。
[31]黄振华《粟特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5页。
[32]Sims-Williams N., “From Aramaic to Manchu: Prehistory, life and after life of the Sogdian script” , p. 415.
[33]L'Ubomir Novák, Problem of Archaism and Innovation in the Eastern Iranian Languages. Univerzita Karlova v Praze, 2013, p. 12.
[34]Sims-Williams N., “From Aramaic to Manchu: Prehistory, life and after life of the Sogdian script” , p. 414.
[35]Sims-Williams N., “From Aramaic to Manchu: Prehistory, life and after life of the Sogdian script” , p. 415.
[36]Sims-Williams N., “From Aramaic to Manchu: Prehistory, life and after life of the Sogdian script” , p. 415.
[37]Sims-Williams N., “From Aramaic to Manchu: Prehistory, life and after life of the Sogdian script” , pp. 415, 417.
[38]Yoshida Y. Turco-sogdian Features, Sundermann W., Exegisti Monument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Nocolas Sims-Williams. Wiesbaden: [s. n. ], 2009, pp. 571-585.
[39]《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08页。
[40]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1—82页。
[41]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43—145、159页。
[42]Hambis L., Grammaire de la langue mongole écrite. p. 28.
[43]A. von Gabain., Alttürkische Grammatik. p. 15.
[44]A. von Gabain., Alttürkische Grammatik. pp. 7-12.
[45]A. von Gabain., Alttürkische Grammatik. pp. 16-17.
[46]杨富学《回鹘文源流考辨》,《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第70—77页。
[47]李经纬《回鹘文的字形与字体》,《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第49—64页。
[48]其余比如匈牙利学者卡拉·捷尔吉的专著《蒙古人的文字与古籍》以及海西希的《蒙古文文献及其古体字》、包力髙和道尔基的《蒙古文字发展概述》和贾晞儒的《蒙古文字的演变及其改革》三篇论文,均曾系统论述过蒙古文字的发生发展史,介绍了蒙古族人民用作书写的载体和工具,简单评论了具体文献中古体字以及蒙古族在历史上使用过的多种文字及其优缺点。
[49]《元史·塔塔统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50]包力高、道尔基《蒙古文字发展概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第62页。
[51]包力高、道尔基《蒙古文字发展概述》,第63页。
[52]李琴《粟特回鹘系文字发展史略》,中央民族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0页。
[53]包力高、道尔基《蒙古文字发展概述》,第63—65页。
[54]我国作为满族和满语的发祥地,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满学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尤其在满文的创制与发展上,国内学者有着极大的发言权。周澍田和王明志的《论满族语言文字的演变》、赵志强的《老满文研究》、庆丰的《满文》,于鹏翔的专著《满文形体学原理》及其相关论著,都对满文从形体学上进行了分析。
[55]爱新觉罗·乌拉熙春《满语语法》,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6页。
[56]李民寏校释《栅中日录校释、建州闻见录校释》,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第72页。
[57]李民寏校释《栅中日录校释、建州闻见录校释》,第63页。
[58]按:季永海先生在《满语语法》一书中使用的“加圈点满文”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在满文创制之前,老蒙古文和回鹘文就已经开始用“符号点”来区分辅音了。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加圈增点”。
[59]Sims-Williams N.,“From Aramaic to Manchu: Prehistory, life and after life of the Sogdian script” ,p. 414.
[60]季永海《满语语法》,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86页。
[61]满语是从左向右,从上到下来阅读的,之所以这里的满文词汇产生了逆时针旋转,在于文章里采用的是水平排版模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