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理论草案和创新的教学构想(见第13章)似乎已经结束。教学模式的多样性已经在务实的行为方式和实践定向上得到巩固。大卫·埃利奥特(David Elliott)的实践音乐教育理论[5]在德语文学和音乐教育中几乎不被接受。与此相反,音乐教学诠释法出现一个向生活领域强有力靠拢的现象。埃亨福特的人类学根据和沃尔夫冈·里希特的注释学理解苗头是基于对缩小人类形象理性比重的批判。为了在理解主体(学生)和理解客体(艺术作品)之间建立理解对话的沟通渠道,一个“地方”的结构(埃亨福特),涉及“聚会场所”(里希特)在方法上被作为比喻和梅塔音乐的关键概念,被引入教学计划中,在其帮助下,作品和学生应该在一个共同的经历中相遇。这个从作品中获得的共同经验参照点,融合了从胡塞尔现象学中借鉴的一般现实生活的观点。基本的生活经验被认为是艺术经验的人类学基础,因此音乐的教学诠释方法被延伸到现实生活的教育理论中去。[6]
在20世纪80年代,这是一种常见的论证模式(见第15章),学校必须向社会开放,让自己进入日常生活中,由此可见它们必须成为一个有各种培训可能的公共聚会场所,以防止学校生活让孩子变得“愚笨”。在20世纪90年代,音乐课的论据转向:“音乐让人变得聪明”,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使用这里概念,也是杂志[7]和书籍[8]传播的格言,强烈地影响了教育政策的讨论。如果能够展现音乐演奏的积极作用,那么这当然会在有关音乐在学校中的合法性辩论中提供强有力的教育政策论证。人们选择了一个可能的智力效应,一方面是通过神经实验的结果表明,这是在听完莫扎特的音乐之后,导致在时空观念测试任务中性能显著增加(所谓的莫扎特效应[9])。另一方面,通过在音乐扩展课中的长期在校试验[10],指出音乐课对学生成绩、社会行为和人格发展的正面影响,这一点已经被大脑研究所证实。两种研究苗头的可靠性和重要性一直是争论的主题,最终导致了对音乐对智力发展的可能影响不应被高估的论点的客观化。[11]

图17.1 学生小组在带有音序程序的计算机上工作。
与之相反,在对音乐学习的实践演奏中使用的普遍认识也是有帮助的,各类学校的音乐课,仍旧跟随着更多实践定向和加强体验式学习的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趋势。学校音乐的实践扩展到各种可用的和当代的音乐,并包括所有风格和流派。当前流行音乐和摇滚音乐(朋克、放克、说唱、嘻哈等)在教学中不言而喻地被使用,就像新旧“经典”音乐的学习一样,并且也总是经常演奏一些乐器,例如印度的塔布拉鼓[12]、非洲鼓[13]或印尼的甘美兰乐器[14]。今天有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丰富多彩,在教学上可使用教科书、辅助材料、主题小册子、实用指南、编排和演奏指导教材是很多的。可用的教科书的范围与这种多样性的实际使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可能与这样的发展有关,即在紧随课程改革,音乐课的教学方案开放之后,可以观察到再次出现了一个以教育标准和能力水平为中心的更强的教学大纲,这必然导致个别学校教科书方案的区域化。这要求必须再次与各自联邦州的课程更紧密地连接。因此,教科书出版商为各个联邦州提供了许多单个的地区版本。
第15章所介绍的多媒体技术与音乐课程的融合已经完成。今天的计算机和互联网对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工具”,也可以用来演奏音乐、作曲、改编作品。学校继续与互联网相连,并拥有计算机实验室。但由于市场的快速发展,计算机实验室的维护和更新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成本因素。在某些学校中,迷你光碟(MiniDisc)和数字通用光盘(DVD)如今已被认为和用演示文稿(PowerPoint)的数据投影仪一样,是音乐教室的标配。从对新的可能性的迷恋开始,学校在处理这些辅助技术工具方面,学生提供了理智的服务制度。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学校使用电脑的争论早已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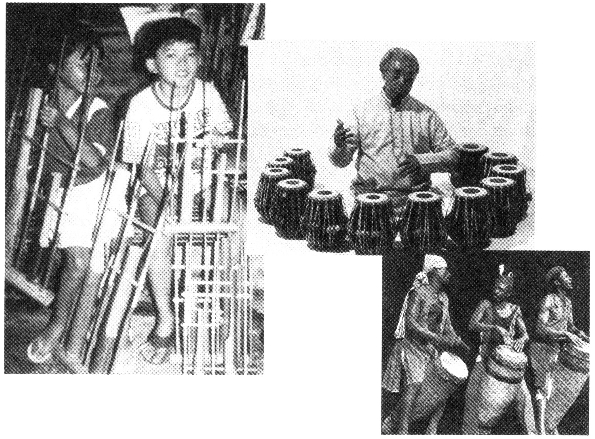
图17.2 非西方音乐领域当时属于音乐课固定组成部分,以及开始时能找到很多新的相关教材。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型移民运动的背景下,我们社会多元化结构被塑造,并有许多外国儿童进入学校学习。由于与穆斯林“文化冲突”[15]的不幸辩论,学校加强了对多民族和多元文化问题的重视,特别使音乐课在学校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空间。由此,今后,只是对非西方音乐演奏形式了解的可行模式并不是那么重要,而是要反思真正的教育问题,怎样对待陌生文化的不同生活意义,在理解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文化障碍,并发展音乐教育模式。这在学习理论方面也是有保证的。
在学习理论领域中,未来渴望有新的音乐学习理念出现。从长远来看,在音乐的使用中提到认知转移效应,这无法独自解决社会地位的合法化压力。相反,神经生物学对学习的研究[16]已经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音乐学习的神经生理过程。针对方法论教学形式和个性化学习方式发展的重要意义,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设立神经教学学[17],研究适应大脑神经生理学发展的学习条件,以此代替在学校条件上建立的儿童式学习。神经生物学研究已显示音乐家和非音乐家在其神经脑组织训练功能和结构上的差异。所以,音乐学习可以在神经生理学上得到反映,并可被描述为神经的过程。[18]对学习神经生物学的进一步探索和教学使用,涉及21世纪音乐教育带来的机遇、任务和挑战。它将继续改变学生的音乐课堂,因此也希望它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注释】
[1]999年6月19日博洛尼亚宣言是一份具有政治意图的宣言,它由欧洲29国教育部
长共同签署,通过它,人们要在2010年之前义务引进可对比相互承认的大学毕业证。
[2]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00)主要研究学生的阅读能力以及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教育。参看J.鲍默特(J.Baumert)等(主编):《2000年PISA:国际比较中学生基础能力》,欧普拉登,2001;J.鲍默特(J.Baumert):《PISA和给教育学研究的结论》,欧普拉登,2003。
[3]第三次国际数学和自然科学研究(TIMMS),切斯纳特希尔,1997。
[4]参看M.克雷斯(M.Kerres):《媒体和远程媒体的环境》,慕尼黑,2001。(https://www.xing528.com)
[5]参看D.埃利奥特(D.Elliott):《音乐书信》,纽约,1995。
[6]关于教学学诠释法在生活领域中的阐述和批判参看J.沃格特(J.Vogt):《生活领域中摇摆不定的立足点》,维尔茨堡,2001。
[7]在这个意义中指的是《新科学》(1996,150,5月18日)、《专用明镜》(1997,Nr.12)、《今天的心理学》(1999,26,Nr.7)、《时代》(2000,Nr.15)。
[8]参看D.克豪史·雅克布(D.Kreusch-Jacob):《音乐使人聪明——儿童如何挖掘音乐的世界》,慕尼黑,1999。
[9]F.豪舍尔(F.Rauscher)、G.肖(G.Shaw)、K.N.凯(K.N.Ky):《听莫扎特增强时空推理:走向神经生理学的基础》,摘自《185封神经学信件》,1995,第44-47页。
[10]对此参看瑞士学校的尝试[E.W.韦伯(E.W.Weber)、M.斯彪奇格(M.Spychiger)、J.-L.帕特里(J.-L.Patry):《学校中的音乐》,埃森,1993]和对柏林小学长期的研究[H.-G.巴斯蒂安(H.G.Bastian):《音乐(教育)和它的作用》,美因茨,2000]。
[11]梅塔分析在《艺术和学术成就:证据显示》里提供一份关于所有现在研究的详细评估,摘自《美学教育杂志》,34,2000,第3-4期。
[12]对此参看G.法雷尔(G.Farrell):《教育中的印度尼西亚音乐》,剑桥,1990。
[13]M.恩泽维(M.Nzewi):《非洲音乐:理论内容和创造性的连续统一体》,欧德斯豪森,1997;V.舒茨(V.Schütz):《黑非洲的音乐》,欧德斯豪森,1992。
[14]D.马克(D.Mack):《来自巴厘和西部爪哇岛的音乐》,欧德斯豪森,2002;D.马克(D.Mack):《世界音乐——巴厘》,马尔沙赫特,2003。
[15]参看F.A.格尔吉斯(F.A.Gerges):《美国与政治的伊斯兰——文化冲突还是利益的冲突?》,剑桥,1999。
[16]这儿是对弗兰格斯·豪舍尔(Frances Rauscher)、伊莎贝尔·佩雷茨(Isabell Peretz)、桑德拉·特雷胡布(Sandra Trehub)、罗布特·查托雷(Robert Zatorre)、史特凡·柯尔施(Stefan Kölsch)、艾卡特·阿尔滕米勒(Eckart Altenmüller)、维尔弗里德·格鲁恩(Wilfried Gruhn)等人关于音乐教育神经学研究的思考。
[17]这个观点往回抓住盖哈尔德·普海斯(Gerhard Preiß,神经教学学,1998)的观点。关于音乐学习的编写参看W.格鲁恩(W.Gruhn):《神经教学学和早期学习的兴趣》,摘自《音乐教育讨论》,第18期,2003,第41-45页。
[18]参看W.格鲁恩(W.Gruhn):《音乐理解》,希尔德斯海姆,1998;M.施皮策(M.Spitzer):《大脑中的音乐》,斯图加特,200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