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爻”是《周易》的专用术语,很少在其他古籍和日常用语中出现,然而,当我们从中国哲学语素论的立场来详究其字形、字义及其所隐喻的道理时,却能够发现它在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世界中极为基础的、无法为他字所替代的独特内涵。从“爻”之字形来看,它既可以意指天地间的四面八方,亦可以指涉四方和四时(春夏秋冬),因此构成了《周易》作者为把握天地万物宇宙世界而产生的形与字,是《周易》的关键词、基本字。正是基于此,《周易》才得以对万物进行归类(万物类象),使人感到这宇宙世界、天地万物皆有常规、常道,从而为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提供了基本的存在规范。从“爻”之生成来看,它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哲人对宇宙社会最原始的经验和体证,因而与此相关的智慧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非常普遍的应用。从“爻”之衍生义来看,“爻”维系着事物的两极端(矛盾、进退、幽明、得失、吉凶等)及它们之间的变化,同时又代表着事物的中正点,防止事物向极端方向发展。正是因为“爻”具有上述深刻而丰实的内涵,所以古人十分倚重以“爻”为基础的《周易》,并以它来指导人的社会生活。
在中华字库里,大概没有什么字能像“爻”字那样使用得如此专门、独特:它(“爻”字)不太会出现在我们常见的报刊上,更不太可能出现在我们的文件、通知中,它只出现在《周易》及相关的古籍里。可以这么说:“爻”字专属《周易》所有。
而站在《周易》的角度来看,“爻”字又比“卦”字更专门、独特,“卦”字还会衍生出我们日常说的“变卦”这样的常用语,而“爻”字则没有这种现象。但是,尽管“爻”字没有衍生出像“卦”有“变卦”这样的日常用语,却有着比“卦”字更多的独特的衍生意义。
“爻”字的形状,是由两个二直线相交(十),并作小角度(45°)旋转(×),撇捺成“爻”字。对此,潘雨廷说:“今视两个×(五)合成爻字。”(26)
要知道,二直线相交成“十”字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义非同一般。如在河南省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上发现的镶嵌圆形铜器(青铜钺)上的“十”字形(也可称十字纹),在先秦古文字那里就是天干地支中的天干“甲”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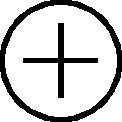 ),商代甲骨文中的“甲”字就作二直线互相交叉成“十”字形。而“甲”字作为二直线交叉成的“十”字形又意指太阳的东南西北这四方。所以以后的许慎会在《说文·十部》中这样说道:“十,数之具也。|为南北,—为东西,则四方中央备也。”所以说,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十”字形符号反映的是古人对天地四方的认知。
),商代甲骨文中的“甲”字就作二直线互相交叉成“十”字形。而“甲”字作为二直线交叉成的“十”字形又意指太阳的东南西北这四方。所以以后的许慎会在《说文·十部》中这样说道:“十,数之具也。|为南北,—为东西,则四方中央备也。”所以说,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十”字形符号反映的是古人对天地四方的认知。
如果说,一个“十”字(两线相交叉)意指天地间的东南西北,那么两个“十”字重叠(就如《周易》中的“卦”一样讲究重叠和拆解),则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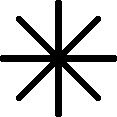 ”,就意指天地间的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四面八方了。同样也直接等同《周易》中的文王后天八卦图。
”,就意指天地间的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四面八方了。同样也直接等同《周易》中的文王后天八卦图。
然而,如果真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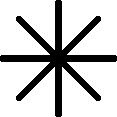 ”形,则很难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汉字,它似乎缺少汉字构成的基本笔画,它尽管有着线条的交叉,但无笔画的撇捺,所以只能算“线条化”的图形,而不是“笔画化”的汉字。而为了制作《周易》及制定《周易》一书的特定用词(“卦”和“爻”),《周易》作者就将两个“十”字不作交叉重叠,而是作分解拆开,并作稍许旋转成“×”,撇捺成“爻”字,这就如潘雨廷所说的:“今视两个×(五)合成爻字。”
”形,则很难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汉字,它似乎缺少汉字构成的基本笔画,它尽管有着线条的交叉,但无笔画的撇捺,所以只能算“线条化”的图形,而不是“笔画化”的汉字。而为了制作《周易》及制定《周易》一书的特定用词(“卦”和“爻”),《周易》作者就将两个“十”字不作交叉重叠,而是作分解拆开,并作稍许旋转成“×”,撇捺成“爻”字,这就如潘雨廷所说的:“今视两个×(五)合成爻字。”
图1 “爻”字的撇捺线条
所以,从“爻”之字形来看,它实际上是意指天地间的四面(东南西北)八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正因为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坤卦中有这样的词句“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即“爻”字一撇维系(也可称“触类”,王弼《周易略例·明彖》)南北,一捺维系东西,一撇维系西南、东北,一捺维系东南、西北,以图1示之,即:
尽管潘雨廷称“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作西南坤卦与东北艮卦相联通(27),而笔者则更倾向于认为“爻”字的撇捺线条维系天地间的四方和四时(春夏秋冬)可能更符合周易的原始含意。
以下让我们来看看《周易》的原始含意及“爻”又是如何比“卦”更符合《周易》的原生态。
在远古时期,人们认识世界和把握天地万物的能力十分低下,在他们的眼里,世界宇宙、天地万物杂乱无章,事无轨度、物无则准、用无常道、行无秩序。这在《系辞下》中也有所流露:“为道屡迁,变动不居,上下无常,刚柔相易。”
而为了能有效地把握天地万物、宇宙世界,深怀忧患意识的《周易》作者(《系辞上》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想用《易》来规范准则天地万物、宇宙世界,使之有序有则有规有度,这就是《周易·系辞上》中说的“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也”;这也就是《周易·系辞上》中所说的“《易》与天地准”,以便能弥纶天地、范围万物。在这里,有意思的是:“与天地准”的“凖”字是以“十”字为“准”的基础,这已隐喻了规范天地弥纶万物离不开它的“十”字形。所以说,用“易与天地凖”,实际上是使用《易》中的“爻”来规范天地、弥纶万物,因为与两个“十”字(×)有着天然血缘关系(如上所述)的“爻”字比“卦”字更符合“与天地凖”的要求:“天垂象,圣人(则用‘十’字)象之”“法象莫大乎天地,天地变化,圣人(则用‘爻’)效之”。它(“爻”字)一撇维系着南北、冬夏,一捺维系着东西、春秋;一撇维系着西南、东北,一捺维系着西北、东南,以配天地四方四时,所以《系辞》说“广大配天地(四方),变化配四时”。正因为这样,“与天地凖”的《易》(实际上是“爻”),能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在这个意义上说,“爻”是《周易》作者为把握天地万物宇宙世界而产生的形与字,并由此构成《周易》的关键词、基本字。
如果明白上述道理,那么“爻”就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字形,而是一个含有丰实内涵的字形,因为它能使人一旦接触之就能马上联想到天地宇宙的四方四时及与此相关的事与物,这正是《易·系辞上》的说法,《易》(实际是“爻”)能“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它的具体表现,就如《说卦》中对四面八方(八卦)的方方面面的规定及对万物的归类(万物类象):
震,东方也,万物出乎震;巽,东南也,言万物之絜齐也;离,南方之卦也,万物皆相见;坤,地也(西南),万物皆致养也;兑,正秋(西)也,万物之所说(悦)也;乾,西北之卦也,言(精气为物)阴阳相薄也;坎,正北方之卦也,万物之所归也;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以图2示之,即:
图2 “爻”字的八卦及万物类象
如再将这里的万物具体化,即“曲成万物而不遗”的话,就是如《说卦》中说的那样:
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肪旉、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 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 、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耳痛、为心病、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耳痛、为心病、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胄、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阍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
有了这方方面面的规定、准则、归类、分档,即“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系辞》),就使人感到这宇宙世界、天地万物皆有常规、常道,如《系辞》说的,一旦“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就可以“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会通阴阳之理而无所不知”,于是直接导致人们生活稍可放心与安心。否则就会使人在无穷的变数中恐惧生活,从而使人失去生活的信心而直接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在这个意义上说:《易》之“爻”足可以“断天下之疑,定天下之业,通天下之志”(《系辞》)。
而之所以有此效果,就不能不归功于这“十”字,及由两个“十”字(×)组成的“爻”字。
上述讲到,由两个二直线相交(十),并稍作旋转45°(×),撇捺而成“爻”字。这样,使我们说到“爻”字,也就不得不说到“十”字。
那么,作为“爻”字的基本构成物——“十”字,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这大概与《易·系辞》中说的“近取诸身”有关。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身体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实体和概念的统一体,当人们在认知天地万物、世界宇宙时,常常念及自身,并将自身纳入其中、参与践履,这也就是《易·系辞》中所谓的“近取诸身”:它(人体)在宇宙天地间,首先是“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换另一说法是“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这样,“天”也即在人体的上前方,“地”也即在人体的下后方;同样,人体在宇宙天地间,生活习惯决定就是面对南面太阳,这样,“南”也就在人体的上前方,“北”也即在人体的下后方。这也就有了许慎在《说文·十部》中的说法:“|为南北。”
有了人面南(太阳)这点,也就必然会有对太阳“东升西落”的观察和认知。而为了更好地把握,人也就自然而然地两手侧平举,以指向太阳的“东升”(左)和“西落”(右),这样也就有了许慎在《说文·十部》中的说法:“—为东西。”于是念及自己、纳入自身的“十”字形也就形成了。按董仲舒的话来说:“木(东)居人左,金(西)居人右,火(南)居人前(上),水(北)居人后(下)。”(《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这样形成的“十”字,实际上是人体直立、两手侧平举以仿效天地四方(四时)的象形图,用《易·系辞》说的话来表达,就是《易》有太极(人),是生两仪(直立以顶天立地),两仪生四象(双手侧平举)——东南西北、春夏秋冬。这“十”字(人站立,双手侧平举)的形成,是人对天地四方四时最基本、最实用的把握,也是人对天地四方四时最原始、最古老的把握。
而由“十”字转变而来的“爻”字也就有了同样的功能和效用,所以《系辞下》会说这样的话:“爻,效也,效(仿)天下之动者也。”
以上讲及,“爻”字是由两个二直线相交(十),并作稍许旋转45°(×),撇捺而成。这样也就必然由“爻”讲到“×”。而之所以能由“十”(东西南北)转变成“×”(西南西北、东南东北),按《周易·系辞》说来是由于“天地日月(阴阳)相推(旋转)而成”:“日来则月往,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系辞下》)这样,这“十”字就能变成“×”字。
同样,这“×”字按潘雨廷的说法,实际上是“五”的原始字形;而这“五”又与“爻”字天然合一,所以上述就提到潘雨廷所说的话:“今视两个×(五)合成爻字。”
潘雨廷还在《易老和养生》一书的《论易学》一文中以图3来表示:
图3
并说,凡“一”为一整体,有阳的意义;“八”为阴阳相对,有阴的意义;“十”这一个整体有分而为二的形象,亦就是阳将变阴;“八”为阴阳相对的二方,又有相交的形象,亦就是阴将变阳。至于由阴阳两端(一与八)经或分或合(十与八)而可相互变化,必须通过中央“‘五’(×)字的作用”。还说:“(×)五有阴阳相交的意义,亦就是阴阳可以互相交化。‘五’须出于中央。”(28)
这里,我们暂且不说数字卦的内容(即“×”最早是“五”这个数的原型),但从上述的引文中可以看到这将“十”字稍作旋转而成的“×”,却有这样的特征:它(“×”)是阴阳互变中的交叉点。所以《说文》会说这样的话:五,“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这“交午”即“交互”,即“交五”,“五”“午”“互”同音通借,意为阴、阳两气互为贯通,指的是日月寒暑、气候节令的变化,所以处中央位置。
而这点,正好符合《说文》对“爻”的判断:“爻,交也”(《说文·爻部》),也符合《系辞》对“爻”的判断:“道(阴阳)有变动,故曰爻。”
上述提到两个“十”(×)相交重叠成东南西北与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天地四面八方。如果三个“十”(×)字相互重叠,就构成一个十二月,配以二十四节气和地支,就成如下图4所示:
图4
如按纳甲(天干、地支)筮法,就构成乾卦的六条爻(见上图4),这大概就是王弼《周易略例·明彖》说的“六爻相错”。并按1、4,2、5,3、6相应的原则,就成了子、午,寅、申,辰、戌相冲的六冲卦……乾是如此,坤、离、坎、震、兑、巽、艮都是如此。
在这个意义上说,“六爻相错”实际上是表示一个(一年)周期,衍生开来,即表示一事物的一个周期变化,只不过是用“卦”的形式表示出来而已,即如王弼所说:“卦以六爻为成”(王弼《周易略例·辩位》)。同样,爻之间的1、4,2、5,3、6相应的原则也就由此产生。
1.“×”之现象的普遍性之一
《说文》说:“爻,交也”,而这种“×”(交)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世界里随处可见。早在远古时期,古人用的黑陶鱼篓形罐上就刻有“|×|”这样的字形(见江苏澄湖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鱼篓形罐)。
而这种“|×|”字形,可能与古代测定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有关;因为这种立竿测影所表现出的图形同样是“×”。
按《周髀算经》说:“冬至昼极短,日出辰而入申……日出巽而入坤,见日光少,故曰寒。”《周髀算经》又说:“夏至昼极长,日出寅而入戌……日出艮而入乾,见日光多,故曰暑。”以图5示之:(https://www.xing528.com)
图5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冬至日出东南(辰—巽),立竿测影的晷影指向西北方(戌—乾);日落西南方(申—坤),晷影指向东北方(寅—艮)。夏至日出东北方(寅—艮),立竿测影指向西南方(申—坤);日落西北方(戌—乾),晷影指向东南方(辰—巽)。
而图中所表现出的实线图形正好是“×”。
2.“×”之现象的普遍性之二
这种“×”现象,我们在后天文王八卦配洛书的图中也能见到。以图6示之:
图6
在先天八卦中,乾、坤为父母,而在后天八卦中则离、坎为乾、坤的继体,成为父母。乾则称为大父,坤则称为大母。离卦,阳生,继乾卦,故为正南方,数为九。坎卦,阴生,继坤卦,数为一。这样,离、坎就成为父母。离的初爻—换成坎的初爻 ,即成艮
,即成艮 ,故次离为艮(次九为八),艮为八。把坎的初爻
,故次离为艮(次九为八),艮为八。把坎的初爻 换成离的初爻—,即成兑
换成离的初爻—,即成兑 ,故次艮为兑(次八为七),兑为七。再将离的中爻
,故次艮为兑(次八为七),兑为七。再将离的中爻 换成坎的中爻—,即成大父乾
换成坎的中爻—,即成大父乾 ,故次兑为乾(次七为六)。坎的中爻—换成离的中爻
,故次兑为乾(次七为六)。坎的中爻—换成离的中爻 ,即成大母坤
,即成大母坤 ,故次坎为坤(次一为二)。离的上爻—换成坎的上爻
,故次坎为坤(次一为二)。离的上爻—换成坎的上爻 ,即成震
,即成震 ,故次坤为震(次二为三)。坎的上爻
,故次坤为震(次二为三)。坎的上爻 换成离的上爻—,即为巽
换成离的上爻—,即为巽 ,故次震为巽(次三为四)。此图按八卦各位次序,即可看出各体之间的“×”关系,从中也反映了各卦之间的阴阳互生的情况(“五”即为两个“×”)。
,故次震为巽(次三为四)。此图按八卦各位次序,即可看出各体之间的“×”关系,从中也反映了各卦之间的阴阳互生的情况(“五”即为两个“×”)。
3.“×”现象的普遍性之三
有趣的是,中医中的十二经脉的循环走向也构成这种“×”交接(叉)联系。按《灵枢·逆顺肥瘦》说来:“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29)
如这种经脉走向绘图的话,即如图7所示:
图7
从图7可见,十二经脉在头部、躯干和四肢呈交叉(接)规则,手足阴阳与头面胸腹之间就构成了一种特定的联系。阴经和阳经,在四肢部交接;阴经和阴经,在胸腹部交接;阳经和阳经在头面部交接(30)。
图8
4.“×”之现象的普遍性之四
两个“十”字重叠相交为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而三个“十”字重叠相交则成一年周期中的十二个月(配以节气、地支)。如果由六个“十”字重叠相交,那么就可能出现像老子所说的“三十辐拱一毂”(《老子·十一章》)的情景。以图8示之,即为“轮”:
这也就如王弼在《周易略例·明彖》中所说的“六合辐辏”。
诸如此类的“×”之现象的普遍性,还有很多。如当今汉字简化中也常能见到这“×”,如“趙”改成“赵”。而汉字中原来就有的“ ”(yi)字,其含意也与这里说的“×”相近,指的是“交叉剪割草”。
”(yi)字,其含意也与这里说的“×”相近,指的是“交叉剪割草”。
更有甚者,在《山海经·海外南经》中记载有“交胫国”,这“交胫国”中的“交胫民”的脚胫都“曲戾相交”(“脚相交切”,高诱语)成“×”。
如此广泛出现“×”之现象,表现出其中有着它的隐喻意义。在这里,如同《老子》从“三十辐拱一毂”中引出的哲学含义一样(31),本节也试图从这“十”(“×”)的普遍性中引出由它们所构成的“爻”的含义。
1.“爻”维系着矛盾(变化)
如上所述,“爻”字形实际上意指天地间的四面(东南西北)和八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一爻中的“线”(一撇)维系着东西或西南东北,一爻中的另一线(一捺)维系着南北或东南西北。所以,这里“爻”中的线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我们日常所说的“直线”,因为直线是只会将事物的一端(如南)一以贯之下去的:“南”只能是“南”,“北”只能是“北”。而这里的“线”是非线性,它(线的一端)维系着的是酷暑难熬的“南”,经过对天地的融入和受阴阳之气的影响,它(线的一端)就会变成严寒难忍的“北”。所以,由“线”构成的“爻”是维系事物的两极端(矛盾、进退、幽明、得失、吉凶),及它们间的变化。正因为这样,所以《易·系辞》会说到“爻”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爻”是刚柔合体;也如王弼所说:“爻,以示变”,以及《系辞上》说:“爻者,言乎变者也”;也就会出现坤卦中说的词句:“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对于这点,王弼有着深刻的体会,所以他会在《周易略例·明爻通变》中说道:“爻,何也,言乎变也。……非数(初等数学)之所求也,巧不能定其算数……度量所历不能均也。”也因为这样,所以在《周易》中就有不少这样的表现。
如吉凶:恒卦六五爻辞说:“妇人吉,夫子凶。”否卦六二爻辞说:“小人吉,大人否。”
又如祸福:无妄卦六三爻辞说:“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还如得失:剥卦上九爻辞说:“君子得舆,小人剥庐。”随卦六二爻辞说:“系小子,失丈夫。”
再如往复:泰卦九三爻辞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以及老少:大过卦九二爻辞说:“枯杨生稊,老夫得少妻”;九五爻辞又说:“枯杨生华,老妇得少夫。”
这些用王弼在《明爻通变》中的话来概括:“爻”是“善迩而远至,命宫而商应,修下而高者降”,“爻”是“情伪相感,远近相追,爱恶相攻,屈伸相推”。“爻”维系着事物的两极端。
“爻”有上述这些含义,所以当我们一旦接触这“爻”字及“爻”的基本撇捺线条后,就能使我们马上明白:事物发展并非如直线那样推进,要好即好到底,要坏即坏到顶。事物往往是:“祸之为福,福之为祸。”这就如刘安在《淮南子·人间训》中说的那样:“欲利之而反害之,欲害之而反利之。”这样,就不会执著于某事,固守于某物,知道矛盾变化是事物的精髓。
一“爻”是如此,爻与爻之间的应、时、位等变化也是这样,所以王弼在《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中说道:“虽远而可以动者,得其应也;虽险而可以处者,得其时也。弱而不惧于敌者,得所据也;忧而不惧于乱者,得所附也。柔而不忧于断者,得所御也。虽后而敢为之先者,应其始也……”没有不可转变的事与物、人与事。
一“爻”是这样,由“爻”组成之“卦”也是如此:乾卦就不必一定与“马”对应、维系,坤卦也不必一定与“牛”对应、维系,这就是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的:“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这就是说,只要合乎乾之刚健之义,就不一定非得维系、对应“马”这物象,只要合乎坤之柔顺之义,就不必非得维系、对应“牛”这物象。天地宇宙间原本就没有非得一一对应和维系的事与物,一切由融入阴阳两气的事物变化发展而决定。这样,八月的桂花不一定非得在八月开,有可能提前或推后;二月的桃花也不一定非得在二月开,有可能提前或推后。
这样,社会领域也并非一定该这样,而不该那样,王弼的社会生活就有可能碰到董仲舒的时代所没有的生活情景和社会现象。所以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意象事物间原本没有固定的搭配和对应、固定的挂钩和维系(乾—马、坤—牛),并强调“得意而忘象”,这样意象间和事物间的关系一旦脱钩,就能变化开创出新时代、新思想来。
2.“爻”交点于中正(贞德)
上述提到,“爻”维系着事物的吉凶、矛盾、进退、得失,及它们间的变化。而为了防止事物向极端方向发展和变化,或处艰难时候,持守中正(贞德)是必要的;而“爻”也正好有交于“中正”点的功能,即“×”(五)是“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说文》),这“交午”(五)就是处事物的中正点,表现在《周易》上,就有不少这样的爻辞。
如屯卦初九爻辞说:“磐桓,利居贞,利建侯”,是说“徘徊艰难时,宜居而守正,这样利于建立诸侯”。
又如讼卦九四爻辞:“不克讼,复即命;谕,安贞吉”,是说“争讼失利,回心归就正理,改变争讼的念头,安顺守持正固可获吉祥”。
再如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是说“没有只平不陂的,没有只往不返的,只要能在艰难中守正即可免遭咎害”。
还如噬嗑卦九四爻辞:“噬干胏,得金矢,利艰贞,吉”,是说“像吃带骨的肉时咬到铜器一样艰难,但是要守中正,就可获吉祥”。
以及大壮卦九二爻辞:“贞吉”,是说“守持中正可获吉祥”。
还有晋卦初六爻辞:“晋如摧如,贞吉”,是说“前进之初就受摧折,只能守持中正方可安吉”。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所以王弼会说:“处璇玑(中心点)以观大运”,“据会要(中心点)以观方来”(《周易略例·明彖》)。王弼还说:“(尽管)古今虽殊,军国异容,中之为用,故未可远也”,是说尽管古今变化极其悬殊,治理军政及国政也极不一样,但是都离不开这中正(×)之道。因为这据处“中心点”正好能照顾、对应好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事与物,使自己能立于不败之地。
而由于这“中心点”(“×”)和四面八方处于等距离,表现出的社会功能也就对来自四面八方的事与物不作厚此薄彼和简单的肯定否定,所以也就省却不少争斗和麻烦。因为对事物不作厚此薄彼和简单的肯定否定,所以用哲学语言来讲又称之为“无”。又因为是持“无”(持中正),所以被王弼时代的哲学家王衍称之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为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无)以化生,万物恃(无)以成形,贤者恃(无)以成德,不肖恃(无)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晋书·王衍传》)
这“中正”(无),因为对事与物不作简单的肯定和否定,不作厚此薄彼之区分;所以,它实际上又表现为“不炎不寒,不柔不刚,不皦不昧,不恩不伤”(王弼《老子指略》),而这又被王弼称之为是万物之母之本;执于这“一”点,就可以御“众”,无往而不胜,按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来“天不以此(无、中正)则物不生;治不以此,则功不成”,“虽今古不同,时移俗易,此不变也”。
这中正(不炎不寒)及无,着力地被王弼歌颂了一番。而究其根本,恐怕一切来自这“×”及由这“×”组成的“爻”字。基于此,所以当我们一旦接触这“爻”字及“爻”字的组成部分“×”时,也就必然会联想到这“×”的交叉点——“中正”这一点,以提醒自己时常“持正守中”,像看到孔子的“宥坐之器”(32)和老子的“风箱”(33)而马上联想到“中”(中正)一样。如此,这“爻”及“爻”的组成部分——“×”,也就不是毫无内涵的字与形,而是有着“持正守中”深刻内涵的字与形,如上所述的那般。
知道了“爻”的特征及含义,也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得到“爻”的功能。对此,王弼在《周易略例·明爻通变》中说到“爻”之功能:“能说(悦)诸心,能研诸虑。”
同样,《易·系辞下》也讲到“爻”之功能,说:“《易》(实际上是‘爻’)彰往而察来,微显而阐幽”,并指出能“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周易·系辞下》中还记载着孔子对此的看法,认为用《易》(实际上是“爻”)来指导人的社会活动,就能有这样的功能:“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