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字是现在所能见到的大批的最古的汉字。这种汉字的特点是一个字只代表一个音节,这与其他民族的拼音文字一个字具有两个以上的音节不同。一个方块汉字只含有一个音节,而中国汉语却可以是单音节或多音节。所以唐兰先生就曾指出,汉语中的“字”(character)和“语”(word)不一致,应当分析清楚。他认为一个方块汉字(character)只有一个音节,而汉语(word)里一个基本单位可以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若一个汉语词包括两个以上的音节,用汉字写出来,就必须用两个以上的汉字才能表达出来。如汉语“葡萄”是外来语,虽然用两个汉字译写,其实是一个双音节“语”(word)。我们决不能把这两个汉字拆开来,去考虑“葡”是什么?“萄”是什么?先秦时代的汉语,可能也是这个样子。例如“参差”、“蟋蟀”这两个“语”,每个“语”都是用两个汉字标记的。把两个汉字分开来,“参”或“差”中任何一字都没有“参差”的意思;“蟋”或“蟀”,任何一字也不代表“蟋蟀”[774]。所以,葡萄、参差、蟋蟀等都是两个音节的语,两个音节的语就用两个方块汉字表达。这样看来,古汉“语”可以有复音节,而古汉“字”没有复音节,也没有必要去创造复辅音了。
这里牵涉到古汉字是否有复辅音的问题。现代一些语言学家,由于看到“印欧语系”一般都有复辅音,于是遇到汉语、汉字一些不好理解的问题,他们就立刻想用复辅音去加以解释。最著名者如高本汉(Karlgren)和林语堂等都主张中国汉字是有复辅音的。但是他们所举的证据并不充分。他们看到来纽的字与见纽的字相通转,可是在语音学上“K”与“L”发音部位不同,是难以通转的。于是,便认为这种现象必然是古有复辅音,才能说得过去。举下列几个字为例,以便说明:
各 :从“各”得声的有“络”、“烙”、“骆”、“酪”
:从“各”得声的有“络”、“烙”、“骆”、“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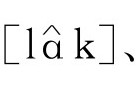 、“略”
、“略” 、“赂”、“路”
、“赂”、“路” 柬
柬 :从“柬”得声的有“阑”
:从“柬”得声的有“阑” 、“炼”,“练
、“炼”,“练 ”等。
”等。
兼 :从“兼”得声的有“廉”、“镰”
:从“兼”得声的有“廉”、“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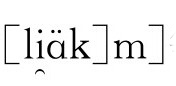 等。
等。
监 :从“监”得声的有“篮”、“览”、“滥”
:从“监”得声的有“篮”、“览”、“滥” 等。(https://www.xing528.com)
等。(https://www.xing528.com)
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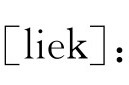 :从“鬲”得声的有“隔”、“膈”
:从“鬲”得声的有“隔”、“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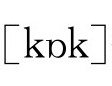 等。
等。
娄 :从“娄”得声的有“窭”
:从“娄”得声的有“窭” 、“屦”
、“屦” 等。
等。
以上之各、柬、兼、监等是见纽字,可是它们的谐声字,很多变为来纽;鬲、娄是来纽字,而其谐声字则入见纽。这种现象,就使得他们设想这些见纽、来纽的字,上古音可能是复辅音 ,以后变为
,以后变为 ,浊纽
,浊纽 易于失落,故后来变成
易于失落,故后来变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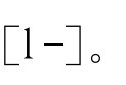 这样委曲婉转地证明汉字古有复辅音,完全近于猜测,说服力太弱了。其实汉字来纽与见纽的通转,完全可以用音韵学的一般规律讲明白。在语音学上,我们知道发音部位相同或相近的声母可以互相转变。来纽的字在现代方言中已发现有两种读音:大部分汉语区读
这样委曲婉转地证明汉字古有复辅音,完全近于猜测,说服力太弱了。其实汉字来纽与见纽的通转,完全可以用音韵学的一般规律讲明白。在语音学上,我们知道发音部位相同或相近的声母可以互相转变。来纽的字在现代方言中已发现有两种读音:大部分汉语区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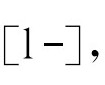 ,可是有部分汉语方言区有时又读
,可是有部分汉语方言区有时又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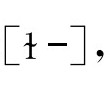 ,如山西大同、文水、平阳和甘肃的兰州读为
,如山西大同、文水、平阳和甘肃的兰州读为 [775]。“路”字,大同人读
[775]。“路”字,大同人读 。高本汉说,
。高本汉说, 除了在
除了在 前面外,都读作
前面外,都读作 [776]。
[776]。 音是浊音,发音部位是口齿边音,同时舌背的后部高起来,等于波兰文的
音是浊音,发音部位是口齿边音,同时舌背的后部高起来,等于波兰文的 ,俄文的Л。这种l有两读的现象在英语里最普遍。一般是l后面不与元音相拼者,如“bowl”、“rule”等字中之l,都读作
,俄文的Л。这种l有两读的现象在英语里最普遍。一般是l后面不与元音相拼者,如“bowl”、“rule”等字中之l,都读作 ,而bowling和ruling中之l读作[l][777]。从这些现象看,我们可以推论汉字上古音的来纽字,其声母也有两类,一为
,而bowling和ruling中之l读作[l][777]。从这些现象看,我们可以推论汉字上古音的来纽字,其声母也有两类,一为 ,一为
,一为 。而
。而 是加舌根作用的辅音,与舌根音见纽的声母
是加舌根作用的辅音,与舌根音见纽的声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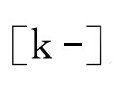 发音部位极相近,当然可以互相通转,又何必用与汉语系统完全相背的复辅音的理论去解释呢?
发音部位极相近,当然可以互相通转,又何必用与汉语系统完全相背的复辅音的理论去解释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