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代主义先锋性的“激发态”
先锋(advance guard)暗涌着变革的力量,解开艺术家满溢热情与爱的困兽之链,野兽派、立体派、表现主义、抽象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等流派顺势出现,践行西方艺术界的现代革命,展示出量子“激发态”(excited state)般瞬间的、具有刺激性的灵感外显。需指出,此时期艺术家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创作映射,同样尤为关切,展示出科学与艺术之间密不可分的同构性。而就当时艺术形态与量子之间的关联而言,主要呈现出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对微观物体(实际上也就是未知、不可见的物体)的想象,带有持久性和双重性。现代主义艺术尤为注重人类潜意识快感、梦境与想象性的建构,在视觉、听觉与视听艺术中找寻未知能够外化的载体,比如首个现代主义艺术流派野兽派即在光色、笔触与形状之间充分寻求人类精神欲望的视觉化,“周围世界对于他们不过是用光线和色彩手段,来表达各种情感和无对象的矛盾感情的动力和借口”[4]。我们从现代主义不断更迭的状态中也不难发现,找寻行为本身就处于某种不断自我肯定/否定的双重心理过程,不断影响创作观念转型,这与爱因斯坦、薛定谔对量子物理既赞同又质疑的态度不谋而合。
第二,与量子概念整体意义对应的视觉艺术化解读。艺术家并非思考量子原初物理概念或公式运用,而将未知领域探索的整体意义转为艺术创作,可能一个名词即指涉一幅耐人寻味的绘画作品。卡西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是至上主义代表人物,作品《黑色方形》(Black Square,1915,图1)被称作“绘画的零点”(zero point of painting)。“零点”指向现代主义与前序艺术的挥手告别,亦暗含黑体辐射(black body radiation)这一量子基石的视觉化表意,画家“把黑体内在不可见的辐射转化为黑色方形里随机碎裂的纹路,并把黑体内的能量转移引申为绘画零点处的真实运动,物理学的发现就此转化为艺术表现的精神原点”[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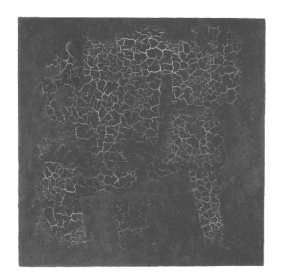
图1 马列维奇作品《黑色方形》
而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作为超现实主义的先锋,从艺术创作的构思阶段就带有源自潜意识偏好的科学属性。埃利纳·冈蒂奥拉(Elena Guardiola)与约瑟厄·贝诺斯(Josep-E.Banos)曾指出,“达利(1904—1989)对科学非常感兴趣。20世纪30年代,他主要集中在双重影像与幻觉制造;20世纪40年代开始转向普朗克量子论,并在1945年之后开始核物理或原子物理时期、核子神秘主义时期”[6]。比如《原子的丽达》(Leda Atomica,1949),虽然达利使用的主视觉元素与当年莱奥纳尔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如出一辙:丽达与天鹅,但从这一对主体物的位置关系可见达利的丽达与天鹅甚至画面中的一切微小物体都处于不相碰撞的“借位”式飘浮状态,凸显质子、光子、中子、π介子等基本粒子的非连续性能量。在此之后,其还创作《核子十字架》(Nuclear Cross,1952)、《由星球组成的伽拉特亚肖像》(Galatea of the Spheres,1952)等作品,展示源自“借着这π介子与凝冻而不确定的微中子,画出天使与现实的美”[7]的冲动。
2.后现代、元现代与波粒二象性(https://www.xing528.com)
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艺术与量子发展带来的双重惊喜,从观念、形式与内容角度都呈现明显的绵延性。在20世纪后半场的后现代主义、元现代主义时期,艺术家从整体走向细节,从感性走向带有某种理性意味的深层感知,对类似保罗·高更(Paul Gauguin)提出“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经典命题进行重构,促使“消解”成为主题,艺术家旨在制造对艺术、自我与世界之间趋于自反式(anti-art)的实验,更体现出人类对自我认知的不确定性精神思考。
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认为不确定性是粒子的内在特质,即波粒二象性。通常,人们会认为电子等微观物质的本质是粒子,但量子理论认为其本质应该是波,单个电子本身也具备波的性质。而正因为波的流动属性,同理,电子也存在流动的不确定性。最为吊诡的是,当我们试图观测电子的时候,波却看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粒子;波与粒子无法单独却可以合体解释某种现象。实际上,看似复杂的波粒二象性,在点彩派时期就已然出现某种观念层面的对位——若画笔的笔触色彩是“波”,观者看到的却是“粒子”,即笔下涂抹的黄色与蓝色,观者却看到了色彩并置(流动性)之后的绿色,这一观念甚至可以延展到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抽象的色域绘画风格以及光效应艺术制造的光幻象。在后现代主义时期,更受技术影响和效果质感制造的艺术形态涌现,与波粒二象性的趋同性也似乎更倾向对细化、微观概念的多元表达。
20世纪60年代初,激浪派诞生。艾尔·汉森(Al Hansen)发出慷慨激昂的呐喊:“激浪无处不在,同时又无处可寻。”[8]在他的作品中,观者可以看到一个完整世界,或理解为一种基于艺术媒介的社会、政治和哲学媒介综合体,每一个“无处不在”而又“无处可寻”的工具、介质抑或手段,都在表明一种波与粒子对立统一的存在状态: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但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能看到激浪。我们熟知的波普艺术将这一理念延伸,在那些挪用、拼贴以及可复制所构成的艺术意识中,又涵盖了娱乐、消费的社会属性。此时,量子正在科技领域应用,一种改变人类命运的新形态——计算机诞生,诸如新媒体艺术因其媒介指向计算机和互联网,所以从溯源上来看,其与量子之间的关系根深蒂固。
人们似乎安于将后现代主义理解为阐释时代、社会发展以及自身思想的某种可备份的场域,这种备份体现在当思想出现模棱两可、不确定的混沌状态而无法言说时,总会称其为后现代的。在当下艺术创作领域,人们依然满足于所谓“后”(post)带来的快感,虽然很可能快感的根源处于量子式的不确定状态,但这对于精神和理念的“麻痹”来说,并不重要。然而,近年也有研究者对这种看似消解一切的“后”属性提出更具有革新性的想象,如卢克·特纳(Luke Turner)发表文章《元现代主义:简介》(“Metamodernism: A Brief Introduction”,2015),将元现代主义视为处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振荡”(oscillation),前缀“meta-”即两个同时使用却互为相反的、波粒二象性式的概念。
再来看量子物理,如今已然让人类逐渐适应将诸多不可知转变为可知的探索过程,越来越多的事物被可视化,甚至波及我们自身。正如保罗·托马斯(Paul Thomas)所述,“这场可视化的进程到了今天已经进入了微观的量子层面并运用到了量子力学,这不仅仅是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更是标志着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代的到来……既然量子现象是无处不在的,我们的直觉可能也与量子隧道相关,只是我们还不知道量子现象在多大程度地主导我们的意识或直觉”[9]。于是艺术家开启诸如量子生物学(quantum biology)的全新探索路径,保罗·托马斯与安德烈·莫雷洛(Andrew Morello)从分属的艺术与量子物理两个领域共同完成的作品《量子意识》(Quantum Consciousness,2015,图2),托马斯将莫雷洛对量子计算机控制处理器电子自旋(spin of the electron)进行可视化、沉浸式的艺术处理,将自己阅读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论文的声音转为微波信号,并激发电子旋转,此时量子意识体现在思想数据(观者)和量子数据(电子)的共时性呈现之中。更具有未来感的是,其实际上也指涉着人工智能与人类意识混合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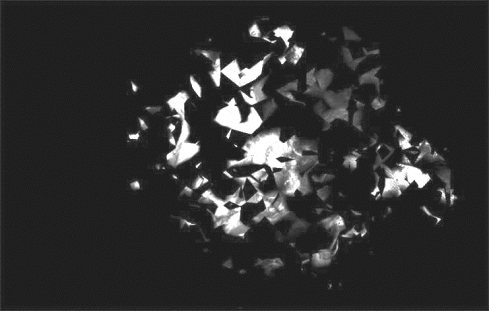
图2 保罗·托马斯与安德烈·莫雷洛作品《量子意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