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史系统里,蜀的早期历史与黄帝及其元妃嫘祖,以及昌意和帝颛顼有着极为深厚的关系。从族系关系看,黄帝族源出西北[10],与氐羌先民同源,而蜀族亦是原居岷江上游山区的氐羌族类,二者属于同一民族集团的不同支系。从婚媾关系看,黄帝族与蜀族又是亲缘族群,蜀族既是黄帝之子昌意的婚族,黄帝之孙颛顼的母家,又是帝颛顼的“支庶”[11]。因此,古代载籍称述蜀人累代“相承云黄帝后世子孙”[12],念念不忘其间的亲缘关系,是有深厚而久远的历史根源的。
(一)黄帝族与古蜀族
黄帝族与蜀族是亲缘族群,这是先秦两汉累世相传的旧说,绝无异词,乃是古人的共识。关于此点,《世本》、《大戴礼记·帝系》、《史记·五帝本纪》等中原所传古史,与《山海经·海内经》所载巴蜀所传古史,以及蜀王后代子孙所传古史,南北两系三方的记载完全一致,足可证明其事属实,绝非伪造。《大戴礼记·帝系》记载:

图2-4 《大戴礼记·帝系》书影
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
这段史料出于《世本》[13]。《史记·五帝本纪》所记,与此大同,其文云: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女,曰昌濮,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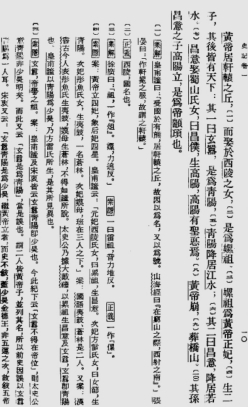
图2-5 《史记·五帝本纪》书影
《史记·五帝本纪》这段资料的来源,司马迁说是“谱牒旧闻”[14],即《世本》一类专记世系来源与分化之书,又有《大戴礼记》的《帝系》和《五帝德》两篇,以及《尚书》、《春秋》、《国语》等先秦时代流传下来的“古文”[15],均出中原系统。
同属中原系统的《吕氏春秋》,也有类似的记载,《古乐篇》云:
帝颛顼生自若水。
若水即雅砻江,纵贯四川西部,东与岷山(蜀山)相近。
按照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所说,他所依据的这些资料,都是源自先秦中原诸夏世代相传的旧说,“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证明确有其事,并非臆造。而且,上引诸书虽同属中原系统,但其取材之处却并不同源,其间有地域和国度的区别,如《世本》形成于赵,《吕氏春秋》形成于秦,其他诸书又有不同的来源。这些来源非一,流传次第非一的文献,对于蜀与黄帝的亲缘关系有着完全一致的记载,也证明事属真实,断非虚构。
先秦南方所传古史《山海经》,对于黄帝与蜀的关系亦有确切记载,《海内经》云:
黄帝妻雷祖(按:嫘祖,嫘雷二字音近相通),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取淖子(郝懿行疏:“濁蜀古字通,又通淖,是淖子即蜀山氏子也。”)曰阿女,生帝颛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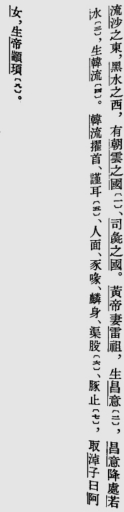
图2-6 《山海经·海内经》书影(https://www.xing528.com)
此篇成书于西周中叶以前[16],它与《大荒西经》所载帝颛顼和蜀王鱼凫的关系等内容,均出自古蜀人之手,同源于西周时已在蜀地流传的蜀王世系谱牒一类家史,或在蜀中世代相传的旧说,颇为信而有征。
《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补曰:
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
这里所说在“汉西南五千里”的蜀王子孙,是指夏商之际南迁于今云南大姚和四川凉山州地区的蜀王蚕丛后代。《史记·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蜀之先……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褚少孙所说蜀王为黄帝后世子孙,即指此而言。而黄帝子孙之说,当从这些蜀王后代朝降时自己称述得来[17]。这种称述,即是在蜀王后代中累世相承的家史,亦即《史记·五帝本纪》所说“谱牒旧闻”,它与《山海经·海内经》和《大荒西经》关于蜀王家史谱系的记载如出一辙,表明同源于蜀王旧史,故才得以在蜀王子孙中世代相传,至西汉时仍相传承而不改。
有关黄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濮,生帝颛顼的记载,除见于上述先秦两汉文献外,还见于其他一些西汉文献,如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扬雄《蜀王本纪》等,以及汉以后的各种文献,如常璩《华阳国志》、皇甫谧《帝王世纪》、杜佑《通典》、罗泌《路史》等。除此而外,历代注家、疏家的注疏当中,也不乏有关内容。
这些文献,从性质上看,可以约略分作四类。一类是先秦列国史官所撰之书,如《竹书纪年》、 《世本》等,也包括西汉直接录自这些先秦史乘的《帝系》、《史记·五帝本纪》。一类是先秦私家所撰之书,如《吕氏春秋》。另一类是汉晋时期兼采先秦载籍和蜀王旧史之书,如《蜀王本纪》、《华阳国志》、《帝王世纪》等。还有一类则是既采上古史籍和蜀王旧史,又采历代相传的旧说,以及当时所见的区域文化的材料,如《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补文、《华阳国志·蜀志》、《路史》等。可以看出,有关黄帝、嫘祖与巴蜀关系的材料来源是多方面的,并不成于一时一地一人之手。而这种多元性来源当中的一致性记载,恰恰能够表明其事属实,绝非伪作[18]。
关于蜀王自当有其家史和家谱,蒙文通先生有精当论述,认为当是《本纪》一类,其中关于“蜀山”的记载,既然见于《路史·国名记》所引扬雄《蜀记》,那么蜀王为黄帝后代之说应早见于《蜀王本纪》,今传辑本之所以无此记载,原因在于清代洪、严诸家辑本漏辑了这一条。而“昌意娶蜀山氏女”之说,既见于中原文献,又见于《蜀王本纪》,说明中原与蜀的相同说法是同出一源的[19]。对此,李学勤先生表示赞同[20]。
除此之外,《山海经》的材料也可以证明蜀王原有家传世系一类家史、谱牒传世。此书中的《海内经》和《大荒西经》均成书于蜀,《海内经》成于西周中叶以前,《大荒西经》成于周室东迁以前[21],此两篇一致叙述了黄帝、嫘祖、昌意、颛顼与蜀的关系,它们就是蜀王旧史中的一部分。从其成书年代看,这些材料本身的形成年代还要早得多,应在西周以前。这些材料在如此之早的年代里被《山海经》摭取,而此二篇并非官修之书,则它们的信息来源必定是蜀人所传的蜀王旧史,其流传年代应与黄帝、嫘祖、昌意、颛顼同蜀山氏、蜀王发生关系的年代一致,在此两篇采摭这些材料时,这些旧说已在蜀王室和蜀人中世代相承了若干年,正如居于姚、巂等处的蜀王后世子孙累代“相承云黄帝后世子孙”一样[22]。由此可见,这些从上古时代蜀人世代相承下来的旧说,出自蜀王家史、家谱,其基本内容是相当可靠的。
蜀王家史的保存流传,在地域上分为三个系统,一是中原系统,一是姚(云南大姚)、巂(四川西昌)系统,一是蜀中系统,三者同源异流,在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形式流传。从先秦到汉魏六朝,三个地区保存流传下来的关于蜀山氏与黄帝、嫘祖关系的内容均大体一致,充分表明它是传自上古的史实,绝不是后人妄言。
从区域文化角度看,蜀王旧史在蜀中长期保存,代相传习,至西汉时为扬雄《蜀王本纪》所收录。至晋时,这些材料仍在蜀中故老当中流传,常璩作《华阳国志》,其材料来源之一,便是“考诸旧纪先宿所传”,“及自所闻”[23],即其证。直至南宋,这些材料仍为罗泌采撷,足见源远流长,充分可靠。这说明,区域文化方面的材料,自有其保存流传的土壤和渠道,而这些材料的基本内涵,往往是有着相当可靠的历史事实为根据的。如果区域文化的材料有其流传系统,足可缕析其源流,或者能够在相邻区域的文献系统以及中原文献系统中取得验证,相互呼应,或者能够从考古学以及民族志等材料中取得证明,那么,就应当而且必须承认它们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而不能简单地根据这些材料的所谓“不雅驯”内容,或者单纯地依据中原人士获悉这些材料的年代早迟,来判定其真伪,以致轻率地作出结论。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在蜀中故老当中长期传习的蜀王旧史,就不能够一概斥之为妄,一概斥之为伪。
(二)嫘祖与古蜀
历代史籍记载黄帝元妃为嫘祖,并尊嫘祖为中国蚕桑丝绸之祖。
根据先秦古籍的记载,嫘祖本为西陵氏之女[24]。
古代蜀人称蜀山为“西山”,乃历代蜀王的“归隐”之地[25]。按古代的归葬习俗,归隐其实是指归葬于所从来之地,即是其所发祥兴起的地区。历代蜀王既归隐于西山,显然就意味着蜀之西山(蜀山)是其发祥之地,其兴于此,来于此,而又归于此。商代的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和成都羊子山土台(大型礼仪中心),方向都朝向蜀山,绝非偶然,它们其实都表现了魂归蜀山或祭祀其先王所从来之地的观念,这就从考古学文化上证明了蜀之西山乃蜀山氏兴起之地这一事实。
蜀之西山与嫘祖之西陵,这两个地名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陵,《说文》释为“大阜”,即大丘陵地区。山与陵,广义上可以互通,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26],即指此。嫘祖为其子昌意娶于蜀山氏,依古代地名随人迁徙的“名从主人”传统,将西陵之名带至那里,而命名蜀山为西山,同时在那里留下了以嫘祖名称命名的地名(叠溪)[27]。这就表明,蜀山氏的确与黄帝、嫘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能够说明嫘祖亲临蜀山并促成蜀山氏驯化桑蚕为家蚕这一重要转变的另一证据是,自从黄帝、嫘祖为其子昌意娶于蜀山氏以后,“蜀山氏”的名称就不再见称于世,而为蚕丛氏这个名称所取代,同时,蜀山氏原来所居的区域,也成为蚕丛氏的发祥兴起之地[28]。这个历史变化不是偶然的,其内涵恰与从蜀(桑蚕)到蚕(家蚕)的驯化演进历程相一致,真切地反映了蜀山氏在嫘祖蚕桑、丝绸文化影响和促进下,由驯养桑蚕转化为饲养家蚕,并以家蚕丝为原料缫丝织帛的历史转变及其进程。从蜀山氏到蚕丛氏名称的变化表明,两者关系是前后相续、次第相接的发展演变关系,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关系,也是生物学上的遗传变异关系,家蚕起源上的驯化桑蚕为家蚕的关系,包含并体现了深刻的历史内容,而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交替[29]。
正因为蚕丛氏上承蜀山氏,并在蜀山建国称王,所以其氏族名称和国号均称为蜀,即使是在蚕丛从蜀山南迁成都平原立国称雄后,虽保持了蚕丛氏的名号,但仍然以蜀命名国号,而以后历代蜀王也因袭蜀名而不改。中原文献称历代蜀王均为蜀,原因也在于此。
至于从“蜀山”到“蜀”的变化,则是与蚕丛氏从蜀山南迁成都平原相适应的。成都平原一望无垠,地理环境与蜀山大不相同,因而去其“山”而仅保留“蜀”。而蜀人对山的怀念,则长久地保存并体现在成都平原的大石崇拜之中。
从蜀山氏到蚕丛氏的转变,初步完成了蚕桑、丝绸的早期起源阶段,进入发展、传播的新阶段。其后,随着蚕丛氏从蜀山南迁成都平原,蚕桑、丝绸文化也一同传布开来,推动了蜀中蚕桑和丝绸业的兴起,并进一步演进成为中国蚕桑、丝绸业的主要基地和一大中心[30]。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