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翻译和分析马塞里努斯著作中有关匈人的记载,借此说明早期匈人的特性及其与匈奴的差异。之所以选择马塞里努斯的著作,是因为他的记载是有关匈人起源的最早、最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记载。还有其他很多有关匈人的历史记载,比如普里斯库斯(Priscus)史著残篇中有作者出使阿提拉宫廷的亲身经历,内容更真实生动。但阿提拉时代的匈人已经与八十年前的匈人有天壤之别。由于匈人刚进入欧洲时极端落后,在扩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大量异族文化习俗与社会组织方式。普里斯库斯对匈人服饰、娱乐、组织、建筑等的记载虽翔实丰富,但较早期匈人的生活已面目全非。另一方面,在所有记载匈人活动的古典史家中,马塞里努斯的历史见识与求真精神皆首屈一指,远胜他人。[672]因此,要了解匈人起源,马塞里努斯史著的价值无疑是最大的。
马塞里努斯对匈人的记载主要集中于第31卷第2章。这部分内容国内已有翻译。其中最重要者为齐思和先生的译文[673],这部分译文译自英文或法文,内容不完整,部分内容跟作者原意有偏差。另有一些译文与原文含义差别很大。[674]因此笔者将这一章由拉丁文全文译出,为保持内容连贯,同时也便于比较分析,与匈人关系密切的阿兰人部分也一并译出。在马塞里努斯对各民族的记录分析中,匈人部分最为独特。因为这部分内容皆来自当代人叙述与作者亲身观察,未借鉴前人记载。[675]有关这些记载的真实性,至今仍存争议[676],主要是因为对当时史家而言,匈人是全新民族。马塞里努斯记载匈人时,罗马人知道该民族存在不过十五年。另一个原因在于马塞里努斯与匈人接触不多,所获得的多为二手资料,更有学者认为马塞里努斯从未见过匈人。[677]不过,对于这些记载的可靠性我们也不应低估。马塞里努斯治史态度非常真诚,在记述匈人时坦承资料有限,“我们的古代历史记载中很少提到这个民族”[678],因而所言内容的可信度相对较低;而对于其他某些民族,比如后面要谈到的阿兰人,“经历长时间的各种探寻和了解,最终我们已经对这个民族的内部实情有所了解”[679],因此相关记载自然更可靠。另一方面,罗马人对匈人也并非完全陌生。在晚期罗马帝国,任何人都能轻易雇用匈人战士。378年的亚得里亚堡会战中就有匈人参战[680];马塞里努斯也提到战后劫掠色雷斯及围攻君士坦丁堡的蛮族队伍中有不少匈人[681];此后罗马军队中也一直不乏匈人雇佣兵。[682]因此马塞里努斯还是极有可能与匈人有过直接交往。[683]他关于匈人的记载被罗斯托夫采夫赞誉为“现实主义杰作”[684],其基本内容的真实性已获得现代学者的充分肯定。[685]
近代以来,史学家曾试图在马塞里努斯之前的古典记载中寻找匈人活动的线索,他们也确实在早期史料中发现了某些可能是匈人的民族。[686]但现代史学家经过审慎分析,认为这些所谓的匈人记载皆不足取。[687]因而他们再三强调:“对匈人起源,现代学者所知并不超过阿米亚努斯。”换言之,对于匈人起源,学者们探索了一千六百年后又回到原点,至今尚无法超越第一位记载者。马塞里努斯作为匈人起源最权威记录者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
在相关篇章里,马塞里努斯记载的第一段讲述匈人来源:
我们要追溯悲剧的源头,也就是彻底的毁灭以及众多失败的起因,是马尔斯的雷霆之怒以吞噬一切的永恒烈焰将其唤醒。这就是匈族,这个居住在麦奥提克(Maeotic)沼泽地以外冰冻海洋之滨的民族,其野蛮超乎想象。[688]
关于匈人进入欧洲前究竟居于何地,古典史料中记载颇多,也存在不少争议。最终的结论是:马塞里努斯的记载依然是最准确的,现代人对此的认知并未超过这位古典学者。[689]亚速海古称“麦奥提克湖”,这里的“麦奥提克沼泽”即指亚速海边上环绕刻赤海峡的沼泽地带,已知匈人最早的栖息地位于高加索山脉以北,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偏南地区。照普里斯库斯的说法,具体地点为今库班(Kuban)河流域。[690]该地区虽然适于放牧,但地形起伏较大,南部山地众多,这使得匈人具有某些与大草原游牧民族不同的特征。“冰冻海洋”所指为何无法确定,可能暗示匈人之前居于更北方。后面会说明匈人在某些方面确实带有极北民族特征,与典型的草原游牧民族有所不同。[691]
第二至第三段描述匈人外貌:
匈人孩子刚一出生,他们的面颊就被刀深深刻划,这样当他们长大时,脸上的刀疤纹路会阻止胡须生长。因此成年后的匈人相貌丑陋,没有胡须,形同阉人。所有匈人都有着紧凑强壮的四肢,肥短的脖子,而且身材畸形,样子可怕。如果见到他们,你会觉得他们像长着双腿的野兽,或者是排列于桥梁上那些粗制滥造的雕像。
匈人相貌凶残,外形粗陋可怕。[692]
关于这两段记载争议颇多,较一致的看法是:抛开种族偏见不谈,马塞里努斯笔下的匈人具有明显的蒙古种族特征。自然,这些描述中不免有作者的误解。比如关于匈人自幼割面以阻止胡须生长的记载,一般认为这是亚欧游牧民族中很普遍的蛈面习俗[693],其他古典记载中有阿提拉葬礼上匈人蛈面的内容。[694]马塞里努斯可能对匈人毛发稀少感到惊奇,想借此加以解释。这些记载与其他古典学者,如普里斯库斯,哲罗姆(St.Jerome),约丹尼斯(Jor-danes)等人说法基本一致。[695]其他古典记载,如佐西默斯(Zosimus)认为匈人即早期古典史著中提到的“扁鼻人”[696],普里斯库斯称阿提拉鼻子扁平[697],也有助于说明匈人的种族特征。这些记载与现代考古发现基本吻合。匈人墓葬的考古分析也证明匈人为混种,特别是进入欧洲后与欧洲人大量混血。但在抵达欧洲之前,匈人的蒙古人种特征应该比较明显。[698]
此外,某些对匈人奇异外貌与自残习俗的记载可能是事实,并非出于种族偏见。例如约丹尼斯称匈人的头颅圆而变形[699],高卢诗人西多尼(Sidonius Apollinaris)称匈人在儿童时期以布缠头,使头颅变形。[700]目前这些说法已获得考古证明,一些匈人贵族妇女的颅骨确实因幼时刻意缠裹而严重变形。[701]这种奇特的头颅变形(cranial deformation)风俗主要存在于一些原始亚洲居民及古代美洲民族中[702],在亚欧大陆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保存此类自残习俗的民族较少见。该原始习俗如果能在亚洲保存下来,最有可能存在于极北与山地等相对隔绝地区。
这里简要说明一下中国历史上匈奴人的民族属性。尽管尚存争议,目前史学界支持者最多的观点是匈奴人属突厥族,该说法与中国史籍的记载最为吻合。[703]另外关于匈奴的种族同样争议颇大,支持者最多之说为:匈奴为种族混杂的民族,其主体为高加索种。
此说法与史书记载以及目前为止的考古发现最为吻合。[704]
第三段主要关于匈人的饮食:
匈人生活需求极低:他们不需要火,也无需可口食物,他们食用野草根和半生不熟的肉类。至于肉类来自何种牲畜,他们概不计较。为了加热,他们会把肉放在自己大腿与马背之间焐一小段时间。[705]
这段记载表明,匈人的饮食习俗即便在游牧民族中也非常原始落后。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匈人不知用火且食用生肉的说法,一般认为这不是事实。[706]门琴黑尔芬已对此做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很多游牧民族到了近代还有将生肉置于马鞍内侧的习俗,为的是防止马匹被马鞍刮伤,同时也便于取食。[707]其实马塞里努斯原文并未说匈人不知用火,而是说他们“不需要火”,用火的技巧匈人应该是掌握的。关于匈人的“吃生肉”习俗,与马塞里努斯同时代的哲罗姆亦有类似记述[708],应该不是空穴来风。这之后有关匈人的史料中就不再有这类记载,因此这里所说的可能是一种被迅速遗弃的原始饮食习俗。笔者认为如果考虑到匈人可能来自极北区域,这段记载就不难理解了,匈人以生肉为食之说可能是对某种生食习俗的夸大记载。直至近代,极北地区居民都有食用生肉的习俗。他们并非不知举火,只是以此方式为身体补充维生素C。因环境所限,这些居民无法获取新鲜蔬菜水果,肉类成为维生素C的主要来源。[709]但维生素C在高温下会分解,因此只能以生食方式加以补充。[710]该段马塞里努斯称匈人还食用“野草根”,此习俗也存在于一些北方民族中[711],同样与补充维生素C有关。自然对任何民族来说,食用生肉与野草都不是愉快体验,因为这会给消化系统及免疫系统带来很大负担。因此在获得其他维生素C补充方法后,他们皆会放弃该习俗。[712]很可能匈人在与其他文明民族接触后就不再食用生肉,所以其他的古典史料中也就不再有此类记载。
第四至第七段以及第十段主要涉及匈人的生活习俗,包括住房、衣着、对马匹的依赖等:
他们从不盖房子,而且避之如同我们躲避坟墓。在匈人之中,你甚至找不到一间哪怕是芦苇编成的陋室。他们漫游于森林和群山,从出生之日起他们就惯于忍受饥渴与严寒。即便身在其他民族之中,他们也不会待在房屋里,除非是迫不得已。因为他们认为身处别人屋顶之下很不安全。
匈人以亚麻衣服或缝在一起的森林鼠皮蔽体,无论在私人场合还是在公开场合,他们都只穿一种衣服。他们偶尔也会穿上我们的束腰外衣,不过这些衣物都很破旧,而且他们不懂得换洗。直到衣服被磨损撕扯成布条,他们才会把它们脱下。
他们戴着弯皮帽,以羊皮遮盖他们多毛的双腿。他们穿的鞋子没有硬底,这使得他们在地面上行走不便。因此,匈人完全不适于徒步作战,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几乎完全生活在马背上。他们骑乘的马匹非常丑陋,但不可否认其忍耐力超群。匈人骑马姿势奇特,有如女人[713],他们就骑在这些马匹上从事日常活动。这个民族的人能够整日整夜待在马背上,他们在马背上做买卖,在马背上吃喝,还会弯下身子伏在他们矮马的脖颈上沉沉入睡,进入梦乡。
即便是遇到重大事情需要认真商议时,他们也待在马背上保持这种姿势。
匈人从不耕作,他们甚至不愿触碰犁耙。实际上所有匈人皆居无定所,四处漫游。他们没有固定村落,不举炉火,不识法度,其生活方式如同流放犯人,与定居民族迥异。匈人主要的安身之处是他们的马车,他们在马车里出生,在马车里把孩子养大。如果你问一个匈人他是哪里人,他肯定无法回答。可能的情形是:他的母亲在某地受孕,而在另一处很远的地方生下他,然后又在其他更遥远的地方将他抚养成人。[714]
这些段落的奇特之处在于无一字提到匈人如何放牧。从这些记载来看,匈人为相对较原始的草原游牧民族,他们接受游牧文化的时间可能并不长,至少在匈人刚进入古典历史舞台时远比其他游牧民族落后。依照当时古典作家的说法,“即便在野蛮人眼里,他们也是野蛮人”。[715]据这些记载推测,此前匈人与定居民族不会有多少接触。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他们对房屋的恐惧,与定居民族有过交往的原始民族不可能对房屋有这种畏惧心理。第五段提到的匈人穿戴,部分为匈人自制(如“缝在一起的森林鼠皮”),其他则可能来自南方定居民族(如“亚麻衣服”和“束腰外衣”)。但这些推测也存在争议,比如门琴黑尔芬认为羊毛和亚麻织物也可能为匈人自制。[716]第六段称匈人“在马背上做买卖”,说明匈人与其他民族已开始有贸易往来,但这类贸易活动的规模不会很大。
这几段有关匈人的记载与中国史籍中对匈奴人的记载差别极大。匈奴人在公元前3世纪之前就有一定农业基础[717],而匈人“从不耕作,他们甚至不愿触碰犁耙”。[718]匈奴与中原文明地区交往频繁[719],除中原外,匈奴人还与中亚甚至西亚的众多文明地区有密切交往。[720]蒙古诺颜乌拉(Noin Ula)山匈奴古墓群中还出土了多种产于欧洲的织物。[721]因此,匈奴人在离开东亚时已是相当文明的民族,其文明程度在游牧民族中首屈一指。[722]中国史籍对匈奴的最后记载之一是匈奴人在中亚建立的悦般国[723],其中特别强调该国居民远比周边民族开化,称他们“清洁于胡。俗剪发齐眉,以醍醐涂之,昱昱然光泽,日三澡漱,然后饮食”。[724]此外中国史籍还提到悦般国与草原霸主柔然间的长期战争,战争起因是匈奴人认为柔然人过于野蛮肮脏。[725]这些记载未必属实,但匈奴人因为与文明世界长期交流而变得较为文明是无可否认的。
第八与第九段介绍匈人的军备与战术:
匈人有时会主动挑衅发动战争[726],他们的作战阵形为楔形,作战时发出各种凶猛的吼叫。为了行动便捷,他们轻装上阵,因而总能出敌不意。在战场上他们会故意遽然分散,然后从各个方向列队进击,他们凭借此战术克敌制胜,给敌人造成惨重损失。由于他们移动极为迅速,他们攻入壁垒与洗劫城堡时,敌人往往尚未察觉。
因此可以确定地说:匈人是一切战士中的最凶猛者。与敌人相隔一段距离时,匈人会向敌人放箭。他们用的箭头与我们的不同,由削尖的骨头制成,他们连接箭头与箭杆的技术非常高超。冲过这段距离之后,匈人会以刀剑与敌人近身肉搏,他们作战勇猛,全然不顾虑自身安危。当敌人全力格挡他们剑刺时,他们会趁机用编结的绳索(或罩网)[727]捆住敌人,使敌人丧失骑马或行走能力,动弹不得。[728]
很多我国学者在提到匈人战术时,除列举其作战方式与中国历史上匈奴战术的相同点外,还喜欢强调欧洲人对此种战术完全陌生,因而“望风而逃”。[729]这些看法实为误解,前述所谓“阿兰人以战车为主力”大概也是基于此类误解。其实不止匈人与匈奴人,所有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均大同小异。相对而言,古代中国人对骑兵机动战术的接触与记载很晚,因为游牧文明传播到东亚地区相对较晚。[730]最早对游牧骑射战术的详细记载——包括套索(lasso)的使用——为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及萨迦提安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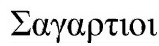 )[731]等换言之,此时正是西亚与中亚的“胡服骑射”时期。游牧民族战术的描述。[732]古典欧洲人对骑射战术并不陌生,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军队中就有骑射手(
)[731]等换言之,此时正是西亚与中亚的“胡服骑射”时期。游牧民族战术的描述。[732]古典欧洲人对骑射战术并不陌生,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军队中就有骑射手( )[733];在马塞里努斯时代,罗马野战部队(Comitatenses)中的骑兵比例已达四分之一以上[734],其中多数为骑射手(Sagittarii),作战与训练方式皆模仿游牧民族。[735]综合分析古典记载可知:匈人的战术优势主要并不在于骑射战术,而在于其战士及马匹的英勇顽强与吃苦耐劳[736],此外还在于他们的作战技能。[737]从匈人进入欧洲直至匈人灭亡,罗马军队中一直有匈人雇佣兵,欧洲人对匈人的战术不可能陌生。[738](https://www.xing528.com)
)[733];在马塞里努斯时代,罗马野战部队(Comitatenses)中的骑兵比例已达四分之一以上[734],其中多数为骑射手(Sagittarii),作战与训练方式皆模仿游牧民族。[735]综合分析古典记载可知:匈人的战术优势主要并不在于骑射战术,而在于其战士及马匹的英勇顽强与吃苦耐劳[736],此外还在于他们的作战技能。[737]从匈人进入欧洲直至匈人灭亡,罗马军队中一直有匈人雇佣兵,欧洲人对匈人的战术不可能陌生。[738](https://www.xing528.com)
第九段称匈人的箭头为骨制,这反映出匈人技术非常落后。[739]该段还提到匈人近战中使用铁剑(ferrum),这些武器不大可能为匈人自制。其他古典记载称匈人铁制武器稀少,这已得到考古证实。[740]考古证据还显示早期匈人装备骨制鳞片甲[741],这也可作为马塞里努斯记载的有力佐证。之后的史料记载与考古发现显示:匈人很快就放弃了自身的原始兵器甲胄,大量采用罗马与哥特武备。[742]与匈人相比,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人铁器文化相当发达,他们对冶铁技术的掌握甚至可能早于中原民族。早在公元前3世纪,匈奴人就具备了批量制造金属武器的能力,能制造大量铁箭镞和其他兵器用于战争及狩猎,这同样为众多考古发现所证实。[743]
从马塞里努斯在这里的记载来看,匈人在战术上与包括匈奴在内的其他游牧民族有一定区别。多数游牧民族都采用所谓“斯基泰战术”(Scythian Tactics),即与敌人保持距离,以大量弓箭消耗敌人。[744]匈人的攻击战术则较为直接:先射箭,冲过箭程后即短兵相接。因而匈人比其他游牧民族更偏重于骑兵正面冲击。[745]马塞里努斯的这些记载与其他古典记载大体一致。此外,马塞里努斯也未提到匈人采用游牧民族惯用的“佯退诱敌”战术。[746]匈人战术何以相对简单独特,原因不详。可能是因为早期匈人并非纯粹游牧民族,加之人口稀少物资匮乏,又缺乏有效组织,所以未能发展出大规模骑射战术;也可能是因为早期匈人的主要敌手是其他游牧民族,这种直接的近距冲击战术相对更有效。
马塞里努斯对匈人马匹的描述与后来古典作家的说法基本一致。据其他古典史料所言,匈人的马匹固然如马塞里努斯所言能吃苦耐劳,但并非优秀战马,因此匈人很快就引进罗马战马。[747]另有古典史家称匈人在降服阿兰人之前为纯狩猎民族[748],物资相当匮乏。这可以解释第四段所言“从出生之日起他们就惯于忍受饥渴与严寒”。匈人的这种“非典型游牧特性”也有助于说明其后匈人战术发展的独特性:跟其他纯粹游牧民族不同,匈人在进入多瑙河平原后就部分放弃了游牧生活[749],他们不再是纯粹的骑兵民族,转而模仿罗马人与周边日耳曼民族发展出自己的步兵战术。[750]此时,马塞里努斯笔下早期匈人的亚洲游牧民族特征,如软底皮靴与尖皮帽等,想必早已消失。匈人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快放弃骑射战术的游牧民族。
第七段与第十一段简述匈人的社会及民族特性:
匈人们不对任何君主效忠,但接受分散首领的统治。在这些首领的统驭之下。他们摧毁所遇到的一切。
即便是在休战时期,他们也反复无常,毫无信用。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全力以赴投入行动。他们没有是非观念,就像那些用于献祭的无知牲畜。他们的意识晦暗不明,令人难以捉摸。他们行事从不为宗教与迷信所困扰,而是受对黄金的无穷贪欲的支配。他们善变易怒,即便是对于自己的盟友,他们也会无缘无故加以背弃,随后又会不假思索与其和好如初,如此情绪反复有时会在一天之内发生数次。[751]
上述马塞里努斯笔下匈人的不知礼仪与贪婪寡义跟司马迁笔下匈奴人的“苟利所在,不知礼义”颇为相似。此类记载皆是基于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的共同视角,很大程度是继承了前辈史家对“野蛮”民族特性的贬义描述。[752]从这些记述看,匈人在社会组织和观念意识方面还相当原始,跟定居文明民族以及其他游牧民族差距巨大,在很多方面甚至难以与这些民族沟通。匈人社会结构松散,大约以部落为单位,一般没有权威超越部落的君长[753],主要可能是因为落后与匮乏。[754]
第十一段着重讲匈人“反复无常,毫无信用”,这可能是因为马塞里努斯等古典作家难以理解匈人那种原始松散的社会结构。匈人无统一领袖,各部落往往自行其是[755],局外人如果把匈人看做单一整体,就不免认为他们“反复无常,毫无信用”,“受对黄金的无穷贪欲的支配”。匈人这种奇特性格让古典作家惊奇不已,任何人只要有钱,都可以雇用匈人为自己效力,哪怕是用于对其同胞作战。比如据马塞里努斯记载,东哥特王维提米利斯(Vithimiris)曾雇用一些匈人抵抗匈人主力进犯。[756]在古典史家眼中,匈人这一特性直到匈人灭亡都少有改变[757],这大概是因为匈人社会从未真正统一。即便在阿提拉统治的短暂鼎盛时期,匈人世界也并未实现完全统一。据普里斯库斯记载,阿提拉在死前第四年还忙于征服黑海东部的匈人部落阿卡茨里人(Acatziri)[758],而且阿卡茨里人也并非唯一独立于阿提拉统治的匈人部落。[759]即便是阿提拉这种不完整的统一,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统治者的个人能力来维持[760],因此阿提拉死后匈人帝国随即土崩瓦解。
由上述分析可知,匈人的社会政治组织从未发展到成熟阶段。这跟中国史籍中匈奴人的社会政治组织可谓有天壤之别。匈奴人很早就从南方农耕文明国家与周边游牧民族中借鉴社会政治制度,加以吸纳改造。到公元前2世纪匈奴全盛时期,匈奴人不仅完全实现了统一,而且其社会政治组织及各类制度已相当完备。单于之下有王、谷蠡王、大将、都尉、当户等官职,形成严密的等级管理体系[761],而且匈奴人还有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与法律体系。[762]相比之下,据普里斯库斯描述,匈人即便在其最后阶段,社会组织程度亦远远逊色。
马塞里努斯有关匈人社会组织的记载是现代学者争议最大的部分,汤普森与门琴黑尔芬对此的看法差别很大。汤普森认为这些记载总体准确可信;门琴黑尔芬则认为早期匈人社会组织没有马塞里努斯笔下那么原始分散,匈人很早就有过统一组织,约丹尼斯称早期匈人在君主巴拉米尔(Balamir,或译为巴兰勃)统一率领下西进可能有所根据。[763]目前多数学者更倾向于汤普森,认为巴拉米尔实为虚构人物。[764]据古典民族史学者希瑟考证,巴拉米尔的原型其实是5世纪摧毁匈人霸权的东哥特王法拉米尔(Valamer)。[765]匈牙利著名学者哈玛塔(Harmatta)曾激烈反对汤普森的观点,后来也承认早期匈人非常落后,开化之后唯有全盘模仿其他民族的社会组织方式,以致匈人社会“毫无自身特色可言”。[766]匈人在同周边日耳曼民族交往后,不只是文化与社会组织,甚至连贵族姓名都模仿日耳曼人[767],可见早期匈人所拥有的文明因素极稀少。匈人组织的原始性和分散性有助于解释匈人向欧洲腹地的扩张何以如此缓慢:匈人主体越过顿河后花了至少四十年时间才进抵多瑙河平原。[768]一个在军事上拥有较大优势的游牧民族,如果有良好统一的内部组织,绝不可能采用这种缓慢渗透的扩张模式。尽管存在上述种种争议,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在社会组织方面,欧洲历史上的匈人与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之间差异巨大,两者鲜有共同点。[769]
马塞里努斯将匈人与阿兰人合在一章介绍,显然是考虑到两个民族间的密切联系,以及两者的共同点和差异。[770]事实上阿兰人是远比匈人重要的民族,这个民族在亚欧草原历史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其影响远达中国。[771]直到今天,阿兰人后裔依然是高加索地区的重要民族。[772]因此,对于这个民族的早期记载我们也应当予以重视。
阿兰人居住在靠近亚马逊人领地的另一片地域,其领土向东伸展。他们分布广泛,远至亚洲,形成一些庞大且人口众多的部落。据我所知的信息,阿兰人的势力甚至延伸到恒河流域。这条大河把印度人的土地分开,最后流入南方的大海。
阿兰人的居住地横跨世界两大部分[773],该民族群所包含的不同族群这里不再赘述。各种阿兰人分散居住于非常广大的地域,他们像游牧民族一样在无边的原野上游荡。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具有很大同一性,他们的各类习俗,野蛮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武器装备等都是一样的,因而他们共同拥有“阿兰人”这一名号。
阿兰人没有固定居住的房屋,也绝不会去扶犁耕作。他们以肉类为主食,还饮用大量乳汁。他们分散居住于广阔无边的荒野,以马车为家,他们的马车式样独特,带有树皮制成的弧形车篷。当阿兰人新到一片牧地时,他们先把马车排列成环形,然后在这马车构成的“城”中间举行狂野庆祝仪式。如果该地区的牧草告罄,他们会把“城”移向其他地方。这些马车实为阿兰人的永久居所:男人们在车中与女人交合;孩子们在车中出生,然后在车中长大。不管阿兰人走到哪里,他们都视马车为自己的天然家园。
阿兰人的放牧方法是把牲畜分成牧群,他们在牧群后驱赶牲畜。他们对马匹特别重视,花很多精力照料马匹。阿兰人的土地总是牧草丰美,其间还有很多地方生息着众多野兽。因而不管他们走到哪里都不缺食物与饲料,湿润的土地以及土地上众多河流为他们提供了一切。
阿兰人中的不适合战斗者,无论其年龄与性别,都待在马车附近承担较轻义务。而那些年轻人则接受各种复杂的作战训练,从孩提时代起就练习骑马。所有年轻阿兰人皆为优秀的马上战士,他们看不起步行作战。阿兰人与波斯人[774]颇为相似,他们有着同样的斯基泰族源,也都非常骁勇善战。
他们使用轻巧的武器装备,因而在战场上行动迅捷。在生活方式与开化程度方面,阿兰人比匈人要略好一些。阿兰人一路劫掠与狩猎,范围遍及麦奥提克湖与辛梅里安博斯普鲁斯海峡[775],他们也以同样方式洗劫过亚美尼亚与米底地区。
阿兰人喜爱冒险和战争,一如平和安静的人喜爱安逸舒适。他们以战死沙场为荣,对那些有幸寿终正寝者则大加恶词嘲讽,视之为懦夫和低等人。[776]对阿兰人而言,最值得夸耀的事便是杀人,至于被杀者是谁他们倒不在意。他们还会把被杀者的头颅割下,剥下头皮[777]作为战利品用于装饰战马。
在阿兰人之中看不到神庙或神龛,也没有一间哪怕是最简陋的草顶小屋。但他们还是有类似于其他蛮族的宗教仪式:把一柄无鞘的剑插于地上,把它当作战神加以虔诚膜拜。在阿兰人游牧的一切地域,战神都是最高保护神。
阿兰人的占卜方式非常奇特:他们挑选特定时间收集一些很直的柳枝,然后将它们分散排列,同时口念咒语[778],如此这般他们就能清楚预知未来。
阿兰人不知奴隶制为何物,他们皆出身贵族,而且他们只选择那些公认久经沙场的战士为首领。[779]
匈人与阿兰人最重要的共同点在于都相对原始。例如他们都以篷车为居所[780],不使用帐篷,连最简陋的房屋都不会建造。这些特征与其他游牧民族差别很大,说明匈人与阿兰人都是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人对帐篷的使用要早得多[781],后来匈奴人还建造了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城镇。[782]匈人固然在与其他民族接触后学会了使用帐篷[783],后来还懂得建造简单房屋[784],但直至灭亡,匈人在居住方面的文明程度远未达到匈奴人西迁之前的水平。[785]
马塞里努斯也明言两族间的差异,“在生活方式与开化程度方面,阿兰人比匈人要略好一些”。比如阿兰人已有成形的宗教信仰与崇拜仪式,而匈人“从不为宗教与迷信所困扰”。马塞里努斯详细记载了阿兰人的游牧活动;但对匈人,则两次强调其“游”而无一字说其“牧”,只在第三段涉及匈人饮食时暗示匈人有各种牲畜。这大概不是记载的疏忽,可能是因为匈人最早游牧的地域的水草不如阿兰人地区的丰美,匈人的牲畜在数量质量上较逊色;也可能是因为与阿兰人相比,匈人畜牧业很落后,或者匈人生活的游牧色彩相对薄弱。
还有一些与种族特性相关的记载容易被忽略:马塞里努斯称阿兰人主食为肉类和乳汁,而匈人主食只有肉类。这些记载包含的信息想必马塞里努斯也没有意识到。如此的饮食习俗差异说明多数阿兰人有乳糖耐受(lactose tolerance)遗传特性[786],而多数匈人则没有。即便后来匈人懂得制作乳制品,也主要食用乳酪与乳酒之类的非乳糖制品。[787]此记载为阿兰人属印欧种族的重要证据之一,也与马塞里努斯对阿兰人相貌的描述吻合:
大体上所有阿兰人都身材高大,相貌漂亮。他们的头发为金色,色泽有些偏暗;他们的目光颇为凶蛮,让人害怕。[788]
马塞里努斯对于阿兰人种族特性的记载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789]而匈人的主体显然不是印欧民族。从这个角度看,匈人为斯拉夫人一支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匈人最可能归属的两个族群(芬族和突厥族)皆为乳糖不耐受族群,这符合马塞里努斯与其他古典作家之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