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卫战争的合法性问题上,这位教士毫无理由地将耶稣会士的所有教条都归于我们,如若我们成功地证明这是早在耶稣会士产生前就存在于圣经中的真理,这位教士便会从他的事业上滚落下来。
教士[1]:勃艮第人(the Begardi)认为,世上没有公正的政府与法律。对此,我从可拉和大坍等故事中就知道了[2]。于是,我就非常害怕我们的时代也会幻想这等邪说。
驳:这好诽谤中伤的教士,紧接着就开始掩饰自己,说:他们自以为与他们一道的人,都真心地认为政府不仅是合法公正的,而且对教会与国家都是必需的。但是,他指责的都不是我们所想的。
教士:有人说,统治权建立在恩典之上,无论是里昂穷人派(Waldenses),还是胡斯派(Hussians)都持这样的教义。此刻,我无法证实或证伪它。格尔森等人坚持认为,人们谈论的这些东西必须重新分类和认证。太多人对诸如此类的理论过于自信了!
驳:1.恩典是统治权得以建立的基础,是它的顶梁柱。因此,恶人因他们的世间之罪就不能掌权。——这种教义是教皇主义者栽赃给最早的新教徒、里昂穷人派、威克里夫派以及胡斯派的。今天,耶稣会士、苏亚雷斯、贝拉明、比卡努斯等人继续这样做。这位教士继续把这些诽谤留在他们身上,以免惹怒教皇主义者与耶稣会士,进而把这些罪名加在我们头上。但是,如果这位教士认为,统治权不是建立在恩典之上,那么,在权力上,统治者应该拥有那圣灵,即降落在七十长老身上的呼召圣灵;而他们就不应该是那些“敬畏神、恨不义之财的人”(《出埃及记》18:21),像格尔森那些人那样。他毕竟是相信圣经的啊!2.格尔森认为,信徒对他们的财产当有属灵上的权力。这点是正确的。我们在圣经中也能找到依据,如《哥林多前书》(4:21)、《启示录》(21:7)等处。
教士:耶稣会士当以他们的诡辩谬误为耻!他们宣扬,教皇拥有直接统治与最高统治之大权,还有管理民事与教会之权。由此,他们给予教皇在君王与国家之上的间接性的正式强制权,而在属灵领域的权力就更不用多说了。所以,教皇便可任意废立君王。我们国家的长老会即使不完全这么行,所行也非常接近于此了。
驳:1.这空话连篇的人装着像一位经院学者。他应该指出,那些持此类观点的经院学者的姓名来!2.君王必须是主教,因为他们要求君王顺服在福音之下,使基督在教会的权杖责备他。他们还认为,基督徒的王当受渎神与虐杀等罪的谴责。相反,教士则用地狱的魔鬼来杀死君王的灵魂。3.其实是教士在立王!我们的不列颠王加冕时,一个天主教的大教士将王冠戴到查理头上,将王者之剑与权杖交到他手中,并在他手上、王冠上、肩上、手臂上膏油。此时,英王必须亲吻大主教与主教。这不是在属灵的国度立王子为王吗?能立王者定能废王。看看大主教斯波茨伍德(Spotswood)与此事的关系。他给英王提供了那些天主教王的誓言,即公开宣誓保持宗教信仰(对真正的新教信仰只字未提),认真地连根拔掉所有的异端与敌人(即他们所认为的新教徒),回归对神的真正崇拜。神的教会应该把这些罪都判在他的头上。这位教士公开宣示,他们不从王那里接受主教之职,而是从教皇那里接受。试问:在属灵的国度,谁才最接近教皇的权利啊?4.这位血口的教士又是如何诽谤长老会废王的呢?他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是关于君主制与长老会制政府间的矛盾的;里面充斥着谎言以及对他受洗之教会的中伤。事实上,小册子中所有的观点只是证明了议会与君主制间的矛盾,以及如何将君王变成最绝对的暴君。单凭这点就当判他忤逆。
教士[3]:那位清教徒说,所有民事权都原初地、根本地根植于民众。这是与耶稣会携手共进的。
驳:他花了六页纸来反复重述这点。1.如果一群人被天主教的暴政赶到了美洲殖民地;他们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那么,这是否是这里讲的异端?整个以色列都是异端了。即使大卫受神的指派与膏礼(《撒母耳记上》16)后,他也不是以色列民的王,直到以色列民在行动中宣誓这权力,即在希伯伦选立大卫为王。2.无论这位教士做什么样的演绎推理,他都是个不择不扣的二道贩子;与那坐在庭上的大腹便便的判官们的逻辑一样,最终只能让他们蒙羞并颜面无存地被赶出法庭。因为,现在英王与两院之间的论战,就如伊拉斯莫斯(Erasmus)[4]在谈论他的神观时,路德没有指控也没有辩护。不管你是谁,只要你外形像清教徒,你就得被赶出法庭,即使没有做过任何反对信仰与国家之事,也没有违背过任何与神的誓言与契约。他的逻辑是这样的:耶稣会士说过,政府的权力源自人民;清教徒也说过,政府之权力原初地来自人民;因此,清教徒就等于耶稣会士。依照这种逻辑,清教徒确实是耶稣会士,因为清教徒与耶稣会士都承认有一个三位一体的神。如要按这种逻辑推理,我们有更确切的证据证明:这位教士包括整个教士阶层,以及教廷的那些圣人们都是耶稣会士。
1.耶稣会士宣扬:(1)教皇并非敌基督者。(2)基督下降到地狱是为了解救一些人出那监禁之地。(3)从巴比伦式的罗马教会分离出来是一种罪。(4)因功称义。(5)禁食的美德不得遭到非议。(6)弥撒不是拜偶。(7)教会是争论的法官。(8)亚米尼教派的教义对信仰更安全。教皇制的本质是真理;天主教的教义应当被广为宣讲与印刷。
2.教士与教廷的圣人,包括这位教士,在所有这些事上都与耶稣会士不谋而合。在那本叫做《坎特伯雷的悔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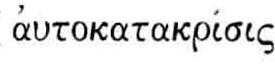 ,the Canterburian self-conviction)檄文里,这一点得到了斩钉截铁的证明。那些高级教职者与罗马教的任何宗派中的任何人都不能扪心回答。此刻,我们便知谁才是耶稣会士了。
,the Canterburian self-conviction)檄文里,这一点得到了斩钉截铁的证明。那些高级教职者与罗马教的任何宗派中的任何人都不能扪心回答。此刻,我们便知谁才是耶稣会士了。
3.耶稣会士还未出生前,律师和新教徒就在倡导这一教义了。教皇主义者也从中吸取养分。博士从不谈论政策问题,直到近些年,他掌管政府之权力;他必须依本性之光,根本地、原生地根植于人民群体。这位教士认为[5],耶稣会士并不是这种观点的首创者。那么,这谎话精如何就能说清教徒与耶稣会士密谋呢?耶稣会士的苏亚雷斯[6]认为,贝拉明大主教发现的不是什么新鲜事;而耶稣会士泰纳[7]认为,他们的耶稣会士不是这种观点的生产者,而是神学家与法理学家们毋庸置疑的共同意见。耶稣会士的托勒特(Tolet)以《罗马书》第13 章为基础,认为民事权利来自神,只借助了人与社会之调节功能。
4.耶稣会士说,没有合法的基督徒社会,真正的政治要有选择和任免官员的正式或类似的权力;这样就要承认顺服;但是,产生官员的合适过程只能属于罗马教皇。我们绝不承认罗马的主教是世界合法的主教与牧师。
这位教皇主义教士却认可这一点,他说[8]:“教皇的最高假定,把自己放在挑战的位置上,即教皇在神圣权力上作为基督在世上普遍代理人的头衔与权利。作为罗马的主教,与他的教区内的最卑微主教相比,教皇没有更多的神圣权力(通过教会法而享有的权力不是我们这里要检讨的),也没有更多的殊荣(除了程度上的大小)。”从他为此所列举的材料看,他唯独没引用圣经经文。圣经才能证明或证伪神圣权力。他对引用居普良[9]的说法,并为此自鸣得意。最后以这样一句话结尾:“神会认可,争论的双方以古代圣教父的言论为准绳。”
驳:1.从第四章开始(其他两章我在后面会涉及)在废王之事上,这位教士把清教徒说得比耶稣会士更恶劣。如君王有缺陷,人民就收回其权力,从而替君王行统治,也就是废王。贝拉明[10]认为人民不能废王,但有些情况除外,即君王滥用自己权力对公共领域行毁灭之事(如对某个城市)。不过,我要对此进行说明,如果教皇主义者认为教皇可以废王,那么,这位教士就刚好成了他们的代言人。因为:(1)我上面节引的他的话就是很好的证明。他在为教皇之最高权力辩护(他如今立王与废王只是他最高权力的一个环节与部分)。(2)这段引文也正好证明了他是一个教皇主义者,因为“教皇的最高假定,把自己放在挑战的位置上,即教皇在神圣权利上作为基督在世上普遍代理人的头衔与权利”。他为何不说这是无权可依呢?直接说:依神的权力,他就不是基督的代理人。很明显,教皇主义者仅依教会之权力认他为基督的代理人;他们所声称的教皇延续至今只能根据传统来证明,而非圣经。
2.教皇主义者明确表示,教皇的至上权来自口头传统。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从圣经来证明这种权力。
3.这位教士明确地说:“通过教会法而享有的权力不是我们这里要检讨的。”他很明晰地表明,在圣经与神圣权力之外,教皇借助某种权力而成为基督的代理人。他不对此做讨论,仅仅是担心惹怒了那些教皇主义者。
4.他说,与其他主教相比,教皇没有更高的特权,但程度上的不同除外。作为职分的主教在本质上与长老会的长老不同(这是他需要强调的);前者从神圣权力那里得到自己的职分。他的意思必须包含这一点,否则他对眼下问题所说的就都是废话了。依据神圣权力,教皇比一般主教在程度上拥有更大的特权。罗马教皇的程度与范围有多大呢?应该是世上所有看得见的天主教教堂吧。所有的主教都是基督特有的使者(《哥林多后书》5:20),也是基督的使节与代理人。教皇则是依神圣权力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主教,就是那称自己是基督普遍代理人的人,如那使所有蛋彼此相像的那个蛋。这位教士所宣讲的教义完全是教皇主义的;他书中的材料及其暗含意义都是粗俗的天主教教义;他所有的小册子都反对长老会。关于教皇之至上权力等为题的争论,他欲将其决定权给古代教父们的观点,就足以证明他就是一个糜烂的教皇主义者。他为何要将这些争论的决定权归于教父呢?为何不在先知与使徒那里寻找根据呢?教父们能比神的话更好地解决结论吗?以教父为根据,而不以圣经为根据,我不理解其中理由何在;除非说经文晦涩难懂。教父的权威与光芒不能决定和审判争辩,除非他们拥有从教父与教会而来的权威。我们知道,这便是所谓的第四属性样式(proprium quarto modo)[11]。耶稣会士与教皇主义者在各种争论中都会呼喊:教父啊!教父!不过,如果教父的言论对我们比对他们更有利,他们就会做两件事:(1)对我们有利的言论,那就随教父们一起腐烂吧!(2)教父犯了错误,如孩子们拒绝这些错误,那就是儿子们的异端!
说我们与耶稣会士为伍,这实在是再错不过了。1.我们宣扬抵制暴君,就运作意义而言,并不比格劳秀斯、巴克利和温扎特斯等人关于罢免君王之言论更甚。在这一点上,保皇党与耶稣会士勾结。2.当君王变成异端时,我们否认教皇有权将臣民从忠诚之誓言中释放。3.在教皇的命令下,人民有权以异端之罪名废王。——这位教士与他那些教皇主义的同伙就这样宣传的。所以,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Ⅶ)便如此践行了。阿奎那[12]也持此说。安东尼奥谈论道[13]:“你要将万事放在教皇的脚下。”基督徒是绵羊;犹太人与异端是公牛;异教徒就是牲口!纳瓦努斯[14]认为异教徒没有司法权。雅各·西门科(Jaco.Symanca)说[15]:“异端男人的天主教妻子没有义务为其还债。很明显,异端不具备所有管辖权,包括本性的、民事的、政治的,等等。如父亲是异端,其子依法律规定便是奴仆。他们只能在侍奉神的事务中才能解脱。”教皇主义者认定,教会神职人员无需顺服在王法之下;这是教士的教会特权。现在,这位教士与他的同伙们一起让英王在其加冕仪式上宣誓:保持教士之所有教会特权,即所有天主教君王所宣之誓言和承诺!
教士:民众将王权直接给君王,通过协调与准许的方式,神只起间接之作用!耶稣会士与清教徒的步调地何其一致啊!见贝拉明[16]、苏亚雷斯[17]等。
驳:说我们宣扬王权是间接来自神,仅需要神的许可,这纯属诬陷。但是,他的一个同伙确实撰文反对过王的最高统治权,那就是安东尼·卡皮尔(Anthony Capell)[18],他说:扫罗与其他王都是在什么允许下才被立为王,且与神的旨意相悖,神为此发怒?这并非我们教义。我们的教义是,神在真正的充足理由中,使人与社会具有理性和社会性;而对于人,他以同样理由使他们拥有本性直觉;通过理性中介,他创造了王。贝拉明与苏亚雷斯说,神并不仅仅以准许的方式造王。
教士:人民可以将君主制变成贵族制或民主制,也可将贵族制变为君主制。我怀疑他们甚至不能对两者进行区分。
驳:1.这位教士并不知道所有的事情——仅从贝拉明与苏亚雷斯他们是耶稣会士,就推出,他们是彻底的耶稣会士。苏亚雷斯说[19]:“权力的给予是绝对的,一旦给出便不能收回,无论是全部还是部分;特别是涉及那些重大权力时。”人民一旦将他们的权力给予了君王就不能无故将其收回。以苏亚雷斯等耶稣会士的理论为基础,我们的信仰便成了异端。他们的确牢牢地抓住了这点:“君王不是百姓良心的主,不能强迫他们去信仰异端邪说。”我们到处宣讲,西班牙王无权强迫他新教臣民的良心,使其信仰拜偶宗教;他们在灵魂上不是他的臣民,仅肉体上是他的臣民。
2.君王堕落为暴君也不是什么大的罪。如果王室血脉断了,人民便有将君主制改为贵族制的自由。耶稣会士否认在没有教皇准许下人民有这项权力。我们认为,无论是作为大主教的教皇还是小主教都不该在立王之事上掺和。
教士:他们说王权来自人民,以交流的方式,而非剥离的方式。因此,人民不会完全丧失这主权。就好像英王在爱尔兰任命了一名中尉,他并不是从自己的王权中放弃这一权力,而是信任他让他任职。如果这是他们的想法,那君王可真够可怜的了!主要权力在代表团那里,所以人民还是法官,君王只是他们的助手。
驳:这位教士担当写手一职,却不知那不是我们的意见。王者作为王,拥有人民的权力;他不是人民的副手。
1.人民并不是主要的法官,而是君王的下级。君王拥有法律执行权,是在人民之上的真正君主。副手一说纯属乌有。
2.人民一次性地将治理、防御与保卫自己的权力转让给了君王,自卫之权力除外。这自卫权是人民不能让渡的。这是无罪本性的生而有之权力,与吃、喝、睡的自由与权力不同。除非君王施暴政,人民不能回收那些权力。君王并未对自己的仆人与助手不可取消地让渡过任何此类权力;他自己就可行使这些权力。
3.一个代表,无论是行善还是作恶,都对那些给予他信任的人负责。君王在正义行为中并不需对任何人负责。如果他的行为没有受到暴政怀疑,无人会质疑他说:你在做什么啊?只有在不公正行为中才会发生这种事。那些非常暴虐之行为与置于君王身上的信任相矛盾。此时,君王就得对代表人民的国会进行解释。
4.作为代表,无论他做得好还是做得差,只要被代表人高兴,他便可继续做代表。即使君王为王是根据神对王位的呼召,基于百姓的自由选举,但除了在暴政情况下,他都可继续为王,而不需简单依据民意。在这一点上,苏亚雷斯和贝拉明与我们所坚持的没什么大的区别。但是,他们所说的要比教士真诚得多。他们宣扬任何一个从地狱来的使者都可刺死一个新教的王。我们知道,教士宣称自己与耶稣会士相反,所行却与他们完全吻合。他们视教皇为基督在世间的代理人,认为神圣权力就是主教;让君王宣誓保持教士、主教以及他们所有的特权(在这所有的特权中,一项主要的权力是,罗马主教在属灵的国度有间接之权力,能废黜那些变为异端之王的王)。我发现,在对抗君王这事上,这位教士与教皇自己一样“深邃”。这位教士完全蒙蔽了世人的眼睛。
这位教士煞费苦心地要证明,在路德与加尔文之前,关于人民在暴政中拥有君王之上权力的理论,格尔森、奥科曼、雅克·德·阿尔曼与巴黎的博士们都持与他相同的观点。他这是自欺欺人。路德、加尔文与我们并不是从耶稣会士那里习来的这些观点。加尔文的思想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20]。国家可以强迫并降低暴君的力量;不然,他们就糟蹋了神给予他们在国家与教会上的信任。这一教义正是保皇党在反对诺克斯,布坎南、朱尼厄斯·布鲁图(Junius Brutus)、阿尔图修斯等人时奔走疾呼的。路德在给牧师的书信[21]中提到了两种形式的抵抗:扫罗要杀自己儿子约拿单时,人民对他的反抗;亚希甘等众首领将耶利米从犹大王手中救出。基拉都斯(Gerardus)对此论证引用了许多圣人,他再次引用了路德以及贾斯特斯·琼拿(Justus Jonas)、尼古拉斯(Nicholas Ambsderffius)、乔治(George Spalatinus)、贾斯特斯·曼纽斯(Justus Menius)、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Hofmanus)等人;以及新教的圣者们,如贝沙、帕瑞尔斯、波兰鲁斯、卡姆(Chamer)等人,还有法国、德国以及荷兰的所有圣者们对此的想法也是众所周知的。这位教士以罗谢尔这个城市以及那里的新教教会的叛变一事为托辞,他们带领下的法国新教徒的自卫战争最后却成了叛乱,与耶稣会士并肩作战。在这些战役中,耶稣会士阴谋杀害新教徒,毁灭新教。
这位教士已表明他对教皇废黜查尔迪瑞克(Childerick)一事的看法了(对此,我无言以对,只能说教皇只是个敌基督的篡位者,这可怜的人啊!他就永不合适戴上王冠)。继而,他根据一些缄默的作者之观点确立了一个自己的想法。依这种方式,他本可臆想出千种想法啊!他想让人相信他居于一个饱学人士的秘密世界中,永远看不到这辩论之底部。在那些大师们缺席的情况下,他被迫模拟成在跟屁虫的苍穹那里升起的一颗新星,揭示所有的梦想,并对所有那些新的文士说教,如布坎南、朱尼厄斯·布鲁图(Junius Brutus)等人。在这个众人皆睡的世界里,这个黑暗之子的撒旦粉墨登场,展示了新的法律与尊严,还有那诡辩家的神学。
教士:他们认为最高统治权主要地、自然地在民众那里;从他们那里,神直接地把它给予了君王。这种想法的理由是,我们无法收获政府的果实,除非我们给自己找些各种各样的麻烦。
驳:1.谁说这位教士不能说“最高统治权主要地、自然地在民众那里”这话呢?!根本地,最高统治权不在民众那里,却自然地、主要地在民众手中,如热在火中,光在太阳中一样!我想这位教士定如此梦想过吧!只有他会这样说。什么属性自然地在一个主体中,我认为,那就是可以直接地、自然地述说主体的东西。这位教士告诉我们一个非常自然性的断言:“民众啊!令人敬畏的最高统治者,可以对这对那发号施令!”
2.君主制不会比民主制更符合理性。我们只能顺服在政府下才能收获果实。(https://www.xing528.com)
3.他说,我们顺服在君主制下必须自寻麻烦。这话说说不打紧,却是对信仰、法律、教会自由与国家的颠倒。如引入教皇教、亚米尼教、拜偶教、圣坛崇拜教、弥撒教;赦免在爱尔兰残杀数十万无辜新教徒的凶手;杀害成百上千的贵族、男爵与平民;借助武装的教皇主义者攻击法制之地;将英格兰变为血染的国度,强行推动拜偶的祈祷书;用军队从海陆两方封锁苏格兰;等等;难道这些都是我们自寻的麻烦吗?
4.这些事情的发生都只是可能的与偶然的吗?如这位教士所行的那样,将君主绝对化与暴政化才是必要的吗?这是罪人能所要的,即将自己神化。如人天生会犯罪一样,他们受到引诱,便会对荣耀与伟大行醉癫与轻浮之举。我们知道,以色列与犹大的王在权力上也不是绝对的。尼禄与朱利安是偶然现象吗?那头上长十个角,骑一血红野兽,身负撒旦之灵的女人,对羊羔与其同伴发动战争也是偶然的吗?
教士:他们推断:1.只要不违背神圣诫命和破坏信仰,人民就无法回收他们放在君王那里的权力。2.抢夺核心权力是大罪一宗。3.这法令并非默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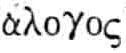 )的,而是宣示性的(
)的,而是宣示性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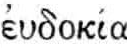 ),并且有紧急理由。
),并且有紧急理由。
驳:1.这些不知姓名的作者不能作此推断,那有条件地确立的誓言被打破了。人民给君王的所有权力都是有条件的,即他必须用它来谋求人民的安全。如果它被用来毁灭百姓,他们就要收回这权力。这并没有破坏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从未在这些条件下立誓放弃自己的权力。同样,也不能说,他们回收他们从未给出的东西。
2.因此,这位教士要使这权力有能力去做前面所说的那些伤害,认为这便是王的核心。巴兰的预言便不值得拿那些钱;王的核心是流血的权力,以及对百姓、法律、信仰、国家与教会自由的摧毁!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宣讲人民从君王那里收回权力,解除教皇主义者的武装,清除嗜血的爱尔兰叛党,就像他们对待我们那样,公正地侍奉他们。
3.人民的这项法令,是给君王以合法权力采取和平与敬神的方式进行治理。这是神所喜悦的,有公正的理性与原因作基础。如果说,人民将这权力转让给一个人,乃是要行以上所谈到那些麻烦,即去行嗜血与毁灭,那就绝对与神和理性无关。
教士:这种意见的理由是:1.统治权力如果不集中在一人手中,便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践行政府的必要职分与行为。2.要不也没法阻止国家分裂为许多权力。他们必须为促进更大的善、防止更大的恶而分享本来就有的全部权力。3.收回或限制这权力的任何部分,即人民已完全放弃了的权力,就会使君权无法正常行统治,也会让整个社会失去活力。
驳:1.除了这位教士在那里自言自语外,我从未听过这等谬论。第一种理由说得倒是押韵,但毫无理性可言。即使没有行善作恶的绝对权力,在君王那里限制性的权力也有足够力量去完成一个公正政府的所有行为,实现统治的目的,即人民的安全。但是,保皇党要的是暴君力量,行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些暴掠嗜血。这便是他们强调的君王核心部分。好像软弱是力量的核心一样,君王如只能行善与保卫百姓,那他便不够拥有力量;除非他也能像暴君一样来作恶,摧毁与毁灭他的子民。这种权力乃是软弱的力量,与那伟大的万王之王的形象不沾边。
2.他提供的第二个理由是谴责民主制与贵族制为非法,认为君主制是唯一的解救良药。这就好像神只命了绝对君主制,除此之外别无政府。神确实没有这样诫命,因它违反了合法王的本性(《申命记》17:3)。
3.人民必须完全放弃他们的自然权利,以便制造一位绝对君主。这就好像是在说,整个身体必须与他们营养分离,等着受精卵膨胀。这无疑是对整个身体的摧毁。
4.人民不能放弃他们的自卫战争权力,就像他们不能与本性分离一样。否则,他们就是把自己置于奴隶之下。况且,奴隶主要变卖奴隶,或不义地侵犯他,或要夺走他的性命之时,奴隶还是可以以暴力反抗这种不义的暴力。他的其他结论也是无效的。
【注释】
[1]马克斯韦尔:《基督教君主的神圣王权》,c.1,p.1,2。
[2]可拉和大坍是两位抗拒摩西的利未人,最后活生生被大地吞噬。参见《民数记》第16 章。
[3]马克斯韦尔:《基督教君主的神圣王权》,q.l,c.1。
[4]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Roterodamus,1466—1536),荷兰人,著名的天主教人文主义者。
[5]马克斯韦尔:《基督教君主的神圣王权》,c.l,p.12。
[6]苏亚雷斯:de primat sum.pontifi.1.3,c.2,n.10。
[7]泰纳(Tannerus),tom 2,disp.5,de leg,q.5,in 12,q.95,96;Dubi.1,n.7.——原注
[8]马克斯韦尔:《基督教君主的神圣王权》,c.5,p.58。
[9]居普良(Cyprian),de unitat.Eccles。
[10]贝拉明,l.3,q.de laic。
[11]第四属性样式是中世纪实在论的一个重要说法。它指的是一种实在的、自在的属性(不在三维空间中存在),可以被所有同类事物分享,但自己并不依赖于这些事物。不过,这些食物却要依靠它才取得那种性质。在近代文献中,这个词大多是指一种绝对确定性。译者无法追踪原始出处。卢瑟福是从讽刺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12]托马斯·阿奎那,22 q.12.ar.2.。
[13]安东尼奥,sum.par.3.t.22,c.3,sect.7。
[14]纳瓦努斯(Navarrus),l.l,c.13。
[15]雅各·西门科(Jaco.Symanca),de Catho.Instit.tit.45,n.25。
[16]贝拉明,l 1.de liac.c.6。
[17]苏亚雷斯,cont.sect.Angl.l.2.c.3。
[18]Tract.contra primatum Regis Angliæ.
[19]苏亚雷斯,De prim po.l.3,n.4。
[20]加尔文:《基督教要义》,Instit.l.4,c.4。
[21]路德,tom.7,German,fol.38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