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发现经过
《景教碑》的发现纯属偶然。明朝天启五年(1625)初春的一天,西安城附近有人掘出一块硕大的石碑,额题“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题“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这块石碑与通常的唐碑并没有多大区别,然而细看却会发现特异之处:在碑额的上方,刻着一个由莲花台烘托着的“十”字,碑文下方和碑的左右两侧,还刻着许多外国文字。该碑出土后,就近安置在西安城西的崇仁寺(俗称金胜寺)内,这座寺院是当时西安最大的佛寺(图3-28)。
一位名叫张赓虞的当地举人,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细读碑文后发现,碑上所讲的“景教”教义,与他十多年前在北京听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宣讲的基督教教义十分相似。惊异之余,他精制了一份拓本,派人专程送往杭州,向教友李之藻求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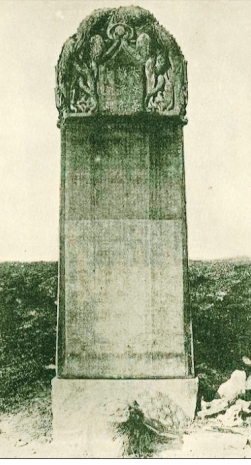
图3-28 竖立于金胜寺的景教碑
李之藻是当时著名的天主教徒,与徐光启、杨廷筠并称“圣教三杰”。他读罢张赓虞送来的拓本,确认此《景教碑》是基督教遗物,这个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景教”,正是利玛窦所传的圣教天学。也就是说,早在一千年前的唐初,基督教就已经传入了中国,并受到唐太宗以下五代皇帝的礼遇和优待。上帝的福音早在千年之前已在中华大地上传播了。作为基督徒,李之藻当然兴奋不已,他抄录碑文,于当年便出版了《唐景教碑钞本》一书,以广流传。
然而,当时的中国知识界,除了徐光启、李之藻等个别具有天主教背景的士大夫之外,对“景教碑”的发现并不重视,没有产生什么反响。到了清代,才开始有金石学家著录此碑,不过他们像著录其他唐碑一样,并没有对其具有独特内涵的碑文做深入研究,且在对景教的认识上多有谬误,分不清它与摩尼教、祆教乃至佛教的区别,更谈不上揭示此碑的价值。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学术界才最终摆脱金石学的局限,开始以近代科学方法对《景教碑》及与景教相关的课题进行研究[30]。
《景教碑》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刻成后,原立于唐长安城义宁坊大秦寺。唐会昌年间武宗灭佛,大秦寺被毁,景教碑随之埋没地下八百余年之久。明天启年间又出土于长安崇仁寺,后遇战乱,寺院碑亭俱毁,景教碑暴露旷野之中。这种状况,直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丹麦人何尔谟(又译何乐模)计划盗运《景教碑》时才告结束。
(2)丹麦人盗运景教碑
《景教碑》出土后,与在中国知识界遭受到的冷遇相比,其在西方教会和学术界引起的关注,大大超乎人们的预料。
【洛阳唐代景教经幢】
2006年5月出土于河南洛阳隋唐故城东郊。其形制模仿佛教陀罗尼经幢,为一面宽14厘米的八面体石灰岩棱柱,残高84厘米。经幢顶端的立面上,刻有两组装饰图案,均以十字架为中心,且分别有一对男相飞天和女相飞天向十字架奉献、瞻礼。其飞翔飘逸的造型,无疑受到唐代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影响。据《经幢记》记载,此幢建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原来树立在一位自中亚移居洛阳、殁后葬于洛阳某地的“安国安氏太夫人神道”,建造者为其“承家嗣嫡”亲子。十五年后,又于唐文宗大和三年(829)“迁举”,但未说明迁于何处。
幢身中段,每面刊刻汉文楷书文字2至6行。第一面至第五面第一行,刻祝文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一部;第五面第二行至第八面,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一篇。经文见于已经发现的敦煌汉文景教写本中,据学者考证,它并非景教原典的译本,而是在华景教僧侣的原创,其模仿佛经的形式,采用中国人更易理解的概念和词汇,向中国人宣讲景教的基本教义。《经幢记》记载了洛阳大秦寺“寺主”和其他两位领导者的名字,其后均以小字注明其“俗姓”,由此可知三人均是粟特出身,并且来自两个中亚国家——米国和康国。此外,还记载了一个移居洛阳的安国景教家族,虔诚信仰景教,却已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
第一个见到《景教碑》的外国人,是法籍耶稣会士金尼阁,他很可能还是《景教碑》最早的拉丁文译本的翻译者。就在《景教碑》出土的当年即天启五年(1625)四月,他应陕西三原人王徵之邀,赴三原为其全家施洗礼。不料金尼阁刚到三原就病倒了,直到十月份才在王徵陪同下来到西安,见到了出土不久的《景教碑》,很可能是他将碑文译成拉丁文寄回欧洲。
《景教碑》的发现,对当时正在中国这块“异教”的土地上艰苦开拓圣教事业的耶稣会士来说,无疑是喜从天降。碑文所揭示的史实,要比他们苦口婆心的说教更有说服力。他们也顾不得当年在中国被称为“景教”的聂斯脱里派的异端性质,将《景教碑》视为“圣教古迹”,在欧洲做了轰动一时的宣传,引起教会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教会和传教士们的宣传无疑带有明显的宗教动机和功利目的,以致反教会人士相当反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便质疑“景教碑”的真实性,甚至说此碑是耶稣会士们伪造的。然而,西方教会和学术界并未因此减弱对“景教碑”的关注,依旧考释者蜂起,而且从那时起三百多年来,研究著作层出不穷。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动乱的时代。各国探险家、学者、军人、僧侣、记者等,打着文化的幌子,到中国大肆进行文化剽掠和考察活动。由于声名在外,“景教碑”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探险家猎取的目标。
1907年5月,一个叫何尔谟的丹麦记者来到古都西安,直奔景教碑的发现之地。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盗运景教碑。在他于1924年出版的《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一书中,毫不掩饰地谈到了这次西安之行的目的:
我对于西安府景教碑有失体面的安放状况在很多年前就知道了。如前所述,去年一月,我与伦敦多个方面的权威们讨论过为科学界获取景教碑的方法和途径,以便于学者和广大民众能够观览景教碑。
我拜访了多位博物馆的官员和某些头面人物,他们对于保护举世无双的历史碑刻具有浓厚兴趣,我在各处都受到鼓舞[31]。
就这样,在考察了金胜寺和景教碑后,何尔谟与金胜寺住持、76岁的老僧于寿进行密谈,订立密约,许以重金购买景教碑。与此同时,他通过于寿在寺内解决施工场地,秘密雇请石匠,欲用相同的石料、相同的尺寸规格精确地复制一碑,以复制品代替原碑。甚至为了得到理想的石料,他亲自到富平采石场挑选。
然而,何尔谟频繁出入金胜寺,难免引起外界注意,尤其是引起西安当地的天主教会的猜疑,因为他曾将自己的计划透露给一位在西安的瑞典籍传教士。而这些外籍传教士对景教碑同样非常关注,他们自认为是这块基督教碑的合法继承人和保护者,甚至曾打算将景教碑当作礼物运回梵蒂冈。

图3-29 现存于碑林博物馆的景教碑
正当秘密协商搬运之际,清廷得悉消息,急电命陕西巡抚妥加保管。于是以此为契机,1907年10月2日,景教碑移置西安碑林(图3-29)。
而何尔谟在原计划败露、地方当局出面制止的情况下,总算没有空手而归,得到了一件非常精确的复制碑。这件复制品运回纽约后,何尔谟以租借的形式交由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公开展出。8年后,纽约一位富有的天主教徒蕾丽夫人,购买了这件复制碑,把它送给了梵蒂冈。
(3)世界四大名碑
尽管何尔谟盗窃景教碑未果,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景教碑价值的称赞与肯定,甚至将其列为世界四大名碑之一。他说:(https://www.xing528.com)
正像分别收藏在伦敦、巴黎和墨西哥城的世上绝无仅有的罗塞塔碑、摩押碑和阿兹特克太阳历石一样,世上也只有一通景教碑——它们当属世界上同类碑刻中的四大代表性碑刻[32]。
了解一下何尔谟所说的其他三大碑刻,也许有助于帮助人们认识景教碑的重要价值。
罗塞塔碑,高114厘米、宽73厘米,镌刻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诏书。由于碑上刻有同一段文字的古埃及象形文、埃及简化文字和古希腊文三种文字版本,由此成为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研究古埃及历史的一把钥匙,使得近代的考古学家有机会在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的意义与结构,而成为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罗塞塔石碑最早是在1799年时由法军在埃及港湾城市罗塞塔发现,但在英法两国战争中辗转到英国手中,自1802年起保存于大英博物馆中并公开展出。
摩押碑,约刻于公元前870—前830年间,当时的犹太人越过河谷进犯摩押王国,摩押王米沙率领摩押人击退了犹太人的入侵,大获全胜。摩押人把这一胜利用摩押文和希伯莱文凿刻在一块高110厘米、宽70厘米、厚40厘米的黑石头上。用34行文字记述了这段历史,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摩押碑。1868年8月德国传教士在今天的约旦发现了摩押碑。现保存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
阿兹特克太阳历石,1790年12月17日在墨西哥城出土,直径360厘米、厚122厘米,重24吨,陈列在墨西哥城国家人类学博物馆中。它是墨西哥人奉献给太阳神的一块纪念碑,在这块太阳历石中央的太阳神周围,刻绘着阿兹特克的历法及与宇宙论相关的图画文字和符号,代表了墨西哥人的宇宙观与世界观,这块太阳历石成为阿兹特克文化的象征。
明天启五年(1625)发现于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螭首龟趺,通高279厘米、宽99厘米。碑额楷书“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9字,其上刻有莲花座及十字架,碑文楷书32行,行62字,由大秦寺僧景净述,吕秀岩书。内记景教教规、教义、东罗马山川、河流、特产以及景教在中国的流传情况。碑下部及两侧刻有叙利亚文字的记事和僧徒题名,两侧还有清咸丰九年武林韩泰华重造碑亭的题记和民国六年的题记。
(4)内容解读
景教碑碑文开篇,使用了相当大的篇幅介绍景教的基本教义和礼拜方式,如讲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创造世间万物和人,原罪,耶稣诞生,耶稣基督的救赎之道,以及景教的圣洗、瞻礼、祈祷等礼拜方式。当然,这些景教的基本教义都是用地道的汉文书面语来表达的,文字优美,言简意赅。
接着碑文通过大量的事实,详细介绍了景教在唐代中国的传播情况。自贞观九年(635)景教初入中土,至景教碑刊刻的建中二年(781),先后经历了太宗、高宗、武则天、玄宗、肃宗、代宗、德宗等不同时期,凡146年。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一位叫阿罗本的主教(上德)携带景教经像来到大唐国都长安,宰相房玄龄率仪仗出城,将其迎入宫中。就在阿罗本到达长安三年后,长安城中建起了第一座景教寺院。唐太宗特为此事而下诏书,见于《唐会要》卷四九:
贞观十二年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第一座景教寺院所在的义宁坊,位于长安郭城朱雀街之西第五街街西从北第三坊,大致相当于今西安市莲湖区桃园路以西、土门以东、桃园西路以南、丰镐东路以北这样一个范围内。
唐高宗时,阿罗本被尊为“镇国大法主”,并“于诸州各置景寺”,一时之间,“法流十道,国富无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虽不免有夸大之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高宗时期景教传播的盛况。
唐玄宗时,曾令其长兄宁国王等五位亲王,亲自到景教寺建坛参拜。天宝初年,又令高力士送去“五圣写真”,即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位先帝的画像,安置于景教寺中供奉。天宝四年(745),玄宗专门下诏,将此前一直称作“波斯寺”的景教寺院,改称“大秦寺”。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登基,是为肃宗。在大唐王朝岌岌可危之际,唐肃宗仍于灵武等五座郡城中重建景教寺院。
唐代宗时,每逢圣诞之日,会给景寺“锡天香以告成功”,还会送来美味佳肴款待景教徒。唐德宗于即位之初,制定了维新景教的方略;第二年,景教碑刻立于长安城义宁坊大秦寺。
此外,碑文还记述了一位名叫伊斯的景教僧侣,对其高尚的德行大加颂扬。伊斯还曾担任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副手——同朔方节度副使,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景教碑是为伊斯而立的颂德之碑。
在景教碑正面,有三处刻叙利亚文,一处在碑文开首撰文者署名的下方,一处在碑文末年款的下方,另一处在碑正面底部,刻叙利亚文间有汉文共24行。
在景教碑左右侧面,刻有70名景教僧侣的叙利亚文署名,左侧41人,右侧29人,其中8人无汉名,其余均刻对应之汉文名号。在碑正面的叙利亚文字,其中有景净、伊斯、灵宝、行通、业利等5人的叙利亚署名,加上未署汉名的萨吉思,再加上年款后面法主宁恕的叙利亚文署名,则碑上有叙利亚文署名之景教僧侣共77人。这些叙利亚文署名,很多附有此人在教内的身份,这为研究唐代景教的教会组织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景教碑左侧第三列的第11个人,其以叙利亚文署名“路加”,汉文名为“僧文贞”。经考证,其全名为李素,字文贞,墓志已在西安东郊出土,下文将会详细介绍。
(5)重要价值
景教碑是保存在中国的最古老的基督教文献,是考证古代基督教东渐历史及中国古代基督教发展历史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文献,在对古代基督教历史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为研究我国与叙利亚、伊朗等国的文化交流及友好往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碑文中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史料,详细讲述了景教在唐太宗至唐德宗之间146年的传播历史,很多记载可以与史书相互印证,如前引唐太宗为建立景教寺院而下的诏书,在碑文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只是个别词句有所不同而已。因此,景教碑是研究唐代前期历史、宗教信仰活动以及印证史书记载真实性的重要实物证据。
《景教碑》之所以具有世界性的研究价值,并吸引几代中外学人孜孜不倦地研究、探索,主要因为此碑是用汉文和古叙利亚文两种文字刻成。通过对叙利亚文碑文的研究,可以揭示许多汉语碑文所忽略、所掩盖的珍贵信息,比如唐代景教的神职体系,当时景教僧团的构成等等。即使对叙利亚文字本身发展演变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此碑书丹者吕秀岩虽未能名添唐代大书家之列,然其书法结体工整而不刻板,字体苍劲有力,圆滑饱满,浑厚不乏秀气,用笔灵动又不失端严肃穆,结构疏密得当,章法布局常有意外的巧妙,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水平。因此,其被国家评定为“书法艺术名碑”(图3-30)。

图3-30b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局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