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和对某些现状的观察,显而易见的是,19世纪早期美国的发展进程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特有的基督教形式,其教会的组织和标准都是独树一帜的。数百年来,基督教首要的传统并非多种宗教“派别”的交融,而是唯一的教会传统。然而,在美国殖民地之初,占领者来自不同的移民群体,代表了欧洲大革命余波之下各式各样的忏悔式信仰——既有“左派”又有“右派”的宗教。在这片领土上,维持垄断和高压的体制是极其困难的,这早已不言自明;到了18世纪中叶,殖民者就已懂得学习接受宗教上的兼容并蓄及律法上的和谐共融。
宗教不统一,随之而来的是宗教多元化,美国人弃除教会建制而拥护宗教自由。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传遍美国全境的宽泛的自由度,令最初仅为异见派系的宗教团体发展为固定组织,它们虽不像昔日的教会那样正式,但架构牢固、组织良好,不应再视为小派系。地位提升的派系和降格的建制,在一个自愿和自由竞争的宗教环境下几乎比肩运作,逐渐稳固下来,称为教派主义。(1)美国的教派主义精要,在于教会成为自愿的组织。教会不享有任何强制性会员的优待,甚至连传统的、承袭的会员身份亦格外弱势,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平信徒得以自行选择效忠于哪个教派。在旧的教会模式下,平信徒出生于哪个堂区常常便被迫留在这一堂区,他获得宗教体验的方式取决于堂内的礼教形式。但美国的平信徒并非出身于某个教派或继承了某种神圣的仪典;教派通常是他在获得一些宗教归化体验之后自愿选择加入的。
这样的选择毫无悬念。18世纪末,美国人的生活状态如此起伏不定,大革命的余韵导致如此混乱无序,以至于约90%的美国人在1790年之时是脱离教会的。后续的数十年间,这种惊人的宗教无组织状态很大程度上有所改观。信教的民众自我规范,大多皈依了某一教派。在此过程中,无数人一次又一次地做出是否加入某一教派的决定。平信徒选择投身的教派经由前人的决策磨砺,满载着美国人与往昔断绝的渴望,对未来的引颈期盼,以及对历史与日俱增的鄙夷。美国的政治信条里充斥着一种观念——欧洲代表着昔日的腐败,必须连根拔除。新教教派也是基于对基督教过往的类似观点。(2)人们普遍相信,基督教的历史沿革并未积淀有价值的体制和规范,反而是一个腐坏和变质的过程,基督教本源的纯粹沦丧其中。因而敬奉的目的并非为了保有形式,而是新一轮出击,以重拾这种纯粹。“这是一个自由的时代,”1844年,杰出的长老会福音布道家阿尔伯特·巴恩斯这样写道,“人们必将自由。宗教形式是僵化的智慧和过往的愚行,不能适应这个时代自由的运动、宽泛的思想和变动的计划。”(3)
为基督教正本清源,经文本身即为最佳途径。哪怕是那些不乐见美国宗教出现这种趋势的人,都意识到它的重要性。1849年,德国改革派教会的一位发言人声称,教派对个人判断和对《圣经》的价值在于(4)
针对一切老旧的历史权威做出了必要的抗议,也许承认已然明确的真理除外,当然,真理的唯一衡量标准完全不是历史的权威,而是某一教派的独立思想……一个真正的教派,在成立之初和其后的任何时刻都不会因为缺少历史根基而感到窘迫。它的志向反而在于突显原始性和自发性,发端于《圣经》或通过《圣经》而得神谕……教会的历史沿革,对于教派而言是无足轻重的。
有鉴于此,尤为重要的是,维系大多数教派的纽带不再是承自传统的忏悔——意即不再是信奉教义的历史体系——而是或多或少经过了重构和新建的目标与动机。既然教派间只需在忏悔上保留微弱的同一性,对神学问题的理性讨论——这是昔日教会智识研究的源泉——便逐渐被视为岔路、分裂之势,尽管未遭彻底摒弃,也已让步于那些被认为重要得多的实用目的。(5)若某一教派的特定观点和实践无利于大众的福祉或共同的愿景,它们投效于这一愿景也并无过多的遗憾。(6)这一愿景本身是由福音主义界定的。在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有那么多尚无教会庇佑之人等待着信仰叩门,教派凌驾于一切其它目标和追求之上的根本目的就是赢得民众的皈依。
教派试图争取那些不论何故未能被传统宗教维系,远离了礼拜形式和教义精要的民众。这些形式和教义已不可能有吸引力赢回民众的效忠。更有效的似乎是重建信仰发轫之时,首批基督教易帜者宣扬的那种原始的情感张力。在传统派兵败之处,奋兴派攻城略地。情感的激荡取代了宗教建制的高压。普通人借助简单的思想重拾信仰,强大的传教士们在播扬这些思想之时有能力剔除繁复,以至臻精义取而代之——是选择天堂,还是选择地狱。救赎也被视为一种选择:罪人应该“找到宗教”——而非宗教找到他。任何能引导他回归正途的方式都是好的。正如孜孜不懈的灵魂拯救者德怀特·慕迪曾经的言论:“只要能将一个人带到主的面前,通过怎样的方式无关紧要。”(7)远在实用主义成为哲学信条之前,是福音派建构了它,尽管是以一种生硬的方式。对于平信徒,宗教的实用性在于归化的体验;对于神职人员,则是激发这种体验的能力。牧师在收获灵魂上的成功,是其所传之道为真理的决定性证据。(8)
教派体系和广布的福音精神,使得教会本身发生变异。教会不论基于何种宗派形制或组织安排,都不同程度地倾向于某种会众制或本地化。本地主义和奋兴主义的合力,极大地加强了异见派和分裂派的实力——只要能保证结果,谁能限制他们呢?平信徒的势力也因此得到加强。牧师无法继续借力强大的中央教会,只得依靠自身的资源维系和会众的关系。他尽可能地谋求和树立权威,然而,美国的生活环境很大程度上偏向平信徒掌权。在南方殖民地,即使是深具教权传统的圣公会也发现,一大部分控制权转到了教区信众手上。美国各地的牧师似乎都在接受平信徒的评判,在某种意义上也为其所用。甚至在18世纪,克雷夫科尔就曾评论一位荷兰籍信徒的态度,后者“认为牧师不过是受雇之人;假如工作出色,就按约付酬;不然就将其解雇,没有他的布道完全可行,就让他的处所关上个几年吧”(9)。
相应地,牧师们再也无法像在旧世界那样仰仗教会的教权和自身的职权;他们中最成功之人,逐渐成为教会事务中长袖善舞的政客,对世俗事务的操控艺术了如指掌。此外,同时通晓宗教和治国方略的牧师获得优待,他们的目标是改造国家,为基督教争夺西部的地盘。致力于这些使命的社会机构,勃兴于1800年至1850年间,一名牧师抱怨道:“对牧师的期望,通常主要是成为社会事务的管理人、慈善机构的幕后操纵者”,对他品行的评断,常是基于“他在社会改革的大磨坊之中,完成了多少切实可见的研磨工作……”(10)结果即如同西德尼·米德所指出的:“牧师之职,实际上已失去了传统的牧道内涵,成为神圣化的公职,以神之名,从事的却是公众视野下有目的的教会活动。”(11)
最后,对牧师事工的评判越来越依凭某个单一层面的成功——救灵的具体数量。对本地牧师的判断标准,一为个人魅力,二为是否有能力引导会众接纳某位巡回布道大师的可以真正唤醒他们的牧道。(12)“造星”系统是先在宗教里普及,而后才进入剧院的。当福音精神广为蔓延并占据主流,牧师的甄选和培养越发取决于奋兴主义者对牧师之所长的评判标准。福音派理想中的牧师应是受人欢迎的十字军和劝诫者,因而以学养深厚的牧师为领袖的清教理想逐渐走向衰落。神学教育本身变得更工具化。简洁的教条形式就已足够。在与世俗社会的智识交流上,教会大规模撤退,舍弃了宗教是整个智识经历的一部分这样的观点,也几乎摒弃了理性研究,视之为本该由科学涉足的范畴。1853年,让一名杰出的牧师愤然的是存在着一种“近乎普遍的印象,即智识丰厚的牧师不够虔诚,而高度虔诚的牧师智才不足”。(13)
事关美国宗教,上述这些泛泛之谈总是有一定风险,原因是存在着地区差异化和宗教实务的多元化。然而,我认为,它们能大略阐明美国教派化宗教的普遍形式,以及福音主义的突出效应。诚然,一些重要的保守教会几乎没有或完全未受福音派影响,例如罗马天主教会和路德会,它们仅在外围受到福音主义的波及;其它如美国圣公会,在不同地点受影响程度不一;而诸如长老会和公理会,则因福音主义运动而自内分裂。
美国革命终结之际的美国社会大部分落脚于阿勒格尼东部地区,而1850年的美国社会疆域大增,教派化模式基本定型。两相比较,福音主义的拥护者此间的收获令人印象深刻。美国革命尾声之时,三支最强大的教派分别是圣公会、长老会和公理会,其中两支建于他处,另一支在美国有着深厚传承。至1850年时,改变是惊人的。其时,罗马天主教成为最大的单一教派。新教团体中排在前二的是曾经不过为异见派系的卫理公会和浸礼会。其后依次是长老会、公理会和路德会。美国圣公会降到了第八位——彰显其作为上层阶级的保守教会,在美国这样的环境下无力自持。(14)
不论是在新开拓的西部乡野,还是发展中的城市,成功保有和发展了基督新教的大体是流行的福音主义教派而非礼拜式教会。卫理公会和浸礼会的大规模开疆拓土,证明它们有能力适应美国的生活环境。福音派大幅超越公理会和长老会一类的教派,也是福音主义思潮改化旧宗教架构之势的铁证。
播扬新教的主要载体是福音派人士,宗教奋兴是最顶级的技巧。18世纪末至19世纪,奋兴运动的浪潮先后席卷了全国各地。第一波大约出现在1795年至1835年,在新西部的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尤为强势,之后蔓延到西纽约州和中西部各州。它方兴未艾,新的一波于1840年前后又一次席卷了城镇,昭示了(这是德怀特·慕迪、比利·桑戴和葛培理等奋兴派的理解)奋兴主义并不仅是一个农村现象。奋兴运动在动荡的1857年到1858年间达到鼎盛,奋兴精神势如破竹地影响了纽约、波士顿、费城、辛辛那提、匹兹堡、罗切斯特、宾汉姆顿、福尔里弗和一系列更小规模的城镇。(15)
奋兴运动并非唯一的途径。跨入新世纪30年之后,福音派创建了一系列信仰学会、《圣经》与经册学会、教育学会、主日学校联合会和戒规组织,其中大多数是跨教派的协作。这些机构为十字军征伐做准备,首要目标是让密西西比河谷地区的人民归信基督,将其从宗教漠然、不忠或罗马天主教的思想中拯救出来;终极目标则是改化所有美国人,进而切实地改化全世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志向使得教派间的歧见让位于怀疑论、被动性和罗马天主教教义(16)这样的公敌。每每教派之间不合作,布善团体为追求共同目标的个人提供了发挥的空间,也让言之凿凿的平信徒有机会主导那些牧师们感到勉为其难的联合善举。福音主义团体在1795年至1835年奋兴运动高潮的大部分时间内保持了合作。然而,至1837年前后,协作之势渐颓,部分是受制于卷土重来的派系之争和内部分歧,部分原因则是福音宗教的征伐已实现了它的主要目标。(17)
按照任何合理的衡量标准,成功都是铁一般的事实。数据显示,这场处境艰难的改宗运动成就斐然。18世纪中叶的基督教世界里,美国是信众人数比例最低的国家。尽管美国宗教数据的不靠谱众所周知,但据估计,1800年每15个美国人中有1名教徒,到了1850年,每7人中就有1个。1855年,2700多万人口中有超过400万名教徒。对知晓绝大部分民众都是教徒的20世纪美国人而言,这些数据也许无足轻重。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现下常是意味索然的教徒身份,在当时是一件更严肃和更高要求的事情,所有福音主义派系都要求归化的个人体验以及颇为严格的宗教戒律。上教堂的人比教徒数量更多——至少我们可以依据1860年的记录判断,当时的人口为3100万,而教堂的座椅就有2600万之多。(18)所有的教派中,成就最为卓著的是卫理公会和浸礼会,两者在新教团体中几乎占了70%。
随着福音派思潮向西蔓延,之后进入发展中的城市,愈见清晰的是美国的宗教远征主要掌握在三大教派之手,即卫理公会、浸礼会和长老会。审视这些教派,有助于解读美国大陆的福音主义文化。
在福音派团体中,展露出最强智识倾向的是长老会,它将新英格兰公理会和殖民地长老会的思想传统不断向西推进。在1801年的联合计划之下,长老会和公理会的协作方式使得公理会在新英格兰以外几乎失去了身份标识。联合计划的基础,是两者从加尔文主义衍生出的共同的神学理念,马萨诸塞地区以外的大多数公理会教徒,对长老会的教会组织并无强烈抵触,这样一来,位于纽约州和中西部地区的公理会组织逐步被纳入了长老会。公理会则向中西部地区的长老会贡献了其独特的文化火种及浓郁的新英格兰特色。
长老会教徒通常是狂热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吸引了进取之士和商人阶级,成为非传统教派里的精英教会。(19)长老会尤其关注发展针对性的高等教育,为教派的志业服务。但他们逐渐被自身对教条的热情所累,进而走向分裂。在公理会的盟友和新纳成员的巨大影响下,一部分长老会人士开始宣传新海芬神学,它是高度自由化的加尔文主义,将神的荣耀带来的希望赋予更多的人,更契合福音奋兴的精神和行止。严谨保守的旧加尔文派,承袭了苏格兰和苏格兰—爱尔兰传统,受普林斯顿学院和神学院栽培,无法接受新派的思想。1828至1837年,教会被纷争和异端之说搅得鸡犬不宁。受到异端指控的包括阿尔伯特·巴恩斯、莱曼·比彻、阿萨·马汉以及莱曼·比彻之子爱德华等长老会福音派领袖。终于在1837年,旧派驱逐了新派,全国的长老会辖区和教会会议不得不各自站队,依附其中一支。除了神学理念上的分歧,旧派认为新派过于包容教派间的传教组织,反对新派里身居高位的废除主义的支持者和煽动者。耶鲁、欧柏林学院和辛辛那提的莱恩神学院,是新派福音主义的主要智识中心。其重要角色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是继爱德华兹和怀特菲尔德之后、德怀特·慕迪之前,美国最杰出的奋兴运动人士。
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的例子,有助于拨开围绕着所谓“长老—公理派”福音主义的迷雾,也能说明对于宗教反智主义,即使是笼统分类都是一项难题。芬尼与他的同侪继承了新英格兰的学统,极为关注教育的发展和持续性。欧柏林和卡尔顿学院是建国之初美国学府的优良传承,足以证明这些传统具有深厚而持久的活力。芬尼、阿萨·马汉和莱曼·比彻这样的博学睿智之人,在其它福音派团体并不多见;自内战以来,又有多少福音运动家能写出可与芬尼的《回忆录》相媲美的自传。这些人的头脑在对加尔文主义和新加尔文主义神学的诛伐中得到磨砺,从不断雕琢自己的神学架构中得到规范。然而,他们的文化素养是极为狭隘的,对于学习的观点目的性极强,他们逐渐缩减而非拓展了所承袭的学养。
我们必须将芬尼视作一位伟人,即使如今只有那些对美国宗教或社会史兴致浓厚之人才会记住他。作为一个受西进运动影响的康涅狄格家庭的后代,他先后在纽约州中部的奥奈达县和安大略湖畔度过了童年。在新泽西州短暂的教学生涯之后,他在一个离尤蒂卡不远的小镇取得了律师资格。他的归信发生在29岁那一年。按他自己的叙述,当时他在一间昏黑的律师办公室里为找寻心灵指引而祈祷,“接受了来自圣灵的强有力的洗礼”,在之后的人生里,他还有过数次这样的神秘邂逅。第二天早上,他告诉一位客户:“我收取了主耶稣的定金,要为他的旨意申诉,所以我不能再为你申诉了。”(20)自那时起,他完全归属了教会。1824年,长老会授予他圣职,1825到1835年,他发起一系列奋兴运动,从同代的福音布道家之中脱颖而出,奠定了作为美国宗教史上最杰出人物之一的地位。
芬尼天生一副大嗓门,在讲坛上极富表演天分,然而他最有力的形象资本是他炯炯有神的、热切的、放电的、先知般的双眼——大约除了约翰·卡尔霍恩以外,这是19世纪美国人的肖像画廊里最令人无法忘怀的眼睛。他的布道时而理性时而感性,时而苛责时而温柔,在信众之中产生了无可比拟的效应。“我主令我用美妙无比的方式释放他们,”关于他早期最成功的奋兴活动,他如此写道,“会众纷纷从椅子上向四周滑落,呼唤主的怜悯……几乎所有人都跪在那里或是俯伏在地。”(21)
在芬尼的神学体系里,他是自我塑造而成,是具有个人主义精神的乡村思想家,正是这类独立的个体让托克维尔相信,美国人可以为追求尚未求证的思想而拼尽全力。作为长老派教会的候选人,他婉拒了一些热切的牧师派他去普林斯顿学习神学的邀请。“我直白地告诉他们,我不会让自己经历他们受到的那些影响;我确信,他们受到了错误的教育,不是我理想中的基督传教士该有的样子。”他是神学理论的新手,但拒绝接受不符合自己观点的指示或纠正。“除了《圣经》,我未曾读过有关这个主题的任何书籍;我对它的解读方式类似于阅读法律书籍。”他反复表示:“我完全无法接受基于权威的教条……除了《圣经》以及我头脑中的理念和思路,我没有任何其它的途径……”(22)
从法律到讲坛,芬尼引入了旧清教徒式的理性和说服力(他曾说,面对教众就如同面对陪审团),在面对高学历的中产阶级会众时尤其如此。即便他这般富有感染力,但很快就有一些福音派同僚认为他过于理性,并在1830年警告他,友人们正质疑他“是否有变成一个知识分子的危险”。(23)然而,芬尼却自豪于自己能根据受众的感知调整传教风格,在小乡村里,他强调情感,而在类似罗切斯特这样更为世俗化的西部市镇,他会添加一些理性劝导的语气。“我的布道改化了大批法官、律师和其它受过教育的人。”(24)
无论如何,芬尼毫无变成一个“知识分子”的危险。大抵说来,芬尼在传教方式和对教会的观念上顺应奋兴派传统。他不欣赏无知的布道,但享受赢得灵魂的结果而不论过程;他鄙夷文字布道,因其缺乏自发性;他将世俗文化看作救赎的潜在威胁。
对于神学教育或是他眼中有教养的牧师的传教方式,芬尼嗤之以鼻。他表示,自己并未享受过“高等教育的优势”,强烈体认到教会视其为外行,别人对他的观感是他不够高尚。他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已知晓,很多人会认为,“如果我在教会中获得成功,会让神学教育陷入争议”。有了讲道的经验之后,他开始相信“学校正在大面积地教坏神职人员”,他们接受了大量的《圣经》导读和神学理论,却不知该如何运用。实践高于一切,“除非通过传教本身,否则无人能学会传教”。学校教育出来的传教士所讲的道,“降格为文艺论文……朗读优美的文艺论文不是布道。它满足了文艺的口味,但并无精神上的开导”(25)。
芬尼反对一切文学和非文学的优雅。不论是衣着、居家装饰,抑或是生活格调和方式,对其而言都等同于吸烟、酗酒、玩牌和看戏之类的堕落嗜好。至于文学,“我难以相信,一个知晓了上帝之爱的人,还能够享受一本通俗小说”。“让我看看你的房间、起居室或任何你用来藏书的地方,”他威胁道,“这里有什么?拜伦、斯科特、莎士比亚,还有一群不务正业和亵渎上帝的人。”甚至连牧师通常必须掌握的古典语言,其益处也值得怀疑。东部地区的学院里,学生要耗上“4年……学习古典学科,那里面没有上帝”。毕业后,这些“学成之人也许通晓hic、haec、hoc,也许会嘲笑一个卑微的基督徒愚昧无知,哪怕此人要比500个这样的学生更懂得如何赢得更多的灵魂”(26)。芬尼让虔诚和智识陷入公开敌对,他发现,年轻的牧师“离开学院之后,心灵和校园的围墙一样坚硬”。“学院式教育”的问题是,试图“赋予年轻人智识优势,却几乎完全忽视了道德情感的培养”。“这是一场智识的比拼。一切的兴奋和热情都因智识而起。年轻人……失去了坚固的精神支撑……他们的智才提升了,心灵却陷入了匮乏。”(27)
芬尼对美国神学教育的描述正确与否难以评断,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的感受代表了广大福音派的观点。不论初出茅庐的牧师们处于怎样活跃的智识状态,他都持反对意见。
我之所以对芬尼如此长篇大论,是因为他是长老—公理派福音运动的代表人物——既非最开化的,亦非最不经雕琢的传教者。福音主义的诉求、探索全新的宗教风格以惠泽民众和救灵所带来的影响,是长老会和公理会强大的智识及教育传统的式微。有意思的是,卫理公会的历史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作为最大的教会组织,卫理公会改化蒙昧的美国人的成效大大超越了长老会。美国的卫理公会在发轫之初并无智识传统,对教育和神职人员的培养不甚在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教派精神的大量丧失令教会停滞不前;他们吸纳的成员对教育的重视与日俱增。19世纪中叶以前,教会在争端中风雨飘摇,一部分人怀念昔日那些无知却有效的巡回传教士,另一部分人则向往未来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牧师向受人尊敬的普通信徒履行神职。卫理公会和浸礼会的历史,是分裂的美国宗教之魂的示范。一方面,教会的众多成员毫无保留地表达高度反智的福音主义,另一方面,在任何大型教会里,总有一批人会为尊重有涵养的、锦上添花的、不具争议的学习过程而大声疾呼。有鉴于此,菲利普·拉夫关于美国文学特征的红脸和白脸说(28),早已在美国宗教里有迹可循。
约翰·卫斯理是在牛津受教育的牧师、一位如饥似渴的读书人,非凡的智识热情和强烈的信任感在他身上奇异地交融。他为卫理公会设立了可靠的智识标准,但他的美国信徒们对维持这些标准兴味索然。福音精神的本质无疑催生了奋兴派的反智主义,然而,美国的社会条件为躁动的反智思想提供了格外宽松的生存环境。(29)
美国卫理公会的首任发起人是卫斯理本人和弗朗西斯·阿斯伯里,他们是巡回传教士——巡回并非图之方便,而是原则使然。他们相信,驻区牧师(正如英国的许多教区牧师)会逐渐丧失活力,无法把控会众,而巡回传教士可以让宗教重获新生。在美国的土地上,巡回传教是卫理公会的一项战略资本,他们尤其擅长说服迁徙中的美国民众重新归信基督教。那些著名的巡回传教士是早期美国卫理公会的支柱和骄傲,他们的流动性、灵活性、勇气、勤奋和奉献,弥补了他们身上可能缺乏的神学教育和贵气。这些传教士自豪于为传递福音而做出牺牲。他们酬劳微薄,超负荷工作,在极端天气和恶劣的旅行条件下毫不懈怠。(当特别猛烈的暴风雨来临,人们常说的是:“今晚外头一个人也没有,除了乌鸦和卫理公会的传教士。”)这样的艰辛足以证明他们的诚心,(30)他们劝服民众归信的成就令人叹服。正是因为他们的投入,1775年的美国卫理公会还只是一个近3000人的小宗派,在阿斯伯里到来4年之后,成长为最大的新教派系,80年后,成员超过150万人。
不论尊贵教派的高学历神职人员如何言说,巡回传教士们明白,他们的方式奏效了。他们催生出一种纯粹的、虔敬的实用主义,核心信条只有一个:尽可能更快更多地救灵。出于这一目的,高学养的教会那一套繁杂的神学工具不仅可以忽略不计,甚至很可能成为严重的阻碍。至于知识和思想储备的局限,巡回传教士们只需一条正当理由,那就是以结果论之,可用归信的人数来衡量。这样的理由无可辩驳。
卫理公会的领袖们知道,正如批评者所观察到的,他们对穷苦和未开化的民众最富吸引力,并视之为一项优势。弗朗西斯·阿斯伯里被耶鲁的学生冒犯,因为他们“太有教养”,连贵格派都过于“尊贵”了——“啊,这个词有死亡的意味”。(31)在广袤的乡野,卫理公会很容易在改化的竞争中超越其它教派。关键在于,新英格兰地区对他们而言如同坚冰,那里的居民更稳定,也更熟知高学养教会的规范,那是他们鲜少涉足的地域。然而,即使在那里,卫理公会也在19世纪初期开始进入宗教生活。最初,他们举起的旗帜颇有新英格兰觉醒运动的怀旧意味:“我们更关心的始终是如何保有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博学的教会。”(32)当新英格兰卫理公会领袖杰斯·李的教育程度受到质疑(卫理公会在当地和高学历牧师竞争,这样的情形司空见惯),他轻描淡写地回答,自己的教育足以在国内行走。(33)新英格兰地区逐渐成为考验卫理公会适应能力的场地,他们不甘示弱。他们逐步接纳了尊贵、涵养和博学,为未来在别处适度调整步伐做好了准备。
例如,1800年的一本小册子这样描述康涅狄格州诺威奇的卫理公会:他们是“最羸弱、蒙昧、无知和卑微的一群人”。(34)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一名公理会教徒回忆附近的里奇菲尔德的卫理公会历经的改变,他的说辞也许在更广的地区同样适用:(35)
虽然它的兴盛似乎依靠的是社会的弃子——如今,那里的人和这里任何一个宗教组织一样受人尊敬。他们敬拜的地点不再是谷仓、校舍或者临时场地;他们不再面黄肌瘦、蓬头垢面;也不再坚持错误的语法、低俗的语言、布道时用鼻子发出谐音……传教士是有教养、文雅和尊贵的人。
当卫理公会向全国挺进,沿着国境线进入南方,在对教育水平无甚要求的社会环境下,原本对尊贵、学养和地位的藐视不断重新自我强化,这一过程的实现,再次迫使它向入侵的尊贵势力发起对抗。在一个去集中化的教会里,本地教区在树立自身特色上往往较为自由。然而,对于卫理公会这样高度集中的教会,有关教派文化基调的争议更具有同一性。通过它的学术媒介之一——《卫理公会杂志和季度评论》(The Methodist Magazine and Quarterly Review),以及在1841年之后得名的续刊《卫理公会季度评论》(The Methodist Quarterly Review),我们得以追踪教会内部不断变化的观点。1830年代初,卫理公会显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传统建制下的宗教团体攻伐的对象;他们的焦虑源于两方的分歧:一方是支持巡回传教士所代表的布道方式的人,另一方是呼吁改革的平信徒和高学历牧师。(36)1834年,罗伊·桑德兰牧师的文章将争议推向了高潮,他建议削减巡回传教士的存在,所有卫理公会传教士都应受过良好的教育。“卫理公会是否,”他热切地诘问道:
在任意一个成员机构内有过这样的做法,让我们可以认为,传递福音之人在取得资格之前,必须要接受某种形式的教育?完全没有。大多数的规定难道不是赤裸裸地给人一种印象即教育并非必需?难道我们没有经常在……集会上说,只要有天赋、恩典和理解能力就足够了?
一名旧派的代表回应桑德兰:主张全面神学教育的人,错在把布道当成了“一种‘行当’,一项交易,一个世俗的职业,就像‘法律或医疗’,才会需要类似的‘培训’”。当下的教会,实际并非蒙昧无知,这些言辞只是“应和了敌人的言论”。卫理公会难道没有开设自己的学校、学院甚至大学吗?“我们的年轻人可以接受教育,但不会因为教师的腐败和不忠而让道德涉险,也不会因为教授或校长的讥讽而泯灭了卫理公会的思想。”(37)随着时间的推移,刊物本身就折射出改革派之于守旧派的胜果。曾经长期占据大量篇幅的老派巡回传教士的回忆文章逐渐减少,而以基本神学理论为主题及符合普遍兴趣的智识话题与日俱增。
事实上,在1830年代到1840年代期间,教会正酝酿着巨大的变革。对被尊崇感的热切追求大幅战胜了前辈们巡回传教、反对智识的传统。针对平信徒和教牧人员的教育大计再度成为焦点。早期的卫理公会在教育上的付出,总体上令人颇为汗颜。(38)最初,教会在教育上的投入不仅受制于人员稀少,也因为下至最低级别的平信徒,上至阿斯伯里自己,都对此兴趣奇缺。(39)大多数卫理公会平信徒本就负担不起太多的教育,对于一个只需向简单的人群传播简单的福音的教会而言,神学教育貌似是在浪费时间。
这些早期的学府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即使兴办起来也极易失败。然而,在1816年阿斯伯里去世之后,一群主要来自新英格兰的意志坚定的教育改革者开始在人数激增、接受度提高的平信徒身上下功夫。到1820年代后期,他们的努力初见成效,卫理公会赞助了数个研究院和口碑良好的小型学院。康涅狄格州卫斯理学院于1831年成立,紧随其后的是迪金森学院(1833年从长老会手中接管)、阿勒格尼学院(1833)、印第安纳州阿斯伯里学院(1833年建立、迪堡大学的前身)以及俄亥俄州卫斯理学院(1842),这只是其中最为杰出的几所。自1835到1860年,教会创办了超过200所院校。和以往一样,很多学校的支持和维护工作依然捉襟见肘。按照卫理公会的普遍观点,教育无疑只是一种工具——然而在那个年代,学习连成为宗教工具的价值都没有——这已然代表了一种进步。一些教会领导人向往高学历的牧师团体,他们越来越需要为自己的神学立场辩护,以应付愈发细致的批评(40),这一切最终打破了卫理公会对高学养教会的顾虑。神学院依然被疑为异端邪说的源泉,因而最早的两所卫理公会神学院是以“圣经研究院”的名义创办的。领导班子依旧来自新英格兰——在那里,卫理公会并非最强大或人数最多,但教育水平的竞争最为激烈。(41)
新模式下的教会拥有众多研究所、学院、神学院和杂志,守旧派始终无法与其和睦共处。赫赫有名的巡回传教士彼得·卡特赖特在1856年写就的非凡自传中,有一段老派福音主义者对于教会的全面且直白的观点陈述,完美地体现了反智主义立场,值得在此大段引用。(42)
假如当年卫斯理先生不得不等待他的牧师团开蒙受训之后才投身于荣耀的事工,那今天卫理公会在卫斯理宗的连接中将是什么?……假如阿斯伯里主教也选择等待高学历牧师团的出现,那么美国将遍地都是背信弃义之人……
长老派和其他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分支争论不休的是,高学养教会、教堂座椅、礼拜音乐、领俸禄的教会究竟公治抑或州治。卫理公会一致反对这些观点;没有文化的卫理公会传教士,实际上用他们的星星之火点燃了全世界(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我并不贬低教育,然而我见过太多高学历的牧师,他们迫使我联想起桃子树荫下长出来的莴苣和迈着步子蹚水的小鹅,令我恶心和眩晕。高学养教会和神学教育不再是一项试验,其它教派早已有过尝试,证明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我为我深爱的卫理公会感到极度担忧。学院、大学、神学院和研究所,还有代理机构、编辑职位也越设越多,让最能干、最高效的牧师为之服务,教会本地化的同时也世俗化了,于是,我们与巡回传教告别。一旦行不通,我们就会一头扎进公理制,回到所有其它教派的起点……
我们如此缺乏普通事工的牧师,难道不就是因为这些代理和职业机构雇用了太多牧师吗?再有,这些校长、教授、代理人和编辑报酬更高,收入也更稳定,而风雨兼程的巡回传教士却收入微薄,经常入不敷出。办公室工作是巨大的诱惑,有资格的人选会因此放弃宣教和救灵……
投身于荣耀的救灵大业、振兴卫理公会的成千上万巡回传教士和教区牧师,其中受过普通英语教育的也许不足50人,多数人连这样的教育也没有,没有一个人上过神学院或是圣经研究院。但其中数以千计的人,他们传播福音的功绩以及对教会的忠诚远超当今一切自以为是的唯唯诺诺的神学博士。后者本该手拿镰刀迈入宽广的心灵沃土,实际却在谋求校长、教授、编辑或任何机构里的高薪职位。他们试图创造出新奇的机构,独享美好生活,而与此同时,在通往地狱的路上却挤满了成千上万贫苦的、处在死亡边缘的罪人,这些人错过了上帝,错过了福音……
我不会委屈自己就此打住,然后说我对学习或者一个进步的教会的态度是友好的。不然就是随意弃掷一条不移之论,让那些博学又有涵养的牧师们有机会说,所有反对我们眼下施行崇高使命的人都是无知论者,以为无知是信仰之母。高学养教会把神学当成一门科学来学习,他们为世界做了什么?看一看教会的历史吧。激发内心的自豪感轻而易举,这种教育的自豪感给众多高学历的福音牧师带来的是挫折与毁灭。但我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感谢教育为上帝所赐,教养出行正路的、胸怀信义的福音牧师。但是,那些高学养教会的拥护者如何能确切知道那么多接受普通教育的牧师,对于我们经常实施的教导,内心作何感受?我们中间许多支持教育和教会进步的人,在言及早年开疆拓土之时创立卫理公会和教会的那些目不识丁的先辈时,满口溢美之词;然而,我不会因为这些嘴巴抹了蜜的唯唯诺诺的神学博士虚情假意的让步而沾沾自喜;假如言能尽意,他们的真实感受应该是,我们的成就归功于民众的无知。
毋庸置疑,这正是一些巡回传教的批评者想要表达的感受;而卡特赖特很可能愿意承认,他们确实言之有理。他的福音派同侪也未必会一致辩驳。正如一群福音派人士多年前对芬尼所言:“高学历的人头脑开化,更易持怀疑态度,面向他们的事工比未教化之人要困难得多。”(43)
在诸多方面,浸礼会的历史就是卫理公会的缩影,只是浸礼会更加去集中化、更不愿妥协,也更倾向于坚持神职人员不需要学历甚至不必支薪。因而相比卫理公会,他们对变化的顺应来得更迟,程度更低。正如威廉·沃伦·斯维特的观察:“对于高学养的支薪教会,浸礼会的偏见之强烈是其它宗教组织所无可比拟的。19世纪初,这一偏见不仅在边境的浸礼会里广泛存在,而且几乎遍布整个教派。”(44)
诚然,高学历牧师和教会旧制曾让浸礼会饱经苦厄,他们在公理会的马萨诸塞州和圣公会的弗吉尼亚州遭到过残酷迫害。他们的特点是,只让自己人加入教会。浸礼会牧师和普通平信徒一样,可能是在田里耕作的农民或在条凳上做工的木匠,只有在主日和平日的布道、施洗及葬礼时才停止劳作。他们几乎没有时间阅读书籍。这些勤奋的公民不乐于和其他传教士竞争,对那些试图与之联合、共同向内地宣教的本地传教士组织表现出极端的反感。他们劝导信众共同抵制“外来”的干涉和中央控制。据传,浸礼会联合会不欢迎任何与传教士组织有关联的人物加入。肯塔基州某浸礼会联合会表示:“我们的团契不接受任何参加非正统组织的堂会或教众。”伊利诺伊州某社团在质疑权威上的表现近乎偏执,它在通告中宣称:“我们再次向各堂提出,不要和‘圣经社团’有任何联系,我们认为,把诠释《圣经》的权力交予一些狡诈之人是十分危险的。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45)我们难免疑惑《圣经》是否由全国性集会来解读,但要知道,早年的迫害和被残酷耻笑的记忆,让浸礼会的顾忌久难止息。(46)
浸礼会抵制布道宣教,很大程度上因着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对中央教会机构的任何让步,都让他们感到离“罗马教皇和淫妇之母”更近了一步。未经教化且不领薪水的牧师,难免会抗拒教养更好、薪水更丰的教会的侵蚀。不计报酬的传道者容易相信,来自东部的高学历牧师都是为金钱而传教。(47)一位当时的观察家总结道,这些未受过教育的传道者对自身的局限一清二楚。然而,“他们并不因上帝赐予他们更好的传递信仰的才能而喜悦,反而因自尊受创而愤然,褊狭和脆弱的心灵一贯如此”。一位牧职领袖指出,毕竟没有人会被迫聆听传道或支付报酬,除非出于自愿。对此,一位浸礼会牧师赤裸裸的辩驳,印证了上述论断:“好吧,教会弟兄,你需要知道,森林里的小树总是被大树遮蔽;这些传教士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人们都会去听他们讲道,而我们就会被冷落。这是我们所抗议的。”(48)
然而,浸礼会和卫理公会的守旧派一样,无法顶住教会需要接受教育的压力。这是出于对自尊和被尊敬的双重渴望。早在1789年,一个弗吉尼亚州的浸礼会联合会在寻求创办神学院时给出的理由如下:(49)
其它教派的弟兄再也不能讥讽我们不懂戒规,我们的牧道不会再因为我们不懂母语或古典语言而遭到抹杀或非难。假如我们的眼中只有主的荣耀(我们所做的一切皆应如此)且依照主的旨意行进,那么就有足够的希望获得主的赞许。
追求受尊敬抑或追求随性且不昂贵的教会,使浸礼会平信徒两级分化。到1830年,浸礼会领袖们在建设有文化、有薪俸的教会方面收获颇丰,平信徒的教育水平也有所提高。然而,浸礼会在扭转最初的偏见上进展缓慢,仍不断在奋兴主义的笼罩之下挣扎。(50)
内战后,教会的地位在结构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向崛起中的城市人口宣教变得愈发紧迫,也愈加困难,原因是教会必须找到契合城市人情感需求的方式,适应贫困者的生存状态,还要顾及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早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城市奋兴主义者就已跃跃欲试,现在更是急不可耐。从慕迪到葛培理,在大城市——在全球范围内亦然——改化的成果是对福音主义重要性的终极考验。影响力囿于农村和小镇的劝诫者,最多只能算三流而已。
慕迪是介于芬尼和比利·桑戴之间的最显要的人物。他是马萨诸塞州诺斯菲尔德一位贫苦泥水匠之子,早年丧父,18岁时受公理会一名巡回福音牧师感召而归信。内战前十年间,二十出头的慕迪已经在城市里从事宗教慈善活动。作为芝加哥一名成功的鞋类批发商,他在1860年毅然弃商投入独立事工。战时,他活跃于基督教青年会,战争刚结束就成为芝加哥分支的主席。他13岁辍学,一生从未领受圣职成为牧师。
1873年前,慕迪的主要成就是基督教青年会和主日学校的事工,尽管他曾两度前往英国考察那里基督教领袖的做法,展现出勃勃的雄心与好奇心。1873年,受英国友人之邀,他在当地主持了一系列福音团契,并因此锋芒初露。1873年夏,他带着风琴手和演唱者伊拉·D.桑基开始了为期两年的系列集会,足迹遍布约克、爱丁堡、格拉斯哥、贝尔法斯特、都柏林、曼彻斯特、谢菲尔德、伯明翰、利物浦和伦敦。据估计,在伦敦一地就有超过250万人聆听了慕迪的牧道。自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之后,英国已久未出现过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布道。他离开美国之际尚默默无闻,回国时已家喻户晓;自1875年起至1899年离世,他不仅是毫无争议的美国新一代福音运动主将,也成为美国新教里最伟大的人物。
慕迪与芬尼全然不同。芬尼加诸听众的,是一种近乎恐吓的压倒性力量,而慕迪温和又招人爱戴,乐于宣扬天国的恩典而非警示地狱的折磨。他酷肖格兰特将军,略微发福的五短身材,满脸络腮胡——这种相似不仅在外形上——慕迪的个性简单,但意志超然。在他感化灵魂的过程中,展现出了类似维克斯堡战役的军团一般的决断力。和格兰特一样,他能激发出克服弱点的强大感召力,直至抵抗消退;他的强势隐藏在朴实无华的外表之下。但两者的相似仅止于此。格兰特尽管缺乏自信,但做了该做的事;在战争生涯以前,他的商业之路低迷,战后在政治上亦无起色。而慕迪自信心爆棚,他放弃了蒸蒸日上的财富,投身宗教之时依然十分年轻;在人生需要坚韧、精明、决策、刚毅和人性化的各个层面,几乎未尝败绩。他才疏学浅——连语法都不会,批评家对其布道的指摘经久不减;然而,他懂《圣经》,也懂他的听众。没有哗众取宠,他只是不知疲倦地重复一个让人难以逃避的诘问:“你是基督徒吗?”在令他声名鹊起的大礼堂里,他用响彻全场的声音和不断喷薄而出的话语助人得救。
慕迪的信义是宽泛的,不分教派——了不起的是,他在不同阶段获得了几乎所有教派的认可,罗马天主教、一位论派(Unitarians)和普救派(Universalists)除外(51)——他对正规的神学辩论不屑一顾(“我的神学理念啊!我不知道我还有这个。我希望你来说说,我的神学理念是什么?”)(52)。时下的讯息、文化、科学,对他而言毫无意义,即使偶尔谈及,每每带有其所能及的嘲讽意味。这一方面,他完全因循主流的福音派传统。虽无意破坏传统教会及其教育体系,但他全心支持平信徒事工,认为经神学院教化的牧师“常常和民众渐行渐远”。(53)他鄙夷一切和宗教目的无关的教育——他表示,世俗的教育不是告诉人们他们有多糟,而是奉承他们“因为受了教育,就变得像天使一样。受过教育的流氓,是卑鄙之极的流氓”。除了《圣经》,他几乎从不阅读。“对于书籍,我的原则是,除非它能帮我理解这一本书,其它的我一概不读。”小说?它们“太浮夸……我没有胃口,也毫无兴致,即使有也不会去看”。戏剧?“你们说看好剧是教育的一部分。让那种教育随风而去吧。”文化?就让它“原地待着吧”,在一个人找到救主之前,谈文化就“跟疯了似的”。学习?它是灵性的累赘,“我宁可要无知的热情;没有热情就只是有学问而已”。科学?在慕迪的时代,它已成为对宗教的威胁,而不是发现和荣耀主的方式。“我们更容易相信,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貌创造的,而不是像眼下一些年轻男女被教导的那样,是一只猴子的后代。”(54)
慕迪对智识和文化的态度符合福音派传统,然而,他也标志着奋兴主义历史上一个新的转折——并非在目标或态度上,而是在方法上。乔纳森·爱德华兹和他的同侪一贯将奋兴运动视为神的蒙召。在他的首部伟大作品中,爱德华兹将北安普顿奋兴运动称为“上帝的惊人伟绩”;这里的修辞,彰显出北安普顿传教士的理念——这并不由人的意志左右。我们揣测,作为资深奋兴主义拥趸的怀特菲尔德,对于人的意志所能发挥的作用必然知晓一二。不论如何,普遍接受的理论是,神的旨意是核心推动力,而人的意志则相对被动。至芬尼之时,这样的观点式微,美国福音派传统里的自愿主义特征日渐走强。芬尼坚信:“宗教是人的事工。”他认为,上帝确实将他的旨意降临到人的身上,令其遵从。然而,这样的旨意始终在那里——按当下的用词,它是一个定量,而人的反应则是变量。只有人的意志随之提升,奋兴才会发生。芬尼断言,宗教的奋兴“不是一项奇迹,也完全不依赖奇迹。它纯粹是正确运用既定的方法,从而得到明智的结果”。因而坐等奋兴如奇迹一般卷土重来,是错误的懈怠之举。“你明白为何你无法实现奋兴。这只是因为你不想要。”(55)
芬尼的《宗教奋兴讲座》便是展示何为正确的方法,如何凭借意志催发奋兴。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芬尼所言的方法不只是机械式的,也不只是一些技巧,而是心灵、头脑和意志齐头并进地实现宗教奋兴大业的一系列指引。为了让奋兴主义符合新工业化时代的精神,慕迪那代人走向了拐点。我们不可妄断像慕迪这样强大和诚挚之人内心缺乏必要的动力源泉;但值得重视的是,他添加了一些其它东西——企业组织的方式。芬尼的奋兴运动发轫于安德鲁·杰克逊和莱曼·比彻的时代,而慕迪则属于安德鲁·卡内基和P.T.巴纳姆的时代。
即使经过精心策划,芬尼的奋兴运动也并无太多技术含量。而慕迪引进了一个强有力的机制。(56)本地福音牧师的邀请函由专人提前派送;广告宣传计划涵盖了海报张贴和报纸宣传(刊载在娱乐版上)。若最大的教堂也容纳不下人群,就需要寻找大型讲堂,假如找不到,就临时搭建。临时的场地在事后议价拆零出售。慕迪的波士顿集会场地花费3.2万美元。一个城市的系列集会可能需要3万(纽约)至14万美元(伦敦),为支付庞大的开支而建立了财务委员会,由他们引入本地的企业家资源。然而,慕迪并非只是依靠小企业家。在芝加哥,他得到了塞勒斯·麦考密克和乔治·阿莫的资助;在费城,是杰伊·库克和约翰·沃纳梅克(57);在纽约,则是J.P.摩根和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二世(58)。集会需要当地的引座员管控大批的人流,布道结束之后,助理们通过“咨询”小会跟进归信者的灵性状态。再就是音乐的安排——桑基的演唱和伴奏,招募本地歌唱团加入唱诗班,每个城市从600到1000人不等。如同一切商业活动,慕迪的集会产生的效应也变成衡量的对象。起初,慕迪本人反对估量救灵的数目——他们的说法是,伦敦要3000个,芝加哥要2500个,纽约要3500个——数年后,他启用了“决定卡”(decision cards),系统地记录下进入咨询室之人的姓名和地址。
我们看得出,芬尼对于将某些法律培训用于理性的布道颇为自豪。慕迪也许并未完全意识到,他的布道折射出其早年的商业经历。他的言辞有时恰似一名贩卖救赎的商人。在一个“咨询”小会上,他一边在椅子上坐下,一边问道:“现在谁要接纳基督?这正是你需要的。有了基督,你就拥有永恒的生命和所需的一切。没有他,你会死去。他把自己奉献给了你。谁要接纳他?”(59)这时,他仿佛是在售卖一件商品。你会听到他说:“如果一个人需要一件大衣,他会想买一件尽可能好的,让钱花得值得。这是普世的逻辑。如果告诉人们宗教是最好的东西,我们就会赢得世界。”我们不得不认同加马利尔·布拉德福德的判断,这正是“卖皮鞋的行话”(60)。在这一点上,同时代的人亦作此想。“当他站在讲坛上,”莱曼·阿博特如此形容慕迪,“看起来就像一位商人,穿着打扮也像;他像商人一样操控着整个集会,使用的语言也是商人的风格。”(61)
对于主要的社会矛盾,芬尼至少在有关奴隶制的问题上态度激进,而慕迪一贯是保守的。奋兴主义的后起之秀们体现出福音精神和商业头脑结合的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他的政见和支持他的共和党企业家殊无二致,他也从不吝于表达福音对有产阶级的助益。“我对芝加哥的富人说,假如共产主义和无神论席卷整个美国,他们的钱财就会一文不值。”又说:“芝加哥的资本家最好的投资,就是将福音这把救世的盐,撒入黑暗与绝望的所在……”然而这并不等同于迎合。他的保守源于前千禧年主义的信仰,内心充斥着社会悲观主义。人生来就是彻头彻尾的恶,什么都指望不了。“我不断听到改革、改革,直到厌倦并感到恶心。我们需要的只是圣灵带来的重生的力量。”有鉴于此,慕迪对任何社会话题的讨论都毫无兴致。(62)过去,人类在所有方面始终一事无成。真正的大业,是让尽可能多的灵魂离开世界这条沉船。
在一个重要方面,慕迪时代的奋兴主义比之先行者要求更多的自我控制。旧时奋兴运动的“狂热”表现——尖叫、呻吟、晕厥、咆哮、狂吠——现已无法被接受。这不仅因为虔敬派愈发克制,也因为城市里的奋兴活动媒体环伺,不容许发生会让公众丧失同情心的状况。在乡村教堂和野外集会上失控无伤大雅,但对于礼堂内的大规模奋兴活动,失控的场面是危险的。奋兴运动最睿智的拥护者始终认为,热情的极端表达方式是一种羞耻。尽管芬尼时而会激发这样的表达,但他视之为必要的累赘与邪恶。慕迪则决意将其摒弃,他会中断讲道,要求引座员将某位表现异常的听众带离现场。甚至对过多的“阿门”和“哈利路亚”还会表示:“没关系,朋友们,让我来喊吧。”(63)他的接班人比利·桑戴相信,“个人的归化不用大张旗鼓”,他坚定地把手伸向听众,要求引座员把不守规矩的人请出去。他曾喊道:“这位弟兄,两人不能同时掌舵,让我来吧。”又在另一个场合说过:“等一下,这位姊妹,控制好你的点火器,省点油吧。”(64)某些体统需要保持;风云人物的表演,不能有任何的打搅。
虽然城市福音运动的环境要求听众有所克制,但似乎将传教士释放了出来。对于研究大众情感的历史学家而言,福音主义发展过程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个层面,是布道用语从白话降格为粗俗之语。虔敬主义一贯的思想是,布道应该朴实无华、不为所动、不含学问、不加修饰,如此才能触及并打动头脑简单之人。芬尼的主张是,真正出色的布道如同真正出色的人生,是剥除了优雅和伪装的。他的布道以白话的风格打动人心,他更喜欢即席演讲而非念稿,原因是即兴的表达更直接,更接近于一般的谈话。他表示,当人们充满热情,“他们的语言是贴切、直接而简洁的,句子简短有力,令人信服”。这将促进行为,并产生结果。“这就是为何比起最博闻强识的神学家和教牧者,曾经无知的卫理公会传教士和热忱的浸礼会传教士造成了更大的影响。他们现在依然如此。”(65)
芬尼对白话式布道的推崇令人信服。毕竟,大多数出色的布道都带有白话元素。例如,路德曾以最为直接和亲近的方式,向他的听众描画诞降的情景:(66)
年轻的新嫁娘结婚才一年,不能在拿撒勒自己的家里生产已经够糟了,她怀着身孕,还走了整整三天的路!……还有更可怜的。没人重视这位临产的年轻母亲,没人把她的状况放在心上……在那里她毫无准备:没有光,没有火,在死亡般寂静的夜晚,在深沉的黑暗里……我不禁想,假如约瑟和马利亚意识到那么快就要生产,也许她会被留在拿撒勒……有谁告诉这个可怜的女孩该怎么做?她从未生过孩子。她没被吓坏,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芬尼质朴的表达风格,也许只是继承了最好的清教布道方式。美国传道史上最伟大的形象,无疑是乔纳森·爱德华兹把灵魂描绘成悬挂在厨房炉台上方的一根由上帝掌控的丝线上的一只蜘蛛。白话风格本身不也构成了美国文学的一大原创特色吗?
这些都真实地反映和阐释了芬尼的布道理念。其后的福音派遇到的问题是,在白话风格尚不能表达乃至夸大民众最原始的情感之时,就要将其稳固下来。与芬尼同时代的贾伯斯·斯万,在描述约拿的大鱼时,无疑只是添加了一些生动的口语:(67)
大鱼拍打着水面,吐着泡泡,上下左右地跳跃,想甩掉这个负担。它感到越来越恶心,索性游到岸边,把嘴里令人作呕的东西吐了出来。
虽然慕迪适时引入了也许会让芬尼感到奇怪的厚重的情感基调,但他以每分钟220个词的语速布道,用词口语化却不粗俗。和芬尼一样,慕迪对他所称的“论文式布道”很不耐烦。他说:“试图表现得能言善道是一件愚蠢的事。”(68)他的口语化和随意性,让保守的听众走了神(“谁要是不抓紧跟上,就会对这些集会感到失望”)。伦敦的《星期六评论》认为,他“只是粗鄙的大叫大嚷之人”(69)。但总体上说,他的布道算不上粗俗。同时代的一些年轻人,如山姆·琼斯,言辞更为宽泛和大胆:“在这个地方,有文化的传教士半数是A.B.、Ph.D.、D.D.、LL.D.和A.S.S.。”(70)“谁要是受不了真理来得比以前更多更快,他最好从这里滚出去。”(71)比利·桑戴模仿的口气正是这样的,而不是慕迪的。
比利·桑戴的福音主义生涯自1896年迄至1935年,随着他的到来,福音派的遣词用句跌入了谷底。与之相比,当代的葛培理等人可谓极其适度和收敛。桑戴的生涯在某些方面和慕迪相似。他的父亲是艾奥瓦州一名砖瓦匠,1862年死于联邦部队。桑戴在贫困的乡村度过童年,高中未毕业即辍学,1883年被芝加哥白袜棒球队选中。1883年到1891年,桑戴靠当棒球手谋生。之后,他的人生仿佛是林·拉德纳故事里的人物——狂妄自大至极的外场手归信了宗教,改奉福音主义。和慕迪一样,比利·桑戴也是在基督教青年会展开福音事工的。1886年归信之后,他开始在基督教青年会宣讲,离开棒球队后担任了青年会秘书,1896年开始传道。不同于接受平信徒身份的慕迪,桑戴渴望被授予神职。1903年,他面对芝加哥长老会检查组的考察,在多次回答“对我来说那太深奥了”之后,考察被取消,理由是因桑戴而归信的人数比所有考察官的都多,对于他升入教会一事再无人质询。
1906年后,桑戴离开了令他初尝胜果的中西部小镇,转战中等规模的市镇,直至1909年功成名就,继承了慕迪的衣钵,成为大城市里数一数二的福音布道家。布莱恩、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等政界领袖,或多或少对他表示了支持;商界大亨像对待慕迪一样向他打开金库;文人雅士认为他值得尊敬;数百万人前来聆听他的布道。1914年,《美国杂志》开展“谁是美国最伟大的人?”的民意调查,读者将他排在了第八位,与安德鲁·卡内基并列。表面上,他开展福音事工的方式和慕迪相当类似,但有两处重要的不同。慕迪需要并争取本地牧师的邀请,而桑戴变本加厉,常常威胁不情不愿的牧师,直至他们屈服。慕迪生活无忧但非大富大贵,而桑戴成了百万富翁,对有关布道费用的批评,他回应道:“我得到的报酬是一个灵魂大约2美金,按比例的话,我救灵的所得比现今任何布道家都要低。”这两人都像极了商人,但慕迪的个人享乐仅限于餐桌上,桑戴则在衣着方面极尽奢侈。他穿着领子笔挺的条纹西装,戴着镶钻的袖扣,锃亮的漆皮鞋还有鞋套,看起来像和女孩约会的产品推销员。和慕迪一样,他也有自己的音乐伴奏师,名唤霍默·洛德海沃(72)。桑基的演唱柔美,而洛德海沃始将圣歌爵士化。(73)
芬尼应该会惊叹于桑戴这位奋兴主义者的风格和娱乐元素,后者雇用马戏团的大个子当门卫,肆无忌惮地模仿他的同侪(反对轻浮是芬尼坚守的庄严信条之一),在激动时刻脱去外套和马甲,每每在讲坛上高谈阔论,还会加上灵活的肢体表演。桑戴为善用俚语而骄傲。“我才不管那些肿着眼睛、磨磨唧唧的牧师怎么叨叨,就因为我用的是最简单的盎格鲁—撒克逊词汇?我要让人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我才要深入他们的生活。”他认为,有文化的牧师试图“取悦高雅派,这样一来就会失去群众基础”。慕迪的语言虽然简明扼要,但对桑戴而言太过淡然无味。慕迪曾说:“教会的标准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桑戴则断言:“教会的门槛低到只要有两三套西装和银行存折,任何老鬼都可以爬进来。”慕迪对这样的说法表示满意:“我们无需智识和财力,只要神谕。”桑戴则进一步表示:“如果所有教众都是超级富翁和大学毕业生,那么美国的教会就会干腐而死,下四十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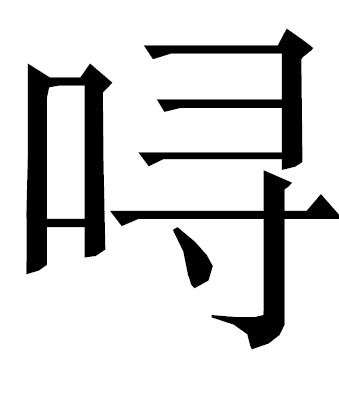 地狱。”(74)
地狱。”(74)
传统的白话布道真实而亲切地布讲《圣经》故事,而桑戴的本领是用时下的市井俚语讲述黑暗和光明。在他的布道里,魔鬼是这样诱惑耶稣的:“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好好地吃一顿吧!弄些货物出来!”他如此讲述面包的神迹:
然而,耶稣四处张望,发现一个小男孩,他母亲给了他五块饼干和一些沙丁鱼当作午餐,于是和他说:“来吧孩子,上帝需要你。”然后他告诉这个小孩他想要什么,男孩说:“耶稣啊,这里没有多少,但你可以尽管拿走。”(https://www.xing528.com)
1920年代,那些被布鲁斯·巴顿的《无人知晓之人》中的粗鄙语言震慑的人,也许尚未意识到,正是桑戴的言辞为巴顿开了先河。后者把基督描绘成实干家:“耶稣经常主动出击,耶稣基督发动起来就像一个六缸引擎,如果你认为他不是这样,那就大错特错了。”他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耶稣“并不是老好人式的存在,而是史上最伟大的斗士”(75)。
(1) 熟悉西德尼·米德有关美国宗教史的杰出论文的读者,应该能在后文中体察到我对他的无比感恩,尤其是他极富洞见的论述,见于“Denominationalism:The Shape of Protestantism in America,” Church History, Vol.XXIII(December, 1954), pp.291-320; “The Rise of the Evangelical Conception of the Ministry in America(1607-1850),”in Richard Niebuhr and Daniel D. Williams, ed.:The Ministr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New York, 1956),pp.207-249。
(2) 有关19世纪美国文学中渴望颠覆过往的启发式探索,参阅R.W.B.Lewis:The American Adam(Chicago,1955)。
(3) “The Position of the Evangelical Party in the Episcopal Church,” Miscellaneous Essays and Reviews(New York, 1855), Vol.I,p.371。这篇论文深刻抨击了宗教形式与福音精神的背道而驰。
(4) John W.Nevin:“The Sect System,”Mercersburg Review,Vol.I(September,1849), pp.499-500.
(5) 这一历史背景,可以进一步诠释维尔·赫伯格所认为的当代美国宗教的一项重大特征——标榜宗教整体的重要性而无视宗教的内涵。(比较一下1952年艾森豪威尔所言:“我们的政府毫无意义,除非它是建立于深厚的宗教信仰之上——我不在乎那是什么。”)这种对信仰的笼统信念,便是几个世纪以来盛行的教派主义的产物之一。参阅Herberg:Protestant, Catholic,Jew(Anchor ed.,New York,1960),chapter 5,尤其是pp.84-90。
(6) 1782年克雷夫科尔就发现,在美国,“派系团体假如并非比邻,假如和其它教派混合,那他们的热情会因缺乏燃料而冷却,很快就尽数熄灭。于是,美国人的宗教将会变得像国家一样,成为大统……所有教派之间和邦联一样互为表里,宗教淡漠感便悄无声息地从大陆一头播散至另一头;这是当下美国人最大的特征之一。无人能预料后果将会如何,也许会留下一个真空,适合接纳其它的体系。世人所称之宗教,赖以生存的是禁锢、宗教自豪感和冲突之爱,这些驱动力在此地都戛然而止。狂热之心在欧洲受到约束,在远涉而来的途中被尽数释放;在那里裹挟起来的粉末,在此地自由的空气里不着痕迹地燃烧殆尽”。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New York, 1957), pp.44,47。当然,1790年以降的数十年间,一些宗教狂热得到复辟,然而,突显不同派系差异化的热情则远未获得同等程度的振兴。
(7) 引自William G.McLoughlin:Billy Sunday Was His Real Name(Chicago, 1955), p.158。诸如华盛顿·格拉登这般更为精明的布道家也表示,自己的神学理念“不得不为了登上每日的讲坛而被精雕细琢,唯一的考验就在于是否具有实用效果:‘它会有用吗?’”Recollections(Boston, 1909), p.163。
(8) Charles G.Finney's Lectures on Revivals of Religion(New York, 1835),其中一个章节的标题是“一名智慧的牧师是成功的”,并引用了箴言XI, 30:“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9) 克雷夫科尔:同前,p.45。这并非意指牧师不受尊重。他们不会因职权而为人所敬,但可以且通常也赢得了尊重。提摩西·德怀特在谈及早期康涅狄格的牧师时说,他们并无官方权威,但很有话语权。“这里的牧师们因品行而受到敬重,与任何外在的原因或自己的职务无关。”Mead:“The Rise of the Evangelical Conception of the Ministry,”p.236。
(10) Andrew P. Peabody:The Work of the Ministry(Boston, 1850), p.7。新教牧师对西部地区基督教化的担忧带有爱国者和政客视角,对此,托克维尔曾表示:“如果和这些基督教文明的传教士对话,你将诧异地听到他们大量谈及俗世事物,你遇到的是一名政客,虽然你期待他是一位牧师。”Democracy in America, ed. By Phillips Bradley(New York, 1945), Vol.I, pp.306-307。
(11) “The Rise of the Evangelical Conception of the Ministry,” p.228.
(12) 对牧师个人魅力的依赖始终是重要的。“个性是真理的标识,”菲利普斯·布鲁克斯如是说,“我们以此来形容真正的布道。”与其同时代的威廉·塔克深表赞同:“一大定律是,传道者的个性越伟大、越有用武之地,人们对真理的反响就越广泛和深刻。”参阅Robert S. Michaelsen:“The Protestant Ministry in America:1850 to the Present,” in Niebuhr and Williams:同前,p.283。
(13) Bela Bates Edwards:“Influence of Eminent Piety on the Intellectual Powers,” Writings(Boston, 1853), Vol.II, pp.497-8。“将智识和心灵剥离、让知识和虔诚对立、为了提升情感而牺牲判断力、广泛制造知识成就和恩典互不相容这种印象,这一切难道不都为我们所擅长吗?”同上,pp.472-473。
(14) 有关各教派的人数、派系分支、神学理念和关联性的出色论述,参见Timothy L. Smith:Revivalism and Social Reform(New York and Nashville, 1958), chapter 1, “The Inner Structure of American Protestantism.”1855年,全部卫理公会团体(包括北部和南部)共计有150万信众;浸礼会有110万;长老会有49万;路德会、德国改革派教会和类似团体共计35万人。公理会约有20万人;美国圣公会只有约10万人。
(15) 我对奋兴主义的观点归功于William G. McLoughlin对整个运动的杰出研究成果,载于Modern Revivalism(New York, 1959);Timothy L. Smith的Revivalism and Social Reform,同前,尤其是1840年后的阶段和城市奋兴运动;Charles A. Johnson的The Frontier Camp Meeting(Dallas, 1955),他对1800至1820年间边疆地区原始状态的描述极具启发性;以及Bernard Weisberger的They Gathered at the River(Boston, 1958)。
(16) Romannism,指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教义,是蔑称,暗讽其带有古罗马气质的制度。——译者
(17) 关于这一时期的协同合作及衰微过程,参阅Charles I. Foster:An Errand of Mercy:The Evangelical United Front, 1790-1837(Chapel Hill, 1960)。
(18) 1800年的大略数据见于Winfred E. Garrison:“Characteristics of American Organized Relig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CCLVI(March, 1948), p.20。1855年和1860年的数据见于Timothy L. Smith:同前,pp.17,20-21。1855年,全部人口中拥有教徒身份的大约占15%,1900年上升到36%,1926年达46%,1958年为63%。Will Herberg:Protestant, Catholic, Jew, pp.47-48。
(19) 新教的一些俗语彰显了不同教派的社会地位,例如:卫理公会教徒是穿着鞋子的浸礼会教徒;长老会教徒是上过大学的卫理公会教徒;美国圣公会教徒是靠投资为生的长老会教徒。
(20) Memoirs(New York, 1876), pp.20,24。Whitney R.Cross:The Burned-Over District(Ithaca, 1950),其中对芬尼和西纽约州宗教热情的阐述很有见地。
(21) Memoirs, pp.100,103.
(22) Memoirs,pp.42,45-46,54。芬尼坚持这份独立,即使知晓自己缺乏独立解读《圣经》的学养。他逐渐习得一些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但“从未掌握足够的古语,从而认为我自己有资格批评《圣经》的英语译本”。同上,p.5。
(23) McLoughlin:Modern Revivalism, p.55.
(24) Memoirs, p.84;参阅pp.365-369。
(25) 这些观点均见于芬尼的《回忆录》,Memoirs, chapter 7, “Remarks Upon Ministerial Education,” pp.85-97;比较芬尼Lectures on Revivals of Religion, pp.176-178。
(26) McLoughlin:Modern Revivalism, pp.118-20。McLoughlin指出,芬尼认可的唯一的教育领域是科学。和旧时清教徒一样,他并不把科学视为对宗教的威胁,而是荣耀上帝的方式。中西部的教会学校保留了这种对待科学的态度,培养出多名学术科学家。有关背后的缘由,参阅R.H. Knapp和H. B. Goodrich:Origins of American Scientists(Chicago, 1952), chapter 19。
(27) Lectures on Revivals of Religion, pp.435-436.
(28) 白脸(paleface)是美洲土著对白种人的旧称,红脸(redskin)是白种人对印第安人的旧称,分别指代白人和印第安人。——译者
(29) “我们的根本原则,”卫斯理在回应一名卫理公会的早期诋毁者时宣称,“是抛弃思辨即抛弃宗教,宗教和思辨并驾齐驱,一切不理性的宗教都是虚假的宗教。”R. W. Burtner和R. E. Chiles:A Compend of Wesley's Theology(New York,1954),p.26。然而,正如诺曼·赛克斯所言,福音主义的奋兴造成智识的退化,它本就源于反对理性主义和由神学的反形式主义运动发展而来的索齐尼思想。相较于主要的神学自由主义者,卫斯理“对神的旨意介入最普通的生活细节的观点近乎迷信”,赛克斯还表示:“怀特菲尔德的情况更糟,因为他从同伴身上得不到丝毫教育和文化的影响……”Norman Sykes:Church and State in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1934),pp.398-399。
麦吉菲特(A.C. McGiffert)在描述英格兰的福音奋兴运动时写道:“在解读人类和人类的需求之时,它有意把脸转向了过去而不是未来。它激化了基督教和当代的矛盾,宣扬的观点是父辈们的信仰未曾传递给下一代任何的信息。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与基督教关联的是它的狭隘和中世纪精神,它的情绪化和智识的缺失,它彻底的超自然属性和《圣经》的教条,它对艺术、科学乃至整个世俗文化认同的渴求,这一切驱使这些人永久地远离了宗教。尽管福音派成就斐然,在很多方面,它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Protestant Thought before Kant(New York 1911),p.175。有关早期美国卫理公会的智识局限,参阅S. M. Duvall: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and Education up to 1869(New York,1928),pp.5-8,12。
(30) 这些早期的传教士认为,他们内心的力量源于自己和所服务的平信徒在文化素养和生活方式上殊无二致。1825年,一名来自英国的访客,见惯了圣公会主教们的养尊处优,在被介绍给印第安纳州卫理公会主教时感到惊愕万分。他讶异地发现,主教的住处是一间普通的农房。他稍显不耐地等待主教现身,一名美国牧师告诉他,罗伯兹主教正在赶来。“我看到那里有个人,”他说,“但不是主教。”“那就是主教呀,”美国人说。“不!不!不可能,那个人只穿着件衬衣。”罗伯兹主教那时正在他的住所工作。Charles E. Elliott:The Life of the Rev. Robert R. Roberts(New York, 1844), pp.299-300。有关边疆地区的主教,参阅Elizabeth K. Nottingham:Methodism and the Frontier(New York, 1941), chapter 5。
(31) George C.Baker, Jr.: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arly New England Methodism, 1789-1839(Durham, 1941), p.18.
(32) 同上,p.14。
(33) 同上,p.72。比较:据称下列言辞来自康涅狄格州的一次布道:“弟兄姊妹们,我所坚持的是:学习不是宗教,教育并不给人任何神灵的力量。荣耀和天赐才是神坛前安放的炭火。圣彼得是一个渔夫——你们觉得他上过耶鲁吗?然而,耶稣在他的石头之上建立了教堂。不,不,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要将耶利哥的城墙推倒,他用的不是黄铜的小号或锃亮的圆号,没有这种东西;他用的是公羊角——最平凡、最普通的公羊角——再自然不过了。他要推倒耶利哥的城墙……靠的不是你们中间文雅的、礼貌的、受过大学教育的某个绅士,而是一个平凡又普通的、公羊角一般的人,比如我。”S. G. Goodrich:Recollections of a Lifetime(New York, 1856), Vol.I, pp.196-197。
(34) Baker:同前,p.16。
(35) Goodrich:同前,p.311。
(36) Methodist Magazine and Quarterly Review, Vol.XII(January, 1830), pp.16,29-68; Vol.XII(April, 1830), pp.162-197; Vol.XIII(April, 1831), pp.160-187; Vol.XIV(July, 1832), pp.377其后。
(37) La Roy Sunderland:“Essay on a Theological Education,” MethodistMagazine and Quarterly Review, Vol.XVI(October, 1834), p.429. David M. Reese:“Brief Strictures on the Rev. Mr. Sunderland's ‘Essay on Theological Education,’” Methodist Magazine and Quarterly Review, Vol.XVII(January, 1835), pp.107,114,115.
(38) 首个卫理公会“学院”——位于马里兰州阿宾顿的科克斯伯里学院——的遭遇可作为例子。这个项目出自卫斯理的使者、托马斯·科克博士心怀的念想,他将牛津的教育理念自异域带入美国,成功说服卫理公会设立学院,尽管阿斯伯里表示反对,后者更愿见到一个像卫斯理在金斯伍德建立的那种综合学校。学院成立于1787年,起初和一所预备学校联合办学(早期美国的学院经常如此),后者的成功远超前者。成立甫一年,学院的全部三名教员都辞了职。1794年,大学部关闭,只剩下级学部;重开大学部的计划因1795年和1796年的两场大火而停滞,之后彻底终结。阿斯伯里认为,这是时间和金钱的浪费。“上帝对怀特菲尔德先生和卫理公会的召唤,不是为了创办学院,我要的只是学校……”The Journal and Letters of Francis Asbury, ed. By Elmer T. Clark et al. (London and Nashville, 1958), Vol.II, p.75。参阅Sylvanus M. Duvall: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and Education up to 1869(New York, 1928), pp.31-36。弗吉尼亚圣公会福音布道家德弗罗·贾拉特,对圣公会的教育方针略通一二,他为卫理公会在阿宾顿的投入感到骇然:“我真的不明白,当指挥者和掌舵人只是一群修补匠、裁缝、织布工、鞋匠和各色各样的修理工——换言之,都是些不识字的、丝毫不了解大学和其内涵之人,只要是有理智的人,怎么会指望这所学府会有任何好的结果。”The Life of the Reverend Devereux Jarratt Written by Himself(Baltimore, 1806), p.181。
(39) 首位著名教会历史学家内森·邦斯曾写道,早期卫理公会对学习的敌视是众所周知和毋庸置疑的。A Histor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New York, 1842), Vol.II, pp.318-321。
(40) 首位著名教会历史学家内森·邦斯曾写道,早期卫理公会对学习的敌视是众所周知和毋庸置疑的。A Histor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New York, 1842),Vol.III, pp.15-18。
(41) 第一所这样的神学院直到1847年才兴办起来——即卫理公会圣经研究院,建于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后转到波士顿,更名为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其后的1854年,在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建立了盖瑞特圣经研究院。第三所此类研究院——德鲁神学院,建于1867年,由著名的“华尔街海盗”丹尼尔·德鲁资助。
(42) Charles L.Wallis, ed.:Autobiography of Peter Cartwright(New York, 1956), pp.63-65,266-268.
(43) Charles C. Cole:The Social Ideas of Northern Evangelists,1826-1860(New York,1954),p.80.镀金年代最成功的奋兴运动家之一山姆·琼斯后来表示,他更愿意在南方地区的事工:“我发现,越往南去,那里的人民越容易被打动。他们的头脑不会复杂到去诅咒来自国内其它地方的事物。”McLoughlin:Modern Revivalism,pp.299-300。
(44) Relig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ulture(New York, 1952), p.111.
(45) W.W. Sweet, ed.:Religion on the American Frontier——The Baptists, 1783-1830(New York, 1931), p.65n.
(46) 比较早期弗吉尼亚州浸礼会的版本:“有的人嘴唇长毛,有的看不清东西,要么背是驼的,要么腿是弯的,要么脚是笨的。他们和其他人太不一样了。”Walter B. Posey:The Baptist Church in the Lower Mississippi Valley, 1776-1845(Lexington, Kentucky, 1957), p.2。
(47) Sweet:Religion on the American Frontier, p.72。“我们担心,金钱和神学教育成为当今太多传教士的骄傲。”同前,p.65。
(48) 同前,pp.73-74。有关浸礼会牧师的智识状况及牧师和平信徒对教育的抵制,参阅Posey:同前, chapter 2。
(49) Wesley M. Gewehr:The Great Awakening in Virginia, 1740-1790(Durham, North Carolina, 1930), p.256.
(50) 有关教育方面的努力,参阅Posey:同前,chapter 8。
(51) McLoughlin:Modern Revivalism, pp.219-220.
(52) Gamaliel Bradford:D. L. Moody:A Worker in Souls(New York, 1927), p.61.
(53) McLoughlin:Modern Revivalism, p.273.
(54) Bradford:Moody, pp.24,25-26,30,35,37,64,212.
(55) Lectures on Revivals of Religion, pp.9,12,32。芬尼对奋兴运动中人的作用的论述十分全面,此书第一章里的阐述极为中肯,而我只是管窥而已。
(56) 关于慕迪奋兴运动的运作方式,参阅McLoughlin:Modern Revivalism, chapter 5, “Old Fashioned Revival with the Modern Improvements.”。
(57) 美国百货业之父。——译者
(58) 美国铁路和航运大王。——译者
(59) Bernard Weisberger:They Gathered at the River, p.212.
(60) 同前,p.243。
(61) Silhouettes of My Contemporaries(New York, 1921), p.200.
(62) McLoughlin:Modern Revivalism, pp.167,269,278; Bradford:同前,pp.220-221。
(63) McLoughlin:Modern Revivalism, p.245;参阅Bradford:同前,p.223。
(64) McLoughlin:Modern Revivalism, p.433-434;以及Billy Sunday Was His Real Name, pp.127-128。
(65) Memoirs, pp.90-91。下文详述了芬尼的布道理念:Lectures on Revivals of Religion, chapter 12。对于宣教的演讲风格,他的定律是:“必须是谈话式的。”“必须要用生活化的语言。”它应该是类比式的——即要从真实的或假设的日常生活场景,以及“一般性的社会运作”里寻找范例。需要重复,但不可以单调。
(66) Roland H. Bainton:Here I Stand:A Life of Martin Luther(New York and Nashville, 1940), p.354.
(67) McLoughlin:Modern Revivalism, p.140.
(68) Bradford:同前,p.101。有关他的布道风格,参阅McLoughlin:Modern Revivalism, pp.239其后。在J. Wilbur Chapman:The Life and Work of Dwight L. Moody(Boston, 1900)一文中有大量的示例。
(69) Bradford:同前,p.103。
(70) A.B.为学士,Ph.D.为博士,D.D.为神学博士,LL.D.为法学博士,A.S.S.即英语中ass一词,意为傻瓜。——译者
(71) McLoughlin:Modern Revivalism, p.288.
(72) 中国教会称罗海孚。——译者
(73) 有关桑戴的一生,参阅William G. McLoughlin所著的全面而深刻的传记:Billy Sunday Was His Real Name。
(74) McLoughlin:Billy Sunday, pp.164,169.
(75) Weisberger:They Gathered at the River, p.248。McLoughlin:Billy Sunday, pp.177,179。桑戴的语言是一种新的暴力表达,在一战时期的牧师身上十分常见。参阅Ray H. Abrams:Preachers Present Arms(New York, 1933)。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