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神话信仰作为精神文化要素,先于秦始皇的武力征服约2000年,就开始了统一中国的历程。从距今8000年到距今5000年,玉文化用了3000年时间由北向南传播,主要覆盖到中国东部,随后向西传播,在距今5000—4500年时进入中原,形成黄河以东晋南地区的玉礼器体系。这一史前信仰文化的传播过程可概括为“东玉西传”。接下来是继续向西北地区的传播。约距今4000年前后,位于新疆昆仑山的和田玉开始输入中原,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这种西部优质玉石资源的东传,可称为“西玉东输”。石峁遗址及其玉器的新发现,给东玉西传和西玉东输这两种双向运动同时找到新的传播交汇站点,成为考察玉石神话信仰率先统一中国历程的实证性前沿个案。其意义首先在于提示“玉石之路黄河段”的存在可能性,预示着中国东部与西部之间又有一条重要的文化交通路线,比德国人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的“丝绸之路”的历史要早一倍之久,而且对华夏文明形成起到更关键的作用。石峁古城建筑用玉器的新发现,一方面验证了古书上关于夏代帝王修筑玉门、瑶台之类神话建筑记载的可信性;另一方面也验证了中国人信仰玉石避邪驱魔功能的史前渊源之深厚。
大传统新视野为探寻华夏文明独特性找到了重要线索。在距今约4000年之际的文明国家形成期,中原地区金属生产尚处于萌芽状态,与华夏社会共生的核心价值体系来自早于金属生产的玉礼器生产,附属于史前宗教祭祀仪式所形成的一整套玉教神话观。这种玉教神话观通过长期的文化传播逐渐构成中华认同的精神基础,在观念形态上统一了中国多数地区。这要比秦始皇用武力获取行政版图的统一早2000年。
语言是人的“家”,也可能成为束缚思想的“牢笼”。文化理论要有创新,首先必须冲破既定观念的牢笼。2010年,文学人类学界首次提出再造“大传统”和“小传统”这一对人类学概念,用文化媒介符号的根本性变革作为界限,将文字出现之前的文化传统作为大传统,将文字书写传统作为小传统。大与小的区别以时间长短为尺度,二者的关系则是根脉和枝叶的关系。文字小传统后来居上,压抑和遮蔽了更加深远也更加根本的大传统。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是重建大传统新知识的前提,它有效地探寻和解读前文字时代的符号物,是打通史前与文明,恢复大、小传统连续性的关键。在这打破文字中心主义传统知识观的挑战性探索中,神话学能够充分发挥催化、解码、衔接、贯通的重要作用。
就华夏文明而言,经过神话学解读后的前文字时代大传统和汉字记录的小传统能够联成一个整体的文化文本。这方面主要依靠两个法宝:一个是“神话历史”这个黏合剂般的新概念(它有效打通了文史哲分家的不利局面,把神话当作历史不可分割的重要源头);另一个是从史前延续到文明时期的玉礼器实物之神话学研究。围绕这两个研究主题,《百色学院学报》自2009年起开设了文学人类学专栏,呼应《民族艺术》自2008年以来开辟的“神话—图像”专栏,努力倡导和探索跨学科研究的创新范式,从理论探讨和个案研究实践相互结合的意义上,尝试提出和解决本土文化研究中的攻坚类和瓶颈类问题。2013年6月在陕西榆林召开的“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上,文学人类学研究者自觉追踪中华文明起源的学术前沿动向,将大小传统再划分的新理论与深入田野考古第一线的新发现材料有效结合起来,力求依据考古发现材料去阐发华夏文明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及其编码发生过程。该会议论文集后编撰为《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一书,于2015年出版。笔者的会议论文先发表于《民族艺术》2013年第4期,以《玉文化先统一中国》为题,本节拟对上述命题作进一步的申论。
考古发掘材料表明,史前时代的人都是神鬼世界的虔诚信仰者,神话思维决定性地支配着人们的文化创造和行为。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伊安·霍德尔(Ian Hodder)编写的《文明萌生期的宗教:以卡托·胡玉克为研究个案》一书,针对距今9000年前的土耳其中部聚落遗址卡托·胡玉克(又译“加泰土丘”)的文物进行分析,尤其是对宗教象征物进行分析,重建当时社会群体的仪式行为和神话信仰,并以此作为“通向文明起源的关键第一步”。[54]国际上的前沿研究显示,探索地球上最早的古文明的发生,不能只关注文明国家,需要深度考察文明出现之前的数千年文化演进过程。这正是我们重新定义的大传统的新知识范围。伊安·霍德尔强调指出,卡托·胡玉克聚落遗址提供的史前社会案例之所以受到国际上考古学以外的学者关注,如人类学、宗教学和神学研究者的关注和参与讨论,就是因为能够通过交叉科学的视野,在多种因素中寻找驱动文明发生的主导力量。这部作品汇集了多学科研究者的智慧,旨在从个案分析中透视文明起源期的三个观念要素:精神与物质是如何整合的;信念在宗教中起什么作用;宗教的认知基础及其社会作用如何。[55]
如果说西方社会学的创始人马克斯·韦伯当年构想的从宗教观念角度解读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案例,其结论至今还处在持续的争议之中,那么,从宗教和信仰观念角度考察文明起源的做法,如今正在成为主流。实际上,只要意识到人类最早建立的文明——苏美尔诸城邦,基本上是以高大的神庙为中心而形成的,就可以平息很多争议。虔诚的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所建立的文明古国虽然早在4000年前因遭遇闪米特族(阿卡德人和巴比伦人)的入侵而灭亡了,但是其大量泥版文书的现代破译,构成了已知的人类最古老的书面神话遗产,[56]为今人从宗教意识形态方面理解早期文明国家的精神生活,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叙事资料。受到苏美尔神话研究的影响,如今研究古埃及神话的学者也早已走出文学专业的本位主义视角,出现了诸如《埃及诸神的日常生活》[57]这样别开生面的著作,这些研究同样是通过神话叙事去透视古老文明的精神世界奥秘。在同一向度上,国内的文学人类学研究群体一方面用“神话历史”和“神话哲学”的新术语,倡导“走出文学本位的神话观”,在重构神话学知识版图的同时,把研究目标引向中华文明的构成;另一方面也在尝试构建大传统视野的文化文本理论,即一套文化符号分级编码的理论,被命名为“N级编码论”,以及与此相关的研究方法范式——多重证据法。我们期待新理论和新方法能够破解华夏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的特性所在;换言之,找出这个文明与生俱来的、与众不同的核心价值体系。
先秦古书所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58]是将信仰和祭祀神灵(包括神、鬼、精灵等)作为国家社会第一要务,希望通过祭祀来沟通神人关系,求得神灵对社会群体及个人的庇护和保佑。祭祀礼仪行为不是随着文明而来的,而是来自比文字和文明都早得多的史前大传统。例如,3000多年前的殷商文明考古资料表明,虽然当时已经有了甲骨文字,结束大传统并开启了书写叙事的小传统,但是其祭祀行为的极端重要性和严酷性是让后世文明人难以理解的。根据黄展岳《我国古代的人牲和人殉》一文统计,殷墟14座大墓的殉葬人数,总计3900人左右。连同中小墓的人殉以及基址、祭祀遗迹中发现的人牲,估计总数在5000人以上。[59]人祭只是多种多样祭祀活动中较为极端的一种。陕西榆林地区神木县石峁遗址属于龙山文化,新发掘出的近百个女性人头骨,通常以24这个数字为一组,分布在史前石头城池的墙基下和城门路径下,这充分表明文明期的人祭现象是直接承袭史前大传统的宗教礼俗。自龙山文化开始,黄河中游地区祭祀神灵的珍贵物品除了以动物和人作为牺牲以外,还出现了批量生产的玉石礼器,如石峁遗址出土的大件玉刀和玉璋等,还有玉雕和石雕人头像等,[60]以及陶寺遗址的玉璧和玉钺等。而陕西神木县大保当镇新华村1999年发掘的一号坑(K1)出土玉器36件,器形有刀、斧、钺、璋、铲、玦、环7种,显然是以玉兵器为主(图16—8)。其中的有刃玉器以整齐排列的方式插在地上,分为6排,竖直侧立插入土中,每一排的器物数量不等,多者10件,少者2件。犹如一个自西向东排列的玉兵方阵,让人联想到同样自西向东排列的陕西临潼秦兵马俑排列方阵。考古工作者孙周勇有如下分析:
K1出土的玉器以片状器为主,占总数的85%以上。器物形制简单,器形不甚丰富。许多器物没有明显刃部,个别器体极薄,厚度仅仅两三毫米,显非实用器物,当已具有了礼器的性质。K1特殊的形制及玉器整齐排列及埋葬方式,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K1坑底中央埋葬鸟禽骨头的小坑,似乎与殷商时期埋葬中常见腰坑有着相似的功能或含义。这些现象都可能表明了K1作为一种文化遗迹,可能和当时某种祭祀活动有关。[61]
这种动物牺牲加玉礼器的祭祀情况,在华夏文明的三级编码时代即文字书写经典形成期,在《山海经》这样的古书叙事中清晰可见。如《北山经》的两段祭祀叙事:

图16—8 玉兵方阵:陕西神木新华遗址龙山文化玉器坑平面图
(引自孙周勇:《神木新华遗址出土玉器的几个问题》)
凡北次二经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题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其祠:毛用一雄鸡彘瘗;用一璧一珪,投而不糈。[62]
凡北次三经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无逢之山,凡四十六山,万二千三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马身而人面者廿神。其祠之,皆用一藻茝瘗之。其十四神状皆彘身而载玉。其祠之,皆玉,不瘗。其十神状皆彘身而八足蛇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瘗之。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糈米祠之,此皆不火食。[63]
从《北山经》的山神祭祀规定看,祭品是动物加玉器,或只用玉器。描绘山神形象特征的一句“其十四神状皆彘身而载玉”,郝懿行注云:“载亦戴也,古字通。”既然神灵本身就是佩戴玉器的,所以用人工制作的玉器向他们献祭,也算是投其所好。再如《中山经》:
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于阳虚之山,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升山冢也,其祠礼:太牢,婴用吉玉。首山 也,其祠用稌、黑牺、太牢之具、蘖酿;干儛,置鼓;婴用一璧。尸水,合天也,肥牲祠之;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鸡于下,刉一牝羊,献血。婴用吉玉,采之,飨之。[64]
也,其祠用稌、黑牺、太牢之具、蘖酿;干儛,置鼓;婴用一璧。尸水,合天也,肥牲祠之;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鸡于下,刉一牝羊,献血。婴用吉玉,采之,飨之。[64]
这里的祭品出现太牢即牛羊猪,显然比《北山经》要隆重得多。又如《中山经》末尾的记载,祭品中玉礼器的数量大大增加: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荣余之山,凡十万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毛用一雄鸡、一牝豚刏,糈用稌。凡夫夫之山、即公之山、尧山、阳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肆瘗,祈用酒,毛用少牢,婴毛一吉玉。洞庭、荣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瘗,祈酒太牢祠,婴用圭璧十五,五采惠之。[65]
繁复的祭祀仪式活动,必然催生围绕着祭祀礼仪而形成的早期符号——图像和充当符号的物,从陶器、陶文、骨器、蚌器到玉器,再到青铜礼器,这些都是先于汉字的最早形态甲骨文而存在的华夏文化符号。目前看来,最能够体现华夏精神信仰特色的持久性的前文字符号是玉礼器,而生产和使用玉礼器的行为受到神话想象的支配,每一种玉器形式都包含一种神话观念。成功解读这些玉器符号的信仰意义,就相当于找出近8000年的符号物叙事链,这要比甲骨文、金文以来的汉字叙事链在年代上早一倍以上,比《春秋》《史记》等文献叙事早三四倍。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把神话研究从文字和文献本位的窠臼中解放出来,真正走向大传统的新知识。
据史料所传,夏禹创建华夏第一王朝时,有来自四方“万国”的拥戴者贡献各地的“玉帛”。这一说法突出的两种物质——玉和丝绸,均是在史前大传统中早已被神话化的物质。用《国语》中人物观射父回答楚昭王询问祭神秘诀的话说,叫作“玉帛为二精”。[66]东周时期著名知识人的这个说法,是对我们如今寻找华夏文明核心价值由来的极好提示,因为以玉帛为精的信念来自大传统神话,是构成玉教信仰的核心观念;同时也是贯穿小传统全程的神话观念,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夏朝末代帝王夏桀的亡国,很重要的原因是其不自量力修筑攀比天神世界琼楼玉宇的地上建筑物——瑶台和玉门。商朝的末代统治者是纣王,当其王国被周武王大军推翻时,他将王室所藏的宝玉缠在身体上,自焚升天。周人取代殷商建立新的中原王朝,分封诸侯时动用周王室秘传的玉器珍宝做各地方的镇国符号,让周公的儿子去统治鲁国的象征物叫“夏后氏之璜”,是天下独一的神秘玉礼器。西周灭亡后,又经历了春秋战国时追求宝玉和氏璧的传奇历史,再到秦始皇用传国玉玺作为统一帝国至高无上的天命神话符号。一部由玉器神话支配的神话历史展开脉络,清晰可辨,一线贯穿到夏、商、周、秦、汉各个朝代,覆盖从4000年前到2000年前的整个上古史全程。夏禹从天帝那里获得的“玄圭”,夏桀的瑶台玉门,殷纣王用来升天的“天智玉”,鲁国的“夏后氏之璜”,楚王的和氏璧,秦始皇的传国玉玺,等等,总而言之,每一种记载都突出统治者与玉器的关联,而且强调这些神秘玉器的唯一性,这里面当然透露着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所在。
自20世纪初年西方的“历史科学”观念进入中国,以北京大学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学者便怀疑华夏上古史的可信性,不仅要打倒三皇五帝之类的历史偶像,还认为相关的远古叙事都是后人编造的神话传说。这是在考古学还没有完整再现出华夏大传统世界的丰富性和深远性之前,书斋作业的学人机械推崇科学主义历史观而陷入盲区的结果。今天,我们借助考古新发现,能够看到玉文化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发源,足足有八九千年之久,随后逐渐南下,传播到东方沿海地区,南端一直抵达广东和越南。在距今4000年之际,完成自东向西传播的最后一站,到达河西走廊深处,催生出西北地区齐家文化的玉礼器体系。
总括地讲,史前玉文化大传统从8000年前到4000年前,即夏商周三代尚未出现之时,就已经基本覆盖了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以外的华夏大地,以距今5000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和江浙地区良渚文化为其巅峰状态。其神圣符号标记是以玉钺、玉铲、玉圭象征王权,或以玉璧、玉琮、玉璜祭祀天地。从前所未有的大传统景观看,甲骨文中的“王”字为什么写成一件斧钺形,后世“王”字与“玉”字为何如此近似等问题,均可得到洞若观火般的体悟。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要说“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这是大传统新知识能够超越传统文献知识的学理见证。
古史中还有多少未解的传说与奥秘等待着大传统新知识去重解?以下就用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和平主义理想口号“化干戈为玉帛”为实例,说明从大传统新视野出发,我们还能够获得怎样的超越文献记录的认识和理解。
从先秦儒家创始人孔子所承认的华夏上古史脉络看,并不包括炎帝、黄帝,更不包括燧人氏、伏羲氏等传说的古帝在内,而是以尧舜禹和虞夏商周四代为谱系开端。由于虞夏两代的文字记录迄今尚未见到,商周两代以下才有甲骨文、金文等汉字叙事材料出现,所以我们的考察就可以把视野划分为两段:虞夏大传统和商周小传统。
就目前有限的上古文献提示看,虞和夏如果是中原地区确实存在过的最早的两个王朝,那么它们的先后建立都充分体现出“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主义理念。从尧舜禹统一中原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王朝的核心区域没有变,变化的是中原国家辐射周边地区的面积;而秦帝国统治的2000多年前所覆盖到的北方和南方的多数地区,其实早在4000年前就已经被玉文化率先覆盖到了。[67]正是因为有在全国各地寻找美玉的战略资源自觉,才会出现大禹建立统一政权之际,各地方统治者蜂拥而至,“执玉帛者万国”的奇特景观。
最后列举古文献提示的十个与华夏王朝最高统治者相关的事件,旨在殊途同归地显示:作为隐性宗教信仰而存在于华夏文明发生期的玉教,如何直接催生出这个文明的核心价值并支配着最高统治者的行为。
第一,尧舜北用禺氏之玉而王天下,玉教神话观先统一中原。
第二,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第三,夏桀建瑶台玉门,模拟神话想象中的天国永生理想。
第四,殷纣王:化玉帛为升天媒介——神灵永生信仰。
第五,西周王朝秘密贮备天下玉宝,作为镇国秘宝。
第六,周公东封鲁国用“夏后氏之璜”,具有震慑与和亲双重意义。
第七,周公为病重的武王举行仪式,求祖先在天之灵为武王延寿,他与神明对话的媒介物是两件玉礼器:璧和圭(可参考图16—9、图16—10)。
第八,周穆王用玉帛和亲于北方的河宗氏与西方的西王母邦。
第九,秦昭王试图以15座城池换取天下第一美玉和氏璧。
第十,秦始皇化干戈为玉帛:销天下之金与制作唯一象征大一统政权的传国玉玺。
秦始皇统一中国所开创的以传国玉玺象征国家最高统治权的制度,历代传承和延续(图16—11),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为止。

图16—9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玄圭,距今约4400年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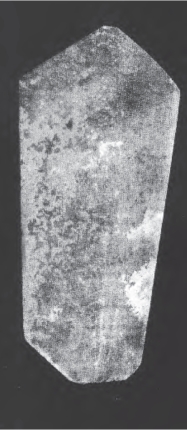
图16—10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的玉圭,距今约3000年
(甘肃省博物馆藏;引自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15卷)

图16—11 清光绪“光绪之宝”青白玉玺
(2016年摄于首都博物馆特展“走近养心殿”)
【注释】
[1]王炜林、孙周勇、邵晶等:《2012年神木石峁遗址考古工作主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2年12月21日。
[2]戴应新:《我与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见《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228—239页。这批玉器如今收藏在陕西省博物馆,有一小部分作为展品常年展出。
[3]戴应新描述的地理位置是:“石峁遗址属高家堡公社石峁队,西距高家堡1.5公里,东北距县城60公里,北距长城10公里。榆林到府谷的公路沿着洞川沟从遗址山脚下经过。”见戴应新:《陕西神木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77年第3期。
[4]王炜林、孙周勇、邵晶等:《2012年神木石峁遗址考古工作主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2年12月21日。
[5]石峁遗址墓葬的报告尚未发布,但与石峁遗址处在同一地区的朱开沟遗址第三期墓葬却发现多处异性双人或三人合葬景象:一位男性葬于木棺内,棺外陪葬一位或两位女性。考古工作者推测唯有男性家长享有同穴合葬的权力,陪葬者或许为妾。墓葬形式表明4000年前河套地区父权制社会的确立。参看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30页。
[6]郭璞著,王招明、王暄注:《山海图赞译注》,岳麓书社,2016年,第222页。
[7]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上,见方诗铭等:《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3页。
[8]叶舒宪:《玉的叙事——夏代神话历史的人类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1日。
[9]叶舒宪:《三星堆与西南玉石之路——夏桀伐岷山神话解》,《民族艺术》2011年第4期。
[10]《文选·吴都赋》注引,转引自方诗铭等:《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页。(https://www.xing528.com)
[11]同上书,第19页。
[12]《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纪年》。
[13]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256页。
[14]费正刚等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0页。
[15]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52页。
[16]王平、顾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81页。
[17]参看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第七章第七节“颂仪原始:猎头与祭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15—529页。
[18]台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种学研究室调查,杨南郡译注《台湾原住民族系统所属之研究》第一册本文篇(1935年),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南天书局有限公司,2011年,第72页。
[19]同上书,第72页,注释84。
[20]萧兵:《避邪趣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1]吕大吉等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壮族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22页。
[22]郭大顺、张克举:《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23]宋镇豪:《中国上古时代的建筑仪式》,《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
[24]宋镇豪:《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25]吴小强:《秦简日书》,岳麓书院,2000年,第78—79页。
[26]台湾旧惯习调查会:《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第6册布农族,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编译,2008年,第62页。
[27]同上书,第63页。
[28]同上书,第105页。
[29]吕大吉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丛编·哈尼族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06页。
[30]叶舒宪:《中国戈文化的源流及其文明起源意义》,《民族艺术》2013年第1期。
[31]钟敬文主编:《中国民俗史(先秦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8页。
[32][英]戈登·柴尔德:《考古学导论》,安志敏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25页。
[33][英]戈登·柴尔德:《欧洲文明的曙光》,陈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110、116页。
[34]同上书,第52页。
[35]参看叶舒宪:《苏美尔青金石神话研究——文明探源的神话学视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金枝玉叶——比较神话学的中国视角》,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4—182页。
[36][英]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李宁利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77—78页。
[37][英]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李宁利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81页。
[38]同上书,第61页。
[39]同上书,第66页。
[40]Fleming,Fergus,and Alan Lothian,The Way to Eternity:Egyptian Myth,London:Duncan Baird Publishers,1997,p.60.
[41]Kunz,George Frederick,The Magic of Jewels and Charms,New York:Dover,1997,p.282.
[42]Ibid.,p.316.
[43]Kunz,George Frederick,The Magic of Jewels and Charms,New York:Dover,1997,p.317.
[44]杨伯达:《“一目国”玉人面考——兼论石峁玉器与贝加尔湖周边玉资源的关系》,见《巫玉之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0—151页。
[45]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罗宏才:《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石雕像群组的调查与研究》,见《从中亚到长安》,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0页。
[46]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文物》1978年第7期;吴汝祚:《试论石峡文化与海岱、太湖史前文化区的关系》,见广东省韶关市曲江人民政府编:《曲江文物考古五十年》,(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年,第177—183页。
[47]图版见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3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2页。
[48]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图版三五。
[49]孙周勇:《神木新华遗址出土玉器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参看韩建武、赵峰等:《陕西历史博物馆新征集文物精粹》,见《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
[50]马明志:《河套地区齐家文化遗存的界定及其意义——兼论西部文化东进与北方边地文化的聚合历程》,《文博》2009年第5期。
[51]艾有为:《神木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5期。
[52]姬乃军:《延安市芦山峁出土玉器有关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1期。
[53]孙周勇:《神木新华遗址出土玉器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
[54]Hodder,Ian,ed.,Religion in 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Catalhὄyűk as Cace Stud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2.
[55]Ibid.,p.27.
[56][美]萨缪尔·诺亚·克拉莫尔:《苏美尔神话》,叶舒宪、金立江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3年。从考古学视角看苏美尔文明,参看哈里特·克劳福德:《神秘的苏美尔人》,张文立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57]Meeks,Dimitri,and Christine Favard-Meeks,Daly Life of the Egyptian Gods,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G.M.Goshgarian,London:Pimlico,1999.
[58]《左传·成公十三年》。
[59]黄展岳:《我国古代的人殉和人牲——从人殉、人牲看孔丘“克己复礼”的反动性》,《考古》1974年第3期。
[60]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戴应新:《我与石峁龙山文化玉器》,见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228—239页;罗宏才:《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石雕像群组的调查与研究》,见《从中亚到长安》,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0页。
[61]孙周勇:《神木新华遗址出土玉器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该文收入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109—123页。
[62]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84页。
[63]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99页。
[64]同上书,第135页。
[65]同上书,第179页。
[66]左丘明:《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70页。
[67]南方有广东韶关史前的玉文化发现,以及香港和珠海、越南等地发现的祭祀用玉璋。分别参看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文物》1978年第7期;吴汝祚:《试论石峡文化与海岱、太湖史前文化区的关系》,见广东省韶关市曲江人民政府编:《曲江文物考古五十年》,(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年,第177—183页;李岩:《广东地区文明进程的玉器传播与使用浅见》,见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四编上,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第325—334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