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张謇(1)、郑观应等实业家的发声,航海技术教育被更多人关注,此时虽没有开设专门学校的条件,但航海技术教育已在新创办的西式学堂中进行试水。
洋务派首先发声,指出了问题的端倪所在。19世纪60—70年代,我国招商局轮船只有三万吨,船长、轮机长均为洋人,洋务派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没有专业学堂培养航海人才。1873年《轮船招商章程》中提到,对航海方位、风向等不熟悉者不能胜任船长,对船上机械不熟悉者不能管理轮机。当时,精通这些技能的华人不多,所以在招商局开办之初,向洋行雇佣洋人船长、船员等数人,等到华人技术人才培养起来后,招商局也已积累了一定资本,就可以雇佣华人进行驾驶。清末一些官僚和学者也纷纷上奏清政府,希望兴办航海教育学校来培养航海人才[3]。
清末实业家张謇(见图7-1)是高等航海教育的早期倡导者之一。甲午战争战败之初,张謇就认识到人才对立国自强的重要性,他认为“父教育而母实业”,也是因为这种观念,张謇创办和协办了370多所各类学校,这些学校分布在乡村或城市,学段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均有涵盖。1903年5月,张謇应日本驻江宁(今南京)领事天野恭太郎的邀请第一次参加了日本大阪举办的“劝业博览会”,张謇视此为考察日本和研究博览会的好机会,欣然前往。大阪劝业博览会有6万多平方米,其中馆舍面积有1万多平方米,分为工业、农业、矿冶、染织、教育、美术工艺等10多个门类,每一个门类又分为8个馆,展品达22万多件,其场面之大,参观者之多,前所未见。他参观了通运馆、水产馆,“舟车法度咸备。最精者,环球航路之标本,内国山海之模型,台湾模型极精审”,思想意识为之一新。可也令他惊诧的是“乃并我福建诸海口绘入,其志以黄色,亦与台湾同”,这涉及中国领土主权,曾引起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的愤怒抗议,而一些清廷的王孙贵族以至官员却视而不见,张謇对此极为不满。从日本考察回来后,张謇结合其所见所闻,进行了思考,深感中国的渔业发展、航政建设、渔界海权之重要。他明确提出,渔业和航政的范围到哪里,国家的领海主权就到哪里。假如只有海,而没有渔业航政,试问主权从何表现?我国政府应努力挽回已失的权利并大力发展沿海渔航业。他还指出,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互相维系,各界皆然,中国向无渔政,形势涣散。洋面海船所到地段,散见于《海国图志》等书,已不及英国海军图册记载之详。至于海权之说,士大夫多不能究言其故,际此海禁大开,五洲交会,各国日以扩张海权为事。若不及早自图,必致海界因含忍而被侵;海权因退让而日蹙。滨海数千里外即为公共洋面,一旦有事,人得纵横自如,我转堂澳自囿,利害相形,关系极大[4]。就这样,张謇在探索实业救国之路中,也逐渐把目标投向广袤的大海,并提出进行航海教育,开发蓝色国土,对高等航海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图7-1 张謇
有晚清“四大买办”之一称谓的郑观应也是航海教育的大力提倡者。郑观应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5]。在其著作《盛世危言》(2)一书中,他提到,想要克敌,首先需要掌握他们成功的法门,其次需要进行变通,这样才是制胜之道。作为实业家,他提倡进行专门的技能学习,呼吁不要顽固守旧,不要将西方思想通通视为“异学”,从而受制于人。对于航海学习,他认为必须要娴熟掌握地理、测量、驾驶等,这样才能知晓行船的方向,通晓水文,善于躲避海上的风暴和礁石。
他指出中国的海关、制造、矿物、轮船、电报、铁路、纺织等产业初创时期因为华人没有相关经验,不得不聘用洋人。而外轮无论是船长、大副还是其他船员都聘用本国人。日本引进西学后设立了各式学堂,东洋邮船会社的轮船已发展到六十五万吨的规模,而且驾驶人员都是日本人。中国还没有商轮驾驶学堂,但对外国轮船来往于各关口通商已经放开,相关人才紧缺,如果不设立驾驶学堂,所有的国内外船舶都聘用洋人不是长久之计,因此急需要模仿国外开办商船驾驶学堂来培养高级航海人才,选择中学毕业并且精通英语的少年入校学习,毕业后派往招商局轮船同外籍船长实地学习,对学成后能承担船长一职的毕业生给予奖励。
凭着自己对西式教育的了解,他推崇德国的教育方式,认为我国驾驶与轮机人员的培养需要效仿德国的教育模式,多设立大大小小的学堂来开化人民、培育人才。他将“泰安”号兵船改造为实习船,先招收一些学生来学习驾驶等技术,并专门在《泰西练船学生应学驾驶诸法》一文中翻译了西方的航海教育课程,列出了30门航海教育必修课,除数理等基础课程外,还有航海驾驶课程、天文课程、水文课程等,建立了我国高等航海教育课程体系的雏形。
此时,社会各界对高等航海教育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一些教育杂志等也刊登文章介绍国外航海学校的情况,清政府甚至派官员考察了日本的高等航海教育机构。这一切都为高等航海教育的出现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19世纪60年代开始,学习西学的新式学堂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开设起来,此时虽然没有专门的商船学堂,但已有部分学堂设有航海技术相关课程,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建船政学堂、轮船招商局练船等。(https://www.xing528.com)
京师同文馆是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学校,由洋务派领袖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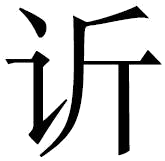 和文祥于1861年1月(咸丰十年十二月)奏请开办,并于1862年8月24号正式开办,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6]。课程开始时只设英文,后来增设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同治六年(1867年)又添设算学馆,教授天文、算学。学制初定为三年,1876年后,分五年、八年两种,学习外语译本的学生五年毕业,进修天文、化学、测地等学生需八年毕业。八年制又分前馆、后馆,后馆学有成效者升入前馆。无论学制五年还是八年,在制订的课程表中均需学习“航海测算”,具备一定的航海基础知识。学生学完后为“附生”,可以参加科举,并充任各衙门及海关“翻译官[7]”。
和文祥于1861年1月(咸丰十年十二月)奏请开办,并于1862年8月24号正式开办,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6]。课程开始时只设英文,后来增设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同治六年(1867年)又添设算学馆,教授天文、算学。学制初定为三年,1876年后,分五年、八年两种,学习外语译本的学生五年毕业,进修天文、化学、测地等学生需八年毕业。八年制又分前馆、后馆,后馆学有成效者升入前馆。无论学制五年还是八年,在制订的课程表中均需学习“航海测算”,具备一定的航海基础知识。学生学完后为“附生”,可以参加科举,并充任各衙门及海关“翻译官[7]”。
上海广方言馆(见图7-2)成立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由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仿京师同文馆,奏设于上海,是上海建立的第一所外国语专科学校,校址初设于老城厢内旧学宫(今学院路四牌楼附近),冯桂芬(3)被委任广方言馆馆长。“广方言”意为推广方言,清政府认为京畿所用语言为官话,其他地方语言为方言,外语也不例外。上海广方言馆成立后培养出了第一代精通西文和西学的中国学生[8]。1872年,30名14岁学童作为第一批中国官派留学生在陈兰彬(4)、容闳(5)的带领下赴美留学,中国近代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6)便是其中一员。广方言馆开设时,仅设英文一馆,后加设法文馆、算学馆[9],1891年增设天文馆,之后又设翻译馆、东文馆、铁船馆、工艺学堂等。招收14岁以下(后改15岁至20岁)“师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10]。定额40人,最多时达80人。入学后分上、下两班,先入下班,一年后择优升入上班,选定一门专业进行精修,其中便有航海、轮机等课程。对于这种学习方式,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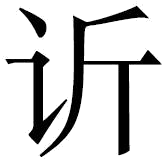 在1866年上奏增设天文算学馆的奏折中评论只是学习了皮毛,没有太大实用价值。
在1866年上奏增设天文算学馆的奏折中评论只是学习了皮毛,没有太大实用价值。
图7-2 上海广方言馆
与将航海教育作为一门科普课程了解的两座西文学堂不同,一些海军教育学堂对航海教育的学习更为深入,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都开设航海、轮机等专科。福建船政学堂由左宗棠(7)奏请创办,在船政大臣沈葆祯的主持下于1866年在福州成立,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也是中国近代航海教育和海军教育的发源地,初建时称为“求是堂艺局”,1867年搬迁至马尾改名为船政学堂(见图7-3)。
图7-3 福建船政学堂
船政学堂分为前后学堂,前学堂为制造学堂,学习造船,又称“法语学堂”,目的是培育船舶制造和设计人才,主设有造船专业。后学堂为驾驶学堂,学习航海,亦称“英语学堂”,旨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主要专业为驾驶专业,后增设了轮机专业[11]。除了理论学习外,船政学堂也十分注重实践教学,安排学生上船实习,1877年派出留学生赴英、法等国学习。
在船政学堂四十多年的办学中,驾驶班毕业生共十九届241名,管轮班毕业生共十四届210名,为海军培养了一大批驾驶、轮机人才,邓世昌(8)、严复(9)、萨镇冰、詹天佑等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位列其中,对我国航海教育和海军教育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除学堂外,轮船招商局作为最早的民族航运企业也非常关注高级船员的培养,早期创办航海实习教育机构练船(实习船)来进行理论和实践学习,培养高级船员。练船上的教学活动虽有良好的效果,但成本高昂,无法推广,却也为后期专门学校的开设提供了一定的借鉴。至此,各类航海科普教育、职业培训、海军航海教育等探索为中国高等航海教育的创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