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财富大体上以商品、货币和资本三种形式存在。马克思的财富思想主要是在批判汲取前人的观点基础上日渐形成的,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研究过程中日渐成熟的。马克思从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两个方面来看财富问题,“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33) 49。马克思的财富思想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财富与人的发展、财富与社会生产关系等内容,成为研究其经济、社会思想的一条重要线索。
(一) 财富的本源:自然富源与劳动的结合
马克思认为,最本源意义上的财富即是大量存在的具有使用价值的天然物品、资源或自然条件,抑或称为自然富源。马克思指出:“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绝对必须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产者在为自己从事的劳动之外来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越多。 无论是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还是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均为使用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是与人们的物质生活直接相关的“物质生活条件”,当然,两种自然富源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或不同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同的,“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无论是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还是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均为使用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是与人们的物质生活直接相关的“物质生活条件”,当然,两种自然富源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或不同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同的,“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财富生成的主要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变化,劳动,以及隐含在劳动中的技术因素等等,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
。财富生成的主要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变化,劳动,以及隐含在劳动中的技术因素等等,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
马克思在许多场合都提到类似的观点,一切财富的源泉并不只是劳动,“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34) 428。在人类劳动介入之后,“财富的对象、财富的材料立即获得了自然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普遍性,因为它们作为自然界仍然是直接的对象性的财富 。自然富源经过人的社会性的劳动,或改变性状,或改变用途,或改变满足物的有效性的量能,进而转化为具有交换意义的经济财富,“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一般劳动
。自然富源经过人的社会性的劳动,或改变性状,或改变用途,或改变满足物的有效性的量能,进而转化为具有交换意义的经济财富,“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一般劳动 ,即包含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财富,既具有物的使用价值,也具有物的交换价值。换言之,财富是物质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而“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也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由于生产过程而作为现实性存在于劳动之外,但这种现实性对于劳动来说是他人的现实性,它构成同劳动相对立的财富”
,即包含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财富,既具有物的使用价值,也具有物的交换价值。换言之,财富是物质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而“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也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由于生产过程而作为现实性存在于劳动之外,但这种现实性对于劳动来说是他人的现实性,它构成同劳动相对立的财富” (35) 。马克思由此揭示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控制与奴役,揭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条件。
(35) 。马克思由此揭示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控制与奴役,揭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条件。
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德国经济学家弗·李斯特提出过财富的生产力理论。他认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36) 118。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数次引用了李斯特的财富生产力观点。马克思在肯定其财富思想的同时,更指出了李斯特的认识缺陷——将物质财富视为交换价值:“弗·李斯特永远不能理解……两种劳动的区别:一种是协助造出有用物即使用价值的劳动,一种是造出财富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即交换价值的劳动。”(37) 429
马克思在不同场合或不同语境下分别表述了使用价值与财富的关系,即“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内容 ,“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38) 49,“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39) 8。凡财富都具有使用价值,但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并非都是财富,财富必须是具有“剩余效应”或者“累积效应”的“使用价值”。由此,马克思给出的结论是:“财富的最初的自然发生的形式,是剩余或过剩的形式,是并非作为使用价值而直接需要的那一部分产品,或者说,是对那些其使用价值不属于最需要范围的产品的占有。”(40) 521应当可以认为,当马克思把财富界定为具有“剩余效应”或“累积效应”的那个“使用价值”时,就已经为我们认识财富的形态由商品形态向货币形态再向资本形态转变或者说由商品财富向货币财富再向资本财富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三种财富的表现形式,不仅构成了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主线,而且还清晰地展现出财富形态演变的历史逻辑。
,“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38) 49,“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39) 8。凡财富都具有使用价值,但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并非都是财富,财富必须是具有“剩余效应”或者“累积效应”的“使用价值”。由此,马克思给出的结论是:“财富的最初的自然发生的形式,是剩余或过剩的形式,是并非作为使用价值而直接需要的那一部分产品,或者说,是对那些其使用价值不属于最需要范围的产品的占有。”(40) 521应当可以认为,当马克思把财富界定为具有“剩余效应”或“累积效应”的那个“使用价值”时,就已经为我们认识财富的形态由商品形态向货币形态再向资本形态转变或者说由商品财富向货币财富再向资本财富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三种财富的表现形式,不仅构成了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主线,而且还清晰地展现出财富形态演变的历史逻辑。
(二) 财富形态的演变: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就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41) 47在《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中,马克思起初的表述是这样的:“商品,作为资产阶级财富的元素形式,曾经是我们的出发点,是资本产生的前提。另一方面,商品现在表现为资本的产物”,“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在事实上成为财富的一般元素形式”(42) 423、427。《资本论》手稿及《资本论》中上述表述的核心思想高度一致地都将商品或者说财富的商品形式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
研究商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在商品经济时代,商品是作为使用价值的“自然存在”和作为价值的“纯经济存在”的内在统一,亦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因而具有财富的物质内容。现实中,“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并且,“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满足一种特殊的需要,构成物质财富的一种特殊的要素。而商品的价值则衡量该商品对物质财富的一切要素的吸引力的大小,因而也衡量该商品占有者的社会财富”(43) 47、156。由此,商品取得了财富的等价物的形式,商品的丰裕程度亦反映了财富的多寡。
“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货币的商品本质表明,“其他一切商品只是货币的特殊等价物,而货币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货币形式只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固定在一种商品上面的反映”(44) 106、109。商品的交换价值建立在商品价值的衡量基础上,作为同商品本身并列的特殊存在,就是货币(45) ,货币即是一般等价物。由于货币兼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等基本职能,“财富的形式和内容是同一的”,“在货币上,一般财富不但是形式,而且同时就是财富本身”,又是“作为财富的普遍物质代表”,而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作为“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46) 156、154,其支配权力也增大了。“货币形式只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固定在一种商品上面的反映”,“是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化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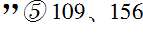 。在马克思那里,货币是个人一般劳动的对象、劳动的目的,“生产一般财富,就是为了占有一般财富的代表”(47) 176。在此,货币是作为财富的一般等价物的身份出现的,财富的计量依赖于货币单位的设定与计量,“货币单位的这一物质符号的量,这一符号的数目就具有本质意义
。在马克思那里,货币是个人一般劳动的对象、劳动的目的,“生产一般财富,就是为了占有一般财富的代表”(47) 176。在此,货币是作为财富的一般等价物的身份出现的,财富的计量依赖于货币单位的设定与计量,“货币单位的这一物质符号的量,这一符号的数目就具有本质意义 。总体上来看,货币“在质的方面,或按其形式来说,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48) 156,即繁重而无效的劳动。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是现实财富的纯粹抽象,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只有当它重新投入流通,和特殊形式的财富相交换而消失的时候,才能够实现(49) 367。货币的贮藏手段和流通手段为财富的积累和发挥支配权提供了可能。
。总体上来看,货币“在质的方面,或按其形式来说,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48) 156,即繁重而无效的劳动。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是现实财富的纯粹抽象,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只有当它重新投入流通,和特殊形式的财富相交换而消失的时候,才能够实现(49) 367。货币的贮藏手段和流通手段为财富的积累和发挥支配权提供了可能。
在这里,马克思特别强调,“在货币上,商品的特殊性质消失了;一般财富作为精炼的概括而同财富在商品世界中的扩散和分散相对立。在特殊商品上,财富表现为商品的一个要素,或者说,商品表现为财富的一个特殊要素,而在金和银上,一般财富本身集中地表现在一种特殊物质上”(50) 172。但如果“把实在的金属货币(或者甚至是纸币,结果一样),简言之,把作为实在货币的价值的形式看成财富或发财致富的一般形式,那只是货币主义的幻想”(51) 101。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作为财富形式的货币,在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演进中发生了多次变化,金银在货币材料的竞争中胜出有其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通过批判布阿吉尔贝尔而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财富观:金“是‘万物的结晶’,是社会财富的概括。从形式上说,它是一般劳动的直接化身,从内容上说,它是一切现实劳动的总汇。它是表现为个体的一般财富,在作为流通的中介的形态上,金受到种种虐待,被刮削,甚至被贬低为纯粹象征性的纸片。但是,作为货币,金又恢复了它那金光灿烂的尊严。它从奴仆变成了主人,它从商品的区区帮手变成了商品的上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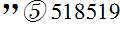 。金银之所以“变成了商品的上帝”,是因为金银的拥有者取得了对商品的支配权,金银的购买力象征着财富的权力,即财富反过来可以支配财富和劳动者。正是在货币上实现了财富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金银之所以“变成了商品的上帝”,是因为金银的拥有者取得了对商品的支配权,金银的购买力象征着财富的权力,即财富反过来可以支配财富和劳动者。正是在货币上实现了财富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在货币上,一般财富不但是形式,而且同时就是内容本身。可以说,财富的概念实现在一种特殊对象上了,个体化了。……在货币上,价格实现了,货币实体就是财富本身,后者既作为财富特殊存在方式的抽象,又作为财富总体。交换价值构成货币实体,交换价值就是财富。因此,另一方面,货币又是与构成财富的所有特殊实体相对立的财富的物体化形式。因此,如果就货币本身来考察,那么,一方面,在货币上,财富的形式和内容是同一的,另一方面,货币与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在它们面前是财富的一般形式,而这些特殊性的总体则构成财富的实体。根据前一规定,货币是财富本身,根据后一规定,货币是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这个总体作为想象的商品总汇存在于货币本身中。由此可见,财富(既作为总体又作为抽象的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其他一切商品被排斥,才作为个体化在金银上的财富而存在,作为个别的可以捉摸的对象而存在。因此,货币是商品中的上帝。……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形象,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 (52) 。
(52) 。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或者是一个个具体的交换价值,货币必然是一般人类劳动的产物,同时也是人类劳动手段的指代物,当然亦是劳动的目的。“劳动必须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必须直接生产货币。因此,劳动必须是雇佣劳动。因为每个人都想生产货币,所以致富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这种欲望创造了一般财富。因此,只有一般的致富欲望才能成为不断重新产生的一般财富的源泉。由于劳动是雇佣劳动,劳动的目的直接就是货币,所以一般财富就成为劳动的目的和对象。作为目的的货币在这里成了普遍勤劳的手段。生产一般财富,就是为了占有一般财富的代表。这样,真正的财富源泉就打开了。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揭示了货币转变为资本的奥秘。以货币形态存在的财富,只有在其拥有者雇佣到自由劳动者并将其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投入生产过程时,才能转变为获取增殖的资本财富。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揭示了货币转变为资本的奥秘。以货币形态存在的财富,只有在其拥有者雇佣到自由劳动者并将其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投入生产过程时,才能转变为获取增殖的资本财富。
资本形态的财富的逻辑起点是资本完成对劳动力的雇佣。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生产与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然而仅仅“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53) 171、198。在这里,马克思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作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54) 256,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创造建立在能够雇用到劳动力的资本与活劳动的结合的基础上。就资本而言,“资本吃掉这个果实以后,可以重新结出果实。它可以代表享用的财富,而并不失为财富一般形式的代表,这是简单流通中的货币不可能做到的。从前,货币必须实行禁欲,才能继续成为财富的一般形式;或者说,货币如果被用去购买现实的财富,被用于享受而耗尽,它就不再成为财富的一般形式” (55) 。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产生时作为前提的唯一积累,是货币财富的积累”(56) 166,资本家的货币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并非自然就转变为资本,“仅仅有了货币财富,甚至它取得某种统治地位,还不足以使它转化为资本”,因为资本的形成需要特殊的条件,即“要使货币财富有可能转化为资本,一方面,就要能找到自由的工人,另一方面,就要能找到这样的生活资料和材料等等,这些生活资料和材料原先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下是那些现已丧失自己客观条件的人们的财产,现在同样也变成自由的、可以出卖的了
(55) 。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产生时作为前提的唯一积累,是货币财富的积累”(56) 166,资本家的货币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并非自然就转变为资本,“仅仅有了货币财富,甚至它取得某种统治地位,还不足以使它转化为资本”,因为资本的形成需要特殊的条件,即“要使货币财富有可能转化为资本,一方面,就要能找到自由的工人,另一方面,就要能找到这样的生活资料和材料等等,这些生活资料和材料原先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下是那些现已丧失自己客观条件的人们的财产,现在同样也变成自由的、可以出卖的了 。于是,劳动的客观条件和活劳动本身都可以成为手握货币财富的资本家的交易对象了。当劳动的客观条件与活劳动本身相分离,就为货币财富转化为资本创造了可能。
。于是,劳动的客观条件和活劳动本身都可以成为手握货币财富的资本家的交易对象了。当劳动的客观条件与活劳动本身相分离,就为货币财富转化为资本创造了可能。
“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57) 198资本形成之后,“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 。进而,这一扩张力集中地表现在资本对他人劳动的役使和对他人财富的占有上,这构成了资本权力的基础。因此,财富的权力不仅表现在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资本形态上,资本的支配甚至统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权力的核心。在资本权力的支配下,资本的本性与财富贪欲天然地具有同一性。资本“作为财富,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作为起价值作用的价值而被固定下来的货币,是一种不断要超出自己的量的界限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过程。它自己的生命力只在于此;它只有不断地自行倍增,才能保持自己成为不同于使用价值的自为的交换价值”
。进而,这一扩张力集中地表现在资本对他人劳动的役使和对他人财富的占有上,这构成了资本权力的基础。因此,财富的权力不仅表现在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资本形态上,资本的支配甚至统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权力的核心。在资本权力的支配下,资本的本性与财富贪欲天然地具有同一性。资本“作为财富,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作为起价值作用的价值而被固定下来的货币,是一种不断要超出自己的量的界限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过程。它自己的生命力只在于此;它只有不断地自行倍增,才能保持自己成为不同于使用价值的自为的交换价值” (58) 。马克思的研究表明,资本具有内在的贪婪性和天然的扩张性,因而无法由其自身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悖论,即资源的稀缺性或有限性与资本逐利的无限性的矛盾。具体而言,“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即自我生产的货币了”。然而,现实社会生产积累的财富总量是有一定限度的,作为资本形式的财富投入再生产过程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一财富积累的有限性制约了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能力,”资本作为资本创造的是一定的剩余价值,因为它不能一下子生出无限的剩余价值
(58) 。马克思的研究表明,资本具有内在的贪婪性和天然的扩张性,因而无法由其自身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悖论,即资源的稀缺性或有限性与资本逐利的无限性的矛盾。具体而言,“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即自我生产的货币了”。然而,现实社会生产积累的财富总量是有一定限度的,作为资本形式的财富投入再生产过程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一财富积累的有限性制约了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能力,”资本作为资本创造的是一定的剩余价值,因为它不能一下子生出无限的剩余价值 。正因为现实社会资本积累的速度与程度远远无法满足资本内在的扩张欲望,资本积聚这一财富聚集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
。正因为现实社会资本积累的速度与程度远远无法满足资本内在的扩张欲望,资本积聚这一财富聚集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
从西方世界的发展轨迹来看,“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59) 43。可以说“没有资本,地产是死的、无价值的物质;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然而其结果表明,“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我们看到,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的力量”(60) 287、293。而“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对象化的死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 (61) 。因此马克思才会有社会的财富越大、相对过剩人口(多余人口)或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的感慨。
(61) 。因此马克思才会有社会的财富越大、相对过剩人口(多余人口)或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的感慨。
在现代国家,尽管财富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并且各种财富形态同时存在,但以资本为表现形式的财富日益成为最重要的和最具有支配力的财富形态。因为“从现实性来看,财富的发展只存在于这种对立之中;从可能性来看,财富的发展正是扬弃这种对立的可能性”,“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关系……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而在这种发展状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62) 380、593、286。由此可以认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并且“通过这种形式,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 。
。
可以认为,正是从“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这一辩证角度出发,马克思才科学分析了资本的本质及其“历史使命”,认为作为“现代形式”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必将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过程中成为历史的“被扬弃之点”。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这是因为,这种分离不仅使得“生产过程不断地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增殖手段和消费品”,而且工人本来应该是“财富的人身源泉”,却“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63) 658,这亦是资本逻辑的起点。
社会财富的分配中,资本拥有绝对的权力。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社会财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更不平衡了”,导致“横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了”(64) 495、497,因而马克思总结道,“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资本不仅像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态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65) 338、61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以往一切生产方式的地方,正在于资本的扩张本性,对资本来说,“发财致富就是目的本身。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 (66) 。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创造的目的与获取财富的手段发生错位甚至倒置。
(66) 。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创造的目的与获取财富的手段发生错位甚至倒置。
资本财富的权力导致财富分配上的对立。马克思指出:“物质财富的对立的社会规定性,——物质财富同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之间的对立,——离开生产过程,已经表现在资本所有权本身中”(67) 398,“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68) 130而资本所有权的获得,“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断产生的结果,并且作为这样的结果又是它的不断存在的前提;这个要素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现在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货币,商品也一样,自在地,潜在地,在可能性上是资本,它们能够作为资本出售,并且以这个形式支配他人的劳动,要求占有他人劳动的要求,因而是自行增殖的价值。这里也清楚地表明了:占有他人劳动的根据和手段,就是这种关系,而不是资本家方面提供的任何作为对等价值的劳动” 。作为这一趋势的后果,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作为这一趋势的后果,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 ,换句话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69) 156。并且,由人类劳动所具有的社会劳动的属性,“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70) 430。这事实上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财富的主体结构发生了资产阶级财富累与劳动者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
,换句话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69) 156。并且,由人类劳动所具有的社会劳动的属性,“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70) 430。这事实上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财富的主体结构发生了资产阶级财富累与劳动者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
除生产劳动对资产阶级的财富积聚的影响之外,“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和抵押的产生,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这同样造成了这样的一种后果,即“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71) 187。(https://www.xing528.com)
(三) 财富能力的提升:科学进步抑或资本对科学的驾驭
在马克思看来,“单是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科学“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的发展”,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72) 539。财富是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或者说劳动实践的产物,因此可以认为,物质财富的形成都包含着人类智慧的凝结,或者说包含科学技术工艺的因素。马克思评价道:“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73) 172。人类进入大生产以后,财富尺度是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而不再是此前的劳动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是在同剩余劳动时间相的对立中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实际上产生了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对立,“直接劳动时间的量,作为财富生产决定因素的已耗费的劳动量。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运用”(74) 104、100。在马克思那里,“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在一方创造出剩余劳动,所以在另一方才创造出非劳动和剩余财富”(75) 86。
那么,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怎么来?在马克思看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推升的劳动生产率是重要的手段,“资本积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对原资本或已经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发生反作用”(76) 697、698。科学技术作为精神财富或精神生产的典型代表,其最大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不仅是社会财富生产的结果,而且能够反过来成为社会财富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巨大的力量。科学既是财富创造的成果和沉淀的形式,又形成和积累为财富创造的工具和能力,财富创造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发展水平。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得到较为充分的阐述。此后的研究中,尤其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转而从经济学的实证层面,研究了科学技术对于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作用与意义。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因素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因素并入资本——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 。
。
科学技术原本是财富生产过程中的产物和生产条件,“科学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独立力量这一范畴。并且正是科学的这种分离和独立(最初只是对资本有利),同时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 (77) 。基于科学技术的工具性力量,资本把构成物化劳动的一些要素——如自然资源、自然力、科学技术和社会力等——直接变成了与活劳动对立的工具,造成活劳动受物化劳动的支配和奴役,“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
(77) 。基于科学技术的工具性力量,资本把构成物化劳动的一些要素——如自然资源、自然力、科学技术和社会力等——直接变成了与活劳动对立的工具,造成活劳动受物化劳动的支配和奴役,“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 。正是资本的统治能力,使得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被资本所雇佣的财富创造的重要手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由于大量采用了机器等先进工具和适应机器生产的组织体制,这些由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超额剩余价值促使资本家持续进行不变的资本投资,其结果造成机器对普通劳动者的代替,机器力对活劳动的替代,在这里,“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其中,“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
。正是资本的统治能力,使得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被资本所雇佣的财富创造的重要手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由于大量采用了机器等先进工具和适应机器生产的组织体制,这些由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超额剩余价值促使资本家持续进行不变的资本投资,其结果造成机器对普通劳动者的代替,机器力对活劳动的替代,在这里,“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其中,“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 ,进而“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78) 427,“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
,进而“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78) 427,“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 。
。
马克思也关注到分工对财富生产的重要性。他提出,“关于分工的性质——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不得不被理解为财富生产的一个主要动力”,“分工和使用机器也决定着财富从而决定着产品的大量生产,”“分工对于社会财富来说是一个方便的、有用的手段”(79) 353、357。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马克思认为更重要的是,分工“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 。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外溢效应,最直接地表现在生产效率的提升上,从而为节约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创造条件,因而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化大生产中。
。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外溢效应,最直接地表现在生产效率的提升上,从而为节约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创造条件,因而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化大生产中。
在财富创造的进程中,科学技术改进了投入要素的劳动效率,但正如劳动力依附于资本一样,科学技术同样依附于资本。科学技术已经把活劳动变成了“只不过是死劳动的一个有意识的器官”,不仅“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且“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功能”,“正像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资本的形式无代价地合并了在它的旧形式不近情理实现的社会进步”(80) 699。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协作中的集体统一,分工中的结合,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表现为机器的劳动产品的应用”,“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被运用于实践的科学——但是,这只是通过使劳动从属于资本,只是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81) 537、363、538,由此,资本实现了对作为工具手段的科学技术与作为社会进步目标的科学技术的支配。
(四) 财富的本质:从劳动时间到自由时间
财富的本质问题,实际上是财富及财富生产所反映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把财富换算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进而转化为货币数量符号,具有标志性的社会历史意义。在人类社会迄今的多数发展阶段,积累货币财富至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目标和动机,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国家,皆是如此。就这一趋势出现的结果,马克思认为,“货币的量越来越成为货币的惟一强有力的属性;正像货币把任何存在物都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货币也在它自己的运动中把自身归结为量的存在物。”(82) 339进而,“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预备时期,是以个人的和国家的普遍货币欲开始的。财富源泉的真正开辟,作为取得财富代表的手段,似乎是在具有货币欲的个人和国家的背后进行的”(83) 177。只要存在着交换,货币就最终成为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化身。
恩格斯认为:“财产,同人的、精神的要素相对立的自然的、无精神内容的要素被捧上宝座,最后,为了完成这种外在化,金钱、财产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84) 534、544。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成为完备的形式,在财富的表现形式上亦由货币财富拓展为资本财富。在马克思看来, “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 。
。
马克思不仅仅把目光停留在财富的具体形式上,更重要的是,他从财富的具体的物质的形式中抽象出财富的社会形式。马克思高度评价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提出的把资产阶级经济学称为“发财致富的科学”(85) 413,进而,马克思不仅从社会性的角度探讨了财富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而且从历史性的角度探讨了财富与人的自由发展之间的关系,由此,马克思实现了财富的“对象性本质”与“主体本质”的统一(86) 4、25。
在马克思看来,财富首先是一种物质产品,物质产品的生产与物质财富的创造始终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动因,进而,生产过程是物质生产与价值增值的统一,财富实际上体现为一种价值关系,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方面,财富是物,它体现在人作为主体与之相对应的那种物及物质产品中;另一方面,财富作为价值,是对他人劳动的单纯支配权,不过不是以统治为目的,而是以私人享受等等为目的。在所有这一切形式中,财富进取心物的形态出现,不管它是物也好,还是以存在于个人之外并偶然地同他并存的物为中介的关系也好。……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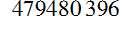 (87) 。“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88) 520因此,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来审视,财富的本质属性是价值,体现为一种社会的价值关系——建立在物的关系上的人与人之间关系。
(87) 。“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88) 520因此,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来审视,财富的本质属性是价值,体现为一种社会的价值关系——建立在物的关系上的人与人之间关系。
那么,作为衡量财富指针的价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马克思进而指出,“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这一矛盾的存在促使资本家“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生死攸关的问题,”在手段上,“一方面,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89) 197。
资本唤起的“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理论上包含着剩余价值生产中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马克思进而论证科学成为财富的形式,衡量财富的尺度由劳动时间转变为科学技术,实际上要阐述他所坚持的自由时间在财富创造中的地位,也就是说,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财富——或者只能说的生活必需品——是维持劳动者生存所必需的,只有自由时间才是衡量财富的高级的尺度,而“创造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财富整个发展的基础”(90) 376。他指出,“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这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对别人劳动时间里创造出来的东西的享受,都表现为真正的财富” (91) 。他甚至援引查·迪尔克在《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中提出的观点:“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财富〈现实的财富〉不是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支配,而是除了耗费在直接生产上面的时间以外,每一个个人和整个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92) 197 他强调,“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
(91) 。他甚至援引查·迪尔克在《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中提出的观点:“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财富〈现实的财富〉不是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支配,而是除了耗费在直接生产上面的时间以外,每一个个人和整个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92) 197 他强调,“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 ,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是在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中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
,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是在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中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 。由此,即使工人勤奋且辛劳,他依然未能摆脱剩余劳动时间对自由支配时间的侵占,也就依然无法摆脱贫困的境地。
。由此,即使工人勤奋且辛劳,他依然未能摆脱剩余劳动时间对自由支配时间的侵占,也就依然无法摆脱贫困的境地。
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马克思认为,“剩余劳动时间不仅创造他们的物质基础,而且同时创造他们的自由时间,创造他们的发展的范围”,“剩余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从而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93) 217、257。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把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两种形式的财富,即以物质基础形式存在的财富——单纯的物的维度的财富和以自由时间形式存在的财富——主体发展维度的财富联系起来进行了论述,因而意味着剩余劳动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着人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自由时间。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人的发展的最终目的,也可以是在创造财富的实践活动中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的发展的最终目的,也可以是在创造财富的实践活动中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从劳动主体出发,把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看成人的最原始、最根本的财富,即人的主体生产力,他担忧工人自身变成了机器和生产组织体制的一个简单的零件。这种令马克思担忧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精辟地指出:“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
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 (94) 。财富形成的基础也表现为一种能力,财富创造的方式就是对能力的一种运用,即财富的创造既消耗了人的各式劳动,又为人的自身的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提供了消费品,而人在创造财富的活动中增进了自身的能力及能力运用的水准。正是财富本身和财富创造的进程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马克思正确处理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且始终把财富生产与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联系起来进行考查。马克思在不同语境下多次提到,“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95) 104,“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96) 127;“财富不过是通向真正人的现实的道路“(97) 319。这大概是马克思研究财富问题的旨趣。
(94) 。财富形成的基础也表现为一种能力,财富创造的方式就是对能力的一种运用,即财富的创造既消耗了人的各式劳动,又为人的自身的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提供了消费品,而人在创造财富的活动中增进了自身的能力及能力运用的水准。正是财富本身和财富创造的进程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马克思正确处理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且始终把财富生产与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联系起来进行考查。马克思在不同语境下多次提到,“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95) 104,“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96) 127;“财富不过是通向真正人的现实的道路“(97) 319。这大概是马克思研究财富问题的旨趣。
(五) 财富形态演变的趋势
从总体上来看,财富形态的演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随着分工的发展,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提高,商品生产与交换也因此得以极大发展,商品的剩余与积累也逐渐增加,远距离贸易也大量出现。货币的产生在成为交易媒介的同时,也成为财富的一般代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只表示财富的一个极其个别化的方面,与此相反,在货币上,价格实现了,货币实体就是财富本身……交换价值构成货币实体,交换价值就是财富。因此,另一方面,货币又是与构成财富的所有特殊实体相对立的财富的物化形式……货币是财
富的一般物质代表”(98) 173。近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财富代表的货币经历了实物货币(例如贝币、各种金属货币)——纸币——虚拟货币的阶段性演进过程。财富的社会功能则经历了储藏与消费(例如西班牙王室对金银的奢侈性消费)——投资性消费(作为资本的财富)——投机性消费(例如层出不穷的虚拟货币、电子货币、金融衍生品)的阶段性演进过程。总体上的一个趋势是,货币的名义价值逐渐与财富的实际价值相分离,财富的实物形态逐渐转化为“数字”“符号”等虚拟形态。
马克思在研究物质财富时很自然地也研究了精神财富问题。他认为,精神财富不过是社会财富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是物质财富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是人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的必然结果。他指出:在人类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99) 412。马克思更多地是从精神财富生产对物资财富生产的作用上来看待精神财富的。马克思认为,精神财富的生产,是“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变成的东西,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 ,亦即“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活动就是由这两者决定的,进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因此,在理解“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时,必须“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而“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否则,“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100) 346。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精神财富亦是财富的一种虚拟的形态,但这种虚拟的形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主观评价。考察人的精神活动和精神财富生产必须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与人的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因精神财富的生成机理、计量方式等尚需要深入研究,故而本书不讨论专门的精神财富的生产。
,亦即“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活动就是由这两者决定的,进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因此,在理解“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时,必须“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而“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否则,“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100) 346。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精神财富亦是财富的一种虚拟的形态,但这种虚拟的形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主观评价。考察人的精神活动和精神财富生产必须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与人的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因精神财富的生成机理、计量方式等尚需要深入研究,故而本书不讨论专门的精神财富的生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