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唐建中元年(780年)实行的两税法包括地税、户税两部分。地税的征收以田亩的多寡为据,户税的征收以户等的高低为本。定户等的标准则是“量其资产”,“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1) 这里,据以定户的资产是否包括奴婢?占有奴婢与交纳户税有什么关系?史书中有关两税的令文未作明确交待,治唐史者亦尚未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为此,就所见资料提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
两税的征收是以资产为宗的,因此,要搞清楚两税与占有奴婢的关系,首先应搞清楚唐代奴婢的属性,即唐代奴婢是否属于资产。然后说明其与户等的关系。为此,我们不能不从唐代以前的情况谈起。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是被压迫、被剥削的主要阶级,“奴隶不仅不是公民,而且不算是人”(2) 。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毫无生命保障,可以被任意买卖、转让、屠戳。因此,奴隶的财产属性是无须多言的。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奴婢的身份、地位有所提高,奴婢所有者已不能任意杀害奴婢了。东汉即有“杀奴婢不得减罪”的规定,(3) 但总的看,奴婢被视作财产这一点,并没有根本变化。汉代“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4) 。在居延汉简中,更有奴婢作为家资计算的明确记载。如《居延汉简甲乙编》三七·三五(乙叁贰版)载,“候长觻所得广昌里公乘礼忠年卅,小奴二人,直三万。用马五匹,直二万。宅一区,万。大婢一人,二万。牛车二两,直四千,田五顷,五万。轺车两乘,直万。服牛二,六千。凡赀直十五万”。在这个财产登记簿里,“货直”共十五万,其中即包括了三名奴婢作为财产的五万。显然,这里奴婢是被视作财产的。
这点还可以从四川郸县出土的东汉残碑碑文得到进一步证明,其碑文中有这样的记载:“王岑田□□,直□□万五千。奴田、婢口、奴多、奴白、奴鼠并五人……田顷五十亩,直卅万。何广田八十亩,质□□五千。奴田、□□、□生、婢小、奴生,并五人,直廿万。牛一头,万五千。”“故杨汉□□□奴主、奴□、□鼠共五人,直廿万。牛一头,万五千。”(5) 这里,奴婢同田地、牛并列在一起,并标明价格,显然也是作为资产来计算的。
汉代征收的财产税亦包括了奴婢,例汉武帝“伐四夷、国用不足,故税民田宅、船乘、畜产、奴婢等”(6) 。可见,汉代奴婢确属财产无疑。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已,更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带来了落后的生产关系,奴婢数量仍然很多。当时地主官僚无不争相扩大自己的奴婢队伍。
占有奴婢的多寡成为当时衡量财产的一个重要标志。如《南史·沈庆之》传载:“(沈庆之)家产累万金,奴僮千计”;《北史·薛辩传》载:“辩家素富,僮仆数百人”;《魏书·高崇传》载:“(高崇)家资富厚,僮仆千余。”当时的统治者还常常将奴婢连同牛马等财产赏与臣下,如《北史·陆腾传》载:“(陆腾)凡赏得奴婢八百口,马牛称是。”《南史·萧景传》载,梁朝萧励进攻俚族,“所获生口宝物,军赏之外,悉送还台。”可见奴婢也同宝物一起用来军赏。
在这一历史时期,固然有些奴婢身份在向佃客转化,但就相当多数的奴婢来说,在法定的意义上无疑仍属财产之列。当时政府所征的财产税、交易税都包括了奴婢。例如南朝“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历宋、齐、梁、陈以为常”(7) 。有些日本学者如堀敏一氏甚至认为只是到了魏晋以后,奴婢是“物”的观念才固定下来。(8)
唐以前诸代奴婢的资产属性,为唐代的奴婢制度所沿袭和继承。从现有史料来看,唐代奴婢无论是在法律规定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都具有资产的属性。
现存唐代法典《唐律疏议》,明确规定了奴婢的财产属性:“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奴婢畜产,类同资财”(9) 。“生产藩息者,谓婢产子、马生驹之类。”(10) “奴婢同于资财,不从缘坐免法。”(11) “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12) “奴婢同资财,故不别言。”(13) 类似条文还有很多。可以说,唐代奴婢在法律上的财产属性是再清楚不过了。
从唐代社会的实际生活来看,奴婢也的确是被视作财产的。敦煌文书中,有一件编号为S4374/b5941的唐代分家书样文,其中说道:“家资产业,对面分张;地舍园林,人收半分。”在谈到具体资财时,列有“车、牛、羊、驼马、驼畜,奴婢、庄园、舍宅、田地乡籍、渠道四至”等等,并说:“右件家产,并以平量,更无偏党丝发差殊。”(14) 从这个分家样文所列的财产来看,在唐人的观念中,奴婢是属于“家资产业”之列的。而且从各种家产的排列顺序来看,(由轻到重,)唐人是把奴婢视作仅次于田产房舍的“重物”的。
在编号为S2199/b7570的另一件敦煌文书中,有一份唐咸通六年(865年)敦煌僧尼灵惠处理身后财产的遗嘱,文中曰:“灵惠只有家生婢子一名威娘,留与侄女潘娘,更无房赀。灵惠迁变之日,一仰侄女潘娘葬送营办、以后更不许诸亲悕获,恐后无凭,并对诸亲,遂作唯书,押署为验。”(15) 遗嘱中“更无房贫”一语,明言家生婢威娘便是唯一家货。
在史籍中,我们也可以见到类似记载,如刘弘基病危,“给诸子奴婢各十五人、田五顷,谓所亲曰:使贤,固不籍多财,即不贤,守此可以脱饥冻。”这里所讲的财,显然也包括奴婢。在唐代的交易市场上,奴婢也是与牛马驴骡同处口马行的。敦煌文书中就有《唐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估》,详细规定了不同等级的奴婢、马匹的价格。唐代地主官僚之间相互赠送财产物品时,亦往往包括奴婢。凡犯罪之家,其家产被籍没时,亦包括了奴婢。
以上事实说明:无论是从历史的传统来看,还是从唐代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奴婢都具有财产的属性。两税中的户税既然以资产作为划分户等的依据,那么占有奴婢理应与户等的判定、户税的交纳有直接关系。
二
唐代民户的等级,高祖武德六年(623年)规定,“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三等”。至武德九年(626年),又重新划分为九等。(16) 定户等的原则是:“量其资产,类其强弱,定为九等,其户皆三年一定,以入籍帐。”(17) 天宝四载(745年),唐玄宗敕令,“自今以后,每至定户之时,宜委县令与村乡对定,审于众议,察以资财,不得容有爱憎,以为高下,徇其虚妄,令不均平。使每等之中,皆称允当”(18) 。从这些原则的规定可以知道,唐代民户的等级皆三年一定,定户等的依据主要是“资财”。至于资财包括了哪些内容,具体讲是否包括了奴婢,史籍的记载是不甚清楚的。所幸近年在新疆吐鲁番509号唐墓中出土了一件《唐开元廿一年西州蒲昌县户等案卷》,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兹摘引此文书的B、C断片如下:(19)
(B断片)
1. 蒲昌县
2. 当县定户
3. 右奉处分,今年定户,进降须平,仰父老等
4. 通状过者。但蒲昌小县,百姓不多,明府
5. 对乡城父老等定户,并无屈滞,人无怨词。
6. 皆得均平,谨录状上。(后欠)
(C断片)
1. 肆户下上户
2. 户韩君行,年七十二,老。 部曲,知富,年廿九。宅一区,莱园坞舍一所。
3. 车牛两乘, 青小麦捌硕,廪粟肆拾硕。
4. 户宋克隽, 年十六,中。 婢叶力,年卅五,丁,宅一区,菜园一亩,车牛一乘。
5. 牡牛大小二头,青小麦伍硕,廪粟拾硕。
6. 户范小义,年廿三, 五品孙。 弟思权,年十九。婢柳芸,年七十,老,宅一区。
7. 廪粟拾硕。
8. 户张君政,年卌七,卫士。 男小钦,年廿一,白丁,赁房住,廪粟伍硕。
9. 已上并依县 (后欠)
对于这个定户等簿的性质,不少学者已进行了研究,认定此系开元廿一年蒲昌县官府与乡城父老对定户等后向州呈报、州司详覆后予以批复的牒文。这里,我们主要对其中贱口、主要是奴婢与定户的关系进行探讨。
定簿的C断片是随牒文一同呈报的附件,虽然文书已断残,但四户下上户一组完整无缺,详细记载了户主姓名、年龄、劳力、园宅、车、畜、小麦、廪粟等,其中也包括了部曲、奴婢。文书中韩君行户有部曲一人,名知富,年二十九。宋克隽户有婢一人,名叶力,年三十五,丁。范小义户,有婢一人,名柳芸,年七十,老。这里登录的三名贱口,与户等之间有什么联系?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认为:“每户登载户主姓名和户内的丁中男及部曲、婢,不外是区其强弱,而登录宅、园田、车、牛、谷,乃是计算其资产,这可以说是一目了然。”(20) 池田氏认为部曲、奴婢与“区其强弱有关”,这一见解是无误的,但他将奴婢排除在资产之外,这恐怕值得讨论。
分析一下定簿,我们可以看出,定簿中除了户主及丁男、中男以外,凡女子、老男、黄男、小男皆未登录。这是因为,制定九等定簿的目的是为了根据户等确定差科的数量和先后,与差科无关的人口没有必要登录(四户之中除了户主丁中以外,不可能别无妇女、老小),按此分析三名贱口,部曲知富年二十九,属成丁部曲;婢叶力,年三十五,属丁婢。从考察其劳力强弱的角度看或可登录,但范小义家婢柳芸,年已七十,属于老婢,如果仅从考察劳力强弱的角度看,完全没有必要登录。假如需要登录,四户中其他老口、妇女及黄小为何都没有登录?史籍中我们还没有见到七十岁的老妇仍然按劳动力计算的先例。因此答案只能是婢柳芸作为财产进行了登录。由此分析婢芸力,显然也是作为财产进行登录的。正由于奴婢是财产,所以在对定户等时,不受年龄、性别的限制,一概登录。至于部曲知富,因唐律明文规定“部曲不同资财”,所以,有可能仅是作为劳动力而登录的。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奴婢既然属于资产,那为什么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奴婢都注入民籍、乡账?(21) 又为什么在上面九等定簿和其他些文书中,奴婢都像良人一样明确地区分为黄、小、中、丁、老?这是否意味着唐代定户等时奴婢并不被当作财产看待?
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应当从奴婢这一“财产”的特殊性来考察。首先,奴婢虽具有财产属性,但在封建制度高度发展的唐代社会中,奴婢毕竟是封建政府控制下的属民。法律明确规定其为贱人,还并不等于说奴婢“非民”,统治阶级出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的考虑,有必要掌握全国贱口包括奴婢总的情况。有唐一代,唐政府关于奴婢问题的大量诏敕,显然是在掌握奴婢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发布的。(22) 因此,奴婢计入民籍,是统治阶级统治的需要。日本有些学者据此认为唐代奴婢具有“半人半物”的性质,是不无道理的。(23)
其次,奴婢虽属资产之列,但他们并不一般地等同于其他资产。奴婢的价值就在于他能够为主人劳动,能够创造财富。从这点来说,奴婢本身劳动能力的强弱,反映了他本身价值的高低。而区别奴婢劳动能力强弱最一般、最可靠的方法,则是从人体生理发展的角度将其区分为黄、小、中、丁、老,这点也可以从敦煌文书中得到证明。敦煌文书中曾出有一份《唐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沽》,其全文如下:(24)
[前缺]
1. 上家生中婢壹口
2. 上蕃丁奴壹口 直钱肆拾 


3. 上蕃中奴壹口 直叁拾伍仟文 次叁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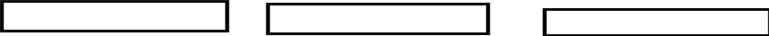
4. 上蕃丁婢壹口 直钱叁拾仟文 次贰拾伍仟文,下贰拾仟文
5. 上蕃中婢壹口 直钱贰拾柒仟文 次贰拾伍仟文
6. 上家生细敦父马壹匹直柒拾仟文 次陆拾伍仟文
7. 上家生□敦父马壹匹 直贰拾叁□□次贰拾壹□□ [后缺]
从这件唐代市场上奴婢马匹的价目单可见,奴婢之分为丁中,目的是为了根据奴婢的劳动能力,确定奴婢的身价。文书中丁奴身价高于中奴,丁婢身价高于中婢,其原因正在于丁奴婢的劳动能力高于中奴婢。因此,奴婢按丁中制进行登录,与奴婢的资产属性并不矛盾。实际上,也只有将奴婢区分为黄、小、中、丁、老,官府才能在与民户对定户等时,确定奴婢劳动能力的强弱,亦即确定奴婢作为资产计算时价值的高低,从而定出比较合理、公允的户等。
在上面所引九等定簿的四户下上户中,三户拥有奴婢或部曲。这说明在西州的七等或七等以上户中,拥有奴婢或部曲的民户还是为数不少的。笔者曾对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下中户和下下户的占奴婢情况进行过统计。下列表一是家口齐全的十七户下中户的情况:
表一 唐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中部分下中户占有奴婢情况
续 表
上表十七户下中户中,占有奴婢的仅有索思礼一户,其他户均无奴婢。下列表二是家口齐全的三十三户下下户的情况:(25)
表二 唐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中部分下下户占有奴婢情况
续 表
该表二十二户下下户中,没有一户拥有奴婢。
由上可见,唐代敦煌吐鲁番地区占有奴婢或部曲的,一般都是在七等户以上人家。八等户占有奴婢的仅属个别,九等户占有奴婢的基本不存在。在吐鲁番文书中,还有不少占有数个奴婢的民户,(例《唐贞观十四年李石住等手实》《唐西州高沙弥等户家口籍》所反映的情况)(26) 由于文书残缺,已不能确定其户等,但正像唐长孺先生分析的那样,这些民户,通常也不是一般的农户,而是户等较高者。(27)
能够证明占有奴婢与户等的确有关的证据还可以找到一些,例吐鲁番阿斯塔那三十五号唐墓曾出有《武周先漏新附部曲客女奴婢名籍》,这份名籍中记载了许多此前不附籍账的贱口,现将其列成表三:(28)
表三 吐鲁番出土《唐武周先漏新附部曲客女奴婢名籍》
在《武周先漏新附部曲客女奴婢名籍》文书中,有数处明确记有:“右件口并漏,已从寄庄处通□□□……”,“右件口并漏,寄庄已从□□□□”,“右件部曲、客女奴婢先漏不附籍账。今并见在,请从手实为定,件录年名如前”等字句。这样多的奴婢漏附籍账,显然不是由于一时大意疏忽。按唐代均田时期,奴婢不受田、不纳课,地主、官僚之所以要隐瞒自己的贱口,其目的无非是为了降低自己的户等以求减轻差科负担。这说明占有奴婢的多寡确与户等的高低有关(因劳力的强弱是定户的根据之—,所以部曲、客女也在地主隐瞒的贱口之列)。
虽然我们上面所用的资料基本都是唐代前期的,但实际上唐代两税法以前判定户等的原则到实行两税法时,并没有大的改变。在两税法下,定户等的财产同样包括了奴婢。在占有其他资产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占有奴婢愈多,其户等必然愈高,相应地其应交纳的户税钱也就愈多。
二
上面我们论证了奴婢与定户等的关系,那么在史籍中有没有关于两税法下奴婢需要纳资产税的比较明确的记载呢?笔者认为还是存在的。
《文苑英华》卷四八三《策》部,载有唐宪宗时左拾遗独孤郁的《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其文曰:“今天下困于商税不均可谓甚矣,百姓之忘本十而九矣。昔尝有人有良田千亩,柔桑千本,居室百堵,牛羊千蹄,奴婢千指,其税不下七万钱矣。然而不下三四年,桑田为墟,居室崩坏,羊犬奴婢十不余一,而公家之税曾不稍蠲,督责鞭笞,死亡而后已。”
查《旧唐书》本传,独孤郁乃唐宪宗时常州刺史独孤及之子,“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元和初,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入第四等”(29)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载:“元和元年三月丙午,策试制举之士,于是校书郎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校书郎下邽白居易、前进士萧 、沈传师出焉。”由此可知,独孤郁策文作于元和元年(806年)三月,即唐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二十六年之后。对策文中没有提到两税,却提到了商税,根据对策文内容及其历史背景的分析,笔者认为此“商”字系“两”字之误,根据如下:
、沈传师出焉。”由此可知,独孤郁策文作于元和元年(806年)三月,即唐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二十六年之后。对策文中没有提到两税,却提到了商税,根据对策文内容及其历史背景的分析,笔者认为此“商”字系“两”字之误,根据如下:
其一,独孤郁策文中谈到“百姓忘本十而九矣”,百姓为什么会忘本呢?这显然是由于与农业直接有关的土地税和户税太重造成的,与商税不均无关。按两税法规定“为行商者,在所在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不久,又“以军兴,增商税为什一”(30) 。后来商税虽有变化,但除了盐税之外(策文所讲显然不指盐税),并不存在商税过重或严重不均的问题。在史书中,我们并未见到贞元、元和年间商税不均的记载,却看到贞元、元和年间两税不断加重的情况。例如,两税法始立,户钱多折绫绢,初时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三百文。而到贞元十年(794年)左右,纳绢一匹,只当钱一千五六百文,户税钱数虽末变,而两税实际提高一倍。(31) 到元和十四年,绢价落到初定两税时的三分之一,纳税户的负担实际增加了三倍。(32) 此外,两税外加税的现象也日益严重。独孤郁对策文作于元和元年,所说情况显然是指两税,而非商税。
其二,策文接着谈道:“昔有人有良田千亩,柔桑千本,居室百堵,牛羊千蹄,奴婢千指,其税不下七万钱。”这里所提到的良田、柔桑、居室、牛羊、奴婢,无一属商业性质的产业。假如是商税,不能没有店铺、商品、货币等资财。由此可见,这里所纳七万钱,乃是“田亩之税”和“财产之税”,而不是商税。
其三,独孤郁在对策文中还谈到赋税不均的几个原因:第一,地方官吏将逃户之赋,“均其所存”,以至农户“展转奔逃……是以赋益重而人益贫,不均之甚一也”(33) 。这与陆贽奏议中所说两税摊逃的情况是—致的。第二,商人“乘时射利,贸迁有无,取倍息之利”,而农夫“尽悴出赋”,“糠麸不足”。这里尽悴出赋的是农夫,取倍息之利的是商人。联系前面所讲,赋税不均显然是指两税,而不是商税。第三,“自兵革以来,人多流散……屋室聚为瓦砾,田野俱为榛芜,赋税不均,居者日困,又为此也”。随后,独孤郁建议:“是故欲人之财赋均一,而无日蹙之患,宜视通邑之盈虚,使乡户坐乎(于)田,迭相隐覆其上下,不使贪官赃吏纷动其间,则有无轻重可得而均也。诚能宽农人之征而优之”,“禁人为商,以反其耕绢(织)”,“杜众邪之门而因辱之,则农桑益而衣食有余也”。可见,赋税不均是指两税,而非商税。
其四,与独孤郁同应制举的元稹,在同一策目答文中也一再提到“惰游之户转增,而耕桑之赋愈重。昔时之十室共输而犹不给者,今且数家一夫矣”。“赋重则恋本之心薄,惰游之户众”。(34) 白居易在同一策目答文中亦指出农户赋税不均的问题。(https://www.xing528.com)
其五,“两”字在字形上与“商”字是比较接近的,在历代辗转抄刻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将独孤郁对策文中的“两”字误为“商”字。亦有可能是无识文人的误改,《文苑英华》中,类似这样的误字、错字现象是屡见不鲜的。
以上事实说明,独孤郁对策文中的“商税不均”应是“两税不均”之误。因而证明了两税法下,占有奴婢如同占有田产房屋牛马一样,是要交纳资产税的,占有奴婢愈多所纳户税也就愈多。七万税钱中,“奴婢千指”的资产税能占多大比重,这是难以搞清楚的。但我们知道,唐代中后期,奴婢作为财产计算的价值是比较高的,这从唐代奴婢的价格便可反映出来。天宝年间一婢可以折合十牛。(35) 唐朝后期奴婢的价格,据笔者大略的考证,一般都在二十万到四五十万钱之间,折合绢约二百五十至五百匹。(36) 奴婢是仅次于田产房舍的资财。因此,在九等定户和户税的征收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恐怕是没有疑问的。
独孤郁对策文中所讲的人和事可能是虚构的,可是,其反应的事实必然是以唐代两税法时期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的。独孤郁出身官僚世家,熟谙唐代典章制度,不至于把奴婢是否属于定户纳税的资产搞不清楚。(37) 这方面,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的证据。例如唐德宗时,以军费不足,行借商钱,规定商人“留万贯为业,有余官借以给军”,“京师嚣然,如被贼盗,都计富户田宅奴婢等估,才及八十八万贯”。(38) 据《资治通鉴》记载,此次行借商钱在建中三年(782年)四月,距实行两税法的建中元年(780年)只隔一年。(39) 商人的估产既然包括了奴婢,那么两税法中的户税在计算财产时,肯定也不会将奴婢排除在财产之外。
三
上面我们重点讨论了占有奴婢与户等、户税的关系。现在进一步探讨两税法的实行对奴婢阶层的影响,这需要从魏晋以来奴婢与赋税的关系谈起。
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赋税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以人丁为本”,即以丁、以口、以户为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而按土地、按财产、按户等所征收的赋税只占很小比重。魏晋时期的户调制、南朝后期的丁调制基本都是不问资产,按户、按口征敛的赋税。占有奴婢的多寡与交纳赋税的多少关系不大。唐朝前期“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40) ,按户等征收的户税、地税只不过是正赋的补充。因此,从赋税的角度来看,地主官僚占有奴婢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赋税相应地提高。(买卖奴婢的交易税除外)
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北魏到唐前期实行均田制时期,占有奴婢与交纳赋税的关系。北魏太和九年均田令规定:“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诸还受之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卖买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还受”。(41) 所谓奴婢受田,其田土当然属奴婢主人所有。从上面规定可见,奴婢受田数,同于良人。有奴婢则受田,无奴婢则还田。同一均田令还规定,奴婢亦须交纳租调:“奴任耕婢任织者,八口当末娶者四”。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即帛一匹,粟二石。这个数量与奴婢主占有八名奴婢可以获得的土地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八名奴婢,且以四奴四婢计之,每奴受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四奴应受田二百四十亩。每婢受露田二十亩,四婢应受田八十亩,如果再将露田加一倍计算,那么四奴四婢合计可受田五百六十亩。五百六十亩土地只需交纳二石粟、一匹帛,占有奴婢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按占有奴婢的多少受田,扩大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最大限度地照顾了那些占有大量奴婢的地主官僚和贵族的利益,这从北齐《关东风俗传》的记载便可得知:“广占者,依令,奴婢请田,亦与良人相似。以无田之良口,比有地之奴牛。宋世良天保中献书,请以富家(奴)(42) 牛地,先给贫人,其时朝列,称其合理。”(43)
北齐时期,随着土地的不断开辟,可用于还受的土地愈来愈少,因而无限制地以奴婢名义占田,必然要影响到小农的利益和国家的税收。北齐河清三年(564年),均田令对据以受田的奴婢数量作了一定限制:“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止—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下)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以上限止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给田者皆不输。”(44) 虽有如此的限制,但即使是按六十个奴婢来计算,奴婢主人可以得到的田土仍是相当可观的。如果说地主官僚不是对以奴婢的名义受田有兴趣,统治者做出这样的强制性规定就很难理解了。
当然,正像我们在前文所论,均田制下的授田并不一定是实际授予土地,它主要是一个可以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但这一点对地主来说依然十分重要,因为有了足够的“受田”数量,地主的私有土地即可以得到合法承认,甚或得到进一步兼并土地、扩大土地占有的权利。
隋代均田令没有明确记载奴婢是否受田,但据隋炀帝“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45) 的情况来看,隋朝前期,奴婢仍然可以受田,至炀帝时可能停止了。
唐代的均田令明确取消了奴婢受田的规定,占有奴婢已不能像过去一样相应地占有大量土地了。这使占有奴婢的经济意义下降了。但从榨取奴婢的无偿劳动及占有奴婢几乎不需要交纳赋税这一点来看(户税仅是辅助税),占有奴婢仍是有利可图的。
由上可见,魏晋直到唐朝前期,占有奴婢与交纳赋税之间基本不存在相对应的关系,而占有奴婢为地主官僚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却是巨大的。唐建中元年(780年),杨炎建议实行了两税法,明确宣布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46) 这就使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以丁、以口、以户为主要征税根据的制度,向主要征收资产税的方向转变,唐代原来只是作为租庸调附加税的户税、地税,一跃而成为主要的赋税。财产的多少成为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这样一来,作为财产之一的奴婢在赋税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特别是在唐朝后期,国家财政日益困难,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47) 。“通津达道者税之,莳蔬艺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48) 。在这种情况下,仅次于田产屋舍的奴婢,焉能被封建官府轻易放过。
奴婢纳税,这对唐代整个社会必然产生影响,一些地主官僚贵族不能不考虑占有大量奴婢在经济上是否有利的问题。当占有奴婢可以为地主官僚带来利益、增加剥削量时,他们总是贪得无厌地扩大自己的奴婢队伍,例如像南北朝时期那样。可是,奴婢一旦成为两税法下国家征收赋税的重要对象,地主官僚们就不会像过去一样无限地增加自己的奴婢了。中唐以后,甚至有些官僚已将一些奴婢变为佃户了。如文宗大和年间,梁州城固人崔觐,“为儒不乐仕进,以耕稼为业……以田宅家财分给奴婢,令各为生业。觐夫妻遂隐于城固南山,家事一不问,约奴婢递过其舍,至则供给酒食而已”(49) 。在两税法下,官吏的免税特权已被取消,任何官僚占有奴婢都不能不交纳一定的资产税。对于那些拥有大量奴婢的官僚贵族来说,奴婢已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两税法的实行之所以遭到一些地主官僚的反对,恐怕与此亦有一定关系。中唐以后,社会上从事生产的奴婢数量的减少及奴婢放良现象的增多,(50) 与奴婢资产税的提高显然是有着因果关系的。
当然,两税法的许多原则,后来并未得到很好的实行,一些地主官僚也必然会采取各种手段来规避应纳的资产税。但是,在中唐以后土地制度发生变化,契约租佃制、雇佣制日益发展,农民阶级依附关系逐步减轻,奴婢劳动愈来愈不合时宜的历史溯流下,两税法的实行无疑对唐代奴婢制度的变化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总结以上所论,主要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从历史的传统来看,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唐代奴婢无论是在法律规定上还是在社会实际生活中,都具有资产的属性。
第二,奴婢既然属于资产,那么占有奴婢的多少必然与判定户等的高低直接相关。在占有其他资产基本相同的前提下,占有奴婢数量愈多,其户等必然愈高,所纳的户税也就愈多,这点可从敦煌吐鲁番文书及史籍的记载得到证明。而部曲作为劳动力亦与定户等有关。
第三,两税法实行以前,封建政府征收赋税主要以丁、以口、以户为依据,作为财产计算的奴婢与赋税的多少没有直接的联系。实行均田制时期,占有奴婢虽然需要交纳一定赋税,但地主官僚以奴婢名义可以占有的土地则更多。唐朝前期,奴婢不纳课,而当时的户税仅是正赋租庸调的补充,因此奴婢在赋税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两税法实行以后,地税户税一跃而成为唐朝的主要税收,这样作为资产计算的奴婢在赋税中的地位陡然提高了,地主官僚贵族不得不因为占有大量奴婢而交纳较高的户税,这显然是与地主阶级不断增加剥削量的愿望相抵触的。同时,由于土地制度的变化、契约租佃制及雇佣关系的日益发展,奴婢的生产积极性日益低下。面对这样的形势,地主官僚自然会减少其奴婢的使用量而代之以更多的契约租佃农民或雇佣劳动者,因此,两税法的实行,无疑是导致中古良贱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之一。
(原刊《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
(1) (唐)陆贽:《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第49页。
(3)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
(4) (汉)班固:《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5) 《四川郫县犀浦出土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第4期。
(6)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二,《张汤传》引张守节正义。
(7) (唐)魏征:《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8) [日]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333页。
(9) (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六。
(10) (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四,《名例》四。
(11) (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三,《名例》三。
(12) (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一四,《户婚》。
(13) (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三,《名例》。
(14)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187页。
(15)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153页。
(16) (唐)杜佑:《通典》卷六,《食货·赋税下》;(宋)王溥:《唐会要》卷八五,《定户等第》;(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四八六,《户籍》。
(17) 《唐六典》卷三〇,《县官吏》。
(18) (宋)王溥:《唐会要》卷八五,《定户等第》。
(19) 国家文物局古历史研究所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第98—99页。
(20)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账研究》中译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88页。
(21) 见国家文物局古历史研究所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第六册中所载唐代户籍、手实、籍账。
(22) 《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载,都官郎中员外郎“凡公私良贱必周知之”。这显然是以掌握全国各州县随户口上报中央的贱口数字为基础的。
(23) [日]仁井田陞:《中国身份法史》,第937页。
(24) 张勋燎:《敦煌石室奴婢马匹价目贱纸的研究》,《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25) 表中资料来源于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账研究》录文部分。
(26) 国家文物局古历史研究所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第78页。
(27) 唐长孺:《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第182页。
(28) 国家文物局古历史研究所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455页。
(29)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八,《独孤郁传》。
(30)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纪》四二,德宗建中二年五月丙寅条。
(31) (唐)陆贽:《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 (清)纪昀:《李文公集》卷九《疏改税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四八三,独孤郁《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
(34)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四八三,白居易《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
(35)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一三四,《杨慎矜传》。
(36) 李天石:《唐代私奴婢初探》(署名李军),载《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2期。
(37) 独孤郁之父独孤及熟悉朝廷财政,见(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一六二,《独孤郁传》。
(38)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三五,《卢 传》。
传》。
(39)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七,《德宗本纪》。
(40)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二。
(41) (北齐)魏收:《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
(42) 联系前文,此处显然脱一“奴”字。
(43) (唐)杜佑:《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下》引《关东风俗传》。
(44) (唐)魏征:《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45) (唐)魏征:《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46) (唐)陆贽:《翰苑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7)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渤传》。
(48)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
(49)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二,《崔觐传》。
(50) 敦煌文献中有不少时代较晚的唐五代奴婢放良样文,反映了奴婢放良现象的增多。见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5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