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导演艺术:真实的谎言
(The Art of Film Directing:True Lies)
西班牙现代绘画大师毕加索说过:“艺术是一种谎言,这种谎言让我们明白真理——至少是上帝允许我们理解的真理。”中国已故的诗人顾城也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向以“天生说谎者”自居的意大利电影大师费里尼更声称,“我几乎虚构了一切:童年、人物、乡愁、梦想、回忆,为的是叙述它们。”[1]真实与虚构、真理与谎言、真相与伪装俨然成为艺术创作中二元对立的核心问题。
真与假既截然对立,又相互依存(像太极双鱼图的黑白分明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会相互转换(真与假是一种相对性的概念,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在生活中,我们也会用“画得跟真的一样”来夸奖一幅肖像画,会用“美得跟假的一样”来称赞一道风景。有假才有真,有真才有假;真可以变假,假也可以变真。这就是真与假的辩证法,也是艺术创作的根本出发点。
康德说:“在一个美的艺术成品上,人们必须意识到它是艺术而不是自然。但它在形式上的合目的性,仍然必须显得它不受一切人为造作的强制所束缚,因而它好像只是一自然的产物。”[2]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说:“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所以说,艺术的真谛在于假戏真做和以假乱真,而对最具写实意义(也最能全方位模拟真实世界)的电影艺术来说,真与假的辩证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纪录电影注重对真实的记录,其开山之作《北方的纳努克》曾陷入物质现实真实的悖论和哲学论断的虚妄,对于爱斯基摩人生活的搬演本身就违背了纪录电影的实质。“真与假”的论断从此成为纪录电影,乃至所有电影的一大难题。兰妮·里芬斯塔尔坚持说,《意志的胜利》“没有倾向性的评论,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根本没有评论。它是‘历史——纯粹的历史’”。苏珊·桑塔格也说,“《意志的胜利》代表了一种经过成功改换后的、特有的激进真实:历史变成了戏剧”。从这里可以看出,真实的事件与虚构的情景在电影艺术中可以没有障碍地自由转换,这恰恰构成了电影世界最独特的魅力。
德国现代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坚信:“要揭示人与人之间的任何一点东西,都必须借助于某种‘人工的’东西。”[3]自然与人工、真实与虚构成为导演艺术创作互为表里的同一枚硬币和彼此依存的同一幅太极双鱼图。张艺谋虚构了看起来绝对真实(纪实风格)的《秋菊打官司》和《一个不能少》,观众信以为真(创作者的真诚与影片的真实感),是因为观众确实受骗了(电影的虚构和观影的想象)。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自于丹麦“九五教义派”,其“十诫”规则的每一条都在提倡和推崇极端的写实主义,但其主将拉斯·冯·提尔居然很快就拍出了《狗镇》这样极端写意的影片。《狗镇》最突出的特征恰恰是与写实主义(“九五教义派”之根基)南辕北辙的写意与虚拟,这与中国传统戏曲的程式化写意表演和虚拟化时空处理形成绝佳的照应,同时也印证了布莱希特的“不要让观众相信舞台上的戏是真事”的著名论点。中国传统戏曲的写意元素包括人物造型(行头和脸谱,长袖善舞、靠旗飘扬,红忠白奸、包公黑脸)、场景环境(“一桌二椅”可以代表任何环境,一切以演员的表演而定)和人物动作(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其虚拟元素则包括空间的流变、时间的演进、周边环境和动作对象的虚拟等。按照费穆的说法,“中国剧的生、旦、净、丑之动作、装扮皆非现实中之人……然而最终的目的,仍是要求观众认识它们是真人,是现实的人,而在假人假戏中获得真实之感觉。这种境界,十分微妙。”[4]拉斯·冯·提尔的《狗镇》正是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东方艺术)的表现手法的精髓,在摄影棚里建造了一个明显虚拟的舞台场景(简单的布景和用粉笔画在地上的房屋结构),而且人物的表演也带有浓烈的写意色彩。但是这部在物理现实性上看似虚假和风格化的电影,却表达出极为严酷的主题和极为真实的氛围。更为重要的是,场景和人物的抽象和虚拟使观众将全部的关注重心集中到故事和主题上,避免了物质性细节的干扰,极大地刺激了观众的知性感受,从而使《狗镇》成为“故事假、道理真”的得意忘言之作。日本导演伊丹十三的《蒲公英》也体现了类似的“以假写真”倾向。
对于真相的执著出于人类好奇与探究存在的本能,电影导演经常会用艺术的手段伪造真实,以探寻生命的真相,进而形成一个颇具哲学意味的悖论(像禅宗的故事和玄学的寓言)。希区柯克对于真相的执著充分体现在《蝴蝶梦》、《爱德华大夫》、《后窗》、《迷魂记》和《精神病患者》当中,对真相的揭示也就意味着这种探寻过程的完结。罗伯-格里耶和阿兰·雷乃合作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则将电影的叙事前提置于怀疑的目光之下(到底有没有去年,到底有没有马里昂巴德,根本无法确定),真理的相对性被推向极致。到了大卫·林奇的《妖夜荒踪》和《穆赫兰大道》、彼得·威尔的《楚门的世界》(虚假的世界比真实的世界更为真实)和克利斯托弗·诺兰的《失忆》(记忆成为真相的迷雾),真相与假象已经变得不可捉摸,完全印证了英国著名剧作家哈罗德·品特的说法:“真实和虚幻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
受到希区柯克的《后窗》的启示,安东尼奥尼推出了著名的影片《放大》,借用一个伦敦时装摄影师的故事,对真实影像进行“确认”。摄影师拍摄的“虚的”照片与公园里存在的“实的”犯罪形成一对二元对立的矛盾体,并在影片结局,通过“虚的”网球赛与“实的”生活的对比,对其加以阐释,成为对笛卡尔的哲学观点“我思故我在”和佛教“色与空”观念的精彩的电影化演绎。而《放大》又为弗朗西斯·科波拉的《谈话》提供了创意上的灵感,导演利用一个旧金山的窃听专家的故事,聚焦于对真实声音的“确认”。以监听别人为生的顶尖高手发现自己也在被人监听,这一挥之不去的噩梦极度困扰着他,导致了他最后对真实存在的幻灭和对自身认同的迷失。
电影艺术中的真实与虚假经常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电影文本中真实与虚假的矛盾和对立统一,常常会表现为对真相的探寻(侦探片和悬疑片之类);二是虚构的电影文本本身与真实的现实世界(物理的和精神的)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统一,既可以像布列松(《乡村牧师日记》)、安东尼奥尼(《红色沙漠》)、贾木什(《天堂陌影》)、阿巴斯(《樱桃的滋味》)和彼得·威尔(《楚门的世界》)一样,以最直接的纪实手法创造最间接的虚幻世界,表达抽象的哲理,也可以像布努艾尔(《一条安达鲁狗》)、阿兰·雷乃(《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费里尼(《八部半》)、艾伦·帕克(《迷墙》)和奥利弗·斯通(《天生杀人狂》)一样,以最虚幻的表现手法摹写最真实的人类世界和最贴切的知性感受。中国传统文论和书画理论中的“以实写虚”和“以虚写实”观点在这些电影中得到了相当集中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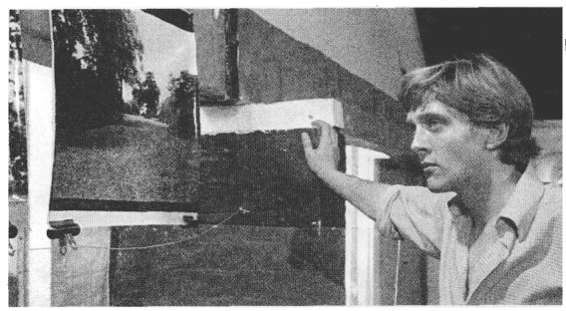
图11-1 《放大》中难辨真假的摄影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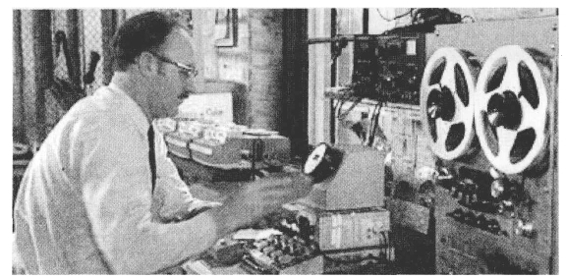
图11-2 《谈话》中遭遇反窃听的窃听专家
坚持“电影是生活的渐近线”的巴赞曾经说:“客观世界的影像赋予它自身一种可信的品质,即能把它自身与其他正在制作的影像区别开来。”但是现代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巴赞关于电影影像真实性的论断遭遇空前的颠覆和挑战。电脑动画和数字化技术制作的虚构影像正在迅速地接近(甚至超越)传统意义上的真实影像,影片《西蒙妮》就代表了当代高科技对“眼见为实(seeing is believing)”观念发出的强有力的挑战,而“真实的相对性是绝对的”这一说法也再次得到印证。
电影是一种多层面、多维度和多向量的二元存在,既是物质性的(胶片、拍摄现场和放映现场),又是形而上的(创意概念、意象、情感、知性和超验)。电影也是一张弥散的网络,由点、线、面、体以及无处不在又超然物外的“(气)场”等共同构成无法言传、难以把握的艺术生命体。电影还是一次流变的历程,从物理性的视听感官到精神性的知觉、情感、理性、体悟和通感,统统都融入这一历程之中。电影艺术的二元辩证性、弥散性和流变性使之成为一个真假难辨、变幻莫测的自在生命体,而导演艺术研究的目标则是探寻这个自在生命体的成分结构和运行机制,这也恰恰就是本书勉力而为的努力方向。(https://www.xing528.com)

图11-3 《西蒙妮》中的导演(上帝)和他的作品(虚构的影像)
电影导演艺术是一个充满一系列二元矛盾的复杂体系,这些既对立又统一的二元因子通过复合的形态,融合成一个庞大的电影艺术表意系统,而超越且统领这一表意系统的则是另一个维度的二元论对立统一,即“真与假”的辩证法:真实(正题)、谎言(反题)与电影(合题),形成电影导演艺术终极性的辩证法悖论。
特吕弗的影片《日以作夜》的法文片名是《美式夜景》(La Nuit Américaine),特指好莱坞的“日拍夜”手法(在大白天通过缩小光圈或借助滤色镜来拍摄夜景效果),蕴涵着对电影艺术的“真实的谎言”特性的丰富指涉。而斯特劳亨的《贪婪》则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人类贪得无厌的天性,这种贪婪体现在电影领域就是一方面顽固地留恋往昔(巴赞所谓的“木乃伊情节”和雷乃对记忆的纠缠),另一方面又放纵地憧憬不一样的未来(艺术电影的“精神超越”和好莱坞的“物欲梦幻”),正是这些不屈不挠的留恋与憧憬为人类创造出一个亦真亦幻又如痴如醉的“天堂电影院”。
爱德华·默里说过:“电影是艺术,而不是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历史学家关心的是一个一个的事件,而诗人(导演艺术家)关心的是总体——是把这些事件结合在一起的那些必要的或可能的原则。”[5]电影导演艺术汇聚了难以计数的二元元素,并在不同的层面、维度和向度上进行辩证式的自主运作,以期达到电影艺术的终极目标(那些必要的或可能的原则),而这个终极目标依然是一个辩证法悖论——“真实的谎言”(套用詹姆斯·卡梅隆一部电影的片名),即用虚构来传递真理,用水滴来把握沧海,用瞬间来参悟永恒,用此在来达至彼岸。
2006年夏秋完成初稿
2007年春节改稿于北京
2007年圣诞节定稿于巴黎
【注释】
[1]《我是说谎者:费里尼的笔记》,第223页。
[2]转引自《中国电影与意境》,王迪、王志敏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7—18页。
[3]《论电影的体系》,〔德〕布莱希特著,载《电影艺术译丛》1979年第3期,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
[4]转引自《中国电影与意境》,王迪、王志敏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6页。
[5]《十部经典影片的回顾》,第136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