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 非线性(上):现代电影的心理结构 |
非线性电影叙事结构的最大特征在于单一时间向度被打破和解构,时间成为不连贯的片断且前后颠倒。情节、事件和动作的事理逻辑(因果关系)被(人物的或导演的)主观心理逻辑取代,经典的事理结构演变成现代的心理结构。心理叙事线索的介入使得现代电影更加注重非理性的本能和直觉,逻辑性、戏剧性被淡化消解,偶发性得到增强,而线性结构相对单一的内涵也往往发展成非线性结构的复合式多声部主题交响。
其实,作为人类史诗典范的希腊史诗,一开始就埋下了非线性结构的叙事伏笔。一个关键证据就是荷马史诗通常从故事的中间(in medias res)开始,然后回溯去表现开头的部分,但叙事的主体仍然是现在部分的发展,即“双向发展”,也就是中国章回体所谓的“话分两头,各表一枝”:《伊利亚特》从阿喀琉斯的愤怒开始(因为阿伽门农王夺走了他美丽的女俘),帕里斯对海伦的勾引和特洛伊战争的爆发是通过交代背景的方式表现的;而《奥德赛》则是从特洛伊战争结束后的撤军开始,特洛伊战争的始末和奥德赛回乡的历程同时成为史诗的叙述主体。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荣格的集体潜意识学说的兴起,以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毕加索和勋伯格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浪潮席卷了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而此时正值电影艺术诞生的初期,精神分析学和现代主义思潮(包括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对电影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影响。不论是“意识流”、“心理小说结构”,还是“立体画派”、“十二音体系”,都对传统理性主义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具体到电影导演艺术的范畴,叙事结构从事理结构到心理结构的转变就是一个突出的方面。
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曾试图用“绘画逻辑”来替代“线性故事逻辑”,这与布努埃尔(《一条安达鲁狗》和《黄金时代》)、维尔托夫(《带摄影机的人》)和安东尼奥尼(《奇遇》和《红色沙漠》)等现代派大师在电影中的努力极为相似。线性的事理结构被非线性的心理结构取代,体现为“(圆环形)可缝合式”、“(戏中戏)套层式”、“散点式”和“片断式”等非线性结构形式,情节、事件和动作可以按照(心理)叙事逻辑重新组合,正像戈达尔所坚持的,打乱或颠倒开端、发展和结局的顺序。
一般认为,最早的非线性心理结构可以追溯到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主导影片叙事结构的是导演头脑中的“不宽容理念”及其电影化呈现。格里菲斯的表现核心在于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四个故事的并置这一现代非线性结构模式,通过四个故事交织发展的同一叙事趋势,深化影片的寓意和主旨。当然,由于其深刻的思辨性主题和非线性叙事结构的先锋性,《党同伐异》没有能够再造《一个国家的诞生》的辉煌,但它在电影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则是不容置疑的。
作为现代电影的开山之作,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Citizen Kane,1941)经常被誉为最伟大的美国电影,乃至最伟大的世界电影(参见美国电影学会[AFI]和英国《画面与音响》[Sight and Sound]杂志的相关评比),究其原因是《公民凯恩》充分体现了革命性创新精神和大胆先锋的表现手法,尤其是其心理叙事结构的整体运用让人称道。
“的确,从叙事结构的角度来看,《公民凯恩》深受广播的影响(奥逊·威尔斯曾是著名的广播剧主播)。该故事是采用叙述者的口吻来讲述的,而这恰恰就是广播剧剧情设置的核心。威尔斯在影片中一口气用了五个叙述者。”《公民凯恩》涉及报业大王传奇而颇具争议的一生,讲述了凯恩一生不同时期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这五个叙述者分别是监护人撒切尔先生(凯恩的孩提时代)、《问询报》总经理伯恩斯坦(凯恩少年得志的成功)、好朋友李兰(凯恩首次婚姻和竞选的失败,与李兰的决裂)、第二任妻子苏珊(歌剧演出的失败和第二次婚姻关系的解体)和贴身男仆雷蒙(凯恩之死)。如果算上新闻片和调查记者(也就是摄影机)的叙述,《公民凯恩》的叙述视点多达七个。因此,如何有效地结构这些相互分离甚至相互冲突的叙事段落,就成为奥逊·威尔斯面临的主要难题。
奥逊·威尔斯借鉴戏剧与广播剧的经验,采用了多视点和闪回重叠的叙事结构手法。“在《公民凯恩》里,一个闪回的跨度还与此前的闪回的广度有关,例如,伯恩斯坦讲述的《问询报》的故事是从撒切尔私人日记中断的时间开始的,而李兰详细描述的凯恩和埃米莉的相遇是由伯恩斯坦开始的。正如人们常说的,这些闪回使拼图游戏(苏姗的拼图游戏可以看做一种隐喻)似的凯恩生活得以重现。”[8]
《公民凯恩》中五个剧中人物(还包括新闻片)的叙述都是带有强烈心理色彩的“主观性(各人的立场不同)”叙述,而摄影机所谓的“客观性”叙述(小凯恩打雪仗、越过夜总会天棚、早餐蒙太奇、焚烧雪橇和“闲人免进”等镜头)毫无疑问也带有电影制作者鲜明的主观心理倾向。所以布鲁斯·F.卡温认为:“观看这部电影的乐趣之一,即在由主观中找出客观的表现,以及将我们的注意力游移于多种同时进行的叙述间。”[9]
其实,《公民凯恩》运用非线性、多视角的心理结构模式无非是要打破传统的时间向度(顺时)和空间向度(定点透视),创造一种时间上的错乱化与片断化以及空间上的多点透视(类似于中国画的散点透视)与流变式的立体感,目的是要消解理性主义的确定性,拥抱现代主义的多义性和暖昧性,从而深化和泛化对于人类自身和社会万物的理解和探求。
奥逊·威尔斯自己就说:“他们(指《公民凯恩》的五个叙述者)讲了五个不同的故事,各抒己见,因此关于凯恩的真相,就像关于任何人的真相那样,只能按照人们讲述的关于他的一切的总和加以衡量。”[10]的确,关于凯恩这个人的真相是很难从某个单独的角度来阐释的,而有关一个杀人和强暴事件的真相,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向观众呈现呢?这成为另一部伟大的现代主义影片《罗生门》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按照热拉尔·热奈特的《修辞》卷三的说法,叙事可以区分为四种讲述形态:(1)一次叙事讲述一次故事;(2)一次叙事讲述不定次数的故事(大场面中的个性细节:战场、囚犯和罢工之类);(3)不定次数叙事讲述一次故事,格里耶的小说《嫉妒》就是如此,而在他1968年编导的电影《说谎的人》(L’homme qui ment)中,叙述者不断地更改叙述词,以至于观众根本不知道哪些才是真实的,影片真正的用意并不在于叙述内容的真假,而恰恰在于叙述者说谎这一事实;(4)不定次数叙事讲述不定次数的故事。
黑泽明的《罗生门》由同一事件的不同复述组成,相互摧毁彼此的真实性,也可以视为同一事件的不同解释。影片显然属于不定次数讲述一次故事这种讲述形态,因为它至少有三次复述(强盗、武士之妻和假托巫师之口的武士亡魂),而这些自相矛盾的复述使发生在树林里的所谓强奸和决斗显得相当不确定,真相的相对性和事件(以及人物态度)的暧昧性也就成为影片最引人注目的话题。

图6-2 《罗生门》中的三位当事人
非线性心理结构经常与重组的电影时空关系结合,形成复杂多变的叙事线索。伯格曼的《野草莓》在24小时的现实时空中回忆了老教授埃萨克·波尔格漫长的一生,雷乃的《广岛之恋》穿越了1959年的日本广岛和二战时期的法国内维尔两个时空,科波拉的《教父(续集)》则采用两个时空平行双线的交叉剪辑,来体现黑帮精神的世代传承和情感纽带的恍若隔世。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的叙事线在波兰和法国的两个薇罗妮卡之间穿梭,传达一种冥冥之中宿命的神秘通感。而台湾导演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1992)则将“桃花源”的古装喜剧和“暗恋”的现代悲剧两个话剧故事共融于一个舞台,在穿插对位中表达中国人跨越时空的悲欢离合。王家卫的《重庆森林》(1994)在“重庆大厦”与“午夜特快”这两个有着微妙关系的故事之间进行结构性的交叉叙事。
塞尔乔·莱昂内在《美国往事》中以心理情感为依据,建构起三个时空的交错性网络,将“从前或往事(once upon a time)的特殊意味与感念”和情感张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The Dawn Is Quiet Here,1972)也在二战的现实战斗、女兵战前幸福生活的回忆和当代年轻人对战争的追忆这三个时空之间进行结构处理,产生对战争和生命的深沉反思;而侯孝贤的《戏梦人生》(1993)则是通过现实叙述、往昔回忆和戏曲表演这三个时空的非线性结构,摹写布袋戏老艺人艰难而复杂的社会人生体验。(https://www.xing528.com)
现代电影的非线性心理结构还有三种相对稳定的模式:
(1)片断性叙事结构:主要利用时间向度来构成不连贯、偶发和非顺时的情节线索。戈达尔的《随心所欲》就是片断性叙事结构的典型例子,该片的副标题为“12个生活场景(Film en douze tableaux)”。苏珊·桑塔格在论及此片时认为:“它拒绝因果性,叙事的那种常见的因果秩序因情节被极其任意地分割成了十二个插曲而遭到瓦解——这些插曲不是因果地,而是顺次地彼此相连。”同样,戈达尔的《筋疲力尽》、《狂人比埃罗》和《周末》都注重于情节的偶然性(非线性、非逻辑),以表达“无序的世界和无序的人生”这一执著的主题。

图6-3 《随心所欲》中的娜娜和哲学家
此外,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1960)串联了花花公子、记者马尔切洛的12个叙事片断,罗姆的《一年中的九天》(Nine Days in One Year,1961)选取了九个片断展现苏联核物理学家的工作和生活,吴贻弓根据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城南旧事》,也是由“疯子”、“小偷”和“宋妈”三个相对独立的小英子童年生活片断组成的,这些影片的共同特征就体现在叙事结构的时间向度的非线性处理上。
(2)散点性叙事结构:以空间向度为主,结合时间向度来构成相对分离的、偶然的和非顺时的情节线索,相当于绘画中散点透视的综合效果。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可以视为最早也最著名的此类作品,罗西里尼的《游击队》(Paisan,1946)中的六个故事,曼凯维奇的《三妻艳史》(A Letter to Three Wives,1949)中三个女人对自己婚姻生活的交错回忆、伍迪·艾伦的《性爱宝典》(Everyt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Sex,1972)中的七个故事,贾姆什的《地球这分钟》(Night On Earth,1991)中发生在洛杉矶、纽约、巴黎、罗马和赫尔辛基的五个故事,马利克的《细红线》(The Thin Red Line,1998)中三个士兵的内省诗意片断叙述和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木兰花》(Magnolia,1999)中三个人物的故事等等,也属于这一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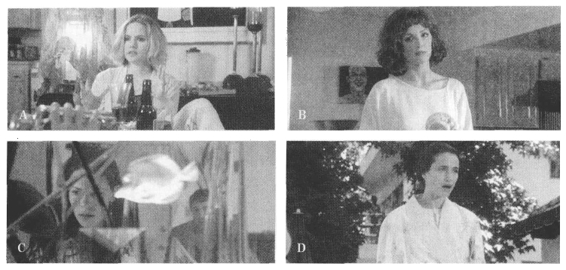
图6-4 《短片集》的人物谱
日本导演伊丹十三在《蒲公英》(Tampopo,1987)中通过贯穿蒲公英寿司店这条主线,将寿司的正规吃法、法国大餐点菜、妻子林中所做的晚餐、丐帮美食家等多个散点集结起来,对日本的餐饮文化及其寓意进行了有趣的探讨。而真正长期致力于散点性叙事结构的则是著名导演罗伯特·奥尔特曼,他在《纳什维尔》(Nashville,1975)、《短片集》(1993)、《云裳风暴》(Ready toWear,1994)和《高斯福特庄园》(Gosford Park,2001)中都运用了这种非线性的结构形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奥尔特曼根据雷蒙德·卡维尔的一系列短篇小说综合改编的《短片集》将散点式的非线性结构模式推向极致,发展出空间形式上的网状辐射。中国清代戏剧家李渔所说的“令观者如入山阴道中,人人应接不暇”[11],正是观看《短片集》后的感觉。启蒙主义戏剧家狄德罗说,在(传统的)舞台上“我们只能表现一个场面,然而在现实中,各种场面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假如能够把它们同时表现出来,使之互相加强,那么就会给我们以动人心魄的印象”[12]。近期,非线性网状结构、密集型群像式影片不断涌现,且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票房、评论和奖项)。比如,帕斯卡尔·费朗的《与死者和解》(Petits arrangements avec les morts,1994)、索德伯格的《毒品网络》(2000)、保罗·哈吉斯的《撞车》(Crash,2005)、斯蒂芬·加格汉的《辛瑞纳》(Syrana,2005)以及罗德里格·加西亚的《九条命》(Nine Lives,2005),都获得了观众和评论界的肯定。
散点性叙事结构电影被著名影评家罗杰·艾尔伯特称为“插曲式电影(episodic film)”,而最近的网络博客又为它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名字——“超文本链接电影(hyperlink movie)”。它与片断性叙事结构电影都遵循着现代电影“轻情节,重情境”的叙事策略,产生的是所谓“形散神不散,笔断意不断”的散文电影。
(3)套层叙事结构:所谓的“戏中戏”结构模式表达的正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艺术观念。特吕弗的《日以作夜》(Day for Night,1973)通过拍摄现场和所拍电影的叠加呈现,表达了对电影艺术的思考,他备受赞扬的《最后一班地铁》(Le Dernier métro,1980)也将德国占领时期的剧院生活和舞台演出糅合在一起。卡洛尔·雷兹的《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1981)运用电影和现实的交叉换位、叙述与故事的对位,在叙事结构上呈现“戏中有情人终成眷属,戏外男女主演分道扬镳”之间意味深长的对照。埃托雷·斯科拉的《那时我们如此相爱》(Nous nous sommes tant aimes,1975)套用了德·西卡于1948年拍摄的《偷自行车的人》的情节,而乔思·路易·格兰的《影子列车》(Tren de sombras,1996)则涵盖了费里尼于1963年拍摄的《八部半》的叙事内容,两者都在经典电影和现实故事之间形成套层结构,产生复杂而多义的主题内涵。

图6-5 《日以作夜》是一部关于拍电影的电影
绍拉的《卡门》借用了舞剧角色和舞蹈演员平行发展的爱情悲剧,深作欣二的《蒲田进行曲》(1982)则叙述了电影片场镜头内外的悲喜情感和人生。阿根廷导演赫克托·巴本科的《蜘蛛女之吻》(Kiss of the Spider Woman,1985)将牢狱故事与剧中人讲述的纳粹罗曼史《猫人》(Cat People,1942)剧情相结合,形成现实与幻想的并置、人物身份(同性恋者与革命者)的互换和两个故事的对位(两个主角的死亡)。此外,汤姆·迪西罗的《开麦拉狂想曲》(Living in Oblivion,1995)在戏里戏外写尽独立电影人的挣扎与无奈,而毕加斯·鲁纳的《泰坦尼克号上的女佣》(La Femme de Chambre du Titanic,1997)的男主人公也在现实的疏离与表演的沉醉中走向心理的迷失。
套层结构具有相当强烈的心理倾向,一些反映心理变态和人格分裂的电影往往采用这一结构形式。德国表现主义电影杰作《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就在现实故事和精神病患者的幻想故事之间形成套层,《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中女主人公逐渐陷入男人的圈套而产生意识的分裂(电影故事套进男人叙述的“去年”),被学者称为螺旋状内转的“梅式带圈(Mobius Strip,数学术语)”。至于韩国导演宋一坤的《蜘蛛丛林》(Spider Forest,2004),则表达的是在一系列奸情与谋杀的连环圈套中无法厘清的心理迷局。
李安说过,他的“《冰风暴》采用的结构属于撞击式的,以撞击力使观众产生刺激,经由刺激及其所延伸出来的想法,引发观众产生拼凑式的情绪呼应……它是将不同的元素相互‘撞击’与‘对照’,产生视觉上的拼凑呼应,出现的是相乘的效应,而非相加效果”(这种论点颇有几分神似爱森斯坦的蒙太奇镜头理论)。李安进一步说:“我们一般习惯的结构原理,其力学主要还是用来应付地心引力的重力。如怎样盖房子才不会垮下来。然而自然界生物元素的结构法则却不只这么简单,它是各种张力与压力的有效衔接与力道传送。”[13]这里所说的“自然界生物元素的结构法则”应该包含了事理、心理和超验等结构法则,算是自然法则在人文艺术领域的又一次体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