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 风格类型的辩证法 |
虽然风格本身的界定是约定俗成的,但不同风格类型之间的二元对立则是客观存在的,像前面论及的风格(化)与非风格(化)的对立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在电影导演艺术的风格类型体系当中,有一系列辩证对立的风格,如简约与繁复、浓烈与清淡、紧凑与松散、晓畅与晦涩、明朗与阴郁、精巧与恢宏、细腻与粗犷、内敛与张扬,等等,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成为导演艺术风格图谱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中,简约与繁复是风格类型中最为常见的对立模式,它们也往往与其他对立的风格类型(如浓与淡、隐与显、松与紧等)相关联。其实,在文学艺术的历史长河中,简约派、极简主义和最低纲领派(Minimalism)与奢华派、极繁主义(Maximalism)这两种风格倾向一直是尖锐对立又相辅相成的“欢喜冤家”,既有契诃夫、海明威和鲁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白描式的惜墨如金,也有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和中国汉赋词采飞扬、滔滔不绝的铺陈与挥洒。
俗话说,最简单的往往也是最深刻的。拉丁箴言说:“简单是真的标志。”爱因斯坦也断言:“宇宙的法则是最简单的”,所以他把深奥玄妙的相对论简化成E=MC2(物质的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中国当代作家格非在谈到自己的小说《人面桃花》时坦言:“我希望通过故事,通过简单的生活表达哲学,用简单来表达复杂,而不像过去那样用复杂来表达复杂。”可以说,用复杂来表达简单是无能的蠢才,用复杂来表达复杂是平凡的庸才,而用简单来表达复杂才是智慧的天才。香港武侠片巨匠胡金铨很早便有此体会:“如果情节简单,风格的展示会更为丰富。”侯孝贤也说:“我总觉得总有一天电影应该拍成这个样子:平易、非常简单,所有的人都能看懂。但是看得很深的可以看得很深、很深。”简约风格的电影导演艺术具备简单、朴素、淡雅、浅显和松散特征,强调想象的空间和回味的余地,往往用最简单的语言和方式来传达最深刻的哲理思想(思辨和禅机)和最复杂的情绪感受,德·西卡、小津安二郎、布列松、安东尼奥尼、侯孝贤、贾木什和阿巴斯都可以算作简约主义电影大师的代表。
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Ladri di biciclette,1948)中,父与子牵手的一个简单动作蕴涵着微妙的情感变化;同理,《温贝尔托D》(Umberto D.,1952)中一个犹豫不决、伸手乞讨的细小动作,也道尽了社会的炎凉与冷暖。安东尼奥尼的“情感三部曲”《奇遇》、《夜》和《蚀》不但对情感的关注极为吝啬,就连起码的故事也不屑于叙述完整,甚至出现了长达七分钟的空镜头段落,其简约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新藤兼人的《裸岛》的简约风格集中体现在人物的台词上,生活在荒凉小岛上的一家人除去简单的几个语气词之外,几乎没有对话。同样,贾木什的《天堂陌影》中,结伴出游的三个男女很少有语言交流,甚至没有开口说话的欲望。
伊朗导演大师阿巴斯·基亚洛斯塔米一直强调:“要用简单的方式拍电影。”阿巴斯荣获戛纳金棕榈奖的影片《樱桃的滋味》(Taste of Cherry,1997)被认为是最经典的简约主义电影之一。万念俱灰的中年男子巴迪先生准备自杀,甚至在山坡上挖好了自己的墓穴,他开车四处寻找掩埋自己的人手。一个年轻的库尔德士兵拒绝了他的要求,一个阿富汗的传教士也认为自杀违背《古兰经》的教诲,最后一个上了年纪的博物馆标本制作师同意帮助他,但标本制作师亲身经历的一个关于“樱桃的滋味”的故事,最终让巴迪先生动摇了轻生的决心。影片表达的是一则关于生死、信念和永恒的寓言,继承了以海亚姆的《鲁拜记》和萨迪的《蔷薇园》为代表的波斯文化“崇尚自然、追求永恒”的伟大传统。阿巴斯将故事、人物、场景、对白和镜头的运用都降低到最为克制的程度,却实现了最为深刻和最为动人的传达,这不能不算是“以一粒尘埃参透宇宙奥秘”的惊人奇迹。
简约主义强调空白、清淡和松散的风格倾向,类似于中国山水画的“留白”、中国戏曲的“空场”和戏剧的“无实物抽象”。在这种留白、空场和无实物部分,电影导演艺术家实际上为观众留下了广阔的感性(情感)和理性(思维)空间,这在艺术电影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吴永刚的《神女》(1934)中阮玲玉的出场,用一个包括妓女、抽烟者、捡烟人和警察在内的单一镜头,对女主人公的身份和个性进行了极为含蓄简约的交代。而阮玲玉的三次卖身的隐喻性蒙太奇表达,既为观众留下充分的联想空间,又与卖淫的隐秘性和社会道德的不认同形成微妙的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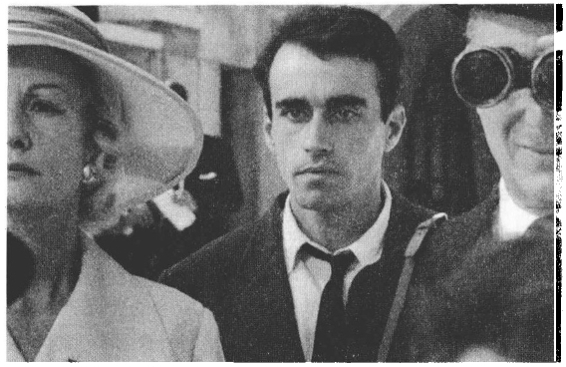
图5-9 《扒手》中扒手作案的画面
再看看另一位简约大师布列松在《扒手》一片中对扒手行窃过程的独特呈现。布列松并没有像主流电影的常规套路一样,将镜头对准扒手偷窃钱包的动作,而是把摄影机长时间地、不动声色地聚焦在扒手的脸部(摄影机变成了一个像扒手一样大气不敢出的灵性人物),不但契合了作案现场的环境气氛,也为观众提供巨大的想象空间,更用惊人的悬念张力将观众的关注点固定在扒手那张波澜不惊的脸上,在想象中体验他汹涌澎湃的内心世界。这一再简单不过的近景镜头,尽显简约风格大师“四两拨千斤”的天才风范。
法国导演阿兰·卡瓦利尔在谈及自己的名作《圣女特莱斯》时甚至说:“少(简约)不光是多(繁复),少(简约)是一切。”[8]他和主演都相信“做减法”是达致完美的源泉,影片的表演、台词、场景、道具、色彩和服装等各个方面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圣女特莱斯》正是以其以少胜多的绝对简约风格,赢得了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会奖和法国电影恺撒大奖。近些年赢得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奖的美国独立电影《日日夜夜》(Day Night Day Night,2006)也以极为简约和朴素的手法,展现了纽约街头少女人体炸弹(肩背炸弹的“恐怖分子”)所经历的外在冲击和内心挣扎。
如果说简约主义电影类似绘画中的白描、速写和淡抹水彩,那么,极繁主义电影则类似绘画中的工笔重彩和古典油画,好比佛兰德斯的鲁本斯、意大利的卡拉瓦乔和西班牙的委拉斯凯兹的作品。电影导演艺术的繁复风格可以大致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主题意义的繁复;第二,情节叙事的繁复;第三,视听手段的繁复;第四,动作节奏的繁复。
在主题意义的繁复方面,《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主题的多重性和多义(暖昧)性颇具代表性。按照编剧、新小说派大师罗伯-格里耶在《〈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序》当中的说法,“主角用自己的想象与自己的语言创造了一种现实……在这个封闭的、令人窒息的空间中,人和物似乎都是魔力的受害者,犹如在梦中被一种无法抵御的诱惑所驱使,无法逃跑或是改变。其实没有什么去年,马里昂巴德在地图上也不存在。这个过去是硬性杜撰的,离开说话的时刻便毫无意义。但是当过去占了上风,过去就变成了现在。”可以说,《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主题涉及意志和潜意识、感知和心理时间、认同与怀疑、强制与暧昧等理念,难怪雷乃要说,“这是一部拍完后可以用25种蒙太奇方案去处理的影片”。此外,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大卫·里恩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塔尔科夫斯基的《安德烈·鲁勃廖夫》和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等,也都在主题的复杂性上做足了文章。
在情节叙事方面,莎士比亚对繁复情节的追求和现代小说对繁复叙事的崇尚都对电影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党同伐异》到《公民凯恩》和《罗生门》,从《广岛之恋》到《美国往事》和《暴雨将至》,都将复杂的情节和多样化的叙事作为电影导演艺术创作的核心。英国导演盖依·里奇曾坦言:“我喜欢拍情节复杂、有悬念的电影,这样观众可以一边看一边跟着思考。”对繁复多样的叙事的迷恋,使后现代电影走向一种叙事风格化的迷局,像《失忆》、《穆赫兰大道》和《蜘蛛丛林》(Spider Forest,2004)就是如此。
在视听手段方面,格林纳威(《情欲色香味》)、绍拉(《戈雅在波尔多》)、阿尔莫多瓦(《关于我的母亲》)和张艺谋(《满城尽带黄金甲》)对于视觉色彩的追求,莱昂内(《西部往事》)、库布里克(《巴里·林登》)和科波拉(《惊情四百年》)对于情绪氛围的关注,都体现了一种铺陈、华丽甚至炫耀的风格特征,在镜头设计、细节处理、场景、服装、道具和化妆等方面追求一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巴洛克古典艺术效果。
至于动作节奏方面,萨姆·佩金帕、吴宇森、塔伦提诺和沃卓夫斯基兄弟以其带有电影暴力美学倾向的“死亡芭蕾”和“血腥舞蹈”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阐释。吴宇森曾说:“我所拍的电影都充满着舞蹈,因为我喜爱优美的东西,若把舞蹈贯注于动作内,观众一定看得赏心悦目。动作电影不一定要火爆,不一定要血腥。”(https://www.xing528.com)

图5-10 《海上花》画面
中国先哲老子说:“物极必反。”大诗人T.S.艾略特在谈及风格的转变(由极端繁复到极端简约)时做过这样的比喻:一人离开自己的家去远方,总有一天他会回来,但是你走得不够远,回来就没有意义。吴贻弓在谈到影片《巴山夜雨》(1980)时,引用“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哲言来说明繁复与简约在影片中的辩证性呈现。侯孝贤则在《海上花》中,将场景设计上的繁(色彩的绚丽和光效的精致)与摄影手法上的简(接近于静态的全景镜头)融合在一起,在简单与复杂、内敛与张扬、沉静与喧嚣、克制与放纵之间,达成不同风格元素的对立统一。
其实,在简约与繁复、浓烈与清淡之间并非只有不可跨越的鸿沟,而是同时也有一座彼此相连的桥梁。连一贯崇尚狂放的酒神精神的尼采都认为:“最高贵的美是这样一种美,它并非一下子把人吸引住,不做暴烈的醉人进攻(这种美容易引起反感)。相反,它是那种渐渐渗透的美,人几乎不知不觉被它带走,一度在梦中与它重逢,在它悄悄久留我们心中之后,它就完全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眼睛饱含泪水,使我们的心灵充满憧憬。”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杜甫的《春夜喜雨》中的名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那浑然天成、水乳交融的境界,才称得上艺术风格的至上表现。
【注释】
[1]《爱森斯坦评传》,〔英〕玛丽·西顿著,史敏图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580页。
[2]《罗贝尔·布列松电影中的宗教风格》,〔美〕苏珊·桑塔格著,载《反对阐释》,第209页。
[3]《导演电影》,第46页。
[4]转引自《十部经典影片的回顾》,〔美〕爱德华·默里著,张婉晔等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112页。
[5][11Conversations with Wilder,Cameron Crown,A Borzoi Book,Alfred A.Knopf,New York,2001,p.53.
[6]The Director’s Idea:The Path to Great Directing,pp.101-102.
[7]〔苏〕奥·科瓦洛夫:《时代的象征》,载《世界电影》1988年第6期,第137页。
[8]Cinema and Painting:How Art Is Used in Film,Angela Dalle Vacche,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Austin,1996,p.225.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