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字的性质
近代研究世界文字发展史的学者,起初把汉字、圣书字、楔形文字这种类型的文字称为表意文字。这一类型的文字都包含大量表音的成分,把它们简单地称为表意文字,显然是不妥当的。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有人提出了“过渡文字”(指由表意向表音过渡的文字)的说法。但是,把这些有几千年历史的成熟的文字体系称为过渡文字,显然也是不妥当的。进入五十年代之后,出现了“词—音节文字”(word-syllabic writing,或译“表词—音节文字”,参看本章注⑤)、“音节—表意文字”等新的说法。国内在五十年代后半期,也有人提出了汉字不是表意文字,而是“综合运用表意兼表音两种表达方法”的“意音文字”的主张。〔1〕下面谈谈我们对汉字性质的看法,重点放在分析汉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上,因为一种文字的性质就是由这种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决定的。至于究竟给汉字这种性质的文字体系安上一个什么名称,那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跟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是不同层次上的东西。例如汉字“花”是汉语里花草之{花}这个词的符号,“艹”(草字头,原作“艸”,即古草字)和“化”则是“花”这个字所使用的符号(“花是一个形声字,“艹”是形旁,“化”是声旁)。
在汉字里,像“花”这样可以从结构上进行分析的字,一般称为合体字。合体字的各个组成部分称为偏旁。秦汉以后所造的合体字,基本上都是用已有的字充当偏旁的(有些字用作偏旁时有变形的现象,如在上方的“艸”变作“艹”,在左边的“水”变作“氵”等,参看〔五(三)〕)。但是,在上古汉字里,有不少可以从结构上进行分析的表意字,却是用不一定能独立成字的象形符号组成的,例如第一章举过的 (射)一类字。这类字是否可以称合体字,是需要商榷的。我们姑且把它们称为准合体字。
(射)一类字。这类字是否可以称合体字,是需要商榷的。我们姑且把它们称为准合体字。
有些汉字从结构上看不能分析,一般称为独体字。对于独体字来说,也存在语言的符号跟文字所使用的符号这两个不同的层次。例如古汉字里的“ 作为{日}这个词的符号来看,是一个有音有义的字;作为“日”字所使用的符号来看,则仅仅是象太阳之形的一个象形符号。这种区别在拼音文字里同样存在。例如英文里“a”,作为英语里不定冠词{a}的符号来看,是一个有音有义的字;作为英文所用的符号来看,则仅仅是一个表示一定语音的字母。为了使概念明确,下面把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称为“字符”。
作为{日}这个词的符号来看,是一个有音有义的字;作为“日”字所使用的符号来看,则仅仅是象太阳之形的一个象形符号。这种区别在拼音文字里同样存在。例如英文里“a”,作为英语里不定冠词{a}的符号来看,是一个有音有义的字;作为英文所用的符号来看,则仅仅是一个表示一定语音的字母。为了使概念明确,下面把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称为“字符”。
语言有语音和语义两个方面,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也必然既有音又有义。就这一点来说,各种成熟的文字体系之间并没有区别。只有根据各种文字体系的字符的特点,才能把它们区分为不同的类型。
英文可以说是一种表音文字。但是这并不是说英文只有音没有义,只是说英文的字符,即二十六个字母,是表音的,不是表意的。例如:英文的“sun”是英语里{sun}这个词的符号。它既有音,即{sun}这个词的音—〔sʌn〕,也有义,即{sun}这个词的义——太阳。但是“sun”所使用的字符s、u、n,跟它所代表的词只有语音上的联系,没有意义上的联系,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表音字。同样,我们所以把古汉字“ ”(日)叫做表意字,是因为“
”(日)叫做表意字,是因为“ ”作为字符,即太阳的象形符号来看,跟{日}这个词只有意义上的联系,没有语音上的联系。如果作为{日}这个词的符号来看,它也是音、义兼备的。〔2〕
”作为字符,即太阳的象形符号来看,跟{日}这个词只有意义上的联系,没有语音上的联系。如果作为{日}这个词的符号来看,它也是音、义兼备的。〔2〕
讨论汉字性质的时候,如果不把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性质,跟文字本身所使用的字符的性质明确区分开来,就会引起逻辑上的混乱。
各种文字的字符,大体上可以归纳成三大类,即意符、音符和记号。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是意符,在语音上有联系的是音符,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是记号。拼音文字只使用音符,汉字则三类符号都使用。
汉字的字符里有大量意符。传统文字学所说的象形、指事、会意这几种字所使用的字符,跟这几种字所代表的词都只有意义上的联系,所以都是意符。我们所说的表意字就是总括这几种字而言的。形声字的形旁跟形声字所代表的词也只有意义上的联系,所以也是意符。
意符内部还可以分类。有的意符是作为象形符号使用的,它们通过自己的形象来起表意作用,如古汉字里的“人”、“日”等字所使用的 等符号,又如构成
等符号,又如构成 (射)字的弓箭形和手形。几何形符号如果不是用作记号,而有以形表意的作用,如
(射)字的弓箭形和手形。几何形符号如果不是用作记号,而有以形表意的作用,如 、
、 、
、 、
、 、
、 (方)、
(方)、 (圆)等字所用的符号,也应该归入这一类。古汉字里的独体字,基本上都是用单个象形符号造成的表意字。
(圆)等字所用的符号,也应该归入这一类。古汉字里的独体字,基本上都是用单个象形符号造成的表意字。
有的意符不是依靠自己的形象来起作用的。这种意符通常都是由已有的字充当的表意偏旁,它们就依靠本身的字义来表意。例如:合体表意字“歪”由“不”、“正”二字组成,它的意思就是“不正”。“不”和“正”在这里就是依靠它们的字义起作用的意符。形声字的形旁一般由依靠本身字义来指示形声字字义的字充当,所以也应该归入这一类(第一章提到的在象形字上加注音符而成的形声字是例外)。
在有必要区分上述这两种意符的时候,可以把前一种称为形符,后一种称为义符。在汉字变得不象形之后,形符基本上就不使用了。
汉字的字符里也有很多音符。假借字就是使用音符的。人们在假借某个字来表示一个跟它同音或音近的词的时候,通常并不要求它们原来在意义上有什么联系。例如第一章曾提到古汉字借{箕}的表意字 来表示语气词{其},{箕}、{其}二词在意义上就毫无联系。又如近代假借花草之{花}的形声字“花”来表示动词{花}(如花费、花钱),这两个{花}在意义上也毫无联系。所以,尽管
来表示语气词{其},{箕}、{其}二词在意义上就毫无联系。又如近代假借花草之{花}的形声字“花”来表示动词{花}(如花费、花钱),这两个{花}在意义上也毫无联系。所以,尽管 本来是表意字,“花”本来是形声字,在它们借来表示语气词{其}和动词{花}的时候,都是纯粹作为音符来起作用的。当然,
本来是表意字,“花”本来是形声字,在它们借来表示语气词{其}和动词{花}的时候,都是纯粹作为音符来起作用的。当然, 和“花”作为假借字,即作为语气词{其}和动词{花}的符号来看,也是既有音又有义的;但是作为假借字所使用的字符来看,则只有表音作用。这跟“
和“花”作为假借字,即作为语气词{其}和动词{花}的符号来看,也是既有音又有义的;但是作为假借字所使用的字符来看,则只有表音作用。这跟“ ”作为{日}这个词的符号看既有音又有义,作为“日”字的字符看则只有表意作用的情况是一致的。
”作为{日}这个词的符号看既有音又有义,作为“日”字的字符看则只有表意作用的情况是一致的。
有时也能看到被假借的字跟借它来表示的词不但同音或音近,而且在意义上也有某种联系的现象。这种现象大概有很多是无意中造成的。在汉语里,彼此的语音相同或相近并且意义也有联系的词,是很常见的。人们在为某个词找同音或音近的字充当假借字的时候,很有可能无意中找了一个跟这个词在意义上也有联系的字。有意假借一个跟某个词在意义上也有联系的字来表示这个词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参看〔九(二)〕)。这种情况不很常见,可以作为假借的特例来处理。
形声字的声旁也是音符。声旁也有两类。一类是单纯借来表音的,如“花”的声旁“化”。另一类跟形声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也有联系。例如一种用玉、石等物制作的耳饰叫做{珥}(与“耳”同音),“珥”字从“玉”从“耳”(“玉”用作左旁时写作“ ”),“耳”就是跟“珥”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声旁。这种声旁可以看作音符兼意符。
”),“耳”就是跟“珥”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声旁。这种声旁可以看作音符兼意符。
汉字的音符跟拼音文字的音符有很大区别。即使撇开汉字还同时使用意符和记号这一点不谈,也不能把二者等量齐观。拼音文字的音符是专职的,汉字的音符则是借本来既有音又有义的现成文字充当的。有很多汉字在充当合体字的偏旁的时候,既可以用作音符,也可以用作意符,而且还能兼起音符和意符的作用。例如“耳”字在“饵”、“铒”(音耳,金属元素名)等字里是音符,在“聪”、“聋”等字里是意符,在“珥”字里是音符兼意符一般拼音文字所使用的字母,数量都相当少。汉字音符的情形就不同了。从原则上说,汉字里每一个字都有可能借用为音符,实际上用作音符的字,数量也很大(古今用作声旁的字超过一千)。同样的字音往往借用不同的字来表示。如果要強調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音符的区别,可以把汉字的音符称为“借音符”。不过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在下文中仍然称它们为音符。
在第一章里已经说过,在文字形成过程的开始阶段,可能有少量长期沿用的记号吸收到文字里来,古汉字里 、
、 、
、 、
、 等数字大概就来自这种记号。除此之外,用记号造字的情况就很难找到了。〔3〕但是在汉字发展的过程里,由于字形和语音、字义等方面的变化,却有很多意符和音符失去了表意和表音的作用,变成了记号。
等数字大概就来自这种记号。除此之外,用记号造字的情况就很难找到了。〔3〕但是在汉字发展的过程里,由于字形和语音、字义等方面的变化,却有很多意符和音符失去了表意和表音的作用,变成了记号。
由于汉字字形的演变,独体表意字的字形大都丧失了原来的表意作用。例如古汉字的“ ”变成隶书、楷书的“日”之后,已经一点也看不出太阳的样子。如果不考虑“日”字的历史,根本无法找出“日”这个字的字形跟{日}这个词有任何联系。可见“日”字的字符已经从意符变成了记号,“日”字已经从表意字变成了记号字。同类的例子举不胜举。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记号文字和拼音文字”节里说:“图画文字和记号文字本是衔接起来的,图画演化得过于简单,就只是一个记号”。(109页)这是很正确的。
”变成隶书、楷书的“日”之后,已经一点也看不出太阳的样子。如果不考虑“日”字的历史,根本无法找出“日”这个字的字形跟{日}这个词有任何联系。可见“日”字的字符已经从意符变成了记号,“日”字已经从表意字变成了记号字。同类的例子举不胜举。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记号文字和拼音文字”节里说:“图画文字和记号文字本是衔接起来的,图画演化得过于简单,就只是一个记号”。(109页)这是很正确的。
有人把“日”这一类字形由象形到不象形的变化,看作由表形到表意的变化,认为“ ”是表形符号,“日”是表意符号。这是不妥当的。所以会产生这种看法,大概是由于没有把字符的作用跟文字的作用区分开来。“日”这一类字使用的字符变为记号这个事实,并没有改变这些字作为语言里相应的词的符号的性质。字形变得不象形之后,这些字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字音和字义。这一点并不能反过来证明它们的字符没有变成记号。如果因为“日”字还有意义,就把它的字符看作表意符号,把它看作表意字,那末根据“日”字还有读音这一点,岂不是也可以把它的字符看作表音符号,把它看作表音字了吗?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是表形符号,“日”是表意符号。这是不妥当的。所以会产生这种看法,大概是由于没有把字符的作用跟文字的作用区分开来。“日”这一类字使用的字符变为记号这个事实,并没有改变这些字作为语言里相应的词的符号的性质。字形变得不象形之后,这些字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字音和字义。这一点并不能反过来证明它们的字符没有变成记号。如果因为“日”字还有意义,就把它的字符看作表意符号,把它看作表意字,那末根据“日”字还有读音这一点,岂不是也可以把它的字符看作表音符号,把它看作表音字了吗?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由于记号字仍然代表着它们原来所代表的词,它们在用作合体字的偏旁,或假借来表示其他词的时候,仍然能起意符或音符的作用。例如“日”字虽然已经变成记号字,“晴”字所从的“日”却并不是记号,而是以“日”字的身分来充当意符的(只取“日”字之义而不取其音);“驲”字(音日,古代驿站用的马车)所从的“日”和假借来记录外国地名日内瓦的“日”,也不是记号,而是以“日”字的身分来充当音符的(只取“日”字之音而不取其义)。总之,尽管它们自身使用的字符已经成了没有表意表音作用的记号,“日”这类字在充当字符的时候仍然能起表意或表音的作用。
所以,汉字字形的演变虽然使绝大部分独体字——它们也是构成合体字的主要材料——变为记号字,却并没有使合体字由意符、音符构成的局面发生根本的变化。汉字绝大部分是合体字。合体字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也就是汉字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记号字跟表意字的不同,又不能过分夸大记号字的出现对汉字的整个体系所发生的影响。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里说:“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文字还不能算是记号文字……还是形声文字”(109页),已经把这个意思很扼要地讲了出来。
在独体表意字之外,还有一些字也由于字形的演变而成了记号字。
准合体字有不少变成了记号字。例如:“立”字本作 ,象人立在地上,“並”字(现已并入“并”字)本作
,象人立在地上,“並”字(现已并入“并”字)本作 ,象两个人并立在地上,(《说文》“並”字从二“立”,跟字义不切合)演变成隶书、楷书之后,就都变成不能分析的记号字了(关于准合体字的演变,参看〔三(一)〕)。
,象两个人并立在地上,(《说文》“並”字从二“立”,跟字义不切合)演变成隶书、楷书之后,就都变成不能分析的记号字了(关于准合体字的演变,参看〔三(一)〕)。
合体表意字也有少数变成了记号字。例如:“表”字本作 (
( ),由“衣”、“毛”二字合成。“表”本是罩在皮衣外面的衣服的名称。古人的皮衣有毛的一面朝外,所以“表”字从“衣”在“毛”上示意。这个字写成“表”之后,也就只能看作一个记号字了。
),由“衣”、“毛”二字合成。“表”本是罩在皮衣外面的衣服的名称。古人的皮衣有毛的一面朝外,所以“表”字从“衣”在“毛”上示意。这个字写成“表”之后,也就只能看作一个记号字了。
形声字偶尔也会演变成记号字。例如从“禾”“千”声的 字,就变成了形旁、声旁全都遭到破坏的记号字“年”。
字,就变成了形旁、声旁全都遭到破坏的记号字“年”。
字形的演变还造成了一些半记号字,即由记号跟意符或音符组成的字。这类字大都是由形声字变来的。例如:“春”字本作“ ”,《说文》分析为“从艸,从日,艸春时生也,屯声”。后来声旁“屯”跟“艸”旁省并成“
”,《说文》分析为“从艸,从日,艸春时生也,屯声”。后来声旁“屯”跟“艸”旁省并成“ ”形。这个偏旁既无表音作用,也无表意作用,是一个只有区别作用的记号。可是偏旁“日”仍有表意作用,所以“春”就成了由记号跟意符组成的半记号半表意字。
”形。这个偏旁既无表音作用,也无表意作用,是一个只有区别作用的记号。可是偏旁“日”仍有表意作用,所以“春”就成了由记号跟意符组成的半记号半表意字。
还有不少字,虽然其结构并没有由于字形演变而遭到破坏,但是由于语音和字义的变化,对一般人来说实际上也已经变成了记号字或半记号字。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是形声字的声旁由于语音的变化丧失表音作用,转化为记号(参看〔八(六)〕)。例如“恥”(“耻”的本来写法)本是从“心”“耳”声的字,后来“耳”、“恥”二字的读音变得毫无共同之处,“耳”实际上成了仅有区别作用的记号,“恥’实际上成了半记号半表意字。“恥”字写作“耻”,始见于东汉碑刻,可能当时“耳”、“恥”二字的读音已经有了很大距离,有的人不知道“耳”是声旁,就把“心”旁改成了读音与“恥”相近的“止”(汉隶中“止”和“心”的字形相当接近)。“耻”可以看作由记号“耳”跟音符“止”组成的半记号半表音字。
合体字的表意偏旁由于字义的变化丧失表意作用,转化为记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例如:形声字“特”的本义是公牛,所以用“牛”为形旁。由于这个本义早已不用,对一般人来说,“牛”旁实际上已经成为记号。
形声字有时会由于语音和字义两方面的变化而完全变成记号字。上面所举的形旁丧失表意作用的“特”字,就是一个例子。它的声旁“寺”的表音作用也已经由于语音演变而丧失,所以对一般人来说,这个字实际上已经完全成为记号字了。
假借字也可能变成记号字。假借字是借用已有的字作为音符来表示跟这个字同音或音近的词的。对根本不认得被借字的人来说,假借字实际上只是个记号字。有些假借字所借之字的原来用法已经被人遗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借之字不是形声字,假借字就会变成记号字。例如:“我”字在较早的古文字里写作 象一种锯或
象一种锯或 形近锯的武器。它本来所代表的词,一定就是这种锯或武器的名称。由于第一人称代词{我}跟那个词同音或音近,古人就假借“我”字来记录它。可是在相当早的时候,“我”字本来所代表的词就已经废弃不用了。因此作为你我之“我”所用的字符来看,“我”已经丧失表音作用,变成了一个硬性规定的记号;作为一个文字来看,你我之“我”已经从假借字变成了记号字。我们现在用来表示虚词{其}的“其”字,〔4〕一般人并不知道它本来所代表的词是{箕};实际上也已经成为记号字了。
形近锯的武器。它本来所代表的词,一定就是这种锯或武器的名称。由于第一人称代词{我}跟那个词同音或音近,古人就假借“我”字来记录它。可是在相当早的时候,“我”字本来所代表的词就已经废弃不用了。因此作为你我之“我”所用的字符来看,“我”已经丧失表音作用,变成了一个硬性规定的记号;作为一个文字来看,你我之“我”已经从假借字变成了记号字。我们现在用来表示虚词{其}的“其”字,〔4〕一般人并不知道它本来所代表的词是{箕};实际上也已经成为记号字了。
如果被借字是形声字,当本义已经湮灭的时候,声旁一般仍有表音作用。例如“笨”本来当竹子里的白色薄膜讲,后来这个字被假借来表示愚笨的{笨},本义不再使用,形旁“竹”实际上已经变成记号,但声旁“本”仍有表音作用。
总之,由于种种原因,在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里,原来的意符和音符有很多已经变成了记号。相应地,很多表意字、形声字和假借字,也就变成了记号字或半记号字。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汉字在象形程度较高的早期阶段(大体上可以说是西周以前),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严格说应该称为借音符)的一种文字体系;后来随着字形和语音、字义等方面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为使用意符(主要是义符)、音符和记号的一种文字体系(隶书的形成可以看作这种演变完成的标志)。如果一定要为这两个阶段的汉字分别安上名称的话,前者似乎可以称为意符音符文字,或者像有些文字学者那样把它简称为意音文字;后者似乎可以称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考虑到后一个阶段的汉字里的记号几乎都由意符和音符变来,以及大部分字仍然由意符、音符构成等情况,也可以称这个阶段的汉字为后期意符音符文字或后期意音文字。
前面说过,有人把汉字这种类型的文字体系称为“词—音节文字”。此外,还有人把汉字称为“词文字”(word writing,或译表词文字)或“语素文字”。〔5〕这些名称应该怎样理解呢?(https://www.xing528.com)
首先应该指出,语素文字说跟词文字说在基本观点上并没有多大分歧。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能够独立活动的语素就是词。上古汉语里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汉字一般都是代表单音节词的。但是有很多单音节词后来变成了不能独立活动的语素,在今天一个汉字往往只是一个语素的符号,而不是一个词的符号。这是有些人不愿意把汉字叫做词文字,而要叫做语素文字的原因。按照这种考虑,语—音节文字这个名称也可以改为语素—音节文字。〔6〕
所谓语素文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体系呢?拼音文字可以按照字符所表示的是音节还是音素,分成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语素文字”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字符表示语素的文字呢?不能这样理解。一般认为“日”这一类字是典型的语素字。但是我们只能说“日”字表示语素{日},而不能直接说字符“日”表示语素{日}。这一点前面早就说明了。有的人是因为看到汉字里一个字通常代表一个语素,称汉字为语素文字的。像这样撇开字符的性质,仅仅根据文字书写的基本单位所代表的语言成分的性质,来给文字体系定名,也是不妥当的(这里所说的文字书写的基本单位,就是一般所说的字。汉字的笔画可以称为用笔的基本单位)。英文里几乎每个字都代表一个词,大家不是并没有把它看作表词文字,而是把它看作音素文字的吗?这样说来,语素文字这个名称是不是根本就不能成立呢?那倒也不必这么看。音素、音节、语素,是语言结构系统里由低到高的不同层次。我们可以把语素文字解释为字符属于语素这个层次,也就是说字符跟语素这个层次发生关系,而跟音素、音节这两个层次没有关系的文字;或者解释为能够表示语言的语素结构(即能够表示词由什么语素构成)而不能表示语言的音素或音节结构的文字。语素—音节文字可以解释为既使用属于语素这个层次的字符,又使用表示音节的字符的文字。
按照上面的解释来看,汉字究竟应该称为语素文字呢?还是应该称为语素—音节文字呢?下面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汉字的意符和记号都不表示语音,前者只跟文字所代表的语素的意义有联系(音节以下的层次无意义可言),后者只能起把代表不同语素的文字区别开来的作用。它们都是属于语素这个层次的字符。所以汉字里的独体、准合体和合体表意字以及记号字和半记号半表意字,都可以看作语素字。
但是,汉字使用的音符,虽然都由原来是语素的符号的现成文字充当,却应该看作表示音节的符号。使用音符的假借字(就记录汉语固有语素的假借字而言),以及由意符和音符构成的形声字,通常也以一个字代表一个语素,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就把它们也都看作语素字。
那些记录具有两个以上音节的音译外来词的假借字,它们表示语素的音节结构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例如元代假借来记录出自蒙古语的官名的“达鲁花赤”这四个字(达鲁花赤的本来意义是统治者、掌印者),显然都是作为音节符号使用的。记录汉语里固有的双音节语素的假借字,如“仓庚”(鸟名)、“犹豫”(关于“犹豫”,参看〔九(三)〕)之类,表示音节结构的性质也很明显。
那些用来记录汉语固有的单音节语素的假借字,其实同样具有表示音节结构的性质。只不过在一个语素只包含一个音节的情况下,语素和音节之间的层次界线容易被忽略而已。作为字符来看,假借来表示动词{花}的“花”跟“达鲁花赤”的“花”,其本质并无不同,二者都是表示huā这个音节的符号。它们的不同在于前者单独用来表示一个单音节语素的音,后者则只表示一个多音节语素里的一个音节。“花”作为假借字所使用的字符看,只有表音节的作用;但是作为记录动词{花}的假借字来看,则既有音也有义(即“花”字的假借义)。“达鲁花赤”这四个字必须连在一起才能表示出一定的意义,其中每一个字都只能看作一个没有意义的表音节的符号。如果不是按照一般习惯以“书写的基本单位”当作“字”的定义,而是以“语素或词的符号”当作“字”的定义的话,只有“达鲁花赤”这个整体才有资格称为假借字。
英文里表示不定冠词的“a”字所使用的字母“a”,其本质并不因为单独成字就跟与其他字母拼合成字的“a”有所不同。汉字里表示动词{花}的假借字“花”,以一个字代表一个语素这一点,当然也不会影响到它所使用的字符的表音节的本质。所以假借字都可以看作音节字。
形声字的声旁也是表音节的符号。例如:读音相同的“饵”、“洱”、“珥”、“铒”代表四个不同的语素,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表音成分——声旁“耳”。这个“耳”显然应该看作表音节的符号(“珥”所从的“耳”兼有表意作用,已见上文)。由于形声字的形旁只跟语素的意义有联系,可以把形声字看作介于语素字跟音节字之间的一种文字。半记号半表音字的性质,也可以这样看。
前面曾经指出,汉字使用的音符跟拼音文字的音符有很大区别。这种音符作为表音节的符号来看,跟音节文字的音符当然同样是有很大区别的。汉字既使用表音节的符号,也使用属于语素这个层次的符号。表音节的符号都是借现成的文字,即语素的符号充当的,而且借来表示同一个音节的字往往有很多个。〔7〕这些都是跟音节文字不同的地方。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汉字不应该简单地称为语素文字,而应该称为语素—音节文字。不过,对汉字使用的表音节的符号跟音节文字的音符之间的区别,也应该有足够的认识。
语素—音节文字跟意符音符文字或意符音符记号文字,是从不同的角度给汉字起的两种名称。这两种名称可以并存。意符和记号都是属于语素这个层次的字符,所以语素—音节文字这个名称对早期和晚期的汉字都适用。
最后,谈一下汉字在形式上的主要特点,以及记录具有两个以上音节的语素的汉字跟一般汉字不同之处。
前面已经说过,汉字的书写单位就是一般所说的字。每个字通常都念一个音节。在现代汉字里,只有表示儿化作用的“儿”字不能自成音节,是一个例外。有人把这种“儿”字写得比较小,以示区别。“瓩”(千瓦)“浬”(海里)等一小批表示计量单位的字可以念两个音节,但是其性质类似古文字里的合文(两个以上的字合写成像一个字的样子),不是正规的汉字(这种类似合文的单位字现已规定停止使用)。在汉语里,单音节语素占绝对优势。通常,一个汉字是为一个单音节语素而造的。这是汉字形成一个字念一个音节的局面的主要原因。
在字的形式上,汉字很早就形成了要求每个字大体上能容纳在一个方格里的特点。因此组成合体字的字符的配置,缺乏严格的规律性,有左右相合、上下相合、内外相合等等不同情况(参看〔八(四)〕);总之,以拼合成字后能写在一个方格里为原则。一般以“方块字”之称表示汉字形式上的这个特点。
在汉语里,除了占绝对优势的单音节语素之外,也存在一些双音节语素,而且还通过音译外来词而不断增加具有两个以上音节的语素。对于这些语素,就需要用两个以上的字来记录它们。〔8〕
具体地说,汉字记录具有两个以上音节的语素,有用假借字和造专用字这两种方法。
用假借字记录双音节语素是很常见的,古代就已出现的如前面举过的“倉庚”、“犹豫”,现代的如“沙发”、“尼龙”。三个以上音节的语素,几乎都是用假借字记录的,如古代的“璧流离”(“琉璃”的旧译名)、“达鲁花赤”,现代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在记录具有两个以上音节的语素的时候,假借来的字必须连在一起才能表示出意义,各个字只具有表音节的符号的性质。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了。
造专用字的办法通常只用于双音节语素。〔9〕所造的字绝大多数采用形声结构,例如古代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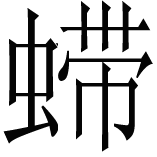
 ”(虹的别名)、“徜徉”,现代的“咖啡”、“噻唑”(一种有机化合物)。非形声结构的如“旮旯”(gā lá,角落)之类,极为少见。
”(虹的别名)、“徜徉”,现代的“咖啡”、“噻唑”(一种有机化合物)。非形声结构的如“旮旯”(gā lá,角落)之类,极为少见。
为双音节語素造的形声字,往往是通过加偏旁或改偏旁等办法,由假借字改造而成的。例如上面举过的“徜徉”,就是由假借字“尚羊”(也作“常羊”)改造而成的。又如“蜈蚣”本作“吴公”(《广雅·释虫》),也是假借字,后来在上一字上加“虫”旁而作“蜈公”(《庄子·齐物论》释文引《广雅》),最后才出现两个字都加“虫”旁的写法。上面举过的“仓庚”,后来也有了“仓 ”、“鸧鹒”等写法(关于把记录双音节语素的假借字改造成专用字的情况,参看〔一一(一)/cd〕)。
”、“鸧鹒”等写法(关于把记录双音节语素的假借字改造成专用字的情况,参看〔一一(一)/cd〕)。
为双音节语素造的字,跟记录双音节语素的假借字一样,也必须两个字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才有意义。而且,记录具有两个以上音节的语素的一组假借字,分开来之后每个字尚有它本来固有的字义;为双音节语素造的字,单个地看连这种字义也没有。这是它们不同于一般汉字的一个特点。
如果不受一字一音节原则的拘束,“徜徉”、“蜈蚣”(或“蜈公”)、“
 ”(或“仓
”(或“仓 ”)之类记录双音节语素的字,本来完全可以写成“
”)之类记录双音节语素的字,本来完全可以写成“ ”、“
”、“ ”、“
”、“ ”这样的形式。在圣书字里,在包含几个符号的一个音符组之旁加上一个定符而构成的形声字,是很常见的。在古汉字的合文里,偶而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例如战国时代的印章有时就把“邯
”这样的形式。在圣书字里,在包含几个符号的一个音符组之旁加上一个定符而构成的形声字,是很常见的。在古汉字的合文里,偶而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例如战国时代的印章有时就把“邯 (鄲)”合写成“
(鄲)”合写成“ ”(《古玺文编》361页)。在这种合文里,形声字声旁的表音节的性质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古玺文编》361页)。在这种合文里,形声字声旁的表音节的性质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注 释
〔1〕周有光《文字演进的一般规律》,《中国语文》1957年7期。又见《字母的故事》,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修订版2—7页。
〔2〕以上一段所说的意思,大体上根据赵元任的《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105页。
〔3〕天干中的“ ”(甲)、
”(甲)、 (乙)、“
(乙)、“ ”(丁)等字,可能也是源于原始社会所使用的记号的,参看上章注⑩所引文164页。
”(丁)等字,可能也是源于原始社会所使用的记号的,参看上章注⑩所引文164页。
〔4〕“其”由 变来,演变情况大致如下:
变来,演变情况大致如下:
有人认为“ ”(音基)是加注的音符。“箕”是由“其”分化出来的一个字。
”(音基)是加注的音符。“箕”是由“其”分化出来的一个字。
〔5〕词文字说是美国的布龙菲尔德在三十年代发表的《语言论》中提出来的(袁家骅等译本商务1980年版360页)。词-音节文字说是美国的Gelb在1952年发表的《A Study of Writing》中提出来的(参看上章注⑥)。语素文字说是赵元任在1959年发表的《语言问题》中提出来的(商务1980年版144页)。
〔6〕赵元任在注②所引书中“文字”章的一个小标题里,曾称汉字为“语素—音节文字”(103页),但是他在正文里又说汉字是典型的语素文字。看来,他所说的“语素—音节文字”的含义,跟这里所说的不一样。
〔7〕这种现象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本来不同音的字演变为同音字而造成的。例如《《新华字典》yī音节下所收的全部形声字使用了“意”、“衣”、“奇”、“殹”、“咠”、“伊”、“韦”、“多”等十来个不同的声旁,这些形声字有很多在古代并不同音。为了区别同音词而借用不同的字来表示同—音节的现象也是常见的。例如:“潢”和“湟”,“蟥”和“蝗”,都是同音的。为了从字形上把它们区别开来,分别使用了“黄”和“皇”这两个声旁(这跟拼音文字有时为了区别同音词把它们拼得不同形的情况相似)。此外,借用不同的字来表示同一音节的现象,当然也有很多仅仅是由于选择音符缺乏规律性而造成的。
〔8〕早期的汉字在记录双音节语素时是否一定都如此,还不能肯定。汉语里的一部分双音节语素,大概早在汉字萌芽时就已经存在了。对于有的作为具体事物名称的双音节语素,最初很可能只造一个表意字来代表它,一个字念两个音节。甲骨文里的“凤”字,除了在{凤}的象形字上加注“凡”声的写法之外,偶尔还有加注“兄”声的写法。张政烺先生认为加注“兄”声的应该读为凤凰的“凰”(《邵王之諻鼎及簋铭考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刋》八本三分。“兄”、“皇”古音极近)。也许{凤}的象形字本来就是为双音节语素{凤凰}而造的。看来,有可能古汉字里本来是有念双音节的字的,但是由于汉语里单音节语素占绝对优势,绝大多数汉字都念单音节,这种念双音节的字很早就遭到了淘汰。
〔9〕为三音节语素造的专用字,如见于《说文》的“珣玗琪”(东夷玉名)和清代曾经使用过的“ 咭唎”等外国名,是很罕见的。
咭唎”等外国名,是很罕见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