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地亚洲元代历史地名的沿革
韩百诗
在由弗拉基米尔科夫和鲍罗夫卡于1927年,在列宁格勒发表的一部著作集(《北蒙古》第2卷,第36-42页)中,弗拉基米尔科夫发表了一篇有关他于1925年在蒙古地区从事语言调查工作的初步报告。在这些研究中,他试图重新找到一定数量的地名。由于《元朝秘史》才使我们得知在那里曾存在过这样的地名。但他的研究却是徒劳无益的,所以他很快就深信在该史籍中保留下来的大部分地名,目前已经无人知晓了。
大约在同一时代,弗拉基米尔科夫于1929年的《科学院报告》第169-174页中,又发表了一篇论文,涉及了范围更为广泛的内容,篇目叫做《鄂尔浑河流域碑铭中以蒙文保留下来的地名》。他从中一共发现了不足20个名词,其中有10个是地名,其余的是民族名称。地名中主要是指河流的地理名词,如阿鲁河(Aru=Aga)、布哈拉河(Buqaraq)、额尔齐斯(Ertis)、谦河(K m)、鄂尔浑河(Orqun)、土拉河(Turla)和色勒纳河(S
m)、鄂尔浑河(Orqun)、土拉河(Turla)和色勒纳河(S l
l n
n )等,它们实际上都是高地亚洲一些大江大河的名称。然后是两座山的名称:Altun(y
)等,它们实际上都是高地亚洲一些大江大河的名称。然后是两座山的名称:Altun(y s)系指阿尔金山或阿尔泰山(Alta
s)系指阿尔金山或阿尔泰山(Alta ),Qtüka
),Qtüka 是于都斤山脉,可能是指抗爱山(Khangai)。此外还有一个地名,即拜城(Ba
是于都斤山脉,可能是指抗爱山(Khangai)。此外还有一个地名,即拜城(Ba -bal
-bal q),它一直沿用至今,在蒙古文中作Baewalxgixure Baebalaq。
q),它一直沿用至今,在蒙古文中作Baewalxgixure Baebalaq。
元代所使用的地名与河流名称的消失时代,似乎不会越过15世纪。因为我们在明代初期有关蒙古人的载籍中,还可以发现其中的某些地名与河流名称。虽然由弗拉基米尔科夫所指的那些河名和地名,至少从公元9世纪起就开始使用了。然而,我还可以指出,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一直沿用到当代的一个蒙古地名,即海剌儿(Qa lar)。此名既指一个地名,又指位于此地附近的一条河流①。它在《圣武亲征录》第22节和《元史》卷1第8页中,均作“海剌儿”,指一地名;在《元史》卷10第2页和卷15第10页中,它又指同一名称的一条河流;它在《四夷考》(《宝颜堂秘籍》版本)卷5第3页中,也是以同一形式出现的。此外,拉施特在其《史集》与《圣武亲征录》和《元史》相对应的一段文字中,未曾提到“海剌儿”;但他却在有关成吉思汗的幼弟哈撒尔(Qasar)及其儿子们生平历史的一段文字中(原文第2卷第89页,译本第56页),都提到了它,写作Qa
lar)。此名既指一个地名,又指位于此地附近的一条河流①。它在《圣武亲征录》第22节和《元史》卷1第8页中,均作“海剌儿”,指一地名;在《元史》卷10第2页和卷15第10页中,它又指同一名称的一条河流;它在《四夷考》(《宝颜堂秘籍》版本)卷5第3页中,也是以同一形式出现的。此外,拉施特在其《史集》与《圣武亲征录》和《元史》相对应的一段文字中,未曾提到“海剌儿”;但他却在有关成吉思汗的幼弟哈撒尔(Qasar)及其儿子们生平历史的一段文字中(原文第2卷第89页,译本第56页),都提到了它,写作Qa lar或者是Qala
lar或者是Qala r(原文卷1第3页,译本第3页),即“海剌儿”。
r(原文卷1第3页,译本第3页),即“海剌儿”。
因此,“海剌儿”一名从12世纪起就已经存在了,一直不断地在汉文载籍中反复出现(见甘露德:《满洲历史地理辞典》第198—200页中有关Hailar一条目),一直沿用到当代。在明代,《皇舆考》卷12第38页中的对音,与元代完全相同,也作“海剌儿”;到了清代,对音体系才发生了变化。此地名也见诸《朔漠图》(《皇舆图》卷2)中,在《皇舆通志》卷116第8页中,又提到了“海剌儿千户所”。
事实上,《大清一统志》卷717第7页中,又称之谓“开拉里”;《盛京通志》卷28第7和34页中,持同样的写法;《朔方备乘》卷24第3和4页中的写法也相同,而在同卷第3页有一处又对音作“哈拉尔”;《水道提纲》卷25第4页,也写作“开拉里”;《龙沙纪略》第2页中,也持同样的写法;虽然《黑龙江志稿》卷4第60页所提供的两种对音名称,也出现在《龙沙纪略》中了:“海喇尔”和“哈拉”,但我本人却没有从中找到它。
《黑龙江志稿》在卷3第26页和卷4第52页中转写作“海拉尔”,卷3第26—27页和卷4第53、55和57页等处又转写作“海喇尔”。《黑龙江外记》第1页中写作“海兰儿”和“凯喇尔”。富克斯在《康熙时代的耶稣会士舆图》(1943年北京版,第115页第637条目)中写作“开拉里河”。《东三省政略》在卷1《边务》卷上第5、9、11和14页,卷下第7、9、12、16和33页中均写作“海拉尔”;《黑龙江水道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709页中写作“开拉里”(Kailar)。1760年的《清代一统地图》第84页中写作“海拉尔”。开拉里河沿途并入了许多支流,诸支流均源出于兴安岭,《大清一统志》卷711第10页中就曾提到过该地。最后,海拉尔河也出现在西方的地图上,分别转写作Kha lar和Ha
lar和Ha lar等等形式。
lar等等形式。
然而,只有极少数地名才沿存下来了,因为出于我所不知道的原因②,元代的许多地名都由其他地名所取代,其时间肯定为明代。因为其中的某些地名,也见诸明代的载籍中,但几乎都是一些河流或湖泊的名称。其中有许多位于东蒙古,而其他(除了由弗拉基米尔科夫所引证的那些之外)则出现在西蒙古。这主要是由形成阿穆尔河上游的湖泊和河流名称组成的第一类地名,可能沿存下来了。其原因是由于它们从唐代以来,就成了相继在中国北部出现的小邦和高地亚洲游牧社会边界地区。
阿穆尔河上游的主要组成水系是克鲁伦河,此河在唐代似乎就以”俱伦水”的名称而出现了(见《新唐书》卷217下,第4页),有时又以其谬误的形式“俱伦山”而出现(《旧唐书》卷199下第1页),这后一个名称应该校正为“俱伦水”,即Külün之对音③。它实际上是注入了克鲁伦河的一个湖泊的名称,现今被称为呼伦池(K l
l n-K
n-K l
l n)。然而,我们可以怀疑这里是否是指额尔古纳河(
n)。然而,我们可以怀疑这里是否是指额尔古纳河( rgn
rgn ,Arghun),它是呼伦池的源头,向北流去,与石勒喀河(Silka)汇合之后就形成了阿穆尔河(黑龙江)。事实上,“俱伦水”一名曾出现在《室韦传》中。众所周知,室韦部在唐代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与呼伦池之东北隅。因此,”俱伦水”事实上很可能是额尔古纳河而不是克鲁伦河。
,Arghun),它是呼伦池的源头,向北流去,与石勒喀河(Silka)汇合之后就形成了阿穆尔河(黑龙江)。事实上,“俱伦水”一名曾出现在《室韦传》中。众所周知,室韦部在唐代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与呼伦池之东北隅。因此,”俱伦水”事实上很可能是额尔古纳河而不是克鲁伦河。
克鲁伦河一名仅仅从10世纪起才出现,并一直沿用至今。此河在辽代被称为“胪朐”(《辽史》卷4第5页,卷15第9页,卷37第2页,卷59第1和第3页,卷91第2页,卷93第4页和卷103第2页)。在《契丹国志》卷2第3和5页以及卷40第1页中,此名又转写作“卢沟”。在金代,该河又被对音作“龙驹”(《金史》卷24第10页,卷94第6和13页,卷115第1页,卷132第9页,卷133第8页)。此名也出现在《元史》中,与它的常用对音词同时存在,但却写作“龙居”,见《元史》卷27第10页,卷29第2页和卷122第10页。《大金国志》卷2第3和5页,第40卷第1页的对音法与《契丹国志》完全相同。在元代游记故事的文献中,最为古老的是丘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第1版第13页,其中把克鲁伦何写作“陆局”)和张德辉的《塞北纪行》(《皇朝藩属舆地丛书》版本)第1页中对音作“翕陆连”(Kirül n),后者所附的一条注释指出,“翕陆连”就相当于“胪朐”。在耶律楚材的文献著作集《湛然居士集》(《四部丛刊》版本卷5第11页)中,将上述名称对音作“闾居”。在徐霆对彭大雅的《黑鞑事略》所作的注释(《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第1版,第24页)中,此名又写作“泸沟”④。
n),后者所附的一条注释指出,“翕陆连”就相当于“胪朐”。在耶律楚材的文献著作集《湛然居士集》(《四部丛刊》版本卷5第11页)中,将上述名称对音作“闾居”。在徐霆对彭大雅的《黑鞑事略》所作的注释(《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第1版,第24页)中,此名又写作“泸沟”④。
《元史》在许多段落中都保留了“胪朐‘这种古老形式,它大部分都使用了元代所采纳并由明代作家们一直沿用到16世纪初叶的对音法。《元史》使用了《实录》⑤和当代作家们的文献,《元史》卷3第7页,卷25第3页和卷39第3页等处都写作”怯鲁连’(K rül
rül n);在另外几卷(卷1第16页,卷2第1页,卷12第2页)又写作“怯绿连”⑥,这后一种对音词似乎是引自《圣武亲征录》。我们还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对音形式:《元史》卷117第4页中作“怯缘怜”,卷131第16页中作“怯吕连”,以上二者是用来翻译同一个名称的。相反,《元史》卷7第17页中的对音名称为“怯鹿难”,一看即知有谬误。在《元史》卷19第3页中又作“怯鲁剌”,这后一个对音词的最后一个方块字是难以解释的,因为al
n);在另外几卷(卷1第16页,卷2第1页,卷12第2页)又写作“怯绿连”⑥,这后一种对音词似乎是引自《圣武亲征录》。我们还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对音形式:《元史》卷117第4页中作“怯缘怜”,卷131第16页中作“怯吕连”,以上二者是用来翻译同一个名称的。相反,《元史》卷7第17页中的对音名称为“怯鹿难”,一看即知有谬误。在《元史》卷19第3页中又作“怯鲁剌”,这后一个对音词的最后一个方块字是难以解释的,因为al 的不同而使“剌”与“怯”是难以调和的,因为支配蒙语的规律就是元音的谐调。对于以“难”字结尾的第一种对音词,我们所面对的可能是一种两个元音的音节融合,这种现象可以通过“怯缘连”与“斡难”(K
的不同而使“剌”与“怯”是难以调和的,因为支配蒙语的规律就是元音的谐调。对于以“难”字结尾的第一种对音词,我们所面对的可能是一种两个元音的音节融合,这种现象可以通过“怯缘连”与“斡难”(K rül
rül n-Onan)的结合来进行解释,在《元史》卷117第1页中,提到了一种相似而文字有所颠倒的形式,即“斡难怯鲁之地”。它与鲁布卢克游记中所提到的“斡难怯鲁连”(Onankerule)很相似(万嘉德版本第208、243和268页),在最后二段文字中又写作Onankerule。另外,1285年左右成书的《圣武亲征录》在第20、45和48节中,均作“怯绿连”⑦。
n-Onan)的结合来进行解释,在《元史》卷117第1页中,提到了一种相似而文字有所颠倒的形式,即“斡难怯鲁之地”。它与鲁布卢克游记中所提到的“斡难怯鲁连”(Onankerule)很相似(万嘉德版本第208、243和268页),在最后二段文字中又写作Onankerule。另外,1285年左右成书的《圣武亲征录》在第20、45和48节中,均作“怯绿连”⑦。
在明代,1240年成书的《元朝秘史》的蒙文本,于1380年左右被用汉字作了对音转写,其中第94、96、98和107节中均写作“客鲁连”(K rül n)。然而,《明史》在许多段落中都保留了另外一种谬误的形式“胪朐”,如卷6第8和9页,卷126第5和18页,卷130第14页,卷133第2页,卷327第2和6页。在后一段文字中,有一条注释又指出,“胪朐”又称为“饮马河”。因此,《明史》卷6第12页,卷146第13页,卷155第6页和卷328第2页中,就是以“饮马河”之名而记载克鲁伦河的。此名同样也出现在《皇舆考》卷12第35页中,其中的一条注释也说明“饮马”河即相当于“胪朐”河。《武备志》卷223第8页和《朔漠图》中则写作“岫具河赐名饮马河”。有关这一名称,请参阅笔者旧作:《明代蒙古史文献》第95页注(160)。《武备志》中的地图引自《广舆图》,并由此而传入到《皇舆考》卷2第46页中。《皇舆通志》卷119第3页也对“饮马”一名作了同样的解释⑧。
rül n)。然而,《明史》在许多段落中都保留了另外一种谬误的形式“胪朐”,如卷6第8和9页,卷126第5和18页,卷130第14页,卷133第2页,卷327第2和6页。在后一段文字中,有一条注释又指出,“胪朐”又称为“饮马河”。因此,《明史》卷6第12页,卷146第13页,卷155第6页和卷328第2页中,就是以“饮马河”之名而记载克鲁伦河的。此名同样也出现在《皇舆考》卷12第35页中,其中的一条注释也说明“饮马”河即相当于“胪朐”河。《武备志》卷223第8页和《朔漠图》中则写作“岫具河赐名饮马河”。有关这一名称,请参阅笔者旧作:《明代蒙古史文献》第95页注(160)。《武备志》中的地图引自《广舆图》,并由此而传入到《皇舆考》卷2第46页中。《皇舆通志》卷119第3页也对“饮马”一名作了同样的解释⑧。
清代的舆地书提供了有关此河的大量资料,并将其名对音作各种形式。《大清一统志》卷544第23-33页中有一条关于该河的简介,其中把河名对音作“克鲁伦”河;在第23页中又认为“胪朐河”即为“克鲁伦河”;但在卷711第10页中又对音作“克勒伦”;这种写法又传到《盛京通志》卷28第8和36页中,还可能写作“克呼伦”。《水道提纲》卷24第3页,卷25第1、2和4页,卷27第1页中均采纳了同一对音法。《朔方备乘》卷24第1页中对音作“喀噜伦”,并且在第1页中补充了在清代各种著作中所出现的一系列对音名称:克鲁伦、克鲁连、合缘怜、客鲁连和怯缘怜等。同时,该书还提到了此名一些更为古老的对音形式。它还记载说,《新唐书》卷217下第7页的拔野古(Bayirqu)传中,提到了一条河流,其对音名称为“康干”,可能就是克鲁伦河一名的对音。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作出定论,但很可能应将此名考证为另一条江河的名称(见下文)。《蒙古游牧记》卷9第3、4、5、10、15、18、20、21、23和26页中,均作“喀鲁伦”;在另一段文字中(卷9第9和10页),肯定又以“驴驹”的形式指克鲁伦河,但我不知道这种形式引自何种文献。《龙沙纪略》第2页中写作“克鲁伦”,《黑龙江外记》第3和4页,《黑龙江志稿》卷3第34页,卷4第34、70和第2页中同样也写作“克鲁伦”。《圣武记》卷3第15、16、34、35、40、41和49页中也持同一写法,1760年的《清代一统地图》第85页中也如此。《圣武记》卷4第34页中写作“库伦河”,书中参阅了《水道提纲》,后一部著作又写作“库兰河”。其中出现了某些混淆,类似我们在两《唐书》中所发现的那种混淆,似乎是把“呼伦池”的名字与“河”字结合在一起了。事实上,本处并不是指注入此湖的克鲁河,而是指源出于此湖的额尔古纳河。所以《黑龙江水道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709页)中作“活轮河”。
我还可以指出,图理琛的《异域录》称克鲁伦河(满文对音转写本第70页)为Herulun,在汉译本第76页中作“黑鲁伦”(Kirulun),这种形式不禁使人联想到了《塞北纪行》中的对音。该对音名称同样也出现在附有汉文标注字的地图中,而在附有满文标注字的地图中则作Herulun,我们可以在满文本的《索引》中发现它,参阅了正文中的第17页。由富克斯在《康熙时代的耶稣会士舆图》中所发表的耶稣会士们的地图集里,在《索引》第268、269和270页中写作“客鲁伦”,而在第166页中的第879和880条目中又指出了其满文对音:kerulen-bira。最后,《蒙古源流》卷3第10页和卷4第7页等处,均把萨囊彻辰原书中提到的K rül
rül n(施密德版本,第71、107、139和159页)译音作“克鲁伦”。《东三省政略》卷1的《边务》下中也写作“克鲁伦”(第12页等处)。《皇朝武功纪盛》卷1第17和18页等处,《绥服外蒙古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2帙第7页等处,《征准噶尔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2帙第22、23和24页)中,《西征经略》(同上丛书,第4帙,第705和708页等处)的写法也相同。《蒙古游牧记》卷9第1页写作“噶鲁伦”。这个时代的其他许多汉文、蒙文、俄文和西文载籍中,也都提到了此河的名称,但却是以各种不同的对音形式出现的。
n(施密德版本,第71、107、139和159页)译音作“克鲁伦”。《东三省政略》卷1的《边务》下中也写作“克鲁伦”(第12页等处)。《皇朝武功纪盛》卷1第17和18页等处,《绥服外蒙古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2帙第7页等处,《征准噶尔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2帙第22、23和24页)中,《西征经略》(同上丛书,第4帙,第705和708页等处)的写法也相同。《蒙古游牧记》卷9第1页写作“噶鲁伦”。这个时代的其他许多汉文、蒙文、俄文和西文载籍中,也都提到了此河的名称,但却是以各种不同的对音形式出现的。
克鲁伦河也注入了呼伦池[K l
l n-na’ur(nōr)],再从那里流出来之后便叫做额尔古纳河(
n-na’ur(nōr)],再从那里流出来之后便叫做额尔古纳河( rgün
rgün ,Ergune),而呼伦池在稍靠东部处又吸收了乌尔逊河(Ursi’un’Ursun),后一条河出自捕鱼儿湖(Büyür-no’ur,Buir-nōr),贝尔湖又吸收了自东部流来的哈拉哈河(Qalqa),哈拉哈河又是由许多自兴安岭流下来的小河组成的。
,Ergune),而呼伦池在稍靠东部处又吸收了乌尔逊河(Ursi’un’Ursun),后一条河出自捕鱼儿湖(Büyür-no’ur,Buir-nōr),贝尔湖又吸收了自东部流来的哈拉哈河(Qalqa),哈拉哈河又是由许多自兴安岭流下来的小河组成的。
唐代中国人似乎就已经知道了呼伦池。在《旧唐书》卷199下第9和10页中,均称之为“俱输泊”(应为“俱轮泊”),而《新唐书》卷219下第7页的一个相应段落中又两次对音写作“俱伦泊”。在下文不远的地方,我们将会遇到《太平寰宇记》卷199第6页和《唐会要》卷96第8页的一些非常近似的行文,其中均记载为“俱轮泊”。辽代的汉文载籍中似乎没有提到过此湖名,至少从我个人的探讨整理来看是这样的。在金代,对于此湖的所知也并不在太多,除非是《金史》卷94第3页中所提到的“栲栲泺”是此湖名的另一种对音。请参阅《观堂集林》卷15第8页。
在元代初期的游记故事中,似乎也未曾出现过呼伦池一名。其原因很简单,因为克鲁伦河下游地区偏离从中原到哈喇和林以北的交通大道,以及距元帝国各组成部分之间进行交流的大道也太远了。呼伦池这一湖名仅在《元朝秘史》中出现过,在该书第53节中转写作“阔连海子”,《元史》卷29第15页中也作同样的对音。此名没有出现在《圣武亲征录》中,因而也未曾出现在《元史》卷1中。但在拉施特《史集》的3段文字中都曾出现过,卷1原本第3页和译本第3页中作K k
k -n覾wūr,贝勒津译文中也将之保留下来了,但它似乎是错误的,应该校正为K
-n覾wūr,贝勒津译文中也将之保留下来了,但它似乎是错误的,应该校正为K l
l (n);卷2原本第89、223页和译本第56、138页中作K
(n);卷2原本第89、223页和译本第56、138页中作K l
l (n)-Naw
(n)-Naw r,即“阔连湖”。其中的K
r,即“阔连湖”。其中的K l
l 似乎代表着一种不发音的-n,如同书中多次出现的nara(n)(太阳)和sora(n)(月亮)的情况一般。
似乎代表着一种不发音的-n,如同书中多次出现的nara(n)(太阳)和sora(n)(月亮)的情况一般。
在明代,《明史》卷7第9页中提到了该湖,对音作“阔滦”(K l
l n)。对于该时代的其他史料,请参阅笔者旧作:《明代蒙古史文献》第23页注
n)。对于该时代的其他史料,请参阅笔者旧作:《明代蒙古史文献》第23页注 。这种对音名称也出现在《皇舆考》卷12第46页中,其中的地图转引自《皇御图》(一)《朔漠图》,但有时有讹误。《皇舆通志》卷119第3页中也保留了“阔连”这种写法,它肯定是由于仿古的原因而造成的。
。这种对音名称也出现在《皇舆考》卷12第46页中,其中的地图转引自《皇御图》(一)《朔漠图》,但有时有讹误。《皇舆通志》卷119第3页中也保留了“阔连”这种写法,它肯定是由于仿古的原因而造成的。
在清代,这一名称曾以多种不同对音形式,而在大量地理文献中出现过。《大清一统志》卷544第23页中写作“呼伦海子”,在同卷第26页中又写作“呼伦湖”;卷71第7-11页中同样也提到了此湖,而且还使用了一个修饰词“池”。《水道提纲》卷24第2页,卷25第3和5页中又写作“枯伦(Külün)”。《朔方备乘》卷24第1-4页又提供了一系列的对音名称,我们在《龙沙纪略》第2页也可以发现它,即“枯伦海子”,在《黑龙江外记》第1-4页中又写作“呼轮”,《黑龙江志稿》卷3第26-27页中作“呼轮诺尔”。《大清一统志》又据此而写作“库楞湖”,但本人没有得到写作“库楞湖”的《朔漠方略》。《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中的《索引》第117页第702条目中,写作“枯轮鄂模”(Kulun-Qmo)。《异域录》称此湖(满文对音本第70页)为Hulun-Qmo,而在汉文本第7页中则作“呼伦湖”;满文本《索引》中参阅了正文第17页,作Hulun。《蒙古游牧记》卷9第1页中同样也写作“呼伦”,而第6页中则作“呼伦诺尔”。最后,《蒙古源流》卷3第21页也写作“呼伦”,它相当于萨囊彻辰蒙文版本(施密德译本第87页)中的K l
l n。《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下第6页中,又重复了由《明史》所采纳的对音法。《黑龙江水道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705和709页)中写作“枯伦鄂模”。《大清一统志》卷711第11页中对此湖作了一条简介,其中把该湖的名称对音作“库楞”。这种对音法又被《盛京通志》卷28第6和8页年转引,而在卷28第36页中又写作“呼伦池”。1760年的《清代一统地图》第84页中又写作“库伦”。在现代的大量西文、蒙文和汉文著作中,也以各种拼写名称来称呼该湖。
n。《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下第6页中,又重复了由《明史》所采纳的对音法。《黑龙江水道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705和709页)中写作“枯伦鄂模”。《大清一统志》卷711第11页中对此湖作了一条简介,其中把该湖的名称对音作“库楞”。这种对音法又被《盛京通志》卷28第6和8页年转引,而在卷28第36页中又写作“呼伦池”。1760年的《清代一统地图》第84页中又写作“库伦”。在现代的大量西文、蒙文和汉文著作中,也以各种拼写名称来称呼该湖。
呼伦池同样也吸收了乌尔逊河,而乌尔逊河则又源出于捕鱼儿湖(Bügür或Büir,贝尔湖)⑨。《蒙古秘史》第53页中又称此河为“兀儿失温”(Ursi’un)。甘露德(Gilbert)神父的《满洲历史地理辞典》第690页中提到的另一种写法为“兀儿逊”,但我不知道它自何处而来。通过其对音文来看,它似乎早于15世纪,相当于原文的Ursūn。
清代的地理著作中提供了各种对音法。《水道提纲》卷25第3和4页中写作“乌里顺”,《朔方备乘》卷24第2和3页中写作“鄂尔顺”(Orsūn),同时还举出了另外某些写法,如“鄂尔逊”、“乌顺”和“五顺”等。《蒙古游牧记》卷9第6页中写作“乌尔顺”和“鄂尔顺”。1760年的《清代一统地图》第84页中也写作“乌尔顺”。完全如同《蒙古游牧记》中的写法一样。《黑龙江志稿》卷4第65页持后两种对音法,而卷4第75页则采纳了第2种以及“乌尔繖”,其中最后一个字是错误的,但却出现在《大清一统志》卷711第7、10和11页中。最后,《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中的《索引》第130页第1119条中写作“乌里顺”。其实,这是《龙沙纪略》第2页中的写法,而《黑龙江外记》第3-4页中写作“乌尔逊”。《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下第12页中写作“鄂尔逊”。《黑龙江水道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709页)则分别作“乌里顺”和“乌顺”(原文如此)。
贝尔湖的水源是乌尔逊河。早在元代,人们通过《圣武亲征录》第28节,就已经获悉此名了,其中写作“盃儿”(Buir);我们还可以通过《元朝秘史》而获悉之,后者在第53和176节中写作“捕鱼儿”(Büyür)。
《元史》在有关成吉思汗的相应段落中,似乎没有保留此湖的名字。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保留《元史》卷1第8页的“盃赤列川”这种对音法,因为后者是指一个地名,在《圣武亲征录》第19节中就是以同样的形式出现的,它与贝尔湖没有任何关系。就目前的所知而言,我尚不知道有关这后一个地名的其他记载。另外,拉施特曾多次提到过它,他曾写作(卷1,原本第3、6和123页,译本第3、49和97页;卷2,原本第194、223和229页,译本第120、138和141页)“捕鱼儿诺尔”(Bu r-nāwūr);贝勒津于其书第1卷第123页的注释中认为,D号手稿中作Büyür。
r-nāwūr);贝勒津于其书第1卷第123页的注释中认为,D号手稿中作Büyür。
在明代,《明史》中曾多次提到过此湖,如卷3第6页、卷130第19页、卷144第5页、卷146第11页和卷327第4页等,一般均写作“捕鱼儿”。请参阅笔者旧作:《明代蒙古史文献》牙第15页注 。此名也出现在《皇舆通志》卷119第3页中,而且也是以相同的对音形式而出现的。
。此名也出现在《皇舆通志》卷119第3页中,而且也是以相同的对音形式而出现的。
清代的地理书又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对音形式。《大清一统志》卷544第26页中写作“布伊尔湖”,卷711第7、10和11页中又作“布雨尔”。《盛京通志》卷28第6和8页中也记载有同样的形式,但卷28第36页中写作“贝尔池”。另外,《盛京通志》卷28第89页转写作“乌尔牙”。《水道提纲》卷25第3-4页也具有同样的对音形式,在卷25第3页中又作“布育里”,卷27第4页中作“捕鱼儿”。《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索引》第98页第127条目中作Buir-Omo,用汉文转写出来便为“布育里鄂模”。《朔方备乘》卷24第2和3页中转写作“贝尔”,并且还出现了许多早已为人们知道的拼写法,其中包括我上文已提到的“布雨尔”。《龙沙纪略》第2页中写作“布育里海”。《黑龙江外记》第3、4、6、7和9页中均作“贝尔”,而第1和2页中作“布雨尔”。这后一种史料在第3页中提到了另一种对音形式“乌雨尔”。《蒙古游牧记》卷9第1页中写作“贝尔”,卷9第6和12页中作“诺尔”,它在康熙二十九年六月以下又引用了《朔漠方略》中的对音,写作“波衣尔”。《蒙古源流》卷3第21页中转写作“贝尔”,萨囊彻辰将此名写作Büir(施密德译文第87页),其中此名又成了一个复合名词,变作了K l n-Bu
l n-Bu ra,即“呼伦布雨尔”,用以指包括在上述两湖之间的地盘。1760年的《清代一统地图》第84页中也写作“贝尔”。《黑龙江志稿》卷3第26页和27页,卷4第52页中也对音为“贝尔”。《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下中,仅在有关“呼伦贝尔”的总传中提到过它。《黑龙江水道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709页)使用了《水道提纲》中的对音形式。
ra,即“呼伦布雨尔”,用以指包括在上述两湖之间的地盘。1760年的《清代一统地图》第84页中也写作“贝尔”。《黑龙江志稿》卷3第26页和27页,卷4第52页中也对音为“贝尔”。《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下中,仅在有关“呼伦贝尔”的总传中提到过它。《黑龙江水道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709页)使用了《水道提纲》中的对音形式。
贝尔湖由哈拉哈河供水,我们可以追踪哈拉哈河自金代以来沿革变迁的踪迹。事实上,《金史》卷94第3页中提到了一条河流,其名曰“哈勒”,它似乎确实是对哈拉哈河不完整的译音。请参阅王国维遗书:《观堂林集》卷15第8页。《圣武亲征录》第27和37节中确实曾提到过此河,写作“合勒哈”。《元朝秘史》第175、176、191、192和208节中也持同样的写法。《元史》卷145第9页似乎也以“罕哈”这种形式而提到了该河,但很难形成定论。因为在这一对音名词之后,还附有一个“哈剌海”,这两种成分很可能应形成同一个复合名称。但经过最后的斟酌之后,我还是认为第一个词组系指哈拉哈河。
此名似乎在明代没有出现过。然而,《皇舆考》卷12第38页中提到了一条河叫做“哈剌哈”,它确实就是注入了贝尔湖的哈拉哈河。《皇舆通志》卷116第8页中,又提到了一条“哈剌哈千户所”。
在清代,许多舆地类著作也都提到过哈拉哈河。《大清一统志》卷711第7页(《盛京通志》卷28第6和35页中都沿袭同样的写法)提到它时,对音作“喀尔喀”,该河在清代的几乎所有地理著作中,也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如《水道提纲》卷25第3页、《朔方备乘》卷24第3页、《龙江纪略》第2页、《蒙古游牧记》卷9第3、6、10和12页、67页,另外还有1760年的《清代一统地图》第84页等处的文献。《黑龙江外记》第4页中写作“噶勒噶”,而在第2和3页中又作“喀尔喀”。《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的《索引》第115页第642条目中写作Kalka-Bira,在汉文中对音则为“喀儿喀”,即《黑龙江水道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卷4第709页)中的写法。
由克鲁伦河形成的这一水系,一方面是哈拉哈河和乌尔逊河,它们又注入了呼伦池;另一方面,它们又自该湖中流出而形成额尔古纳河,在右岸获得了许多支流,我将于下文再论述它。
额尔古纳河在元代之前似乎未以此名出现过。《元朝秘史》在第141、144和182节中对音作“额洏古涅( rgüna)”。《元史》中唯有一次提到过它(卷118第5页),对音作”也里古纳”(
rgüna)”。《元史》中唯有一次提到过它(卷118第5页),对音作”也里古纳”( rgün
rgün )。拉施特在《史集》卷1原本第3页和译本第3页中,均写作
)。拉施特在《史集》卷1原本第3页和译本第3页中,均写作 rgüna;在卷2原本第89页和译本第56页中;写作
rgüna;在卷2原本第89页和译本第56页中;写作 rgǖn
rgǖn ,均为“额洏古涅”之对音。在明代,《皇舆考》卷12第37页中“阿儿温河”,《明史》卷2第9页、卷126第5页、卷133第133和20页中都写作“阿鲁浑”(Argun)。我在《皇舆通志》卷176第7页也发现了同一形式,而在卷116第8页中却对音作“哈流温千户所”;“哈流温”一名也出现在《广舆图》中的《朔漠图》上,它可能代表着Har’un(?)这样的原形。将这后一个名词考证成鄂尔古纳河(Arghun)的作法是不太可靠的。但在《皇舆通志》中,具有这一名称的“千户所”则出现在另一组地名中,其中列有“海喇儿”千户所、“哈剌哈”千户所和一个“亦迷河”卫。明代的所有地理文献,似乎均自《大明一统志》衍生而来,唯有《广舆图》例外。《大明一统志》卷89第7页在一张有关行政区的名表中,已提到了一个“阿尔温河卫”。它似乎是涉及了额尔古纳河,因为此名出现在另一批行政机构之前,后者之中包括“海剌儿千户所”、“哈喇哈千户所”和“哈流温千户所”。另一方面,《大明一统志》在同一卷下文不远处(第8页),又提到了“兀鲁温河”。在这些与鄂尔浑河很近似的对音名词之间,具有某些联系,但尚十分难以定夺。
,均为“额洏古涅”之对音。在明代,《皇舆考》卷12第37页中“阿儿温河”,《明史》卷2第9页、卷126第5页、卷133第133和20页中都写作“阿鲁浑”(Argun)。我在《皇舆通志》卷176第7页也发现了同一形式,而在卷116第8页中却对音作“哈流温千户所”;“哈流温”一名也出现在《广舆图》中的《朔漠图》上,它可能代表着Har’un(?)这样的原形。将这后一个名词考证成鄂尔古纳河(Arghun)的作法是不太可靠的。但在《皇舆通志》中,具有这一名称的“千户所”则出现在另一组地名中,其中列有“海喇儿”千户所、“哈剌哈”千户所和一个“亦迷河”卫。明代的所有地理文献,似乎均自《大明一统志》衍生而来,唯有《广舆图》例外。《大明一统志》卷89第7页在一张有关行政区的名表中,已提到了一个“阿尔温河卫”。它似乎是涉及了额尔古纳河,因为此名出现在另一批行政机构之前,后者之中包括“海剌儿千户所”、“哈喇哈千户所”和“哈流温千户所”。另一方面,《大明一统志》在同一卷下文不远处(第8页),又提到了“兀鲁温河”。在这些与鄂尔浑河很近似的对音名词之间,具有某些联系,但尚十分难以定夺。
在清代,《大清一统志》卷544第23和26页,卷711第8和10页、《水道提纲》卷24第3页和卷25第5页、《朔方备乘》卷24(图)第1页、《黑龙江志稿》卷4第74页、《黑龙江外记》第1、2和4页等处,均写作“额尔古纳”,《盛京通志》卷28第8和36页以及1760年的《清代一统地图》第64页中,其写法也相同。另外,《黑龙江志稿》卷3第26页,卷4第52、59、60、72和80页中均写作“额尔古纳”,这可能是由于后者之中的“讷”字系“纳”字之误。《朔方备乘》卷24第1和第4页中写作“鄂尔古纳”,完全如同《龙沙纪略》第2页中所作的那样。《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索引》第103页第267条目中写作Ergunebira,译作汉文后则为“厄勒古挪河”。最后,《异域录》(满文对音本)第70页中写作Ergune,译作汉文之后则为“额尔古纳”,我们在地图上也可以发现这种对音形式,第17页的满文本《索引》中则作Ergune,《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上第5、13和14页等处,卷Ι下第3、4和5页等处的对音也如同上述之“额尔古纳”,而《圣武记》卷6第4页中又写作“额尔乎纳”(Arguna),《黑龙江水道编》(《小方壶斋舆地丛》第4帙第705和709页)则作“额尔古纳”的水流⑩。
额尔古纳河在其右岸获得了海拉尔河水的流量,而海拉尔河左岸的主要支流则是亦迷河,有关该河的近代转写法形形色色,差异很大,所以最好保留其古代的汉语对音。额尔古纳河然后又吸收了根河(K n,Gan/kan)之水,其右岸的主要支流是得尔布尔河(Tülb
n,Gan/kan)之水,其右岸的主要支流是得尔布尔河(Tülb r)。《大清一统志》卷711第10—11页中一一列举了位于呼伦池和贝尔湖地区以东的所有河流名称。
r)。《大清一统志》卷711第10—11页中一一列举了位于呼伦池和贝尔湖地区以东的所有河流名称。
亦迷河首次出现于《金史》卷94第13页中对音作“移密”,《元史》卷132第9页中作“亦迷”,这种对音法同样也出现在《明史》卷129第4页和卷132第6页中。《皇舆考》卷12第37页写作“依奔”,但它同时又提醒人们注意(卷12第38页),此河名有时也写作“亦迷”。《皇舆通志》卷116第8页提到了“亦迷河卫”,同时也提到了此河的名称(卷116第9页)。《大明一统志》卷89第6页提到了一个“依木卫”,在稍后不远处(同一卷第7页)又提到“亦迷河卫”。最后,在同卷第9页中,又提到了“一迷河”。我上文所引证的地理文献,均自该文献衍生而出。
在清代的地理书中,《大清一统志》卷711第10页称此河为“伊棉”。《水道提纲》卷25第5页中作“衣母”,但在第25卷第4页中又列举了另外两种对音形式“依木”和“伊密”,而在第24卷第4页中还曾写作“伊穆”。现代中国地图中写作“伊敏河”,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5第10页)就将它考证为“亦迷”。《黑龙江外记》第3页中作“伊本”,而在第4页则作“伊密”和“伊木”。《黑龙江志稿》卷4第55页中作“伊棉”,在同卷第62页中又提到“伊敏”。《龙沙纪略》第2页中写作“伊密”,在第2和第5页中又作“伊木”。《盛京通志》卷28第32页中作“伊棉”。我在《黑龙江志稿》卷4第52、55、56、57、60和63页等处又遇到过“依奔”的写法,《朔方备乘》卷24第3页中则又作“衣本”。这最后一种对音名称,则是选用“奔”字进行拼写的起源,但“奔”字实际上仅仅是“本”字之误。由“伊木”开始,我们便会追溯到“亦迷”,因为后者与原形相符。《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中的《索引》第160页第700条目和第112页第537条目,都写作“衣本”。《清代一统地图》第84页中写作“依奔”。《异域录》满文转写本第74页中作Ibang,这种形式在原文第18页和对音文第74页注 都出现过,汉文本第8页中作“伊邦”。最后,《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下第10、15、16和31页中均写作“伊穆”,而《黑龙江水道编》卷4第709页则作“衣母”。《盛京通志》提到了各种不同的形式,似乎是指某些不同的河流。据《大清一统志》记载,它在卷28第32页中写作“伊绵”,并且附有这样一条札记,指出它源出兴安岭,向北流去注入海剌尔;在卷28第8页中又提到一条“伊玛”河,它从兴安岭流出,并向西流之后注入了额尔古纳河。在该书下文不远的地方,又是提到了在其他有关亦米河的文献中所出现的两种形式:其一(卷28第34页)作“伊本”,没有提供具体资料;其二(卷28第35页)写作“伊穆”,并且认为该河向西北流去并注入额尔古纳河。在清代的文献中,似乎出现了许多混乱,笔者无法于此进行探讨,因为我没有掌握具体的地理文献。该书中同样还提供了(卷28第58页)另一条有关“伊密”河的札记,伊密河也应为同一条河。
都出现过,汉文本第8页中作“伊邦”。最后,《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下第10、15、16和31页中均写作“伊穆”,而《黑龙江水道编》卷4第709页则作“衣母”。《盛京通志》提到了各种不同的形式,似乎是指某些不同的河流。据《大清一统志》记载,它在卷28第32页中写作“伊绵”,并且附有这样一条札记,指出它源出兴安岭,向北流去注入海剌尔;在卷28第8页中又提到一条“伊玛”河,它从兴安岭流出,并向西流之后注入了额尔古纳河。在该书下文不远的地方,又是提到了在其他有关亦米河的文献中所出现的两种形式:其一(卷28第34页)作“伊本”,没有提供具体资料;其二(卷28第35页)写作“伊穆”,并且认为该河向西北流去并注入额尔古纳河。在清代的文献中,似乎出现了许多混乱,笔者无法于此进行探讨,因为我没有掌握具体的地理文献。该书中同样还提供了(卷28第58页)另一条有关“伊密”河的札记,伊密河也应为同一条河。
在元代之前的汉文载籍中,似乎未对根河俄所记载。《圣武亲征录》第22节中对音作“犍”,因此与《元史》卷1第8页中的写法相同。《元史》卷123第2页中又对音作“坚”。《元朝秘史》第141节中写作“刊河”。《元史》卷3第10页中很可能是以“吉河”的形式而提到此河名称的,而且在针对拔都(B daü)王子时提到该河的(有关拔都王的情况,请参阅笔者旧作《元史》卷107译注第107页注释)。《明史》卷328第7页中又以“赶”河的名称而提到此河,“干赶”很可能是用字重复。《皇舆通志》卷12第36页中写作“坚”,所以《皇舆通志》卷116第6页中提到了一个“亦迷河卫”,有关这一可能比较古老的形式,上文业已有所论述。
daü)王子时提到该河的(有关拔都王的情况,请参阅笔者旧作《元史》卷107译注第107页注释)。《明史》卷328第7页中又以“赶”河的名称而提到此河,“干赶”很可能是用字重复。《皇舆通志》卷12第36页中写作“坚”,所以《皇舆通志》卷116第6页中提到了一个“亦迷河卫”,有关这一可能比较古老的形式,上文业已有所论述。
在清代的地理文献中还曾出现过其他对音形式。《大清一统志》卷711第8页写作“根”,《盛京通志》卷28第34页沿袭了这种形式。《水道提纲》卷25第4页同样也写作“根”。《朔方备乘》卷24第1、3和4页也作“根”,这种写法同样也出现在《黑龙江外记》第4页中,在《黑龙江志稿》卷3第27、29页,卷4第52、58、60、78、80、82页中,在《清代一统地图》第64页中都出现了同样的写法。在《耶稣会士舆图》滿文本中的《索引》第115页第649条目中,均写作Kanai-bira,译作汉文则作“喀尔”(原文如此)。《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卷上第17和18页,卷下第6、12、16和18页等处均作“根”,《西征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2帙第31页)也作“根”。
得尔布尔河自元代以来,同样就为人所熟知。《圣武亲征录》第22节(《元史》卷1第8页沿袭了这种写法)写作“秃律别儿”。在元代的其他文献中似乎未曾出现过此名,甚至明代的文献中也不知该地名。然而,《元史》卷118第5页与额尔古纳河并列提到了另一条河,并将其名对音作“迭列木儿”,肯定应该将其中的“木”改正为“不”字。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得到“得尔布尔河”(D lbür)的变位形式Tülb
lbür)的变位形式Tülb r。唯有清代的地理文献中才提到过此名。《水道提纲》卷25第5页中写作“忒儿布勒”(T
r。唯有清代的地理文献中才提到过此名。《水道提纲》卷25第5页中写作“忒儿布勒”(T bül)。《朔方备乘》卷24第4页中持同一写法;但在该书同一卷第4页中又作“得尔布尔”(D
bül)。《朔方备乘》卷24第4页中持同一写法;但在该书同一卷第4页中又作“得尔布尔”(D rbür)和“得勒布尔”(D
rbür)和“得勒布尔”(D lbür),其换位的对音法与《元史》中的写法相似。《黑龙江外记》第4页中作“特勒布尔”。《龙沙纪略》第2页中写作“特儿布尔”,而《清代一统地图》第64页和《黑龙江志稿》卷4第78和83页均作“特勒布尔”。《盛京通志》卷28第8和34页中的错误拼写法为“特勒古尔”。《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中的《索引》第128页第108条目中作Telbur-bir,译作汉文之后为“忒尔布勒”。《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卷下第13页写作“特勒布尔”,而《黑龙江水道编》卷4第709页中却写作“忒儿布勒”。
lbür),其换位的对音法与《元史》中的写法相似。《黑龙江外记》第4页中作“特勒布尔”。《龙沙纪略》第2页中写作“特儿布尔”,而《清代一统地图》第64页和《黑龙江志稿》卷4第78和83页均作“特勒布尔”。《盛京通志》卷28第8和34页中的错误拼写法为“特勒古尔”。《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中的《索引》第128页第108条目中作Telbur-bir,译作汉文之后为“忒尔布勒”。《东三省政略》卷1《边务》卷下第13页写作“特勒布尔”,而《黑龙江水道编》卷4第709页中却写作“忒儿布勒”。
额尔古纳河然后向东北方向流去,在苏联领土上又获得了石勒喀河注入。而石勒喀河本身又是由音果达河(Ingoda)和鄂嫩河(Onon)汇流而成。石勒河源出距克鲁伦河不远的地方,而克鲁伦河又发源于蒙古领土。在鄂嫩河流域与克鲁伦河河谷之间,有一条乌勒吉河,消失在“巴伦托雷”湖(Barun-torei),也就是西托雷湖。
在元代之前的汉文载籍中,似乎没有出现过鄂嫩河一名。《元朝秘史》第1、24、30和32节等处;《元史》卷1第5、7、12和14页,卷3第2和4页,卷121第1页等处均作“斡难”(Onan)。《明史》卷6第9页,卷146第3页,卷155第6页,卷327第6页等处的写法也相同,但《圣武亲征录》第8、9、18、29、33和40节等处,拉施特《史集》卷1原本第3页(译本第3页)等处均写作ōnan或Onan,也就是“斡难”之对音,卷2原本第168页(译本第103页)中的写法也相同。然而,《元史》卷120第10页中写作“兀难”(Unan),卷119第1页则作“阿难”,也就是“斡难” 。我们在明代的载籍中也会发现该河名。《皇舆考》卷7第47页和卷12第37页,也是以“斡难”这一对音名称而出现的;在《广舆图》、《朔漠图》卷2和《四夷图》卷2中也都写作“斡难”。《皇舆通志》卷116第6页中,提到了一个具有此名的“卫”,同时在卷119第2和3页中也提到了该河。
。我们在明代的载籍中也会发现该河名。《皇舆考》卷7第47页和卷12第37页,也是以“斡难”这一对音名称而出现的;在《广舆图》、《朔漠图》卷2和《四夷图》卷2中也都写作“斡难”。《皇舆通志》卷116第6页中,提到了一个具有此名的“卫”,同时在卷119第2和3页中也提到了该河。
在清代,《大清一统志》卷544第24页中写作“敖嫩”,并且还提到了“鄂诺”和“倭努”等写法。《朔方备乘》卷24第1页,卷25第1和2页同样也对音作“敖嫩”,在卷24第5页中又提到了另一种对音形式“鄂嫩”。《蒙古游牧记》卷9第5、10和20页也写作“敖嫩”。《蒙古源流》卷3第4、11和21页写作“鄂诺”,而卷4第7页则作“鄂嫩”。《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中的《索引》第174页第1078条目、第268和269页也都作“敖嫩” 。《水道提纲》卷24第1页的写法也相同。相反,《清代一统地图》第65和85页中没有提到此河的名称。(https://www.xing528.com)
。《水道提纲》卷24第1页的写法也相同。相反,《清代一统地图》第65和85页中没有提到此河的名称。(https://www.xing528.com)
我已经指出过的最后一条河的名称为乌勒吉河。它首次于《金史》卷94第7页中出现过,写作“斡里札”(Olja)。《元朝秘史》第132和133节中又称此河为“浯氻札”(Uija)。此河名既未出现在《圣武亲征录》中,也不见诸《元史》。然而,拉施特《史集》卷2原本第168页和译文第103页中提到了此河,也作“浯氻札”(ūlja)。在明代的《皇舆考》卷12第13页中提到的也可能是此河,但写作“兀察”。清代的舆地书中又以各种不同的名称称呼此河。但《大清一统志》在卷544第23-24页,中似乎没有提到该河;相反,在卷533中称之为“库伦”,地图上标注为“乌尔匝”(Uldza),卷133第2页中也提到了它。箭内薮五在《蒙古史研究》第555页中,又举出了此河的对音名称为“乌里杂”(Uldza)和“乌尔载”(Uldzai)但他没有提到这些名称的来源,我也无法知道其出处。最后,《圣武记》卷3第31页写作“乌尔匝”,《征准噶尔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2帙第21页)也沿袭了这种写法,其中的-dz-是古蒙文中-j-的现代发音。《读史方舆纪要》卷45第1897-1898页,提到此名时对音作“兀古儿札”(Ugulja),但我不知道其来源如何,它似乎是对Ugulga>U’ulja>ūlja的一种任性和专断的复原法。《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中的《索引》内没有提到此河,在附于该著之后的转载地图4和5中,也没有出现该河名。相反,在《清代一统地图》第65和85页中,此河则以“乌尔再”的形式而出现。
除了这一系列河流名称之外,汉文史籍中还保留下了某些地名,有的是在元代之后不久而出现的,如“彻彻儿”(C kc
kc r)系指一座小山,“撒里哈”(Sāri-k
r)系指一座小山,“撒里哈”(Sāri-k r)之意为“丘陵河谷”。其中的Sa’ari的本意为“皮”,相当于突厥文中的sarri,“皮革”一词意即由此衍生而来;其中的k
r)之意为“丘陵河谷”。其中的Sa’ari的本意为“皮”,相当于突厥文中的sarri,“皮革”一词意即由此衍生而来;其中的k r<k
r<k ’
’ r,却意为“流经的河谷”。另外一个地名具有悠久的历史,这就是杭爱(Qanqrā
r,却意为“流经的河谷”。另外一个地名具有悠久的历史,这就是杭爱(Qanqrā ,Khangai)山脉。
,Khangai)山脉。
彻彻儿和撒里哈等地还分别在15世纪初叶曾出现过,我们可以认为较晚期的记载均引自这个时代的文献。《圣武亲征录》在第21、24和33节中,以及《元史》卷1第8页中,都将C kc
kc r对音作“彻彻儿”。在《元史》卷29第16页中,此地名可能是与另一个地名联合使用的,即“彻彻儿火儿火思”;在卷180第3页中同样也与另一个地名联合使用,指一片山脉,即“彻彻里泽剌之山”。拉施特在《史集》卷2原本第197页和译本第122页、原本第204页和译本第126页又向我们证实了这种读法,因为在后一部史籍中也写作C?kc?r。《元朝秘史》在第61、67和94节中均作“扯克彻儿”,而在第142节中又作“彻克彻列”(C
r对音作“彻彻儿”。在《元史》卷29第16页中,此地名可能是与另一个地名联合使用的,即“彻彻儿火儿火思”;在卷180第3页中同样也与另一个地名联合使用,指一片山脉,即“彻彻里泽剌之山”。拉施特在《史集》卷2原本第197页和译本第122页、原本第204页和译本第126页又向我们证实了这种读法,因为在后一部史籍中也写作C?kc?r。《元朝秘史》在第61、67和94节中均作“扯克彻儿”,而在第142节中又作“彻克彻列”(C kc
kc r-
r- )。这后一种形式首先完整地出现在《元史》中,但后来又脱落了两个“彻”字之间和偏向左侧的小体字“克”。它后来又出现在明代的文献中。事实上,《明山藏》卷4第24页中又写作相同的形式。此外尚可见《岷峨山人译语》第4页在1388年以下,《明史》卷1下第25页、《殊域周咨录》卷16第22-23页、在1392年下;《皇明融华录类编》卷129第12页以及《明史》卷3第6和14页。在1396年下
)。这后一种形式首先完整地出现在《元史》中,但后来又脱落了两个“彻”字之间和偏向左侧的小体字“克”。它后来又出现在明代的文献中。事实上,《明山藏》卷4第24页中又写作相同的形式。此外尚可见《岷峨山人译语》第4页在1388年以下,《明史》卷1下第25页、《殊域周咨录》卷16第22-23页、在1392年下;《皇明融华录类编》卷129第12页以及《明史》卷3第6和14页。在1396年下 ,都出现过此名。17和18世纪某些蒙古文史籍,如《蒙古黄金史》第28页中写作Cik
,都出现过此名。17和18世纪某些蒙古文史籍,如《蒙古黄金史》第28页中写作Cik c
c r,Oduqat Cikacar Cuqurqu qoyar-un Jaqura Qouggirad-un Dii-Sacan Jolraba,翻译出来即为“出发了,他在扯克彻尔和楚呼尔呼两山之间遇到了弘吉剌特的特薛禅”。此名又于下文在第30页和47页中出现过,但都写作“Cakcar”,而在第89页中又作Cakacar。事实上,《蒙古黄金史》中的这段蒙文文献,仅仅是对音转写本的《元朝秘史》的原蒙文本那已有讹变的蒙文形式,所以它除了向我们提供了该文献的传播史之外,其他一无所益。另外,《蒙古黄金史》(我采纳了鲍登的版本,因为它比较容易找到)在提到扯克彻尔这一山名时,其名称也有所讹变,该文献在口头流传中有误,因为使上述名词变成了一个人名的第2个组成部分。因此,此名曾以Tongqur-C
r,Oduqat Cikacar Cuqurqu qoyar-un Jaqura Qouggirad-un Dii-Sacan Jolraba,翻译出来即为“出发了,他在扯克彻尔和楚呼尔呼两山之间遇到了弘吉剌特的特薛禅”。此名又于下文在第30页和47页中出现过,但都写作“Cakcar”,而在第89页中又作Cakacar。事实上,《蒙古黄金史》中的这段蒙文文献,仅仅是对音转写本的《元朝秘史》的原蒙文本那已有讹变的蒙文形式,所以它除了向我们提供了该文献的传播史之外,其他一无所益。另外,《蒙古黄金史》(我采纳了鲍登的版本,因为它比较容易找到)在提到扯克彻尔这一山名时,其名称也有所讹变,该文献在口头流传中有误,因为使上述名词变成了一个人名的第2个组成部分。因此,此名曾以Tongqur-C kic
kic r的形式而出现过,鲍登先生认为应该校勘为Tongsur-Ciugcir,而由贡保耶夫所发表的手稿中的写法为最佳。有关这一问题,请参阅鲍登先生在其著第118页注④中所作的解释。萨囊彻辰的一批手稿中没有提到此地,但如果晚期史著中根据其中所罗列的各种文献而引用它,那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
r的形式而出现过,鲍登先生认为应该校勘为Tongsur-Ciugcir,而由贡保耶夫所发表的手稿中的写法为最佳。有关这一问题,请参阅鲍登先生在其著第118页注④中所作的解释。萨囊彻辰的一批手稿中没有提到此地,但如果晚期史著中根据其中所罗列的各种文献而引用它,那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元朝秘史》而了解撒里客儿,该著在第128、161、177、193、197和280节中均对音作“撒阿里客额尔”,其中的“里”字在右侧又注有一个小小的“舌”字,以表示应该作-ri,如同用-r表示“儿”一般。《圣武亲征录》第4和14节,《元史》卷1第4和7页中均作对音为“萨里”。最后,拉施特《史集》(卷2,原本第148、186和190页,译本第92、115和118页)中都作Sari-Kari-Kahar,即“撒阿里客额儿”之对音。此名可能在当时的文献中也得以保存下来了,例如保存在某些蒙古人的墓志铭中,这些蒙古人的先祖曾是成吉思汗的战友。无论如何,此名也曾出现在明代的史籍中。事实上,明代史籍针对洪武和永乐年间,他们在东蒙古地区亲自统率军队进行战争时,提到了此地。《罪唯录》卷4第24页中作“撒里哈儿”,应改作“撒里客儿”(Sari-Kar)。上述写法借鉴于《万历武功录》卷7第6页中,这后一部著作成书于1612年之前,因为1612年是为其作序的时间。《罪唯录》成书于1655年至1675年。另一方面,1565年的《鸿猷录》在卷8第25页中,将此地对音成“撒里怯儿”。在1431年之前成书的《后北征录》第4页中,也持这种写法。最后,成书于16世纪中叶的《四夷考》(《宝颜堂秘笈》版本卷5第5页)中与《鸿猷录》中的写法一样,都作“撒时怯儿”。此名还出现在《广舆图》(《朔漠图》卷2)以及《皇舆考》第47页中,后者沿袭前者。但此名缺乏任何真实性的传统,仅以一种武断的形式载于这些著作中。
在杭爱山问题上,却更困难一些。因为“杭爱”一名最早与一山脉的名称联合使用,该山脉似乎系指北蒙古的所有大山,但却无法确定其具体方位。人们曾假设认为它们位于“北海”(指贝加尔湖)附近,“杭爱”一名的本义为“沙漠地带”即由此而来。《山海经》(1809年版本)卷11第4页注释中提到了此名,并且写作“瀚海”;《史记》卷110第24页和卷111第12页中提到此地时;也称之为“瀚海。《前汉书》卷55第12页和卷94第21页,《三国志》魏志卷14第9页中均都采纳了这种写法 。
。
《旧唐书》中也多次以同样的对音名称提到该地,如卷4第10页,卷121第1页,卷185上第3页,卷194上第9页,卷194下第1页,卷195第1-2页,卷199第1和4页。《新唐书》卷43下第2页和卷217下第4页中也提到了该地,此外还有卷197第2页,卷215上第10和11页,卷217下第4和9页,卷224上第1页。”翰海”在两段文字中很可能是指贝加尔湖,这就是《旧唐书》卷199第1页和《新唐书》卷217下第4页中记载的情况。
“翰海”一名仅仅出现在元代,用以指从克鲁伦河流域直到阿尔泰山和土瓦山之间的山脉。《元朝秘史》第194节中对音作”康孩”,这两个字在左侧又附有一个小体”中”字,因而就是Qangqai之对音。《圣武亲征录》第37节中对音作”沆海”,这后一种形式又由《元史》卷1第13页所采纳。在《元史》卷17第15页,卷18第2页,卷59第39页,卷119第21和22页,卷128第17页等处,均作”杭海”,在卷168第26页中则作”翰海” 。常德的《西使记》第7页(王国维版本)重新使用了古代的拼写法”瀚海”。《皇舆通志》卷119第3页中写作”瀚海”,而在卷117第5页中则认为是指沙漠
。常德的《西使记》第7页(王国维版本)重新使用了古代的拼写法”瀚海”。《皇舆通志》卷119第3页中写作”瀚海”,而在卷117第5页中则认为是指沙漠 。
。
在明代,此名也以同样的写法而出现在《大明一统志》卷89第21页中,对音作”瀚海”。由道安所作的《西游胜览诗》保存在《野获编》(补遣)中,其中在卷4第46页中向我们提供的一种对音形式即”瀚海”。《皇舆通志》卷119第3页中也写作”瀚海”;而在卷117第5页中,它却是指沙漠。
清代的地理文献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而提到过此地。《大清一统志》卷544第1页作”翰海”,而在卷411第1页中又写作”杭海”。《朔方备乘》卷24第2页和《水道提纲》卷27第4页中作”翰海”。在《蒙古游牧记》卷7第1页和卷9第1页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写法。《朔方备乘》卷4第1页中写作”杭爱”,而在卷33第2页中又作”沆海“。《蒙古源流》卷4第2和第6页中均作”杭爱“ 。《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中的《索引》第156页第588条目中,作Hanggai-alin,即”杭爱山“。《异域录》(满文本第17页,对音转写本第70页)中作Hanggai Han Alin,在汉译本第7页中作”杭爱汗山“。事实上,这类文献中有一大批,其中包括《圣武记》卷3第13和16页,《绥服外蒙古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2帙第7页)和《征准噶尔记》(同上引丛书,第2帙第23—24页)等处明显地把Han-hai(瀚海沙漠)与Han-ngai(杭爱山脉)区别开了。
。《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中的《索引》第156页第588条目中,作Hanggai-alin,即”杭爱山“。《异域录》(满文本第17页,对音转写本第70页)中作Hanggai Han Alin,在汉译本第7页中作”杭爱汗山“。事实上,这类文献中有一大批,其中包括《圣武记》卷3第13和16页,《绥服外蒙古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2帙第7页)和《征准噶尔记》(同上引丛书,第2帙第23—24页)等处明显地把Han-hai(瀚海沙漠)与Han-ngai(杭爱山脉)区别开了。
我们可能还会得到一些在西蒙古残存下来的地名与河名,如现代地图中的乌伦古河(Urungu)、乞则里八海(Kizil-bas)和拜达里格河(BaidariK)。事实上,乌伦古河从元代起就出现在汉文载籍中了。《长春真人西游记》第20页(王国维版本)中作“乌伦古”(ürüngü),《西使记》第7页(王国维版本)中作“龙骨”。《元朝秘史》第158节中作“兀泷古”,而在第177节中又作“浯笼古”。此河名似乎没有出现在元代那些常见的典籍中,但却见诸某些作家们的文献著作中,特别是出现在耶律楚才的著作中。在明代,汉文舆地书中没有出现此河名,完全如同由《广舆图》和其他类似载籍所证实的那样。
清代的舆地书也曾多次提到该地,正如伯希和在《圣武亲征录》译注本第1卷第315页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还可以从中增补“畏隆古河”这种形式,后者出现在《耶稣会士舆图》中,该书满文本中的《索引》第175页第1109条目译作满文Oronggu-bira,即“畏隆古河”之对音。此外,在《水道提纲》卷23第3页和《西北诸水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842-843页)中的一条有关札记中,也是这样写的。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种形式“乌隆古”,出现在《准噶尔荡平述略》,见《朔方备乘》卷4第4页;另外一种形式为“乌陇古”载同一合集本卷33第2页中。《圣武记》卷4第6页中的对音写法与在《耶稣会士舆图》中一样,均作“乌隆古”,《皇朝武功纪盛》卷2第8页和《荡平准部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59页)的对音也相同。《西域水道记》中提到了乾隆时代的许多文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884页)在乾隆二十年和二十一年以下,第884页在乾隆二十年和二十二年以下,此名也都是以同样的对音形式而出现的。此外,我还应该补充《清代一统地图》,该著第69页中也使用了同样的转写法。
《元朝秘史》中也提到了乌伦古湖,其中在第158节中写作“乞湿巴失”(Kisil-bas),“湿”字旁也附有一个小体“ ”字,这就说明应该将之读作-sil;在第177节中作“乞赤巴石”(Kicil-bas),“赤”字旁也附有一个小体“
”字,这就说明应该将之读作-sil;在第177节中作“乞赤巴石”(Kicil-bas),“赤”字旁也附有一个小体“ ”,因此应该作-cil。《圣武亲征录》第15节中写作“黑辛八石”(Kicil-bas),《元史》卷1第7页中沿袭了这后一种写法,而同一部元代断代史卷149第12页中则写作“乞则里八海”[Kizil-ba(s)]。刘郁的《西使记》(王国维版本)第7页中写作“乞则里八寺”。最后,拉施特《史集》卷2原本第182页和译本第112,卷3原本第159页和译本第107页中作Qizil-bas,也是“乞则里八寺”之对音。
”,因此应该作-cil。《圣武亲征录》第15节中写作“黑辛八石”(Kicil-bas),《元史》卷1第7页中沿袭了这后一种写法,而同一部元代断代史卷149第12页中则写作“乞则里八海”[Kizil-ba(s)]。刘郁的《西使记》(王国维版本)第7页中写作“乞则里八寺”。最后,拉施特《史集》卷2原本第182页和译本第112,卷3原本第159页和译本第107页中作Qizil-bas,也是“乞则里八寺”之对音。
此名不见诸明代的舆地著作,而清代的地理著作却大量记载。《朔方备乘》卷33第3页中提到了此名,但采纳了《圣武亲征录》中的写法。《水道提纲》卷23第3页中写作“奇萨尔巴思鄂模”(Kisal-bas Omo)。《耶稣会士舆图》满文本中的《索引》第167页第892条目中作Kisalbas-Omo,即“奇萨尔巴思鄂模”之对音。《西北诸水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842页)中的写法也相同。《西域水道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843页)中写作“噶勒札尔巴什淖尔”,其中在第884页中又提到了另一种写法“赫色勒巴什淖尔”,后一种写法出自于《西域图志》卷25第3页和第14页中的对音法。这种写法同样也传入了《西域同文志》卷上第311页(即第5卷12页)和卷下第77页中(东洋文库版本),其中写作Kesel-basinarur,畏吾儿文为Xizil-basi-nur,即“赫色勒巴什淖尔”之对音,在第72页(大英博物馆藏抄本)中的蒙古文写法与上相同,而畏吾儿文却作Qizil-basi-nur,均为“赫色勒巴什淖尔”之对音。最后,《清代一统地图》第69页中,转写作“和色尔巴斯”。
当代以拜达里格而著称的那条河流的名称,似乎从元代起就已经出现了。事实上,我们在《元朝秘史》第159节中,却发现它以其对音名称“巴亦答剌黑别勒赤列”(Bayidaraq-b lcir
lcir )的形式出现,而在第177节中则作“拜答剌黑别勒赤厅”(Baidaraq-b
)的形式出现,而在第177节中则作“拜答剌黑别勒赤厅”(Baidaraq-b lcir
lcir ),其中的-a则表示方位与格。这种写法也曾出现在《圣武亲征录》第15和27节中,均作“拜答剌边只儿”[Baidara(q)-B
),其中的-a则表示方位与格。这种写法也曾出现在《圣武亲征录》第15和27节中,均作“拜答剌边只儿”[Baidara(q)-B ljiy]。拉施特《史集》卷2(原本第222页,译本第137页)也有此名,事实上应该读作Bāidariq或Báidar
ljiy]。拉施特《史集》卷2(原本第222页,译本第137页)也有此名,事实上应该读作Bāidariq或Báidar q,即“拜答”的对音,第2个名称实际上应读作bèlcir-a,因而也就是“巴亦答剌黑别勒赤列”的对音。这样一来,它就与汉蒙文载籍相吻合了。在明代的汉文地理书中,没有记载这一地段;但清代的地志,却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不同写法。《耶稣会士舆图》中的对音形式为“贝德洛克河”,在满文版中译作Baitarikbira,详见满文本中的《索引》第139页第120和121条目。《水道提纲》卷23第8页中作“贝得勒克”(Baidarak,Baidarik),完全与《西北诸水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843页)中的写法一样。《朔方备乘》卷4第3页中写作“拜达里克”(Baidarik),这种写法也出现在《蒙古游牧记》卷8第8页中,后者同样也写作“拜塔里克”。《圣武记》卷3第26、38、62和63页以及卷4第10页中,也都写作“拜达里克”,完全如同《绥服厄鲁特蒙古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2帙第18页)和《荡平准部记》(同上丛书,第4帙第59页)中的写法一样。
q,即“拜答”的对音,第2个名称实际上应读作bèlcir-a,因而也就是“巴亦答剌黑别勒赤列”的对音。这样一来,它就与汉蒙文载籍相吻合了。在明代的汉文地理书中,没有记载这一地段;但清代的地志,却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不同写法。《耶稣会士舆图》中的对音形式为“贝德洛克河”,在满文版中译作Baitarikbira,详见满文本中的《索引》第139页第120和121条目。《水道提纲》卷23第8页中作“贝得勒克”(Baidarak,Baidarik),完全与《西北诸水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第843页)中的写法一样。《朔方备乘》卷4第3页中写作“拜达里克”(Baidarik),这种写法也出现在《蒙古游牧记》卷8第8页中,后者同样也写作“拜塔里克”。《圣武记》卷3第26、38、62和63页以及卷4第10页中,也都写作“拜达里克”,完全如同《绥服厄鲁特蒙古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2帙第18页)和《荡平准部记》(同上丛书,第4帙第59页)中的写法一样。
以上就是我对东蒙古克鲁伦河、额尔古纳河和鄂嫩河以及西蒙古3条河流的考证,尚不包括位于额尔古纳—克鲁伦河地区以及杭爱山脉两个地名。这些名称历代沿革,同时也具有多种意义。在具有“瀚海”之意的时候,有时指蒙古和新疆,有时也可能是指贝加尔湖,但最常见的则是指北蒙古的山脉,最后是指这一山脉的西半部,在清代被称为“杭爱山”。
其他河名似乎也值得我们进行这样的研究,无论是色楞格—鄂尔浑—土拉河及其支流,还是额尔齐斯河及其组成部分以及叶尼塞河(谦河)水系,它们都值得进行这样的研究。人们从6世纪开始就,已经知道这后一条河流了(请参阅笔者旧作:《叶尼塞河上游谦河考》,载1956年《亚细亚学报》,见第281页)。同样,我们同样还可以追溯自7世纪以来的翁金河的沿革,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河流 。
。
上述考释仅仅是对一个涉及范围很广的内容进行的梗概性介绍,其中包括高地亚洲及其附近地区的地名、河名和山名。这些名称中有少数可能为突厥文或蒙古文,可以追溯到一个比较古老的时代,当时操其他语言的民族还占据着这些地区。所有的假设都是可能的,但很少能够作出定论。我们似乎应该针对这一研究专题而作出一系列的短篇专著。因为资料非常缺乏,所以根据这些地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沿革,而研究对它们进行解释的可能性。窃以私见,唯有这种办法,才可以使我们具体确定哪些民族相继占领过该地区,本人这里所指的是各民族的统治部族,他们在数世纪以来,一直占据这些辽阔的地区。
注释:
①在辽代(公元10—11世纪),海剌儿河很可能就是《辽史》卷4第5中的“于谐里”这一对音名称。然而,津田左吉在《辽代乌古敌烈考》(载《满洲地理历史研究》第2卷,1916年版,第1—16页)中又认为是指哈拉哈河(Qalqa)。
②某些地名,如蒙古古代君主们的圣山不而罕哈里敦山(Burqan-qaldun,大肯特山),以及成吉思汗的诞生地迭里温孛勒答黑(Dali’un-boldaq)以及其他许多地名,都要受避讳。以至于在元王朝崩溃之后,虽然这类地名中有一部分也在明代的舆地书中被保存下来了,但却不可能确定其具体方位。在地图上标注的都是某些引用地名,没有以任何真实的诠释为根据,其方位也是主观武断地被确定的。
③参阅夏德:《暾欲谷碑跋》,第34页注释,载由W.拉德洛夫所著,载《蒙古的古突厥文碑铭》第2集,1899年圣彼得堡版。
④所有这些不同形式,可能均自《前汉书》卷94上第26页(百衲本)中的“卢朐”衍生而来。颜师古认为它是指一座山的名称,但文献本身难以对此作出定夺。
⑤《元史》中的《本纪》主要是依靠《实录》,元代的《实录》很可能是以蒙古最早几位皇帝传记的蒙文著作为基础的,正如《元史》卷19第7页在1296年下针对太宗、定宗、宪宗和世祖实录的译文所指出的那样。当朝皇帝对该译文提出了上些异议。1303年,《实录》的汉译文本被呈奏皇帝(《元史》卷21第11页)。1304年(卷21第13页),又提到了忽必烈的《实录》。1308年(卷22第25页),皇帝降旨于翰林国史院,令其修顺宗和成宗的《实录》。1311年(卷24第9页),皇帝又降旨修先帝铁穆耳以及同一时代皇后及功臣们的《实录》。
自从忽必烈执政时代(1261年)起,他(《元史》卷4第15页)就诏令修《辽史》和《金史》。1262年(《元史》卷5第7页),皇帝便将《先朝事绩录》交给国史馆。1264年(《元史》卷5第18页),皇帝又诏令修国史和译书。1268年(《元史》卷6第17页),皇帝又诏令作“起居注”。1293年(《元史》卷18第5页),皇帝降旨令翰林院修一部国史;然后在1294年又令修世祖的《实录》(《元史》卷18第5页),此书于1295年由翰林承旨董文用及其他人呈奏御案(《元史》卷18第16页)。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他许多有关修纂《实录》的详细情节,所以人称《实录》(卷14第11页)被译成了畏吾儿文(1296年)。只是提到了1348年,才停止了修纂《实录》一类的官方文献或有关皇后、嫔妃及功臣们的传记(卷41第14页),因为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任何有关这类著作的记载了。
《明史》卷2第4页在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日(1369年5月7日)之下记载道,根据皇帝的诏令已经开始修《元史》,在同年八月癸午日(1369年9月22日),又记载说《元史》已修毕。
在17世纪时,人们还掌握有一部分辽、金二朝的《实录》,因为《千顷堂书目》卷4第6页中还注录出过元代世祖、成宗和武宗的《实录》(参阅《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4第17页)。
⑥“怯缘连”这种对音词也在牙忽都(Yaqudu)的传记中出现过,牙忽都为拔绰[B c
c (k)]的孙子,而拔绰又是托雷(Tolui)的儿子。至于“怯吕连”这种转对音,它在《元史》中伯帖木儿(Bai-Tamür)的传记中也曾出现过,《元史》于此可能是引自一篇墓志铭。伯帖木儿是钦差部屈出的次子。事实上,黄晋的《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3第6页中提到了《太傅文安忠宪王家传》,这是一通家族碑文,其中提到了此人及其3位后裔。此人似乎卒于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在至元四年(1338年)受追谥。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他的《神道碑》或其他墓志铭一类的文献中,没有出现对于克鲁伦河的记载。对于后者,我尚不知晓。
(k)]的孙子,而拔绰又是托雷(Tolui)的儿子。至于“怯吕连”这种转对音,它在《元史》中伯帖木儿(Bai-Tamür)的传记中也曾出现过,《元史》于此可能是引自一篇墓志铭。伯帖木儿是钦差部屈出的次子。事实上,黄晋的《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3第6页中提到了《太傅文安忠宪王家传》,这是一通家族碑文,其中提到了此人及其3位后裔。此人似乎卒于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在至元四年(1338年)受追谥。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他的《神道碑》或其他墓志铭一类的文献中,没有出现对于克鲁伦河的记载。对于后者,我尚不知晓。
⑦克鲁伦河的名称在元代也于拉施特的《史集》中多次出现(见贝勒津版本),如原本卷1第3页,译本第3页;原本第120页和译本第94页等处;在卷2原本第7、18、21、22和146页,译本第5、13、15和91页等处,则以字母换位形式而出现,作Klür n。“克鲁连”一名也经常出现(卷2,原本第7、18和146页等处),然后又与“斡难”(Onan)联合使用,因而就成了OnānūK
n。“克鲁连”一名也经常出现(卷2,原本第7、18和146页等处),然后又与“斡难”(Onan)联合使用,因而就成了OnānūK lür
lür n,它肯定与鲁布鲁克所说的“斡难克鲁连”有关。它指的是包括在这两条河之间的地盘,形成了成吉思汗帝国的最早核心。请参阅卡特勒梅尔:《蒙古史》第116—117页;柔克义:《鲁布鲁克游记》第116页注[1]。这里实际上是指与波斯文献中的伊必儿—失必儿(Ibir-ū-Sibir)相同的一种形式。拉施特《史集》(贝勒津版本,原文第168页和译文第130页)中也作伊必儿—失必儿(Ibir-Sibir)。
n,它肯定与鲁布鲁克所说的“斡难克鲁连”有关。它指的是包括在这两条河之间的地盘,形成了成吉思汗帝国的最早核心。请参阅卡特勒梅尔:《蒙古史》第116—117页;柔克义:《鲁布鲁克游记》第116页注[1]。这里实际上是指与波斯文献中的伊必儿—失必儿(Ibir-ū-Sibir)相同的一种形式。拉施特《史集》(贝勒津版本,原文第168页和译文第130页)中也作伊必儿—失必儿(Ibir-Sibir)。
⑧《皇舆图》和《朔漠图》卷1以及后期的《皇舆考》卷12第4页中,同样都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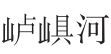 ”,它似乎就相当于克鲁伦河,但本人不知其名的起源。
”,它似乎就相当于克鲁伦河,但本人不知其名的起源。
⑨如同在元代一样,我发现过一种写法为“斡难怯鲁连”,在清代的地理书中也曾出现过。《大清一统志》卷71第7和11页中提到了“呼伦布雨尔界”,或者是简称为“呼伦布雨尔”,如卷711第10和11页那样。
⑩这肯定是由于受到了该河俄文名称Arghun的影响之结果。
 《辽史》卷32第22页中提到了鄂嫩河流域的一个部族,叫做“斡纳阿剌”和“温纳阿剌”。该对音名称的前一部分“斡纳”很可能应考证成“斡难河”一名。
《辽史》卷32第22页中提到了鄂嫩河流域的一个部族,叫做“斡纳阿剌”和“温纳阿剌”。该对音名称的前一部分“斡纳”很可能应考证成“斡难河”一名。
 《读史方舆纪要》卷45第1897页中提到,永乐八年间,在追捕那些外逃者时,皇帝御驾亲征;赶到河边歼灭了他们。元代的后裔本稚失里(Bunyasiri)穷蹩,仑猝率数骑遁去。皇帝赐斡难河名为“元冥河”。《皇舆通志》卷119第3页中,提到了同一事实,但却作“玄冥河”。
《读史方舆纪要》卷45第1897页中提到,永乐八年间,在追捕那些外逃者时,皇帝御驾亲征;赶到河边歼灭了他们。元代的后裔本稚失里(Bunyasiri)穷蹩,仑猝率数骑遁去。皇帝赐斡难河名为“元冥河”。《皇舆通志》卷119第3页中,提到了同一事实,但却作“玄冥河”。
 《蒙古游牧记》卷9第24页中写作“扯克彻尔”。《皇舆通志》卷119第1和3页,则采纳了明代传统的写法,因为它也引自前几部著作。
《蒙古游牧记》卷9第24页中写作“扯克彻尔”。《皇舆通志》卷119第1和3页,则采纳了明代传统的写法,因为它也引自前几部著作。
 我在《北史》卷98第2、5和16页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记载,其史料明显是相同的。
我在《北史》卷98第2、5和16页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记载,其史料明显是相同的。
 拉施特《史集》卷3原本第4页,译本第3页中,把杭爱山写作Qangāi;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波伊勒译本)第585、609和724页中(据波伊勒的看法)是写作QNTAY或QANTAY的,可复原为Qanghai。
拉施特《史集》卷3原本第4页,译本第3页中,把杭爱山写作Qangāi;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波伊勒译本)第585、609和724页中(据波伊勒的看法)是写作QNTAY或QANTAY的,可复原为Qanghai。
 《圣武记》在“瀚海”(指沙漠,见卷3第2、8和11页等处,尤其是第13页)和“杭爱山”(卷3第13、16、31、38、62和67页等处)之间作了明显的区别。
《圣武记》在“瀚海”(指沙漠,见卷3第2、8和11页等处,尤其是第13页)和“杭爱山”(卷3第13、16、31、38、62和67页等处)之间作了明显的区别。
 萨囊彻辰(施密德译本)在《蒙古源流》第104页中作Qangrai-qan,而在第96页中又作Qangqai-qaran,均指“杭爱山”。
萨囊彻辰(施密德译本)在《蒙古源流》第104页中作Qangrai-qan,而在第96页中又作Qangqai-qaran,均指“杭爱山”。
 明代的舆地书有时也会向我们提供某些毫无价值的资料。所以《皇舆通志》卷119第3页提到了东蒙古的地图上的一些地名,如“迭里温孛勒答黑”(Dali'un-boldaq)和“班朱泥”(Baljuni)。前者是成吉思汗的诞生地,后者是一条河名,成吉思汗一旦遇到困境时就撤退到该河畔,此名仅作为元代历史中的著名地名而出现过。我还可以指出西方地图中的一些相似情况,特别是把不里罕哈里敦山(Burqan-qaldnn,大肯特山)说成是克鲁伦河、鄂嫩河和土拉河的发源地,该山脉也出现在维维安等人的世界地图上了。
明代的舆地书有时也会向我们提供某些毫无价值的资料。所以《皇舆通志》卷119第3页提到了东蒙古的地图上的一些地名,如“迭里温孛勒答黑”(Dali'un-boldaq)和“班朱泥”(Baljuni)。前者是成吉思汗的诞生地,后者是一条河名,成吉思汗一旦遇到困境时就撤退到该河畔,此名仅作为元代历史中的著名地名而出现过。我还可以指出西方地图中的一些相似情况,特别是把不里罕哈里敦山(Burqan-qaldnn,大肯特山)说成是克鲁伦河、鄂嫩河和土拉河的发源地,该山脉也出现在维维安等人的世界地图上了。
(译自巴黎1994年出版的《纪念戴密微汉学论文集》第二卷)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