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河考
韩百诗
克姆河(K m)在我们西方地图上作Kem,它至今仍是叶尼塞河上游的名称,中国人一般都将之对音成“谦河”。它在13世纪元代时的发音仍为K’iem。此名原来似乎仅仅是意味着“江”,在萨彦语中的K
m)在我们西方地图上作Kem,它至今仍是叶尼塞河上游的名称,中国人一般都将之对音成“谦河”。它在13世纪元代时的发音仍为K’iem。此名原来似乎仅仅是意味着“江”,在萨彦语中的K m,在萨盖语、科伊巴尔语和卡钦语中为Kem,至今仍具此义①。此字可能并非起源于突厥文,似乎也不应该将它与Kem联系起来,后者是布哈拉运河流域的一个地名,而巴托尔德似乎赋予了此字一般的词意“河流”(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113和495页)。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中,K
m,在萨盖语、科伊巴尔语和卡钦语中为Kem,至今仍具此义①。此字可能并非起源于突厥文,似乎也不应该将它与Kem联系起来,后者是布哈拉运河流域的一个地名,而巴托尔德似乎赋予了此字一般的词意“河流”(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113和495页)。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中,K m再也不是作为普通名词,而是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出现了。
m再也不是作为普通名词,而是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出现了。
古中世纪的剑水
指叶尼塞河的时候,在公元8世纪上半叶鄂尔浑河流域的碑铭中,就已经出现了剑水(K m)一名②,但中国人对它的了解更要早得多。《周书》(修撰于7世纪第2个四分之一年代,其史料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末)卷42,第2页,在有关突厥人的起源问题上,介绍了一个奇怪的传说:在伊质泥师都(他本人由一只母狼所生)的4个儿子之中,“其一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契骨”(Q
m)一名②,但中国人对它的了解更要早得多。《周书》(修撰于7世纪第2个四分之一年代,其史料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末)卷42,第2页,在有关突厥人的起源问题上,介绍了一个奇怪的传说:在伊质泥师都(他本人由一只母狼所生)的4个儿子之中,“其一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契骨”(Q rqut)是对柯尔克孜部族一名的古老对音之一。夏德(Hirth)曾带有保留态度地建议③把“剑水”比定为谦河或叶尼塞河上游;他同时也建议把“阿辅水”考证成阿巴坎河,即谦河的左部分支。他没有想到将这段文字,与《元史》(卷63,第24页)中有关吉利吉思部的章节进行比较。后者记载说:“溓河经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东北有水曰玉须,皆巨浸也,而注于谦……。”“阿辅”可能是Abu的对音,而“阿浦”则可能是Apu之对音,但“浦”也可能是“辅”之误。其错误是由于作者希望在一条河流的对音名中,加入一个带“水”的偏旁;否则就应该承认这一对音不太严格,因为基本可以肯定其原形为Abu。朔特(Schott,他不知道《周书》中的这段记载)从1865年起(见《八吉利吉思部考》第453页)就建议将此名称看做是阿巴坎。事实上,大家都丝毫没有发现另外一种可能成立的解决办法④。
rqut)是对柯尔克孜部族一名的古老对音之一。夏德(Hirth)曾带有保留态度地建议③把“剑水”比定为谦河或叶尼塞河上游;他同时也建议把“阿辅水”考证成阿巴坎河,即谦河的左部分支。他没有想到将这段文字,与《元史》(卷63,第24页)中有关吉利吉思部的章节进行比较。后者记载说:“溓河经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东北有水曰玉须,皆巨浸也,而注于谦……。”“阿辅”可能是Abu的对音,而“阿浦”则可能是Apu之对音,但“浦”也可能是“辅”之误。其错误是由于作者希望在一条河流的对音名中,加入一个带“水”的偏旁;否则就应该承认这一对音不太严格,因为基本可以肯定其原形为Abu。朔特(Schott,他不知道《周书》中的这段记载)从1865年起(见《八吉利吉思部考》第453页)就建议将此名称看做是阿巴坎。事实上,大家都丝毫没有发现另外一种可能成立的解决办法④。
所以,从公元6世纪到14世纪,阿巴坎一名是以“阿辅”(阿浦,Abu)的形式出现的。-qan可能是与其名无关紧要的一个后缀,也很可能如同“骨利干”(Qor qan或Qur
qan或Qur qan)中的Qor
qan)中的Qor 一样⑤。我们似乎仅仅应该承认,Abaqan应为一个更为古老的名称Abuqan。从相反的方面来说,这是与本文有关的此种轮流变化的另一个例证,在一个三音节词的第二个非重读音节中的表现。对于阿八哈这一人名的写法,有时作Abuγa,有时又作Abaγa,这是旭烈兀(Hül
一样⑤。我们似乎仅仅应该承认,Abaqan应为一个更为古老的名称Abuqan。从相反的方面来说,这是与本文有关的此种轮流变化的另一个例证,在一个三音节词的第二个非重读音节中的表现。对于阿八哈这一人名的写法,有时作Abuγa,有时又作Abaγa,这是旭烈兀(Hül gü)的儿子伊利汗(Ilkhan)的名字。所以在明代同文馆的汉文畏兀儿文词汇中,Abuγa一词的意思是指叔叔,即父亲的幼弟,而该蒙古文的真正形式则应该是abaγa。对于这种在-a-和-u-之间轮番变化的用法的解释,要比对一个双音节词尾的解释更难。所以,如果我们应该从Abu<Abuqan> Abaqan这一变化过程开始,那似乎就很难像阿里斯托夫(《札记》,载1896年的《活的古代》第3—4卷,第356页)所建议的那样,把库兹涅茨克的达达尔人和绍尔人(
gü)的儿子伊利汗(Ilkhan)的名字。所以在明代同文馆的汉文畏兀儿文词汇中,Abuγa一词的意思是指叔叔,即父亲的幼弟,而该蒙古文的真正形式则应该是abaγa。对于这种在-a-和-u-之间轮番变化的用法的解释,要比对一个双音节词尾的解释更难。所以,如果我们应该从Abu<Abuqan> Abaqan这一变化过程开始,那似乎就很难像阿里斯托夫(《札记》,载1896年的《活的古代》第3—4卷,第356页)所建议的那样,把库兹涅茨克的达达尔人和绍尔人( or)之中的阿巴(Aba)氏族与Abaqan相联系起来⑥。
or)之中的阿巴(Aba)氏族与Abaqan相联系起来⑥。
仍然是在提到黠戛斯人的问题时,剑水一名在晚期约公元800年左右,又重新在汉文载籍中出现了。《新唐书》卷217下,第11页在《黠戛斯传》中指出:“青山(黠戛斯部驻牙于此)之东,有水曰剑河。”⑦在可以追溯到贾耽的线路之一的时候,《新唐书》卷43下,第15页中又提到了“剑水”。《太平寰宇记》卷199,第13页中又指出:“其国依青山之西,面有金海,分为二河,一曰牟河,一曰剑侧河。从天德军去二百里至西受降城,又北三百里鸟泉,西北回鹘帐一千……”朔特在其书所使用的史料中,又引证了《太平寰宇记》,但仅在《补遗篇》中(第470—471和473页)才使用了本段文字,而且这也使他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太平寰宇记》的体例很不得当,所以如果说“牟河”一名系《新唐书》卷43下,第15页中与剑水同时提到的“牢山”之讹误,那也并非绝无可能;同样,“剑侧”也可能仅仅是“剑”字的一种讹误形式。但文献中的任何讹误形式都无法解释“金海”,以及明确提到存在有两条河这一事端。另外,“剑侧”又会使人非常惊奇地联想到克穆齐克河(K ma ik,德文地图中为Kemtschik)。我将于下文论述这一问题,它是形成叶尼塞河上游的3条主要支流之一。但是,如果“剑侧”确实是克穆齐克河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承认,《太平寰宇记》的作者作掌握了某些不太确切的资料。因为克穆齐克河发源于与叶尼塞河上游,另外两条更大的支流的相反方向。最后,对于“金海”一名,我们可以很自然地联想到西方地图中的库苏古尔(Kossogol)湖,这也是朔特(第470页)最早所作出的考证,虽然叶尼塞河的任何源流都并非自此湖而出。严格地来说,我们可以认为,由于某些相当不确切的资料,故而使人认为叶尼塞河上游的两条东部分支源出此湖,而克穆齐克河本身则被排除在外。
ma ik,德文地图中为Kemtschik)。我将于下文论述这一问题,它是形成叶尼塞河上游的3条主要支流之一。但是,如果“剑侧”确实是克穆齐克河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承认,《太平寰宇记》的作者作掌握了某些不太确切的资料。因为克穆齐克河发源于与叶尼塞河上游,另外两条更大的支流的相反方向。最后,对于“金海”一名,我们可以很自然地联想到西方地图中的库苏古尔(Kossogol)湖,这也是朔特(第470页)最早所作出的考证,虽然叶尼塞河的任何源流都并非自此湖而出。严格地来说,我们可以认为,由于某些相当不确切的资料,故而使人认为叶尼塞河上游的两条东部分支源出此湖,而克穆齐克河本身则被排除在外。
我们还可以考虑另外一种不同的解决方法,即保留《太平寰宇记》中的“牟河”一名,并将此看做是(阿)辅水。也就是(A)-bu的对音。用汉文中的-m来译突厥文中的-b的例证多得不胜枚举,尤其是在唇元音之前更为如此。回鹘可汗B?gü名字的汉文对音恰恰正是“牟羽”(见1913年《亚细亚学报》,第1期,第188页)。在此情况下,《新唐书》中的“牢山”可能正是讹记了贾耽原文中的“牟河”,叶尼塞河上游仅以克穆齐克河所代表,该河的发源地距阿巴坎河很近,它们二者之间仅被萨彦岭所分割。所以唐代的文献确实是提到了黠戛斯人地区与《周书》所记载相同的两条河。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于此遇到了在唐代确实存在的事实。这就是在突厥人地区有一座牢山,虽然由于此名的原形可能是一个声母流音,但这一观点令人十分惊奇⑧。另外,《新唐书》卷217下,第2页中又指出,在9世纪前半叶,黠戛斯君长“遂徙牙牢山之南,牢山亦曰赌满”⑨。这后一个名称似乎确实是其他史料中所提到的“贪漫山”一名的另一种对音,其原形为Taman或Toman、Tuman⑩。夏德曾承认贪漫山脉与《酉阳杂俎》中的曲漫山系指同一地,这肯定也就是鄂尔浑河碑铭中的K gman一名。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实现把牢山考证成曲漫山的目的了,也就是说很可能是今之萨彦岭。但在这一系列的考证中,即在牢山、赌满山和贪漫山之间,还可能存在有一系列的错误。《太平寰宇记》的译本中提供了某些资料,但却没有作具体解释。我可以肯定,“分为二河”的“金海”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在贾耽提供的文献中,所指的并非是一座山,而是指西萨彦岭把克穆齐克河流域与阿巴坎河流域分开了。但在作出这样的校勘之后,原文中的“为”字则令人费解了。最好的办法是保留“金海”的原貌。朔特在其著第473页中,放弃了在第470页中提出的库苏古尔湖一说。他已经提醒我们注意,在由拉德洛夫所记载的一个特勒兀特人的传说中,我们西方地图中所标注的捷列茨科耶湖(比亚河源出此湖)就被称为“金湖”。事实上,此湖距克穆齐克河与阿巴坎河的源头不远。所以无论是在威特林1687年的地图中,还是在1730年施特拉林堡(Strahlenberg)的地图中(见卡昂:《西伯利亚地图》第64、182和343页),此湖均有双名,Alt
gman一名。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实现把牢山考证成曲漫山的目的了,也就是说很可能是今之萨彦岭。但在这一系列的考证中,即在牢山、赌满山和贪漫山之间,还可能存在有一系列的错误。《太平寰宇记》的译本中提供了某些资料,但却没有作具体解释。我可以肯定,“分为二河”的“金海”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在贾耽提供的文献中,所指的并非是一座山,而是指西萨彦岭把克穆齐克河流域与阿巴坎河流域分开了。但在作出这样的校勘之后,原文中的“为”字则令人费解了。最好的办法是保留“金海”的原貌。朔特在其著第473页中,放弃了在第470页中提出的库苏古尔湖一说。他已经提醒我们注意,在由拉德洛夫所记载的一个特勒兀特人的传说中,我们西方地图中所标注的捷列茨科耶湖(比亚河源出此湖)就被称为“金湖”。事实上,此湖距克穆齐克河与阿巴坎河的源头不远。所以无论是在威特林1687年的地图中,还是在1730年施特拉林堡(Strahlenberg)的地图中(见卡昂:《西伯利亚地图》第64、182和343页),此湖均有双名,Alt n湖即“金湖”,这是1697年列麦佐夫(Remezov)地图中所标出的唯一名称(同上引书,第93页),可能指的正是此湖。
n湖即“金湖”,这是1697年列麦佐夫(Remezov)地图中所标出的唯一名称(同上引书,第93页),可能指的正是此湖。
《新唐书》卷217下,第10页提到了豢鹿的一个“鞠” 部,同时又提到了一个“大汉”部,“处鞠之北,与鞠俱邻于黠戛斯剑海之濒”
部,同时又提到了一个“大汉”部,“处鞠之北,与鞠俱邻于黠戛斯剑海之濒” 。我们从这条史料便可再次看到,剑河即今之克姆河,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了。本处所指的是叶尼塞河流域的部族,但我们可以认为“剑海”系“剑河”之误
。我们从这条史料便可再次看到,剑河即今之克姆河,这一点已经毫无疑问了。本处所指的是叶尼塞河流域的部族,但我们可以认为“剑海”系“剑河”之误 。鞠部人应该栖身于叶尼塞河中游。
。鞠部人应该栖身于叶尼塞河中游。
据本人所知,在元代之前,任何大食或波斯史学家或舆地学家的著作中,都未曾遇到过对谦河或克穆齐克河的可靠记载。用谦河一名来解释太和岭(高加索)一带的古厌口哒人的名称Kami ik(这是由马夸特提出来的),至今仍悬而未决 。
。
然而,克穆齐克一名也可能于928年由《世界境域志》提到过。该书提到了此城名,并说明黠戛斯部之君长(可汗)就驻牙于那里(米诺尔斯基译本,第97和236页)。巴托尔德于1927年在伏龙芝出版了一部著作,叫作《吉尔吉斯族史纲》,我本人目前尚未得到此书,但米诺尔斯基则完全可能利用了它。巴托尔德曾假设认为,《世界境域志》所指出的这个名称,可能就相当于“密的支它”(中华书局现行标点本为:“号‘密的支’,它……”——译者)。据朔特在《八吉利吉思部考》第434页认为,《新唐书》中记载说,这是黠戛斯部的牙帐 。我们至今尚无法复原“密的支”的突厥文原形,它似乎是相当于biti一类的词。但我们已看到,这是可汗牙帐的名称,而不是一座城名。另一方面,米诺尔斯基先生曾提醒注意,伊德里奇(Idrisi)在其著第1卷第500页中认为,黠戛斯人地区的主要河流“明显是叶尼塞河”;另一个名称是“对首府名称的错误拼法”。我们可以试原封不动地保留《世界境域志》中的写法,并将之转写成K
。我们至今尚无法复原“密的支”的突厥文原形,它似乎是相当于biti一类的词。但我们已看到,这是可汗牙帐的名称,而不是一座城名。另一方面,米诺尔斯基先生曾提醒注意,伊德里奇(Idrisi)在其著第1卷第500页中认为,黠戛斯人地区的主要河流“明显是叶尼塞河”;另一个名称是“对首府名称的错误拼法”。我们可以试原封不动地保留《世界境域志》中的写法,并将之转写成K m ik
m ik -Kamikk
-Kamikk ,意为“克穆齐克城”。至于伊德里奇书中的那条江名,它可能是由克穆齐克讹变而来。这些事实似乎特别支持了下列假设:应该把《太平寰宇记》中的“剑侧”江之名释读作克穆齐克河。我们在元代所遇到的仍是克穆齐克河。
,意为“克穆齐克城”。至于伊德里奇书中的那条江名,它可能是由克穆齐克讹变而来。这些事实似乎特别支持了下列假设:应该把《太平寰宇记》中的“剑侧”江之名释读作克穆齐克河。我们在元代所遇到的仍是克穆齐克河。
元代的谦河
志费尼(Juwaini)从来没有提到不带其他附加成分的谦河。在贝勒津(Berezīn)版本的拉施特《史集》中,此河名似乎共被提到过两次,拼写作K m。但在两种形式之一处(原本第2卷,第200页,译本第2卷,第124页)明显是由拉施特的错误造成的,尽管贝勒津在注释中(第2卷,第249—250页)作了其他解释,它所指的是根河(K
m。但在两种形式之一处(原本第2卷,第200页,译本第2卷,第124页)明显是由拉施特的错误造成的,尽管贝勒津在注释中(第2卷,第249—250页)作了其他解释,它所指的是根河(K n或G
n或G n),即位于西满的额尔古纳河(Arghoun)的支流
n),即位于西满的额尔古纳河(Arghoun)的支流 。第2段文字丝毫不容置疑,拉施特在有关斡亦剌惕(O
。第2段文字丝毫不容置疑,拉施特在有关斡亦剌惕(O rat,原本第1卷,第100—101页,译本第1卷,第79页)的部族志中指出,他们的地区是八河(S
rat,原本第1卷,第100—101页,译本第1卷,第79页)的部族志中指出,他们的地区是八河(S kiz-mǖr
kiz-mǖr n,这是一个半突厥文、半蒙古文的词)。“在古代,秃马惕(Tūmāt)部居住在这些河流域。诸河从该地区流出,最后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被称为谦河的河流,谦河然后又注入昂可剌—沐涟(ānqaγa-mǖr
n,这是一个半突厥文、半蒙古文的词)。“在古代,秃马惕(Tūmāt)部居住在这些河流域。诸河从该地区流出,最后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被称为谦河的河流,谦河然后又注入昂可剌—沐涟(ānqaγa-mǖr n,即安加拉河)”。所以,拉施特认为昂可剌河是其中的主要河流,而谦河或叶尼塞河仅仅是它的一条主要支流
n,即安加拉河)”。所以,拉施特认为昂可剌河是其中的主要河流,而谦河或叶尼塞河仅仅是它的一条主要支流 。文中紧接着又列举了“八河”之名(谦河也就是由这些河所形成的),其中有些名称令人质疑,值得进行一番探讨
。文中紧接着又列举了“八河”之名(谦河也就是由这些河所形成的),其中有些名称令人质疑,值得进行一番探讨 。无论如何,其中之一,即兀黑—沐涟(ūq-mǖr
。无论如何,其中之一,即兀黑—沐涟(ūq-mǖr n,意为“兀黑江”)肯定应为18世纪地图中的兀赫江(Ouk,Uk和Uhk),参看卡昂:《18世纪的西伯利亚地图》第488和534页;在丹维尔(d’Anville)的地图中作Ouk(见中国和鞑靼地区的第12幅地图);阔阔—沐涟(K
n,意为“兀黑江”)肯定应为18世纪地图中的兀赫江(Ouk,Uk和Uhk),参看卡昂:《18世纪的西伯利亚地图》第488和534页;在丹维尔(d’Anville)的地图中作Ouk(见中国和鞑靼地区的第12幅地图);阔阔—沐涟(K k
k -mǖr
-mǖr n,意为“清江”)和兀忽惕—沐涟(üqūt-mǖr
n,意为“清江”)和兀忽惕—沐涟(üqūt-mǖr n),可能分别指洪钧书中的“库克克姆”(K
n),可能分别指洪钧书中的“库克克姆”(K k-k
k-k m,意为“清谦河”)与“乌古特”(Ugut,见上引卡昂书,第236页)。在有关温—沐涟(On-mür
m,意为“清谦河”)与“乌古特”(Ugut,见上引卡昂书,第236页)。在有关温—沐涟(On-mür n,阿布尔—喀齐同样也指出了这种形式)的问题上,贝勒津没有在雅金甫(比丘林)神父的著作和其他地方,找到其相对应的名称,所以他建议将此名解释作“年”与“江”的合成词。但是,这种看法除了没有具体意义之外,我还必须指出,用来指“年”的蒙古文在13和14世纪的对音中始终写作hon
n,阿布尔—喀齐同样也指出了这种形式)的问题上,贝勒津没有在雅金甫(比丘林)神父的著作和其他地方,找到其相对应的名称,所以他建议将此名解释作“年”与“江”的合成词。但是,这种看法除了没有具体意义之外,我还必须指出,用来指“年”的蒙古文在13和14世纪的对音中始终写作hon 。我们在不应该一律到谦河流径克姆—克穆齐克—博姆(Kem-Kemik-Bōm)之前的地方去寻找“八河”地望的情况下,我甚至可以想到应读作us,甚至还可以是uz,并且还可以将此看做是《元史》卷63,第17页中的“乌斯”。我还必须指出,在“八河”之中没有提到克穆齐克河,这可能就说明应该到克姆河上游的两条支流,即贝克姆河与华克姆河流域去寻找所有八河的方位
。我们在不应该一律到谦河流径克姆—克穆齐克—博姆(Kem-Kemik-Bōm)之前的地方去寻找“八河”地望的情况下,我甚至可以想到应读作us,甚至还可以是uz,并且还可以将此看做是《元史》卷63,第17页中的“乌斯”。我还必须指出,在“八河”之中没有提到克穆齐克河,这可能就说明应该到克姆河上游的两条支流,即贝克姆河与华克姆河流域去寻找所有八河的方位 。
。
另一处遗漏则更为令人惊奇。在《元朝秘史》的第239节中,记载了由术赤所发动的对斡亦剌惕人和叶尼塞河流域其他小部族的战争,其中提到斡亦剌惕部的首领立即就投降了,并带领术赤进入失黑失惕( iq
iq it)地区。李文田的疏注文(《元朝秘史注》卷12,第2页)认为应该到额尔齐斯河上游,去寻求失黑失惕之地,高宝铨(《元朝秘史李注补记》卷12,第2页)则认为失黑失惕是鄂毕河右部支流揭底(Ket)河名称的对音
it)地区。李文田的疏注文(《元朝秘史注》卷12,第2页)认为应该到额尔齐斯河上游,去寻求失黑失惕之地,高宝铨(《元朝秘史李注补记》卷12,第2页)则认为失黑失惕是鄂毕河右部支流揭底(Ket)河名称的对音 。一切迹象均说明,我们所指的方位应位于叶尼塞河上游盆地,而且拉施特也把斡亦剌惕部的八河置于那里。然而,在该盆地的东南,还有一条至今仍叫做西施基特(
。一切迹象均说明,我们所指的方位应位于叶尼塞河上游盆地,而且拉施特也把斡亦剌惕部的八河置于那里。然而,在该盆地的东南,还有一条至今仍叫做西施基特( i
i kit)的河流,注入了科特(Kot)湖,而中国人正是把从此湖中流出来的一条河当作是谦河的源头。西施基特河流,此名过去不仅是指今之西施基特河,而且也指整个华克姆河。丹维尔的地图中误将此河名标作Tchisket(中国和鞑靼地区第2幅图)。列麦佐夫在1697年的地图中,又将此名分解为作为叶尼塞河发源地的希施基西耶(
kit)的河流,注入了科特(Kot)湖,而中国人正是把从此湖中流出来的一条河当作是谦河的源头。西施基特河流,此名过去不仅是指今之西施基特河,而且也指整个华克姆河。丹维尔的地图中误将此河名标作Tchisket(中国和鞑靼地区第2幅图)。列麦佐夫在1697年的地图中,又将此名分解为作为叶尼塞河发源地的希施基西耶( i
i kickiye)湖名和西克希特(
kickiye)湖名和西克希特( ik
ik it)河名(它上叶尼塞河上游的支流之一)。在同一位作者1701年的地图中,上述湖名又变成了西基基耶(
it)河名(它上叶尼塞河上游的支流之一)。在同一位作者1701年的地图中,上述湖名又变成了西基基耶( ikickiye),而河名则变成了西施基特(
ikickiye),而河名则变成了西施基特( i
i kit),这就是在18世纪的地图以及我们今天地图中的西施基特河(参看卡昂:《西伯利亚地图》第96、110和421页)
kit),这就是在18世纪的地图以及我们今天地图中的西施基特河(参看卡昂:《西伯利亚地图》第96、110和421页) 。事实上,我们基本可以肯定,
。事实上,我们基本可以肯定, i
i kit是
kit是 ik
ik it经字母易位后的形式,列麦佐夫1697年的地图中正确地保留了其固有形式,它正是《元朝秘史》中的失黑失惕
it经字母易位后的形式,列麦佐夫1697年的地图中正确地保留了其固有形式,它正是《元朝秘史》中的失黑失惕 。这样一来,我们从《元朝秘史》中得到的证据说明,
。这样一来,我们从《元朝秘史》中得到的证据说明, iq
iq it>
it> i
i kit是用以指谦河上游地区的古地名。但是,失黑失惕并不包括在拉施特所列举的“八河”之列。
kit是用以指谦河上游地区的古地名。但是,失黑失惕并不包括在拉施特所列举的“八河”之列。
元代的谦河与谦谦州
除了没有单独提到谦河之外,志费尼却又多次提到另一个地区。从其手稿来看,两次写作Qam-K b ik(哈兹维尼版本,第1卷,第51页;第2卷,第88页);另一处的写法略有不同(第2卷,第248页),但肯定也是指同一地区;他第3次写作K
b ik(哈兹维尼版本,第1卷,第51页;第2卷,第88页);另一处的写法略有不同(第2卷,第248页),但肯定也是指同一地区;他第3次写作K mihüd
mihüd 。我们可以肯定,Qam就是谦河名称的一种写法,因为志费尼混淆了突厥文或蒙古文中的软腭音和腭音(正如除了拉施特之外的所有波斯学者,继他之后经常所作的那样),该词的真正形式应为k
。我们可以肯定,Qam就是谦河名称的一种写法,因为志费尼混淆了突厥文或蒙古文中的软腭音和腭音(正如除了拉施特之外的所有波斯学者,继他之后经常所作的那样),该词的真正形式应为k m。K
m。K b ik代表着在-b-和-m-之间经常出现的变化,事实上应该是K
b ik代表着在-b-和-m-之间经常出现的变化,事实上应该是K mik,即克穆齐克河。K
mik,即克穆齐克河。K b ik似乎是K
b ik似乎是K m-k
m-k m ik的一种简称形式。K
m ik的一种简称形式。K mihüd也可能是Kam-[K
mihüd也可能是Kam-[K m]ihüd之误。这样一来,它既可能是K
m]ihüd之误。这样一来,它既可能是K m-[K
m-[K m ik]的复数形式,也可能是简化形式k
m ik]的复数形式,也可能是简化形式k mik的复数,都应读作同一个词K
mik的复数,都应读作同一个词K mihüd
mihüd 。以上就是我在通常情况下所能联想到的解决方法,它们被一些人随心所欲地搞混乱了。为了进行深入讨论,我们最好还是引用一下拉施特的《史集》中出现该名称的一段文字。
。以上就是我在通常情况下所能联想到的解决方法,它们被一些人随心所欲地搞混乱了。为了进行深入讨论,我们最好还是引用一下拉施特的《史集》中出现该名称的一段文字。
拉施特始终写作K m-K
m-K m iǖt(谦谦州,有时也作K
m iǖt(谦谦州,有时也作K m-K
m-K m
m j iǖt)
j iǖt) ,而且始终是把此名与吉利吉思部联系起来。他提到了(译本第2卷,第112页)谦谦州地区,“它属于吉利吉思部疆域”
,而且始终是把此名与吉利吉思部联系起来。他提到了(译本第2卷,第112页)谦谦州地区,“它属于吉利吉思部疆域” 。但其书中最为重要的一段文字,却见诸吉利吉思传(原本第1卷,第168页;译本第1卷,第130页):“吉利吉思和谦谦州是两个彼此互为毗邻的地区,这两个地区构成了同一个王国(M
。但其书中最为重要的一段文字,却见诸吉利吉思传(原本第1卷,第168页;译本第1卷,第130页):“吉利吉思和谦谦州是两个彼此互为毗邻的地区,这两个地区构成了同一个王国(M ml
ml k
k t)。谦谦州是一条大河”。
t)。谦谦州是一条大河”。
K miüt即相当于K
miüt即相当于K m i’üt,这是K
m i’üt,这是K m ik正常的蒙古文复数形式,而K
m ik正常的蒙古文复数形式,而K m-K
m-K mik明显是由谦河一名(由东部的两条主要支流而构成的)和克穆齐克河名(该河西部的主要支流)而组成的。恰恰在谦河与克穆齐克河汇合之后的地方,此河越过了斡罗斯国,其河谷至今仍被称为克姆—克穆齐克—博姆河。伯劳舍(Blochet)使这一问题复杂化了。在他为志费尼书(第1卷,第51页)的编辑者所作的一条注释中,把一些彼此之间根本就毫无关系的问题相混淆了,例如把Tamgqut与Tangut(均指唐古忒)并列,把Hül
mik明显是由谦河一名(由东部的两条主要支流而构成的)和克穆齐克河名(该河西部的主要支流)而组成的。恰恰在谦河与克穆齐克河汇合之后的地方,此河越过了斡罗斯国,其河谷至今仍被称为克姆—克穆齐克—博姆河。伯劳舍(Blochet)使这一问题复杂化了。在他为志费尼书(第1卷,第51页)的编辑者所作的一条注释中,把一些彼此之间根本就毫无关系的问题相混淆了,例如把Tamgqut与Tangut(均指唐古忒)并列,把Hül wü与Hül
wü与Hül gü(均指旭烈兀)相提并论。他还声称谦州(K
gü(均指旭烈兀)相提并论。他还声称谦州(K m iüt)应为K
m iüt)应为K m ikhüd或K
m ikhüd或K m ighüd。马夸特(第135—136页)阅读得太潦草了,所以认为K
m ighüd。马夸特(第135—136页)阅读得太潦草了,所以认为K mighüd确实曾在拉施特著作中出现过。此外,马夸特还认为应以在志费尼著作的一段文字中所出现的K
mighüd确实曾在拉施特著作中出现过。此外,马夸特还认为应以在志费尼著作的一段文字中所出现的K mihud为基本出发点。由于在鄂尔浑河流域的碑铭中就提到了在剑河流域的一个乞克族(ik),所以马夸特由此就得出结论认为:“因此,K
mihud为基本出发点。由于在鄂尔浑河流域的碑铭中就提到了在剑河流域的一个乞克族(ik),所以马夸特由此就得出结论认为:“因此,K mi(g)hud明显是谦河和乞克族名字的结合,意指谦河流域的乞克族人;K
mi(g)hud明显是谦河和乞克族名字的结合,意指谦河流域的乞克族人;K m-K
m-K migüt这种形式也明显是根据上述意义(即K
migüt这种形式也明显是根据上述意义(即K m与K
m与K mik相结合)由较晚期所作的解释造成的”。伯希和曾宣称(1920年,《亚细亚学报》第1期,第173页),他不相信谦河与乞克两名结合这种辞源的可能性。我不理解为什么伯劳舍所说的K
mik相结合)由较晚期所作的解释造成的”。伯希和曾宣称(1920年,《亚细亚学报》第1期,第173页),他不相信谦河与乞克两名结合这种辞源的可能性。我不理解为什么伯劳舍所说的K mighüd有利于马夸特的理论。另外,我需要强调以下事实:K
mighüd有利于马夸特的理论。另外,我需要强调以下事实:K m ighüd这种形式纯属伯劳舍的杜撰,因为无论是在志费尼的著作中,还是在拉施特的书中,均未出现过该词。另一方面,志费尼既不是一位优秀的语音学家,也没有熟练掌握突厥—蒙古文。他把K
m ighüd这种形式纯属伯劳舍的杜撰,因为无论是在志费尼的著作中,还是在拉施特的书中,均未出现过该词。另一方面,志费尼既不是一位优秀的语音学家,也没有熟练掌握突厥—蒙古文。他把K mighüd断定为K
mighüd断定为K mihüd的写法,即使不是抄写者对K
mihüd的写法,即使不是抄写者对K m-(K
m-(K m)ihüd之误写的话,至少也是无足轻重的,完全如同在其他段落中转写作Qam而不是K
m)ihüd之误写的话,至少也是无足轻重的,完全如同在其他段落中转写作Qam而不是K m一样。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应以拉施特著作中的K
m一样。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应以拉施特著作中的K m-K
m-K miüt的写法为出发点,因为它是K
miüt的写法为出发点,因为它是K m-K
m-K mik(即克姆河和克穆齐克河)的正常复数形式。K
mik(即克姆河和克穆齐克河)的正常复数形式。K mik与复数形式K
mik与复数形式K mi’üt和k
mi’üt和k m-K
m-K m i’iüt是不可分割的
m i’iüt是不可分割的 。
。
这些相同的复数形式曾多次出现在汉文载籍中 。其主要文献是《元史》卷63有关吉利吉思、撼百纳[Qamqana(s),又称合卜合纳斯,即Qapqanas]、谦州、益兰州等处的地志的末尾部分。初看起来,“谦州”和“益兰州”似乎都是一些州名,也就是说是汉地式行政机构的中心
。其主要文献是《元史》卷63有关吉利吉思、撼百纳[Qamqana(s),又称合卜合纳斯,即Qapqanas]、谦州、益兰州等处的地志的末尾部分。初看起来,“谦州”和“益兰州”似乎都是一些州名,也就是说是汉地式行政机构的中心 ,《元史》的编纂者们也正是这样理解的,因为他们写道:“谦州亦以河(指前文所提到的谦河)为名……益兰者,蛇之称也
,《元史》的编纂者们也正是这样理解的,因为他们写道:“谦州亦以河(指前文所提到的谦河)为名……益兰者,蛇之称也 。初,州境山中居人,见一巨蛇,长数十步,从穴中出饮河水,腥闻数里,因此州名。至元七年(1270年),诏遣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
。初,州境山中居人,见一巨蛇,长数十步,从穴中出饮河水,腥闻数里,因此州名。至元七年(1270年),诏遣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 ,即于此州修库廪,置传舍,以为治所。先是,数部民俗,皆以杞柳为杯皿
,即于此州修库廪,置传舍,以为治所。先是,数部民俗,皆以杞柳为杯皿 ,刳木为槽以济水,不解铸作农器。好礼闻诸朝,乃遣工匠,教为陶冶舟楫,土人便之。”我们在刘好礼的传记(《元史》卷167)中也发现了上述部分资料,其中记载道:至元七年,刘好礼“迁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以比古之都护,治益兰。其地距京师九千余里,民俗不知陶冶,水无舟航……”。
,刳木为槽以济水,不解铸作农器。好礼闻诸朝,乃遣工匠,教为陶冶舟楫,土人便之。”我们在刘好礼的传记(《元史》卷167)中也发现了上述部分资料,其中记载道:至元七年,刘好礼“迁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以比古之都护,治益兰。其地距京师九千余里,民俗不知陶冶,水无舟航……”。
所以,刘好礼奉大都元朝政府的敕令,在蒙古西北和西伯利亚建立了类似唐朝“都护”一般的行政机构。它们各自统辖有一定数目的州,事实上是羁縻州,即元朝政府仅限于批准土著首领任职的保护州。
刘好礼传中也提到了“五部” ,但在《元史》卷63中仅列举了4部名称,其中本来也应该出现刘好礼的正式尊号。我们完全可以确定第5部的名称,即应为乌斯部。
,但在《元史》卷63中仅列举了4部名称,其中本来也应该出现刘好礼的正式尊号。我们完全可以确定第5部的名称,即应为乌斯部。
切勿忘记,刘好礼的传记是以某种家族文献(家族碑、神道碑等)为基础的,其中对这一人物所起作用的记载,肯定言过其实;《元史》卷63《吉利吉思传》(尤其是在最后一部分)也是以一种同类文献为基础的。如果在涉及一个与米努辛斯克盆地相毗邻的地区时,一口咬定“五部”中不知陶冶,那即使不是荒谬的,至少肯定也是不确切的,因为米努锌斯克在青铜器时代就已经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聚落中心了。另外,《元史》卷63的同一篇地志中,还提到了在“国初”定居于谦州的汉人工匠,其时间要比刘好礼出使早得多。洪钧 (以及继他之后的屠寄
(以及继他之后的屠寄 )就已经指出、元王朝从未在满洲西北地区按照汉人模式建立过行政区域,无论是益兰州还是谦州,都是一些对音名称,其中的“州”只起对音的作用。他们的观点完全有可能是有道理的。
)就已经指出、元王朝从未在满洲西北地区按照汉人模式建立过行政区域,无论是益兰州还是谦州,都是一些对音名称,其中的“州”只起对音的作用。他们的观点完全有可能是有道理的。
因此,益兰州似乎是Yilanjiu(t)的对音 。此名可以用突厥文yilan(蛇)来解释。我们从这一名称中可以很正常地得到一个施动词,在突厥文中为y
。此名可以用突厥文yilan(蛇)来解释。我们从这一名称中可以很正常地得到一个施动词,在突厥文中为y lan,在古典蒙古文中则为yilan
lan,在古典蒙古文中则为yilan cin,但还有一些可能的形式分别为yilan i、yilan
cin,但还有一些可能的形式分别为yilan i、yilan ji、yilan
ji、yilan jin等,只是这些形式的蒙古文复数不可能是yilan iut,而是yilan it
jin等,只是这些形式的蒙古文复数不可能是yilan iut,而是yilan it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益兰州一名Yilan iut事实上代表着Yilan i’t,也就是Yilan ik的复数形式。同样,谦谦州的名称K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益兰州一名Yilan iut事实上代表着Yilan i’t,也就是Yilan ik的复数形式。同样,谦谦州的名称K miüt也就是K
miüt也就是K m i’üt,即K
m i’üt,即K mik的复数形式。“益兰州”(Yilan i’ut)一名的意义原则上应为“小蛇”。尽管存在有《元史》卷63中所记载的传说,但它也可能是由一条河呈一座山Yilan或Yilan ik(>Ian或Ian ik)衍化而来。
mik的复数形式。“益兰州”(Yilan i’ut)一名的意义原则上应为“小蛇”。尽管存在有《元史》卷63中所记载的传说,但它也可能是由一条河呈一座山Yilan或Yilan ik(>Ian或Ian ik)衍化而来。
此名似乎在汉文之外的其他任何文献中均未出现过。事实上,确实存在有一条支流河根河,它本身又是叶尼塞河的右部分支,也被称为益兰(益兰斯克城一名即由此而来)。但它似乎过分偏北,过分远离中心了,无法考虑在内。拉施特似乎不知道益兰州,因为他在两种情况下,都令人吃惊地提到,应读作“泰亦赤兀惕”(Tai iut) 一词,各种手稿中的写法都会使人联想到应读作益兰州(Yilan iut)。何秋涛曾以为益兰州是一条小河,即在未与克穆齐克河汇合之前的谦河的支流,被称为图兰河(Turan或Türg
一词,各种手稿中的写法都会使人联想到应读作益兰州(Yilan iut)。何秋涛曾以为益兰州是一条小河,即在未与克穆齐克河汇合之前的谦河的支流,被称为图兰河(Turan或Türg n);洪钧(卷26下,第14页)批判了这种仅以语音近似为基础的考证;屠寄(卷60,第35页)在拒绝这种假设的同时,又声称应该到该地区去寻找益兰州。
n);洪钧(卷26下,第14页)批判了这种仅以语音近似为基础的考证;屠寄(卷60,第35页)在拒绝这种假设的同时,又声称应该到该地区去寻找益兰州。
这个本来就已经错综复杂的问题,又由于一部叫做《朔漠图考》的著作,而变得愈发复杂了,洪钧(《元史译文正补》卷26下,第10页)继何秋涛(《朔方备乘》卷54,第3页)之后,又根据《大清一统志》 而引证了引书。原文是这样记载的:“自河林北行三千里,至昂吉尔诲子,自此又行五百余里,至谦州及吉利吉思。”洪钧认为“昂吉尔”是“昂可剌”(Angara)的另一种对音形式,所指的是贝加尔湖。但“昂吉尔”肯定是angir的对音,意为“鸳鸯”,这是由乾隆钦命校订文献的大学者们所采纳的对音,学者们便作了这样的修改
而引证了引书。原文是这样记载的:“自河林北行三千里,至昂吉尔诲子,自此又行五百余里,至谦州及吉利吉思。”洪钧认为“昂吉尔”是“昂可剌”(Angara)的另一种对音形式,所指的是贝加尔湖。但“昂吉尔”肯定是angir的对音,意为“鸳鸯”,这是由乾隆钦命校订文献的大学者们所采纳的对音,学者们便作了这样的修改 。在保存于《元史类编》序中的原文内,当谈到修建哈喇和林地区的各种宫殿之后,文中又补充说:“自此北行三千里,名阿里海子,又行五百里,至谦州、益兰州,再行千里,至大泽。
。在保存于《元史类编》序中的原文内,当谈到修建哈喇和林地区的各种宫殿之后,文中又补充说:“自此北行三千里,名阿里海子,又行五百里,至谦州、益兰州,再行千里,至大泽。 ”《朔漠图考》的作者们当时可能就已经使用了徐松所赋予“大泽”的词义了。“阿只里”是Ajil的对音,也就是At
”《朔漠图考》的作者们当时可能就已经使用了徐松所赋予“大泽”的词义了。“阿只里”是Ajil的对音,也就是At l经蒙古化之后的形式,意指伏尔加河。这种文献明显是不连贯的,似乎可以追溯到公元15世纪。作者作对他们所讲的一切都没有任何具体概念,或者是原文的顺序被搞乱了。从哈喇和林方向来看,在抵达叶尼塞河之前,明显是不能到达伏尔加河流域的。另外,即使是恢复了正常的地理顺序,其方向也不可能是北方,而是西北方。在哈喇和林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之间,有500多里的距离,况且伏尔加河亦不为一湖泊。因此,《朔漠图考》中的这段文献丝毫无助于考证益兰州的方位。
l经蒙古化之后的形式,意指伏尔加河。这种文献明显是不连贯的,似乎可以追溯到公元15世纪。作者作对他们所讲的一切都没有任何具体概念,或者是原文的顺序被搞乱了。从哈喇和林方向来看,在抵达叶尼塞河之前,明显是不能到达伏尔加河流域的。另外,即使是恢复了正常的地理顺序,其方向也不可能是北方,而是西北方。在哈喇和林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之间,有500多里的距离,况且伏尔加河亦不为一湖泊。因此,《朔漠图考》中的这段文献丝毫无助于考证益兰州的方位。
《元史》卷63第17页有关谦州的地志中记载道:“谦州亦以河(指谦河)为名,去大都(北京)九千里,在吉利吉思东南,谦河西南,唐蔍岭(Tanglu)之北 。居民数千家,悉蒙古、回纥人。有工匠数局,盖国初所徙汉人也。地沃衍宜嫁,夏仲秋成,不颊耘耔。或云汪罕始居此地。”这些资料至少可使我们大致确定谦州的方位,谦州即K
。居民数千家,悉蒙古、回纥人。有工匠数局,盖国初所徙汉人也。地沃衍宜嫁,夏仲秋成,不颊耘耔。或云汪罕始居此地。”这些资料至少可使我们大致确定谦州的方位,谦州即K mi’ut或K
mi’ut或K m-K
m-K mi’ut之对音。“谦河西南,唐麓岭之北”可以使我们坚信,这里确实是指克穆齐克河流域。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文中所指的是一个包括汉族工匠居住的屯区。后者从成吉思汗执政末年,也就是在公元1223年之前,就在那里落脚谋生了,但居民中有一部分则是蒙古人。至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回纥”人,应该是指操突厥语的土著居民,也可能是指在征西之后,从今新疆地带迁来的许多穆斯林聚落之一。他们不可能是吉利吉思人,虽然据拉施特记载,在吉利吉思人和谦州之间,有一条政治纽带相联结。因为据本地志记载,吉利吉思人栖身于更靠北—西北方向很远的地方。
mi’ut之对音。“谦河西南,唐麓岭之北”可以使我们坚信,这里确实是指克穆齐克河流域。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文中所指的是一个包括汉族工匠居住的屯区。后者从成吉思汗执政末年,也就是在公元1223年之前,就在那里落脚谋生了,但居民中有一部分则是蒙古人。至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回纥”人,应该是指操突厥语的土著居民,也可能是指在征西之后,从今新疆地带迁来的许多穆斯林聚落之一。他们不可能是吉利吉思人,虽然据拉施特记载,在吉利吉思人和谦州之间,有一条政治纽带相联结。因为据本地志记载,吉利吉思人栖身于更靠北—西北方向很远的地方。
许多汉文载籍都提到了谦州或谦谦州,现在我可以据本人所知而略加引证。
一、道教祖师丘处机奉成吉思汗之召西游后,从俄国突厥斯坦返程时,于1223年6月1日前后抵达阿不罕山。他对此地记载说:“西北千余里,俭俭州出良铁,多青鼠,亦收禾麦。汉匠千百人居之,织绫罗锦绮。 ”“俭俭州”是一种拙劣的对音法,可以复原为G
”“俭俭州”是一种拙劣的对音法,可以复原为G n-G
n-G n i’ü(t),也就是谦谦州,“俭”字的发音在元代尚带有尾音-m。本文献的价值在于说明汉人工匠的屯区,早在1223年之前就在那里建立了,该屯区无疑是建于成吉思汗出兵进攻花剌子模(Khwarezm)的时代。
n i’ü(t),也就是谦谦州,“俭”字的发音在元代尚带有尾音-m。本文献的价值在于说明汉人工匠的屯区,早在1223年之前就在那里建立了,该屯区无疑是建于成吉思汗出兵进攻花剌子模(Khwarezm)的时代。
丘处机仅仅是风闻这一屯区的存在,他提供的资料无法使我们进一步解释,阿不罕山一名尚未能比定。在丘处机西游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这一地区 。韦利(Waley)先生曾断定,阿不罕山“与近代的额尔古纳山脉本为同一地”,位于“乌里雅苏台的西南”。这同样也是王国维的判断,但其论据并不令人心悦诚服。事实上,王国维所据为基础的,是镇海(inqai)的传记
。韦利(Waley)先生曾断定,阿不罕山“与近代的额尔古纳山脉本为同一地”,位于“乌里雅苏台的西南”。这同样也是王国维的判断,但其论据并不令人心悦诚服。事实上,王国维所据为基础的,是镇海(inqai)的传记 。据这篇传记记载,镇海奉命屯田阿鲁欢,他曾自阿不罕山北去会见丘处机。该地区的一座山至今仍被汉人称为阿尔洪
。据这篇传记记载,镇海奉命屯田阿鲁欢,他曾自阿不罕山北去会见丘处机。该地区的一座山至今仍被汉人称为阿尔洪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3,第2页)和布勒士奈德(Breitschneider)就已经承认,阿鲁欢和阿不罕均指同一地点,而张穆又将之考证成阿集尔罕山(A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3,第2页)和布勒士奈德(Breitschneider)就已经承认,阿鲁欢和阿不罕均指同一地点,而张穆又将之考证成阿集尔罕山(A jirhan),但它肯定过分偏西了。王国维在一段时间内甚至考虑阿不罕山是阿尔罕(即阿鲁欢之误)。但《元史》中的任何记载都不允许肯定阿鲁欢究竟是一块领土、一条河流、一座山脉,甚至是一个部族的名称,以至于使屠寄(《蒙兀儿史记》卷48,第1页)竟可以认为,阿鲁欢是鄂尔浑河的对音,并且还自信可以把比鄂尔浑河稍偏东一些的阿不罕山(Abaqan)看做是阿鲁欢山。这些解决办法从地理学角度上来说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完全如同王国维所指出的那样。然而,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则是非常符合规则的,而王国维却要到阿鲁欢(又称阿不罕)地区一带寻求一位乌梁罕,这明显是不值得考虑的
jirhan),但它肯定过分偏西了。王国维在一段时间内甚至考虑阿不罕山是阿尔罕(即阿鲁欢之误)。但《元史》中的任何记载都不允许肯定阿鲁欢究竟是一块领土、一条河流、一座山脉,甚至是一个部族的名称,以至于使屠寄(《蒙兀儿史记》卷48,第1页)竟可以认为,阿鲁欢是鄂尔浑河的对音,并且还自信可以把比鄂尔浑河稍偏东一些的阿不罕山(Abaqan)看做是阿鲁欢山。这些解决办法从地理学角度上来说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完全如同王国维所指出的那样。然而,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则是非常符合规则的,而王国维却要到阿鲁欢(又称阿不罕)地区一带寻求一位乌梁罕,这明显是不值得考虑的 。许多复原法都是可能的,如带有l或r、带有或没有中元音、带有或没有尾音-n或-l。这最后一个音节中的元音从原则上来说应为-o-,甚至是-ō-;可能的复原法是Arqon(Arγōn)或Argol(Arγōl)。除此而外,我不能再讲更多的了。
。许多复原法都是可能的,如带有l或r、带有或没有中元音、带有或没有尾音-n或-l。这最后一个音节中的元音从原则上来说应为-o-,甚至是-ō-;可能的复原法是Arqon(Arγōn)或Argol(Arγōl)。除此而外,我不能再讲更多的了。
在考虑了这些背景之后,我们便会思忖它是否是指额尔古纳山。但事实上,从来不会特别指定一座山作为屯田区。另外,额尔古纳山也不大为人所知,此名的蒙古文形式难以定夺。在那些可以间接追溯到17世纪的中国地图上,“阿尔洪”山位于乌里雅苏台正南和扎布汗河( jabham,德文地图中为Dsabchyn)以南。在出现阿尔洪山名字的唯一一部文献中
jabham,德文地图中为Dsabchyn)以南。在出现阿尔洪山名字的唯一一部文献中 ,又认为此山位于席喇乌苏河(
,又认为此山位于席喇乌苏河( ira-Usu,意为“黄河)的发源地,席喇乌苏河也就是中国地图上的席喇河,本为扎布汗河上游的左部支流。此书将阿尔洪山置于乌里雅苏台的北—东北方向
ira-Usu,意为“黄河)的发源地,席喇乌苏河也就是中国地图上的席喇河,本为扎布汗河上游的左部支流。此书将阿尔洪山置于乌里雅苏台的北—东北方向 。对于镇海屯田之阿鲁欢来说,上述任何方位似乎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尤其是希望将其考证为阿不罕山时更为如此。
。对于镇海屯田之阿鲁欢来说,上述任何方位似乎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尤其是希望将其考证为阿不罕山时更为如此。
在有关阿不罕山的问题上,王国维承认此名的存在,因为元代的一篇碑铭中就提到了一个同样也写作“阿不罕“的部族。严格地说,当涉及一位在成吉思汗时代负责领导阿不罕部那些人物碑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承认文中所涉及的是居住在阿不罕山的工匠。然而,我感到相当奇怪的是,文中竟如此称呼镇海的屯田区,该屯田区在整个元代都非常著名,而且始终被称作“镇海屯田”,或者是简称为镇海。我基本可以肯定,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所指的是不同名称,但却是同名异义词。屠寄错误地认为此处是指鄂尔浑河以东的阿巴罕山,但他的复原法从原则上来说是正确的,阿不罕就代表着蒙古文中的Abuqan,其正常的和常见的异体字就是Abaqan。确定此山的方位是困难的,但如果要将之确定在乌里雅苏台西南某一地方,大概也不会大谬。
二、《元史》卷6,第1页中记载道:至元“二年正月……癸酉(1265年元月21日)……勅徙镇海、百八里、谦谦州诸色匠户于中都(北京),给银万五千两为行费” 。镇海就是inqai之对音,指由镇海所创立的屯田区
。镇海就是inqai之对音,指由镇海所创立的屯田区 ;“百八里”不为人所知,但它很可能是对别失八里(
;“百八里”不为人所知,但它很可能是对别失八里( )的讹误对音,位于今之古城的西北,所以很可能应读作“百失八里”。
)的讹误对音,位于今之古城的西北,所以很可能应读作“百失八里”。
三、《元史》卷6,第18页中记载说:至元六年二月“丁酉(1269年4月3日)……赈欠州人匠贫乏者,米五千九百九十九石” 。
。
四、《元史》卷12,第11页中记载:至元十九年十一月“甲子(1282年12月9日),给欠州屯田军衣服”。
五、《元史》卷151,第15页中的贾塔剌浑(Tarqun,Tqrγun,意为“胖子贾”) 中记载说:“师还(可能是指从1225年西线战役中回师),驻谦谦州,即古乌孙国也”。把谦谦州考证成汉代的古乌孙国,当然是毫无价值的,虽然屠寄(卷59,第7页)对此确信不疑。由于这一比定毫无道理地打乱了传记中的时间体系,所以才出现了不连贯的现象。
中记载说:“师还(可能是指从1225年西线战役中回师),驻谦谦州,即古乌孙国也”。把谦谦州考证成汉代的古乌孙国,当然是毫无价值的,虽然屠寄(卷59,第7页)对此确信不疑。由于这一比定毫无道理地打乱了传记中的时间体系,所以才出现了不连贯的现象。
六、《元史》卷193,第8页中讲到了“伯八”[Baibe(q)]。伯八为晃合丹(Qongqotan)氏,是脱伦阇里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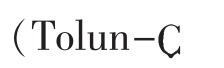
 rbi)的儿子,也是明里也赤哥[Mingli(k)-
rbi)的儿子,也是明里也赤哥[Mingli(k)- ig
ig ,M
,M nglik-
nglik- ig
ig ]的孙子
]的孙子 。他在忽必烈执政初年(也就是1260年之后不久)擢为万户。文中接着又记载说:“命领诸部军马屯守欠欠州”
。他在忽必烈执政初年(也就是1260年之后不久)擢为万户。文中接着又记载说:“命领诸部军马屯守欠欠州” 。
。
七、《元史》卷167,第12页有刘好礼传,此人在1270年迁任“五部”断事官( jarγu i),置其府于益兰州。文中记载说,时隔不久,蒙古诸王相断叛乱,刘好礼被执军中,后又获释。到了1279年春,“叛王召好礼至欠欠州”。
jarγu i),置其府于益兰州。文中记载说,时隔不久,蒙古诸王相断叛乱,刘好礼被执军中,后又获释。到了1279年春,“叛王召好礼至欠欠州”。
八、《山居新语》(《武林往哲遗书》版本,第2页)提到了“谦州”,它很可能就是谦谦州之误。
因此,汉籍中有时作“谦谦(欠欠)州”,有时又仅作“谦(欠)州”。其简化形式的用法可能是由于疏忽大意,或者是由于原文中重复了第一个字而造成的错误。我在这两种情况下,又发现了颠倒的作法,这就说明类似的错误是多么容易犯啊!事实上,王国维在其《圣武亲征录》的版本中(第60页),更为赞成《元史》卷63中的“谦谦州”这种写法,但原文中却仅作“谦州”。同样,波波夫在《蒙古游牧记》译注本第404页(对《蒙古游牧记》卷10,第5页的译文)中仅作“克木齐克”,而原文中却作“克木—克木齐克(K m-K
m-K mik)。然而,志费尼也可能作K
mik)。然而,志费尼也可能作K b ik,无论如何也应为
b ik,无论如何也应为 。
。
“谦州“一名后来在蒙古文中仍作为氏族名称而沿存下来了。我在《蒙古黄金史》中就遇到了谦州(写作K migüt)一名(贡布耶夫版本,第174和186页)
migüt)一名(贡布耶夫版本,第174和186页) ,在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中,该名称出现了3次(施密特译本第171、191和257页)。它在满文中作Kamigut
,在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中,该名称出现了3次(施密特译本第171、191和257页)。它在满文中作Kamigut 。汉文本
。汉文本 中的一条札记中,强调了蒙古族氏的“通谱”。据此认为,人们当时还知晓“克穆齐特氏”(K
中的一条札记中,强调了蒙古族氏的“通谱”。据此认为,人们当时还知晓“克穆齐特氏”(K m ik)和“克穆楚特氏”
m ik)和“克穆楚特氏” 輪輯。我们可以思忖,K
輪輯。我们可以思忖,K mi’üt>K
mi’üt>K mit和K
mit和K mü一名是否都应该上溯“谦谦州”。因为除了克穆齐克河(即小谦河)
mü一名是否都应该上溯“谦谦州”。因为除了克穆齐克河(即小谦河) 之外,还有另一条克穆齐克河,徐松
之外,还有另一条克穆齐克河,徐松 认为它位于额尔齐斯河谷地。另一条河叫做克姆楚克(Kemug)河,位于鄂毕河流域,其名基本与克穆齐克河相同。这种怀疑是可能的。在历史上曾起过作用的,并一直维持到近代蒙古地名表中的唯一一条克穆齐克河,就是谦谦州的克穆齐克河。在蒙古人中出现的最为古老和近代之前的记载,应为1620年,载高加索人伊万·彼得林(Ivan Petlin)的游记中,他曾经到过阿巴坎河和克穆齐克河流域
认为它位于额尔齐斯河谷地。另一条河叫做克姆楚克(Kemug)河,位于鄂毕河流域,其名基本与克穆齐克河相同。这种怀疑是可能的。在历史上曾起过作用的,并一直维持到近代蒙古地名表中的唯一一条克穆齐克河,就是谦谦州的克穆齐克河。在蒙古人中出现的最为古老和近代之前的记载,应为1620年,载高加索人伊万·彼得林(Ivan Petlin)的游记中,他曾经到过阿巴坎河和克穆齐克河流域 。
。
我现在应该回到《元史》卷63有关谦河的地志中了。文献中是这样记载的:“谦河经其中(吉利吉思人之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东北有水曰玉须,皆巨浸也,会于谦,而注入昂剌河,北入于海”。昂可剌河当然就是安加拉河(Angqara),在拉施特的《史集》中作Anqara,在我们西方的地图中则作Angara。在近代人的地理观念中,把安加拉河看做是克姆河或叶尼塞河的支流,中国学者们的考证都是受到了这种观点的影响。徐松 认为,谦河就是昂噶剌河,阿浦水是厄尔库河(Irku),玉须水是伊里穆(Ilim)。屠寄
认为,谦河就是昂噶剌河,阿浦水是厄尔库河(Irku),玉须水是伊里穆(Ilim)。屠寄 谨慎地修正了原文,以便于他说明在谦河的西南是阿浦水(阿巴坎河),而在东北则是安加拉河,后两条河都注入了谦河,谦河随后也就变成了玉须水,也就是叶尼塞河。这两种理论都毫无价值。事实上,中世纪的地理观在中国人和穆斯林作者们中是一致的:安加拉河被看做是一条主要的江河,而谦河则被看做是其支流。这种观点是完全可以经得起反驳的,因为我们考虑到安加拉河源出于贝加尔湖,色楞格河从东南方注入贝加尔湖,而色楞格河的下游又常常被称为安加拉河的上游。由色楞格河与安加拉河所补充了流量的河流,要远比克姆河从源头直到安加拉河汇合处的流程长得多。
谨慎地修正了原文,以便于他说明在谦河的西南是阿浦水(阿巴坎河),而在东北则是安加拉河,后两条河都注入了谦河,谦河随后也就变成了玉须水,也就是叶尼塞河。这两种理论都毫无价值。事实上,中世纪的地理观在中国人和穆斯林作者们中是一致的:安加拉河被看做是一条主要的江河,而谦河则被看做是其支流。这种观点是完全可以经得起反驳的,因为我们考虑到安加拉河源出于贝加尔湖,色楞格河从东南方注入贝加尔湖,而色楞格河的下游又常常被称为安加拉河的上游。由色楞格河与安加拉河所补充了流量的河流,要远比克姆河从源头直到安加拉河汇合处的流程长得多。
我们通过上文已经看到,《元史》中的阿浦水,完全如同《周书》中所记载的最古老的阿辅水一样,很有可能是阿巴坎河。玉须水的情况提出了更多的难题。朔特(同上引书,第453—454页)指出,人们应该把玉须水看做是Ijus的对音,但汉文载籍中误认为此河位于叶尼塞河的东北而不是西北。这种错误事实上要严重得多,因为玉须水(Ijus,也就是Iyus或Yus,更应该是Iyus的复数)事实是指白玉须河和黑玉须河两条河,它们汇合之后就形成了我们西方地图中的Tschulym河,它是鄂毕河的右部分支,所以这一错误相当严重。另外,玉须河也不能确切地被比定为Iyus或Yus 。实际上,在元代,-s这种尾音一般应译作汉语中的“斯”。“玉须”可以使我们联想到许多复原法,如Yüsü、üsü、Yüsü(t)、Yüsü(k)、üsü(k)等。如果它确实是一种已经蒙古文化了的突厥文形式,那么原突厥文就可能含有一个-z-,在蒙古文中就变作-s-。如果在这种假设中再加入一种双重的地理错误,那还不如在语音方面不太确切更好。最为聪明的办法,就是承认此处确实系指汇入安加拉河之前的谦河之右翼分支。如果该地区唯一一条堪称“大河”者,即为根河,那么玉须水就可以用以拼写根河的古名
。实际上,在元代,-s这种尾音一般应译作汉语中的“斯”。“玉须”可以使我们联想到许多复原法,如Yüsü、üsü、Yüsü(t)、Yüsü(k)、üsü(k)等。如果它确实是一种已经蒙古文化了的突厥文形式,那么原突厥文就可能含有一个-z-,在蒙古文中就变作-s-。如果在这种假设中再加入一种双重的地理错误,那还不如在语音方面不太确切更好。最为聪明的办法,就是承认此处确实系指汇入安加拉河之前的谦河之右翼分支。如果该地区唯一一条堪称“大河”者,即为根河,那么玉须水就可以用以拼写根河的古名 。在此情况下,人们甚至还可以认为益兰河(根河的支流)即为谦谦州。
。在此情况下,人们甚至还可以认为益兰河(根河的支流)即为谦谦州。
注释:
①拉德洛夫:《突厥方言辞典》第2卷,第1202—1203页。在此之前还有朔特:《八吉利吉思部考》,载《柏林科学院丛书》,1864年柏林版,第441—442页。
②汤姆森:《鄂尔浑河流域碑铭》第123页(第2版,第26页);奥尔昆:《突厥碑铭集》,1936年伊斯坦布尔版,第60页。大家同时还可以参看兰司铁:《回鹘—鲁尼文碑铭集》,第21、25页;上引奥尔昆书,第2卷,第170、174页。
③《暾欲谷碑跋》,载《在蒙古发现的古突厥文碑铭》第2辑,第42—43页。
④屠寄:《蒙兀尔史记》卷160,第33页。作者与朔特和夏德的观点不谋而合,各自分别得出了这一结论。
⑤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本第1卷,第64页。
⑥Aba之意为“阿爸”,这类词经常倾向于产生此字本身及其派生词的讹误形式。如,我们在察合台突厥语和特勒兀特语中,还发现一种写法为abū(阿爸,见上引拉德洛夫辞典,第1卷,第631页),而在蒙古文中则是abu(科瓦烈夫斯基书,第45页)。一方面,对于aba来说,阿里斯托夫所指出的“熊”仅是次要意义,这可能是由于对熊的真正名称的忌讳而引起的。另一方面,如果某些部族确实可以根据河名而命名,那么阿里斯托夫似乎赋予了这种辞源学系统一种过分夸大的意义。根据亲属关系而命名的部族也为数不少,如有两个蒙古部族分别被称为阿巴嘎(Abaγa)和阿巴嘎纳尔(Abaγanar),意为“阿爸”。
⑦沙畹:《西突厥史料》第98页。
⑧同上,第62页。
⑨在通常所引用的版本中,“蒲”字是一个印刷错误。
⑩事实肯定不是夏德在《暾欲谷碑跋》第42页、87页中所说的那样,即[K ngü]-Tarman。
ngü]-Tarman。
 《太平寰宇记》卷198,第8页中仅仅出现了第一种形式。大家同样还请参阅《新唐书》卷43下,第15页。
《太平寰宇记》卷198,第8页中仅仅出现了第一种形式。大家同样还请参阅《新唐书》卷43下,第15页。
 在《太平寰宇记》卷198,第9页中,此名误作“大漠”。大家还可以参阅《新唐书》卷43下,第15页。
在《太平寰宇记》卷198,第9页中,此名误作“大漠”。大家还可以参阅《新唐书》卷43下,第15页。
 我不认为似乎应该把我们已经遇到的“金海”理解为“谦海”(“剑海”是该名的另一种对音法)。(https://www.xing528.com)
我不认为似乎应该把我们已经遇到的“金海”理解为“谦海”(“剑海”是该名的另一种对音法)。(https://www.xing528.com)
 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第362页,它参阅了马夸特于1929年《匈牙利年鉴》第98页的考释。
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第362页,它参阅了马夸特于1929年《匈牙利年鉴》第98页的考释。
 这其中有朔特的一个旧错误。《新唐书》卷217下,第11页确实指出,黠戛斯君长“驻牙青山,周栅代垣,联毡为帐,号‘密的支’,它首领居小帐”。“密的支”一名也出现在《太平寰宇记》卷199,第14页中,其中记载说:“阿热衙立为栅,坐大毡帐,号为密的支。其首领以降皆有小毡帐,皆以木皮为屈。”所以,朔特把“密的支”与下一个“它”字联在一起使用,是不顾最为明显的事实,因为后一个字只指“其它”,仅起一种语义学作用。
这其中有朔特的一个旧错误。《新唐书》卷217下,第11页确实指出,黠戛斯君长“驻牙青山,周栅代垣,联毡为帐,号‘密的支’,它首领居小帐”。“密的支”一名也出现在《太平寰宇记》卷199,第14页中,其中记载说:“阿热衙立为栅,坐大毡帐,号为密的支。其首领以降皆有小毡帐,皆以木皮为屈。”所以,朔特把“密的支”与下一个“它”字联在一起使用,是不顾最为明显的事实,因为后一个字只指“其它”,仅起一种语义学作用。
 参阅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本第1卷,第425页.
参阅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本第1卷,第425页.
 谦河的名字第2次出现在有关达达族的传记中,其中包括有一段关于“
谦河的名字第2次出现在有关达达族的传记中,其中包括有一段关于“ 马部”地区的奇怪文字,也就是17和18世纪在俄文著作和地图中出现的P?straya Orda(见卡昂:《西伯利亚地图》第74、147和171页)。这段文字后来又被阿布尔—喀齐摘要转载于其著作第44—45页,拉施特在那里提到一座位于谦河和昂可剌—沐涟(安加拉河)分支上的城市。这一段文字已由哈默(Hammer)连同克拉普洛特的注释,一并发表于1832年6月号的《亚细亚学报》第523—524页中,这就是贝勒津未宣而删的那段文字,因而致使巴托尔德在《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186页中误入歧途。“
马部”地区的奇怪文字,也就是17和18世纪在俄文著作和地图中出现的P?straya Orda(见卡昂:《西伯利亚地图》第74、147和171页)。这段文字后来又被阿布尔—喀齐摘要转载于其著作第44—45页,拉施特在那里提到一座位于谦河和昂可剌—沐涟(安加拉河)分支上的城市。这一段文字已由哈默(Hammer)连同克拉普洛特的注释,一并发表于1832年6月号的《亚细亚学报》第523—524页中,这就是贝勒津未宣而删的那段文字,因而致使巴托尔德在《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186页中误入歧途。“ 马”部成了一系著作所研究的对象,详见内梅特(Németh)于《西洛支·乔玛档案》第1卷,第345—352页的分析,《匈牙利年鉴》第10卷,第32页;尤其是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中的“Cala-cian”条目,其中提到了
马”部成了一系著作所研究的对象,详见内梅特(Németh)于《西洛支·乔玛档案》第1卷,第345—352页的分析,《匈牙利年鉴》第10卷,第32页;尤其是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中的“Cala-cian”条目,其中提到了 马部。
马部。
 见德梅松所译阿布尔—喀齐书,第45页。大家同样也请参阅比丘林附在《民族史》第3卷中的地图,其中将河流的发源地确定得不够准确;大家还可以参阅贝勒津书第1卷,第250页;由霍渥斯在《蒙古史》第1卷,第682页中所指出过各种歧义很大的解释。
见德梅松所译阿布尔—喀齐书,第45页。大家同样也请参阅比丘林附在《民族史》第3卷中的地图,其中将河流的发源地确定得不够准确;大家还可以参阅贝勒津书第1卷,第250页;由霍渥斯在《蒙古史》第1卷,第682页中所指出过各种歧义很大的解释。
 《元史译文正补》卷26下,第14页。
《元史译文正补》卷26下,第14页。
 对于克姆河上游的两条东部支流,人们今天仍把北部的一条称为贝克姆河,把南部的一条叫做华克姆。它们汇合之后就形成了乌鲁克姆河(Ulu-K
对于克姆河上游的两条东部支流,人们今天仍把北部的一条称为贝克姆河,把南部的一条叫做华克姆。它们汇合之后就形成了乌鲁克姆河(Ulu-K m),意为“大克姆河”。有时也把贝克姆河称为乌鲁克姆河,汉文载籍和地图在18世纪之前,从未曾提到过这些名称。在西方,这些名称也没有标注在威特森(1687年)和列麦佐夫(1697年)的地图上。但到了1730年,施特拉林贝又指出,叶尼塞河又称克姆河(Kemm),由贝克姆河和乌鲁克姆河(G’hokem)及西施基特(Tschisch kisch,即
m),意为“大克姆河”。有时也把贝克姆河称为乌鲁克姆河,汉文载籍和地图在18世纪之前,从未曾提到过这些名称。在西方,这些名称也没有标注在威特森(1687年)和列麦佐夫(1697年)的地图上。但到了1730年,施特拉林贝又指出,叶尼塞河又称克姆河(Kemm),由贝克姆河和乌鲁克姆河(G’hokem)及西施基特(Tschisch kisch,即 iskit)所组成(见卡昂:《18世纪的西伯利亚地图》,第185页)。这些名称明显是比较古老的。完全如同乌鲁克姆河(Ulu-K
iskit)所组成(见卡昂:《18世纪的西伯利亚地图》,第185页)。这些名称明显是比较古老的。完全如同乌鲁克姆河(Ulu-K m)是Uluγ-K
m)是Uluγ-K m的柯尔克孜文形式,贝克姆河(Bei-K
m的柯尔克孜文形式,贝克姆河(Bei-K m)也可能是B
m)也可能是B g-K
g-K m的一种柯尔克孜文形式,意为“王子的克姆河”。突厥文Uluγ和b
m的一种柯尔克孜文形式,意为“王子的克姆河”。突厥文Uluγ和b g等形式都不一定是现代的。巴托尔德曾指出(《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28页,法译本第21页)用bi(应该做bī)来代替B
g等形式都不一定是现代的。巴托尔德曾指出(《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28页,法译本第21页)用bi(应该做bī)来代替B g的作法,在15世纪之前未曾出现过。这种论点对于bī本身来说也可能是正确的,但有关黠戛斯部的汉文史料曾3次(《新唐书》卷217下,第12页)对音为“辈”,它只能是相当于b
g的作法,在15世纪之前未曾出现过。这种论点对于bī本身来说也可能是正确的,但有关黠戛斯部的汉文史料曾3次(《新唐书》卷217下,第12页)对音为“辈”,它只能是相当于b g,应复原为b
g,应复原为b i。因此,尾清喉音的脱落至少从800年起,就已经在黠戛斯语中形成了。
i。因此,尾清喉音的脱落至少从800年起,就已经在黠戛斯语中形成了。
 那珂通世于《成吉思汗实录》第398页中,极力避免对此作任何解释;同样也请参阅施世杰:《元秘史山川地名考》卷10,第2页。
那珂通世于《成吉思汗实录》第398页中,极力避免对此作任何解释;同样也请参阅施世杰:《元秘史山川地名考》卷10,第2页。
 大家可以参看李默德(Grenard):《高地亚洲》第251页中的sistig条目。
大家可以参看李默德(Grenard):《高地亚洲》第251页中的sistig条目。
 对音词中的-q-说明,失黑失惕
对音词中的-q-说明,失黑失惕 是
是 经蒙古文化之后的形式。在阿尔泰地区的突厥方言中,
经蒙古文化之后的形式。在阿尔泰地区的突厥方言中, 之意为“颌”。
之意为“颌”。
 参阅第1卷,第51页的注释,这就是拉施特《史集》(伯劳舍版本,第2卷,第102页)中相对应的段落。
参阅第1卷,第51页的注释,这就是拉施特《史集》(伯劳舍版本,第2卷,第102页)中相对应的段落。
 -h-是用以标注-k-的音标,在词尾之前又变成了-g-,事实上最后导致成了一个元音重复符号
-h-是用以标注-k-的音标,在词尾之前又变成了-g-,事实上最后导致成了一个元音重复符号 。-d是尾音-t的一个发音音标,志费尼由此而早于施密特和俄国蒙古学家们使用了这些音标。
。-d是尾音-t的一个发音音标,志费尼由此而早于施密特和俄国蒙古学家们使用了这些音标。
 拉施特以及志费尼的手稿,均无法使人断定究竟应读作
拉施特以及志费尼的手稿,均无法使人断定究竟应读作 还是
还是 。
。
 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本第1卷,第316—317页。大家同样也请参阅贝勒津书第1卷,第89页,第3卷,第107页;伯劳舍版本第2卷,第397页。
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本第1卷,第316—317页。大家同样也请参阅贝勒津书第1卷,第89页,第3卷,第107页;伯劳舍版本第2卷,第397页。
 马夸特:《库曼语辞典》第135页。多桑(d’Ohsson)译文第1卷,第103页和贝勒津(第1卷,第130页)的译本,是一种误解。其正确的写法,见诸贝勒津原文第1卷,第168页和马夸特书第135页。
马夸特:《库曼语辞典》第135页。多桑(d’Ohsson)译文第1卷,第103页和贝勒津(第1卷,第130页)的译本,是一种误解。其正确的写法,见诸贝勒津原文第1卷,第168页和马夸特书第135页。
 马夸特本人曾把克穆齐克一词解释作克姆河的小品词,但却没有去研究乞克族。
马夸特本人曾把克穆齐克一词解释作克姆河的小品词,但却没有去研究乞克族。
 汉籍中曾多次提到“谦河”,这是最通用的对音法。但在《元史》卷128,第8页中,还有两次提到“欠河”,这些对音词在元代时都附有一个尾音-m。
汉籍中曾多次提到“谦河”,这是最通用的对音法。但在《元史》卷128,第8页中,还有两次提到“欠河”,这些对音词在元代时都附有一个尾音-m。
 朔特在《八吉利吉思部族考》第454页中,也承认这一点。
朔特在《八吉利吉思部族考》第454页中,也承认这一点。
 突厥文中的Y
突厥文中的Y lan也具有“蛇”之意。
lan也具有“蛇”之意。
 译自蒙古文
译自蒙古文 ,意为“法官”,本处的意思为“命官”。
,意为“法官”,本处的意思为“命官”。 原文为“杞柳”。屠寄(卷103,第1页)希望将此改作“桦木”,但却没有充分根据。
原文为“杞柳”。屠寄(卷103,第1页)希望将此改作“桦木”,但却没有充分根据。
 《元史》卷128,第17页《土土哈传》中同样也提到了“五部”。有关土土哈的问题,请参阅笔者旧作《〈元史〉卷108注释》第61、163页。
《元史》卷128,第17页《土土哈传》中同样也提到了“五部”。有关土土哈的问题,请参阅笔者旧作《〈元史〉卷108注释》第61、163页。
 《元史译文正补》卷26下,第13页。
《元史译文正补》卷26下,第13页。
 《蒙兀儿史记》卷160,第34页。
《蒙兀儿史记》卷160,第34页。
 这里也可能为
这里也可能为 ,第一种形式从理论上来说是正确的复原,但其中所采用的“州”字也可能有损于这种对音的正确性。
,第一种形式从理论上来说是正确的复原,但其中所采用的“州”字也可能有损于这种对音的正确性。
 海涅什(Haenisch)先生于其辞典第4、60页中,提供了诸如
海涅什(Haenisch)先生于其辞典第4、60页中,提供了诸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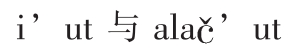 等写法,并认为它们是
等写法,并认为它们是 的复数形式。事实上,我们应将之读作单数
的复数形式。事实上,我们应将之读作单数 和
和 ,它们原则上都是“黑色的”(qara)和“红色的”(alaq)等形容词的阴性形式,即带有
,它们原则上都是“黑色的”(qara)和“红色的”(alaq)等形容词的阴性形式,即带有 的形容词。
的形容词。 是具有一个以-i’ut结尾的复数形式,而不是名词。
是具有一个以-i’ut结尾的复数形式,而不是名词。
 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本第1卷,第14页。
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本第1卷,第14页。
 此文献同样也由在《蒙古世系谱》中所补充的注释内引证,本人至今尚无法对此进行考证,也没有在《大清一统志》第532中找到这段引文。
此文献同样也由在《蒙古世系谱》中所补充的注释内引证,本人至今尚无法对此进行考证,也没有在《大清一统志》第532中找到这段引文。
 《元史语解》卷6,第7页,其中把《元史》卷63中的“昂可剌”对音为“摩和尔”。
《元史语解》卷6,第7页,其中把《元史》卷63中的“昂可剌”对音为“摩和尔”。
 “大泽”是《前汉书》卷91,第17页《西域传》中对康居的称呼,当时只能是指咸海。像徐松(《西域水道记》卷5,第35页)那样的一批学者,也都承认它系指“北海”。后者自唐代之前开始,就常常用以表示中国人对北冰洋的含糊概念。对于夏德(《暾欲谷碑跋》第40页)的假设,不值得我们予以任何重视。
“大泽”是《前汉书》卷91,第17页《西域传》中对康居的称呼,当时只能是指咸海。像徐松(《西域水道记》卷5,第35页)那样的一批学者,也都承认它系指“北海”。后者自唐代之前开始,就常常用以表示中国人对北冰洋的含糊概念。对于夏德(《暾欲谷碑跋》第40页)的假设,不值得我们予以任何重视。
 Tanglu>Tangnu,完全如同蒙古文manglai>mangnai一样。这里指的是唐努—乌拉山。在tanglu和突厥文Tob’tongl
Tanglu>Tangnu,完全如同蒙古文manglai>mangnai一样。这里指的是唐努—乌拉山。在tanglu和突厥文Tob’tongl (好极了)之间,也可能存在有某种关系。参阅拉德洛夫辞典第3卷,第812页。
(好极了)之间,也可能存在有某种关系。参阅拉德洛夫辞典第3卷,第812页。
 王国维版本,卷下,第8页;布勒士奈德:《中世纪研究》第1卷,第10页;韦利:《炼丹术家的游记》第124页。
王国维版本,卷下,第8页;布勒士奈德:《中世纪研究》第1卷,第10页;韦利:《炼丹术家的游记》第124页。
 王国维版本,卷上,第19页;布勒士奈德译本第1卷,第60页和韦利译本第73页。另请参阅波波夫:《蒙古游牧记》译注本第409、438—439页。
王国维版本,卷上,第19页;布勒士奈德译本第1卷,第60页和韦利译本第73页。另请参阅波波夫:《蒙古游牧记》译注本第409、438—439页。
 《元史》卷120,第4页。
《元史》卷120,第4页。
 韦利先生在其译文(第33页)中明确指出,镇海曾奉诏在额尔古纳山脉附近建工匠屯区,而《元史》中明确记载那里为农业屯区。但镇海的一位后裔的墓志铭说明,那里既有工匠,又有农夫。参阅《圭塘小稿》,载《中州名贤文表》卷22,第8页。
韦利先生在其译文(第33页)中明确指出,镇海曾奉诏在额尔古纳山脉附近建工匠屯区,而《元史》中明确记载那里为农业屯区。但镇海的一位后裔的墓志铭说明,那里既有工匠,又有农夫。参阅《圭塘小稿》,载《中州名贤文表》卷22,第8页。
 波波夫(第439页)把“阿鲁欢”原复为Aru-Khuan,这种作法明显是错误的。
波波夫(第439页)把“阿鲁欢”原复为Aru-Khuan,这种作法明显是错误的。
 《蒙古游牧记》卷10,第3页,波波夫译注本第404页。
《蒙古游牧记》卷10,第3页,波波夫译注本第404页。
 见施泰勒地图集中的第57页,恰恰写于“塔尔巴哈台”中的“T”字母以下,即第24行的右下角。
见施泰勒地图集中的第57页,恰恰写于“塔尔巴哈台”中的“T”字母以下,即第24行的右下角。
 韦利:《炼丹术家的游记》第124页。
韦利:《炼丹术家的游记》第124页。
 一部分工匠由于无法忍受当地气候,所以又被迁至弘州(今河北省阳原)。他们的队伍在那里又扩充了新成员,共同组成一个纺织中心,在三代人期间仍继续由镇海家族所统治。请参阅屠寄书卷48,第11页。但直到1265年,在镇海的屯田区,仍有工匠在此。
一部分工匠由于无法忍受当地气候,所以又被迁至弘州(今河北省阳原)。他们的队伍在那里又扩充了新成员,共同组成一个纺织中心,在三代人期间仍继续由镇海家族所统治。请参阅屠寄书卷48,第11页。但直到1265年,在镇海的屯田区,仍有工匠在此。
 1石为10斗。“欠”的发音仍带有一个尾音-m。这里是指谦谦州的简称谦州。
1石为10斗。“欠”的发音仍带有一个尾音-m。这里是指谦谦州的简称谦州。
 在成吉思汗炮兵队伍中服役的一位汉人。
在成吉思汗炮兵队伍中服役的一位汉人。
 有关伯八及其父脱伦阇里必的身世,主要请参看屠寄书卷44,第1—3页,其中汇集并讨论了所有有关文献。
有关伯八及其父脱伦阇里必的身世,主要请参看屠寄书卷44,第1—3页,其中汇集并讨论了所有有关文献。
 这可能就是王国维在他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第8页中提到的那部文献。
这可能就是王国维在他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第8页中提到的那部文献。
 参阅鲍登(Bawden):《蒙古黄金史》第99节(原本第85页,译本第174页)和第108节(原本第96页和译本第186页)。
参阅鲍登(Bawden):《蒙古黄金史》第99节(原本第85页,译本第174页)和第108节(原本第96页和译本第186页)。
 见海涅什:《蒙古源流》译注本第74页。
见海涅什:《蒙古源流》译注本第74页。
 《蒙古源流笺证》(沈曾植版本)卷5,第23页。
《蒙古源流笺证》(沈曾植版本)卷5,第23页。
輪輯《蒙古佛教史》中误认为Khem-Khem 是蒙古文中的“钦察”
是蒙古文中的“钦察” ,见胡特:《佛教史》卷2,第33页)。这部近代著作中充满了来自汉文载籍中的名词。
,见胡特:《佛教史》卷2,第33页)。这部近代著作中充满了来自汉文载籍中的名词。
 请勿忘记,如果谦河是叶尼塞河上游的名字,那么K
请勿忘记,如果谦河是叶尼塞河上游的名字,那么K m同时也是一个其意本身就为“河”的词。
m同时也是一个其意本身就为“河”的词。
 《西域水道记》卷5,第21页。
《西域水道记》卷5,第21页。
 布勒士奈德:《中世纪研究》第2卷,第156页;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73页。
布勒士奈德:《中世纪研究》第2卷,第156页;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73页。
 《西域水道记》卷5,第36页。
《西域水道记》卷5,第36页。
 《蒙兀儿史记》卷160,第33页。
《蒙兀儿史记》卷160,第33页。
 在斯特拉林贝1730年的地图中作Juss,列麦佐夫1697年的地图中作Iyus。请参阅卡昂:《18世纪的西伯利地图》第93、182页。
在斯特拉林贝1730年的地图中作Juss,列麦佐夫1697年的地图中作Iyus。请参阅卡昂:《18世纪的西伯利地图》第93、182页。
 拉施特《史集》(伯劳舍译本第2卷,第397页;哈默:《伊利汗国史》第1卷,第222页)提到了一条江名,位于克姆—克穆齐克河的汇合处。阿里不哥(Ariq-b
拉施特《史集》(伯劳舍译本第2卷,第397页;哈默:《伊利汗国史》第1卷,第222页)提到了一条江名,位于克姆—克穆齐克河的汇合处。阿里不哥(Ariq-b ga)在最终被忽必烈的军队于“蝇湖”(
ga)在最终被忽必烈的军队于“蝇湖”( imūltū-nawur<Sima’ultu-na’ur)击败之前,似乎是在那里窝冬。我们可以试将拉施特所提到的这一条神秘河流的名称读作Yus,但是由于存在有我们在前面业已提到的一条Us河,所以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imūltū-nawur<Sima’ultu-na’ur)击败之前,似乎是在那里窝冬。我们可以试将拉施特所提到的这一条神秘河流的名称读作Yus,但是由于存在有我们在前面业已提到的一条Us河,所以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译自《亚细亚学报》1989年)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