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姓乌古斯与十姓回鹘考
哈密屯
在蒙古高地发现的用鲁尼文撰写的古突厥碑铭充分证明,在8世纪上半叶,曾经有过一个叫作九姓乌古斯(Toquz-Oruz)的民族,或者简称乌古斯(Oruz)。从9世纪开始,这个民族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尤其是向西部扩张,在伊斯兰作家们的著作中,分别称之为Toruzruz、Tuz或Tozz,而在拜占庭的作者们笔下却称之谓Uz。一般来说,在对8世纪之前的东方这一辽阔领域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将突厥人考虑在内。从汉学家到芬兰—乌戈尔学家,他们都不拘一切形式地到处觅寻乌古斯民族的古代踪迹,而且都倾向于将该民族追溯到至今尚不太明朗的突厥民族起源时代。从一切迹象来看,现代东方学似乎都不恰当地受到了有关乌古斯汗(Oruz Khan)著名传说的影响,乌古斯汗就是使乌古斯民族获名的一位神话先祖。然而,有关这一传说现有形式的起源,最早不会超过元代①。它还可能是深受蒙古人在13世纪进行征服之影响,而该传说在伊斯兰教徒们中间的流传,肯定是由于乌古斯人在10世纪左右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原因。相反,我们没有于其中发现过反映任何更为古老历史事件的迹象。
我们就来研究一下乌古斯这一名称吧。马夸特(Marquart)曾猜测,它本为On-oq,即“十箭”部族,这是西突厥部族联盟的名称。另外一种写法可能为On-Oruz,即“十姓乌古斯”,但未曾出现过。其中的乌古斯一词可能是由Oq(箭)+uz(人)而组成的,其意思就是“会射箭的人”②。同样,内梅特(Néme th)在《十姓回鹘》第152页中也认为,Oruz是由oq(箭)再加上某个带有-z的后缀而组成的,普里察克(Qmeljan Pritsak)在1952年的《乌拉尔—阿尔泰年鉴》第59页中,也认为Oruz系由Oq< oqu(箭、部族)演变而来。有关这些词的辞源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认为突厥语中的oquz或oquz与Oruz并不完全相同③。卜弼德(Boodberg)于1939年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4期,第238页中,又绞尽脑汁地企图将阿尔泰语中一个人所共知的词ugur复原为Oruz,意为“角”,但这一点是很难令人置信的,因为他既滥用了r这一颤喉声,又有点过于钻牛角尖了。巴赞(Louis Bazin)先于1953年在《东方学报》第6卷,第315页中曾试图把乌古斯民族考证为oruz或ogus这些普通的字,在某些近代突厥方言中,其意为“小岁口的公牛”,尤其是因为在国立图书馆所藏的一卷有关乌古斯汗传说的薛爱国(Shefer)藏卷中,确实是画有一头公牛,它可能就是乌古斯汗先祖的形像。然而,只要我们没有在古突厥语中发现过oruz(公牛)一词,也没有在古代文献中发现过,在乌古斯民族与“牛”这一概念之间的某种联系,那就完全有理由将这幅15世纪左右的图案当作是相当晚期的一种民间辞源学方面的表达方式。
1930年,伯希和在《通报》第27卷中,发表了《论回鹘文本乌古斯汗的传说》(第256页),其中主张将这一民族的名字读作Uruz,因为传说中似乎是将这一神话先祖的名字乌古斯或乌古斯汗追溯到一个意为“初乳”的词,所以伯希和认为应该读作uruz。然而,稍后不久,他又改弦易张,“坚信这也是一个由民间起源的词,但忽略了元音音调上的区别”(见《金帐汗国史札记》,第26页注),所以他主张还应该恢复到Oruz的读音上来。他于1914年在《通报》第15卷,第257页中,又将此字与古突厥文中的orus(姓)进行了比较。他当时确实曾这样写道:“鄂尔浑河流域的碑文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常见的字oruz,它与回鹘文中的orus一样,也相当于汉文中的‘姓’。众所周知,Toquz-O uz就恰好相当于汉语中的‘九姓’……即使不用完全肯定鄂尔浑河流域碑铭中的突厥文oruz与回鹘文文献中的oru (orus)完全相同,笔者也认为应该提出这种假设以供我的同事们进行考证。”然而,我坚信伯希和所说的这个字,确实是起源于Oruz的。现在可以肯定,oru
(orus)完全相同,笔者也认为应该提出这种假设以供我的同事们进行考证。”然而,我坚信伯希和所说的这个字,确实是起源于Oruz的。现在可以肯定,oru (姓)中的最后一个音应读为-
(姓)中的最后一个音应读为- ,这一点尤其是被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所证实。从各种迹象来看,此字是由组成名词的后缀-
,这一点尤其是被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所证实。从各种迹象来看,此字是由组成名词的后缀- 与词干or-或oru(其意可能为“生育”)所派生而来,再加上后缀-L也可以形成orul(后裔)。
与词干or-或oru(其意可能为“生育”)所派生而来,再加上后缀-L也可以形成orul(后裔)。
但是,应该如何解释oru 的尾音字母-
的尾音字母- ,变成了Oruz中的-z呢?在古突厥语中,-
,变成了Oruz中的-z呢?在古突厥语中,- /-z的交替变换使用或-
/-z的交替变换使用或- >-z的发展,可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另外,从最早期的突厥文献,即8世纪的碑铭时代起,oru
>-z的发展,可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另外,从最早期的突厥文献,即8世纪的碑铭时代起,oru (姓)就与表示民族的名词Oruz共同使用了。我的解释大致如下:最早,曾经有过一个叫作“九姓”的部落联盟,即“九姓乌古斯”,这一术语很快就被当作专有名词使用了。然而,古突厥语中语音谐和的总趋势以及“回声字”喜欢成双的嗜好,可能对Toquz-oru
(姓)就与表示民族的名词Oruz共同使用了。我的解释大致如下:最早,曾经有过一个叫作“九姓”的部落联盟,即“九姓乌古斯”,这一术语很快就被当作专有名词使用了。然而,古突厥语中语音谐和的总趋势以及“回声字”喜欢成双的嗜好,可能对Toquz-oru 演变为Toquz-oruz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前一种形式给人一种音韵不谐的印象,而后一种形式的音韵则相当完善了。总而言之,在Toquz和oru
演变为Toquz-oruz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前一种形式给人一种音韵不谐的印象,而后一种形式的音韵则相当完善了。总而言之,在Toquz和oru 之间产生了一种非常巧妙的结合,与古突厥语中无数对合韵词一样,它们也都有一个共同的半谐音(例如,axsaq-buxsaq、ya
之间产生了一种非常巧妙的结合,与古突厥语中无数对合韵词一样,它们也都有一个共同的半谐音(例如,axsaq-buxsaq、ya il-yu
il-yu ul、qatilranquarilran、
ul、qatilranquarilran、 art-
art- urt等等,这都是可以从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中信手拈来的例证),其变化过程与qaradi alqadi变作qaradi arqadi(他诅咒)一样(参阅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第1卷,第284页)。所以人们普遍又都作出了相反的猜测,九姓乌古斯这一名称可能先于“乌古斯”而存在,而后者在开始的时候也仅仅是“九姓”联盟部落一名的简称。然而,难道关于Toquz-Oru
urt等等,这都是可以从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中信手拈来的例证),其变化过程与qaradi alqadi变作qaradi arqadi(他诅咒)一样(参阅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第1卷,第284页)。所以人们普遍又都作出了相反的猜测,九姓乌古斯这一名称可能先于“乌古斯”而存在,而后者在开始的时候也仅仅是“九姓”联盟部落一名的简称。然而,难道关于Toquz-Oru >Toquz-Oruz>Oruz的假设可能会与我们通过其他史料,而对九姓乌古斯和乌古斯的了解相一致吗?这就是我在本论文中试图证实的问题。
>Toquz-Oruz>Oruz的假设可能会与我们通过其他史料,而对九姓乌古斯和乌古斯的了解相一致吗?这就是我在本论文中试图证实的问题。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几篇伯希和著作所证实的那样,Toquz-O uz一名在汉语中也称之为“九姓”④。九姓部落联盟是由属于同一个部族的许多部落组成的。在6—8世纪期间,即在隋代和唐代,汉人称它们为“特勒”或“铁勒”。然而,据《通典》(卷199)⑤和《唐书》(卷217上,第1页)记载,“铁勒”是由于“敕勒”的讹传而造成的,在拓跋族统治的北魏时代(386—558),又称之为“高车”。《魏书》卷103,第9页记载说:“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勑(作者用作“敕”——译者注)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作者断句为“高车的丁零”——译者注)”。接着在第9页中又记载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尽与蠕蠕同,唯车轮高大,幅数至多”。因此,汉语中的转写字“铁勒”就相当于一个突厥部族的名称,由于该民族的人多乘高轮车,所以汉人又称他们为“高车”部。然而,“铁勒”可能为突厥文T gr g在古突厥语中的确义是“半圆形的环”⑥,因而也就是指“高车”部所拥有的车轮的特点。俄国人在阿尔泰山的一座古陵墓中曾经发掘过这种东西⑦;车轮虽然很大,但却很轻巧,用弯曲的树枝所制造,带有无数的精细幅条。至于“丁零”一词,它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在当时的汉语中也可以用来转写同一个词T gr
gr g,很可能是用-ng来转写外来词中的-g,而T
g,很可能是用-ng来转写外来词中的-g,而T gr
gr g在后来则就转写成了“铁勒”。另外,在匈奴以北的贝加尔湖和咸海之间地带,在3世纪之前是丁零部族辗转的地方,而且“高车”部中的铁勒部落从这个时代起也就在那里游牧⑧。
g在后来则就转写成了“铁勒”。另外,在匈奴以北的贝加尔湖和咸海之间地带,在3世纪之前是丁零部族辗转的地方,而且“高车”部中的铁勒部落从这个时代起也就在那里游牧⑧。
《隋书》(隋朝断代史,581—617年)中的《铁勒传》(卷85,第8页)是这样开始的⑨:“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可能指黑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洛河(Torlar,Tola)北有仆骨(Toqut)、同罗(Toηra)、韦纥(Uyrur)、拔也古(Bayarqu)、复罗并号俟斤(Irkin)⑩,蒙陈(-?)、吐如纥、斯结(Siqir)、浑(Xun)、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伊吾(Hami)以西,焉耆(Qara ahr)之北,傍白山(指天山)
ahr)之北,傍白山(指天山) ,则有契弊
,则有契弊 、薄洛、职乙(Cigil?)、咥苏(-?)婆那曷(-?,此处与现行中华书局标点本的断句不一样,后者的断句为:“薄落职、乙咥、苏婆、那曷”——译者注)乌灌言(-?)纥骨、也咥(Y
、薄洛、职乙(Cigil?)、咥苏(-?)婆那曷(-?,此处与现行中华书局标点本的断句不一样,后者的断句为:“薄落职、乙咥、苏婆、那曷”——译者注)乌灌言(-?)纥骨、也咥(Y diz=
diz= diz?)
diz?) 、于尼灌言等,胜兵可二万。金山(指阿尔泰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儿十槃达契(中华书局现行标点本为:“咥勒儿、十槃、达契”。——译者注),一万余兵。康国(Sogdiane)北,傍阿得水
、于尼灌言等,胜兵可二万。金山(指阿尔泰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儿十槃达契(中华书局现行标点本为:“咥勒儿、十槃、达契”。——译者注),一万余兵。康国(Sogdiane)北,傍阿得水 ,则有诃咥曷截(Adil Xazir?)
,则有诃咥曷截(Adil Xazir?) 、拔忽比干具海比悉何山养、苏拔(Suβar)
、拔忽比干具海比悉何山养、苏拔(Suβar) 、也末(Yamar?参阅喀什噶里大辞典)、渴达等(中华书局现行标点本为:“诃咥、曷嶻、拔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苏、拔也末喝达”。——译者注),有三万许兵。得嶷海(T
、也末(Yamar?参阅喀什噶里大辞典)、渴达等(中华书局现行标点本为:“诃咥、曷嶻、拔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苏、拔也末喝达”。——译者注),有三万许兵。得嶷海(T ηiz)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咽蔑
ηiz)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咽蔑 、促隆忽(中华书局现行标点本为“三索咽、蔑促、隆忽。——译者注)等诸姓,八千余。拂林(拜占庭)东则有恩屈、阿兰(Aian)、北褥、九离伏、嗢昏(中华书局现行标点本为:“北褥九离、伏嗢昏”。——译者注)等,近二万人。北海(贝加尔湖)南则都波(Tupa)
、促隆忽(中华书局现行标点本为“三索咽、蔑促、隆忽。——译者注)等诸姓,八千余。拂林(拜占庭)东则有恩屈、阿兰(Aian)、北褥、九离伏、嗢昏(中华书局现行标点本为:“北褥九离、伏嗢昏”。——译者注)等,近二万人。北海(贝加尔湖)南则都波(Tupa) 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
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
从最早的史料记载开始,九姓联盟就包括以下铁勒诸部落:韦纥或袁纥(Uyrur)、仆固(Boqu)或仆骨(Boqut,可能为Boqu的复数形式,在于阗文中称之为Bākū)、浑(Xun/Qun) 、巴也(野)古(Bayavqu/Bayirqu)、同罗(Toηra)、思结(Siqir/ Siqar)
、巴也(野)古(Bayavqu/Bayirqu)、同罗(Toηra)、思结(Siqir/ Siqar) 、契苾、阿跌或
、契苾、阿跌或 跌(
跌( diz)。在各个不同的时代,至少还有另外四五个部落同样也属于这个联盟,这一点正如浦立本(Pullyblank)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数年之中,这个部落联盟的具体组成也发生过某种变化,但始终保持了九姓的基本结构
diz)。在各个不同的时代,至少还有另外四五个部落同样也属于这个联盟,这一点正如浦立本(Pullyblank)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数年之中,这个部落联盟的具体组成也发生过某种变化,但始终保持了九姓的基本结构 。
。
在汉籍中,当论述到629—630年的事件时,首次提到了“九姓”之名:当时突厥颉利可汗被中原人所击败,曾试图到大漠(戈壁)以北“九姓”部族中寻找避难栖身之处 。但是,在此之前,无论是在汉籍中,还是在其他史料中,从未提及过“九姓”或“九姓乌古斯”。这就表明,一直到那时为止,这一部族的存在时间尚不太长。事实上,许多汉文史料又不禁使人联想到,“九姓”确实是于7世纪初叶形成的。《唐书》卷217上,第1页在回纥传的开始部分,是这样论述的:“大业(605年)中,处罗可汗(指西突厥可汗,居住在伊犁河一带)攻胁铁勒部,裒责其财,既又恐其怨,则集渠豪数百悉坑之。韦纥(在隋代的对音是Uyrur)乃并仆骨(Boqut)、同罗(Toηra)、拔野古(Bayarqu)叛去,自为俟斤(irkin),称回纥(唐代前期的对音是Urrur)。”《旧唐书》(卷195,第1页)中相应的段落已由沙畹(《西突厥史料》第89页)和刘茂才(《关于东突厥史的汉文资料》,第350页)翻译发表。此外,我们还认为两唐书中的这些文献大部分都是对这类事件的概述,《隋书》(卷84,第8页)《铁勒传》对这些事件的记载更为详细:“大业元年(605年),突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
。但是,在此之前,无论是在汉籍中,还是在其他史料中,从未提及过“九姓”或“九姓乌古斯”。这就表明,一直到那时为止,这一部族的存在时间尚不太长。事实上,许多汉文史料又不禁使人联想到,“九姓”确实是于7世纪初叶形成的。《唐书》卷217上,第1页在回纥传的开始部分,是这样论述的:“大业(605年)中,处罗可汗(指西突厥可汗,居住在伊犁河一带)攻胁铁勒部,裒责其财,既又恐其怨,则集渠豪数百悉坑之。韦纥(在隋代的对音是Uyrur)乃并仆骨(Boqut)、同罗(Toηra)、拔野古(Bayarqu)叛去,自为俟斤(irkin),称回纥(唐代前期的对音是Urrur)。”《旧唐书》(卷195,第1页)中相应的段落已由沙畹(《西突厥史料》第89页)和刘茂才(《关于东突厥史的汉文资料》,第350页)翻译发表。此外,我们还认为两唐书中的这些文献大部分都是对这类事件的概述,《隋书》(卷84,第8页)《铁勒传》对这些事件的记载更为详细:“大业元年(605年),突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 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为变,遂集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由是一时反叛,拒处罗,遂立俟利发(Elt
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为变,遂集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由是一时反叛,拒处罗,遂立俟利发(Elt β
β r)
r) 俟斤(Irkin)契弊歌楞
俟斤(Irkin)契弊歌楞 为易勿真莫何(bara)
为易勿真莫何(bara) 可汗,居贪汗山
可汗,居贪汗山 。复立薛延陀内俟斤子
。复立薛延陀内俟斤子 也咥(Y
也咥(Y diz=
diz= diz,现行中华书局标点本为:“……内俟斤,字也咥”。——译者注),为小可汗。处罗可汗既败,莫何(Bara)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绝伦,甚得众心,为邻国所惮,伊吾(Xamil)、高昌(Qocˇo)、焉耆(Argi)诸国悉附之。”然而,时隔不久,从611年左右开始,由于东突厥人复又强大起来。薛延陀、契弊以及金山一带的铁勒诸部又重新归附了西突厥人,回纥人与另外5个仍居留于蒙古高地于都斤山林的部落,即拔也古(Bayarqu)、也咥(
diz,现行中华书局标点本为:“……内俟斤,字也咥”。——译者注),为小可汗。处罗可汗既败,莫何(Bara)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绝伦,甚得众心,为邻国所惮,伊吾(Xamil)、高昌(Qocˇo)、焉耆(Argi)诸国悉附之。”然而,时隔不久,从611年左右开始,由于东突厥人复又强大起来。薛延陀、契弊以及金山一带的铁勒诸部又重新归附了西突厥人,回纥人与另外5个仍居留于蒙古高地于都斤山林的部落,即拔也古(Bayarqu)、也咥( diz)、同罗(Toηra)、仆骨(Boqut)和巨霫也归附了东突厥人。到了628年左右,在西突厥人中发生了辄乱,薛延陀人便去投靠东突厥人。但由于东突厥人随后不久又衰弱了下来,薛延陀人于是再次很快转而反抗东突厥人,并将他们的大本营设置在于都斤山脚下。630年,在东突厥部落覆没之后,薛延陀人继续东迁,重返他们在独洛水以南的故地,并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都城。在630—645年这15年间,薛延陀人和回纥人共享对蒙古高地的控制权,尽管前者明显处于优势地位,但他们之间似乎仍是和睦相处的。然而,在646年,回纥人与汉人联合起来,从而结束了薛延陀人作为独立部落存在的地位,蒙古高地就落入了处于九姓部族之首的回纥人手中了
diz)、同罗(Toηra)、仆骨(Boqut)和巨霫也归附了东突厥人。到了628年左右,在西突厥人中发生了辄乱,薛延陀人便去投靠东突厥人。但由于东突厥人随后不久又衰弱了下来,薛延陀人于是再次很快转而反抗东突厥人,并将他们的大本营设置在于都斤山脚下。630年,在东突厥部落覆没之后,薛延陀人继续东迁,重返他们在独洛水以南的故地,并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都城。在630—645年这15年间,薛延陀人和回纥人共享对蒙古高地的控制权,尽管前者明显处于优势地位,但他们之间似乎仍是和睦相处的。然而,在646年,回纥人与汉人联合起来,从而结束了薛延陀人作为独立部落存在的地位,蒙古高地就落入了处于九姓部族之首的回纥人手中了 。
。
因此,我想根据汉文史料而概述一下:在600年之后不久,正值尖锐的冲突分裂突厥人之际,铁勒九部,其中确实也包括回纥、仆固、同罗、巴野古、浑、思结等生活在蒙古高原的诸部落又组成了九姓部落联盟(Toquz-Oru )。然而,如果认为这一部落联盟创立的时间不是600—605年间的话,那么肯定就是在628—630年间,继铁勒诸部叛变之后,东突厥汗国就土崩瓦解了。另外,丝毫不用怀疑,薛延陀和契弊人(还可能有也咥人)从一开始就是九姓部族的成员;我们甚至还可以认为,在铁勒两可汗定居于中国突厥斯坦以北的时候,这些部落也可能是在他们的主持下而同时组织了九姓联盟部族。
)。然而,如果认为这一部落联盟创立的时间不是600—605年间的话,那么肯定就是在628—630年间,继铁勒诸部叛变之后,东突厥汗国就土崩瓦解了。另外,丝毫不用怀疑,薛延陀和契弊人(还可能有也咥人)从一开始就是九姓部族的成员;我们甚至还可以认为,在铁勒两可汗定居于中国突厥斯坦以北的时候,这些部落也可能是在他们的主持下而同时组织了九姓联盟部族。
在随后一段期间,在720—740年左右用鲁尼文所写的突厥碑铭中,如果根据Oruz<Toquz-Oruz<Toquz-Oru 这种假设来理解,那就可以认为乌古斯一名在它所出现的各处均系指九姓部族。到了744年左右,九姓部中最强大的部落韦纥人结束了突厥人的统治,而又以“九姓”的名义建立了一个新汗国。在为九姓部汗国的登里罗没密施颉翳德密施毗伽回纥可汗(Qaghanruy ur T
这种假设来理解,那就可以认为乌古斯一名在它所出现的各处均系指九姓部族。到了744年左右,九姓部中最强大的部落韦纥人结束了突厥人的统治,而又以“九姓”的名义建立了一个新汗国。在为九姓部汗国的登里罗没密施颉翳德密施毗伽回纥可汗(Qaghanruy ur T ηrid
ηrid Bolmi
Bolmi El Etmi
El Etmi Bilg
Bilg ,747—759年)纪功而于760年左右撰写的西耐乌苏(
,747—759年)纪功而于760年左右撰写的西耐乌苏( ine-Usu)碑文中,我们在两处(东侧第1行和第3行,参阅:《在北蒙古发现的两块鲁尼文回鹘碑》,第16—19页)发现这样一个术语:S
ine-Usu)碑文中,我们在两处(东侧第1行和第3行,参阅:《在北蒙古发现的两块鲁尼文回鹘碑》,第16—19页)发现这样一个术语:S kiz orur,即“八姓”。但从前后文的联系中便可清楚地看到,“八姓”始终处于“九姓”的范畴之内,只是“八姓”中没有包括回鹘人。上文提到的那位回鹘可汗在汗国的创建者、其父去世后曾竭力企图建立自己对回鹘人的统治。从820年左右起,这一由回鹘人所统治的汗国在喀喇巴勒哈逊(Qara-Balgassun)的汉文碑(第1行和第5行)中称之为“九姓迴鹘”,这是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回鹘古都发现的一块石碑。同样,伊斯兰作家们从8世纪末起,也都普遍使用了Toquzruz这一术语
kiz orur,即“八姓”。但从前后文的联系中便可清楚地看到,“八姓”始终处于“九姓”的范畴之内,只是“八姓”中没有包括回鹘人。上文提到的那位回鹘可汗在汗国的创建者、其父去世后曾竭力企图建立自己对回鹘人的统治。从820年左右起,这一由回鹘人所统治的汗国在喀喇巴勒哈逊(Qara-Balgassun)的汉文碑(第1行和第5行)中称之为“九姓迴鹘”,这是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回鹘古都发现的一块石碑。同样,伊斯兰作家们从8世纪末起,也都普遍使用了Toquzruz这一术语 ,也就是原来的Toquz-Oruz,意为“九姓”,指由回鹘人创建的九姓汗国,该汗国的中心原来位于鄂尔浑河流域,在840年左右才西迁至天山地区的中国突厥斯坦。有关乌古斯(ruz或ruzz)的问题,据伊斯兰史料记载,这些操突厥语的部落在8世纪末年迁移到了巴尔喀什湖与里海之间的草原,而且是从最遥远的突厥领土的东部边界地区(也就是从九姓部族地区)迁来的
,也就是原来的Toquz-Oruz,意为“九姓”,指由回鹘人创建的九姓汗国,该汗国的中心原来位于鄂尔浑河流域,在840年左右才西迁至天山地区的中国突厥斯坦。有关乌古斯(ruz或ruzz)的问题,据伊斯兰史料记载,这些操突厥语的部落在8世纪末年迁移到了巴尔喀什湖与里海之间的草原,而且是从最遥远的突厥领土的东部边界地区(也就是从九姓部族地区)迁来的 。这里当然是指乌古斯部落,它也是九姓联盟部落的成员。当时九姓汗国正处于其全盛时期,他们的一个分支可能向更靠西部的地区扩张起来了,而那里长久以来也是由和他们一样同属于铁勒部的居民占据。
。这里当然是指乌古斯部落,它也是九姓联盟部落的成员。当时九姓汗国正处于其全盛时期,他们的一个分支可能向更靠西部的地区扩张起来了,而那里长久以来也是由和他们一样同属于铁勒部的居民占据。
现在,我们再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即公元600年左右的这一时间上来吧!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九姓部族所创建的时代。我们追溯过去,是为了寻求一些能说明在此之前曾存在过一个叫乌古斯民族的有力证据。当然,如果乌古斯存在于九姓乌古斯之前,那么后者明显就是由前者演变而来的。这样一来,我们对于Toquz-Oru >Toquz-Oruz>Oruz的假设,骤然间就变得不能成立了。
>Toquz-Oruz>Oruz的假设,骤然间就变得不能成立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汉文史料中的那些转写词,一般都把它们看作是Oruz一名的古例。V.汤姆森(Thomsen)在其于1896年发表的权威著作《鄂尔浑河流域碑铭解读》(第148页)中认为:“但是,我们在古代还发现过一个具有同一意义的汉文形式:乌纥或乌护。据我认为,此名并不相当于突厥文中的‘回鹘’(Ouigour),而是相当于Oruz,即ogouz之对音。”同在1896年,汉学家施古德(Gustav Schlegel)在《喀喇巴勒哈逊回鹘文和汉文碑铭考释》一书的第1页中,就明确地肯定:“袁纥部(üngir)也称为乌护。根据这一点,汤姆森十分正确地考证出了Oguz的名称。”从此之后一直至今,这种看法被一大批学者们原封不动地沿袭下来了,甚至一些最杰出的学者们也都持这种观点 。
。
许多人都参阅了《唐书》回鹘传(卷217上,第1页)的开篇部分,原文是这样的:“袁纥者,亦曰乌护,曰乌纥,至隋曰韦纥。”人们认为在拓跋族执政的北魏时代(386—558),“袁纥”就是后来的回鹘(Uyrur) ,正如此名在隋代的对音是“韦纥”一样。至于“乌护”和“乌纥”等形式,现代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它们是Oruz的对音。《唐书》是于11世纪中叶修成的,为此而辛苦工作的编纂者们明显是参照了于10世纪中叶撰写成书的《唐会要》(卷100,第5页)在结骨(Qirqiz=Kirghiz)传中所加入的一条注释:“今有改称纥扢斯者,亦是北夷旧号。臣按国史叙铁勒种类云。伊吾以西,焉耆以北,旁白山则有契弊、乌护、纥骨子。其契弊即契苾也;乌护则乌纥也,后为回鹘;其纥骨即纥扢斯也。由是而言,盖铁勒之种,曾以称迥鹘矣。”这是一句引自断代史的话,这条记述的作者认为,“纥骨”是Qirqiz(结骨)的一种古老的对音,甚至与他那个时代的最新转写法“纥扢斯”相似。这一点出自于我们上文所引证的铁勒传,在《隋书》和略有所异的《北史》中,都载有该部族的传记。这两部汉籍都是于630年左右写成的,但我们不知这两部著作中的这段文献究竟是谁抄袭谁的。
,正如此名在隋代的对音是“韦纥”一样。至于“乌护”和“乌纥”等形式,现代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它们是Oruz的对音。《唐书》是于11世纪中叶修成的,为此而辛苦工作的编纂者们明显是参照了于10世纪中叶撰写成书的《唐会要》(卷100,第5页)在结骨(Qirqiz=Kirghiz)传中所加入的一条注释:“今有改称纥扢斯者,亦是北夷旧号。臣按国史叙铁勒种类云。伊吾以西,焉耆以北,旁白山则有契弊、乌护、纥骨子。其契弊即契苾也;乌护则乌纥也,后为回鹘;其纥骨即纥扢斯也。由是而言,盖铁勒之种,曾以称迥鹘矣。”这是一句引自断代史的话,这条记述的作者认为,“纥骨”是Qirqiz(结骨)的一种古老的对音,甚至与他那个时代的最新转写法“纥扢斯”相似。这一点出自于我们上文所引证的铁勒传,在《隋书》和略有所异的《北史》中,都载有该部族的传记。这两部汉籍都是于630年左右写成的,但我们不知这两部著作中的这段文献究竟是谁抄袭谁的。
《唐会要》中企图把“乌护”考证成“回鹘”这一点肯定是丝毫不足为信的,尤其是由于在同一传记的上文业已将回鹘考证成了“韦纥”了。至于把“乌护”考证成Oruz的问题,这是由现代东方学家们所提出的建议。但鉴于下述原因,我认为这种考证似乎是很值得商榷的:(一)现在丝毫尚未证明应该将铁勒诸部落之名称的转写词名单分割开来,而其中的大部分名称都是未经考定的。正如《唐会要》的编辑者曾试图将“纥骨”单独提出来进行考证一样。他认为“纥骨”就相当6世纪的古名“纥扢斯”。但在作者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即10世纪时的对音则是Qirqiz或Xirxiz。另外,尽管《唐书》(卷217下,第7页)在黠戛斯传的开始部分是这样记载的。但据我所知,黠戛斯部不是铁勒的一部分,而且在6—7世纪时也并不居住在天山地区,因为《唐书》的记载明显仍是受到了《唐会要》的影响。(二)虽然《北史》中也写作“乌护”,但《隋书》中却写作“乌灌”,这后一个名字与“乌桓”和“乌丸”等对音名称很相似,它是汉代与三国时代一个很著名民族的名称,在10世纪时还存在有他们的一些残余势力 。尽管人们一般都把“乌桓”族的位置确定在东蒙古地区,但也并不完全排除有一些由这一集团分化出来的部落于6世纪时就已经居住在天山地区了。(三)“乌护”实际上是uru或oru的对音,所以它可能是对oruz的一种不完整的转写法。此外,我们还可以认为“乌护”的原形也可能是orul、oru
。尽管人们一般都把“乌桓”族的位置确定在东蒙古地区,但也并不完全排除有一些由这一集团分化出来的部落于6世纪时就已经居住在天山地区了。(三)“乌护”实际上是uru或oru的对音,所以它可能是对oruz的一种不完整的转写法。此外,我们还可以认为“乌护”的原形也可能是orul、oru 、orur等等。
、orur等等。
《唐会要》的编纂者声称“乌纥”是“回鹘”(Uyrur)的古老写法(作者原意更可能是指“迥纥”,这是唐代初期对Uyrur的正式转写名称)。实际上,“乌纥”是回纥可汗吐迷度侄子的名字,他于648年残害了吐迷度 。无论“乌护”是否是Oruz的对音,它丝毫无碍于Oruz<Toquz-Oruz这一假设。因为在648年间,九姓部族已经具有相当悠久的存在历史了。但我坚信,它实际上是orul的对音。Orul的第一个词义就是“一位后代”,但古突厥人却把它当作一种很高的官职名称使用,很可能是由那些具有血缘关系,但并非直系亲属的王族成员享有,正如晚期金帐汗国里的斡兰人(Ulan<突厥语Orlan,复数形式为Orul)一样
。无论“乌护”是否是Oruz的对音,它丝毫无碍于Oruz<Toquz-Oruz这一假设。因为在648年间,九姓部族已经具有相当悠久的存在历史了。但我坚信,它实际上是orul的对音。Orul的第一个词义就是“一位后代”,但古突厥人却把它当作一种很高的官职名称使用,很可能是由那些具有血缘关系,但并非直系亲属的王族成员享有,正如晚期金帐汗国里的斡兰人(Ulan<突厥语Orlan,复数形式为Orul)一样 。另外,我还在《册府元龟》(卷971,第8~9页;卷975,第9~17页)的729—738年以下,发现了一个非常相同的转写名词,这是突厥等民族遣使唐天朝宫廷一位使节的名字:“乌鹘达干”,其原形很可能就相当于Orul、Tarqan,731年参加阙特勒(K
。另外,我还在《册府元龟》(卷971,第8~9页;卷975,第9~17页)的729—738年以下,发现了一个非常相同的转写名词,这是突厥等民族遣使唐天朝宫廷一位使节的名字:“乌鹘达干”,其原形很可能就相当于Orul、Tarqan,731年参加阙特勒(K l tegin)葬礼的一位使节也享有这一尊号
l tegin)葬礼的一位使节也享有这一尊号 。
。
过去曾有人企图把乌护考订成两个互相独立而又同时存在的民族,汉籍在公元前数世纪中就已经对他们有所记载了。这就是栖身于蒙古以西的呼揭人或乌揭人、散居在蒙古以东的乌桓或乌丸人 。更具体地说就是,据内梅特先生分析,“呼揭”和“乌揭”就相当于Orur的对音,也有人认为Orur的另一种写法就是Oruz。然而,如果这两个民族的古代对音确实是Orur的话(这一点尚有待继续考订),那么这些形式也可以用来转写Uyrur
。更具体地说就是,据内梅特先生分析,“呼揭”和“乌揭”就相当于Orur的对音,也有人认为Orur的另一种写法就是Oruz。然而,如果这两个民族的古代对音确实是Orur的话(这一点尚有待继续考订),那么这些形式也可以用来转写Uyrur 。事实上,为了标注uy-这一音节,古典汉语中似乎没有比O或xo更为适宜的音节。因为古汉语中以-i结尾的字,如“韦”和“回”等,在中世纪都用来标注uyrur中的uy-,而据高本汉(karlgren)的分析
。事实上,为了标注uy-这一音节,古典汉语中似乎没有比O或xo更为适宜的音节。因为古汉语中以-i结尾的字,如“韦”和“回”等,在中世纪都用来标注uyrur中的uy-,而据高本汉(karlgren)的分析 ,在古汉语中还有一些尾辅音:giw藜r,g’w藜r等等。但是,据我认为,如果尚未彻底了解中国古代的汉字发音和拼写习惯,甚至还不了解这些转写字当时的发音,就企图考订包括这些字在内的许多当时的转写字,那将是十分冒险的。
,在古汉语中还有一些尾辅音:giw藜r,g’w藜r等等。但是,据我认为,如果尚未彻底了解中国古代的汉字发音和拼写习惯,甚至还不了解这些转写字当时的发音,就企图考订包括这些字在内的许多当时的转写字,那将是十分冒险的。
现在我再来研究一下拜占庭文献。我们在其中5—7世纪的史料中发现了有关Oruz的一些翔实的资料,但始终都是以其所谓的俗体字Orur为代表的。尤其是指一些部落名词:Ughur、Oghor、Uighur、Uighor等等,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词的前面都附有On-或Un-等前缀,肯定是代表着古突厥词中的on,即“十”的意思,如On-Oghur、On-Ughur、On-Oghor、Un-Ighur、Un-Ighor、Un-Ughur、Unn-Ughur等等 。下面我们就扼要地分析一下有关这些部族的拜占庭资料。
。下面我们就扼要地分析一下有关这些部族的拜占庭资料。
一
在461—465年间,萨拉胡尔(Sararur)、回鹘(Oror)和十姓回鹘(On-Oghur)人首次向拜占庭遣使。这些民族是前不久从东方迁移而来的,而且是由萨毗人(Saβir)人将他们从故乡赶出来的,而后者又被阿拔人(Aβar)人所驱逐,阿拔人又被居住在大洋两岸的人所胁迫而迁徙。萨拉胡儿人是为了在匈奴阿卡齐尔人(Huns Akatizir)人中寻求一块立足之地,才到这里来的,而且成功地制服了他们 。
。
——萨拉胡尔(Sararur)一词在叙利亚文中为Sārūrgūr,可能应该分解为sarir(黄色的、白色的)+(U/O/Ui/i)rur,我们上文已经提到了此名的各种形式 。此名可能指的是另外一个民族,而并不是指“黄回纥”人(Sari-Uyghur),黄回纥人从11世纪至今一直居住在中国的西北边疆
。此名可能指的是另外一个民族,而并不是指“黄回纥”人(Sari-Uyghur),黄回纥人从11世纪至今一直居住在中国的西北边疆 。而萨拉胡尔人仅仅在461—550年间左右于拜占庭史料中出现过。
。而萨拉胡尔人仅仅在461—550年间左右于拜占庭史料中出现过。
——人们一般也都把Uror这种形式当作是Ughor的一种误写,也就是指同一个回鹘(Ughur/Oghor/Uighur)部族。
——在萨毗人被阿拔人驱逐之前,他们似乎居住在额尔齐斯河(Irti )流域,至少是居住在阿尔泰山和乌拉尔山之间的西西伯利亚的某处
)流域,至少是居住在阿尔泰山和乌拉尔山之间的西西伯利亚的某处 。
。
——至于阿拔人,从一切迹象来看,他们似乎就是汉人所说的蠕蝡(蠕蠕)人 ,而且当然也是“居住在大洋两岸的人”。事实上,在458—459年左右,由拓跋族皇帝统率的一支强大的北魏军队穿越中国北部的沙漠大碛,并且击溃了蠕蠕人。蠕蠕人中有数千名归降了汉人,但大部分都逃向了北部更远的地方(参阅《魏书》,卷103,第3页)。
,而且当然也是“居住在大洋两岸的人”。事实上,在458—459年左右,由拓跋族皇帝统率的一支强大的北魏军队穿越中国北部的沙漠大碛,并且击溃了蠕蠕人。蠕蠕人中有数千名归降了汉人,但大部分都逃向了北部更远的地方(参阅《魏书》,卷103,第3页)。
——拜占庭史料中在448年首次提到阿卡齐尔人(Akatzir、Akatir、Katzir、Agazir),而且还认为这是一些居住在黑海以北、亚速海附近的部落,他们是阿提拉匈奴人(Huns d'Attila)的盟友。在466年之后的史料中,就不再提及这些民族了。因为在这一年,他们为远征波斯而途经高加索大道的时候,受到了萨拉胡尔人的攻击 。但是,据我认为,拜占庭史料中的阿卡齐尔人实际上几乎肯定就是白哈兹尔(Aq-Qaz
。但是,据我认为,拜占庭史料中的阿卡齐尔人实际上几乎肯定就是白哈兹尔(Aq-Qaz r)人,很可能是指可萨突厥人(Khazar)的先祖,至少是部分可萨突厥人的先祖。从后一个世纪开始,曾有大量史料记载过该地区的这个民族
r)人,很可能是指可萨突厥人(Khazar)的先祖,至少是部分可萨突厥人的先祖。从后一个世纪开始,曾有大量史料记载过该地区的这个民族 。
。
由此看来,中国中原人于458—459年在戈壁沙漠之外对蠕蠕或阿拔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不但把蠕蠕人驱逐到了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而且还导致了许多游牧部落由东至西在西域地区大规模地迁徙。在此之后,萨拉胡尔人、回鹘人和十姓回鹘人等部落(他们明显具有亲缘关系)便到达了高加索以北地区。我们根据拜占庭史料便可以联想到,这些部落都居住在西西伯利亚的萨毗人以西,此地也可能是他们从遥远的东方迁徙之后到达的倒数第二站,而拜占庭人仅仅知道这一站。
二
一方面,据若尔达纳(Jordanes)在551年和阿加蒂亚(Agathias)于552年左右所记载,十姓回鹘人在6世纪的前半叶,居住在高加索以北地区 。另一方面,569年的一部古叙利亚文著作提到这个名称,并肯定是ūn·gūr的同义词,那就只剩下10个了,而这10个部落即使不是归降了十姓回鹘人,至少也是同他们有所联系。十姓回鹘人共包括以下诸部:“ūg(u)r、Sab(i)r、Būrg(a)r(Bulgar)、Kūrtrg(u)r(=Kuturgur)、Ab(a)r、Kas·r、Dirm·r、Sarūrgūr、Bāgrsiq、Kūls、Abd·L、Ept(a)lit
。另一方面,569年的一部古叙利亚文著作提到这个名称,并肯定是ūn·gūr的同义词,那就只剩下10个了,而这10个部落即使不是归降了十姓回鹘人,至少也是同他们有所联系。十姓回鹘人共包括以下诸部:“ūg(u)r、Sab(i)r、Būrg(a)r(Bulgar)、Kūrtrg(u)r(=Kuturgur)、Ab(a)r、Kas·r、Dirm·r、Sarūrgūr、Bāgrsiq、Kūls、Abd·L、Ept(a)lit 。
。
——萨毗人至少从6世纪初起就居住在高加索地区了,他们可能是继回鹘人之后而到达这一地区的,并于460年左右将后者从南西伯利亚地区驱逐了出去。从一切迹象来看,在6世纪时,萨毗人,可能还有厌口哒人[Ept(a)lit]与十姓回鹘人,即使不是处于联盟状态,至少也是友好和睦地相处的。后者居住在里海沿岸。参阅塞诺尔(Denis Sinor):《论5世纪初的一次民族大迁徙》(载《亚细亚学报》,1947年,第235卷,见第19页;《拜占庭突厥史料汇编》,第1卷,第68页)。
——拜占庭史料于480年首次提到了不里阿耳(Bulghar)部族,即在十姓回鹘人到达西部地区之后不久。在此之后,拜占庭史料中就经常提及这个民族,他们居住在拜占庭的北部边境,从高加索一直到达多瑙河,甚至还散居在更远的地方。在7世纪初,他们在黑海以北建立了一个叫作“大不里阿耳”(La grande Bulgarie)的国家,并且似乎还与十姓回鹘人建立了联盟(参阅《拜占庭突厥史料汇编》第1卷,第108页)。
——据拜占庭史料记载,库图尔古尔(Kuturghur/Kutrighur/ Kotraghur)部族与乌图尔古尔(Uturghur/Utrighur/Utighur/Utigher)部族具有亲缘关系。在6世纪初,这两个部族分别居住在顿河的东西两岸。另外,在6世纪前后这一漫长的期间内,这两个部族都不同程度地与居住在高加索和黑海以北疆土中的十姓回鹘人结盟。在7世纪时,人们认为库图尔胡尔人曾是同一地区大不里阿耳国的一部分(参阅《拜占庭突厥史料汇编》第1卷,第66页、第2卷中Kutrighur和Utighur等条目;《十姓回鹘人的历史》,载《匈牙利年鉴》第10卷,1930年,见第75~80页)。
——阿拔人于558年首次入侵高加索地区,与奄蔡(Alan)人为毗邻。在稍后不久,他们可能又取得了对Un-Ighur人、Zal(?)人和萨毗人的胜利 。阿拔人突然间在西方出现,紧接着在551—555年间,突厥人和汉人又摧毁了柔然(即蠕蠕)人的王国,这又是一条将阿拔人考订为柔然人的理由
。阿拔人突然间在西方出现,紧接着在551—555年间,突厥人和汉人又摧毁了柔然(即蠕蠕)人的王国,这又是一条将阿拔人考订为柔然人的理由 。然而,西莫加特(TheophylaktosSimokattes)于630年介绍阿拔人于558年到达高加索地区的情况时说,这都是一些“所谓的阿拔人”,实际上是指两个部落瓦尔人(Uar和Xun),他们在突厥人的打击下溃散了,而且还属于回鹘集团,他们的住地在稍靠东部一些的地方
。然而,西莫加特(TheophylaktosSimokattes)于630年介绍阿拔人于558年到达高加索地区的情况时说,这都是一些“所谓的阿拔人”,实际上是指两个部落瓦尔人(Uar和Xun),他们在突厥人的打击下溃散了,而且还属于回鹘集团,他们的住地在稍靠东部一些的地方 。无论人们是否真正相信这个“所谓的阿拔人”的奇怪故事,因为其中似乎有一些误会。但我们总应该认真地对待有关瓦尔部落的资料,瓦尔很像是阿拔人的一种变形词,而Xun既像是指匈奴人,又像是指铁勒九姓之一的浑人,他们都曾是回鹘人的东部集团。他们在突厥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也四散逃窜开了。事实上,由汉文史料便可以看出,阿拔人、浑族人以及回纥人在6世纪时都属于铁勒部落联盟,他们与突厥人是互相敌对的。
。无论人们是否真正相信这个“所谓的阿拔人”的奇怪故事,因为其中似乎有一些误会。但我们总应该认真地对待有关瓦尔部落的资料,瓦尔很像是阿拔人的一种变形词,而Xun既像是指匈奴人,又像是指铁勒九姓之一的浑人,他们都曾是回鹘人的东部集团。他们在突厥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也四散逃窜开了。事实上,由汉文史料便可以看出,阿拔人、浑族人以及回纥人在6世纪时都属于铁勒部落联盟,他们与突厥人是互相敌对的。
——可萨突厥人(Khazars)从625年起就出现在拜占庭史料中了,而且还是作为拜占庭人在高加索地区对抗波斯人的盟友而出现的。人们一般都称之为“东突厥人”,这可能是取其一般性意义,即由东方起源的突厥人,而并不一定是指东突厥部落联盟的成员。无论如何,他们也在西部取代了西突厥人,并且在7世纪中叶大大地扩大了其汗国的疆域,从高加索起,一直到达不里阿耳人、十姓回鹘人和库图尔古尔人的领土(请参阅《拜占庭突厥史料汇编》,第1卷,第81、82和534页;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52~256页)。
——对于Dirm·r、Bāgrsiq、Kūls和Abd·I这四个民族的名称,我们暂且不予研究,因为对它们的考订尚有待进行。
三
在569年,回纥人还居住在高加索以北和伏尔加河以西,已经归附了突厥可汗,这是拜占庭使节泽玛尔索斯(Zemarchos)的报告,他从突厥王廷归国途中曾经穿越过这一地区 。另外,在576年,突厥可汗向拜占庭使节瓦朗底诺斯(Valentinos)宣布,他已经征服了Un-Ighur人
。另外,在576年,突厥可汗向拜占庭使节瓦朗底诺斯(Valentinos)宣布,他已经征服了Un-Ighur人 。最后,西莫加特于598年收到了突厥可汗的一封信,可汗在信中介绍了他个人及其先任者们的胜利。西莫加特针对此而写道:“可汗开始了另外一项事业(首先战胜了阿拔人,即柔然人),柔然人逃向了桃花石人(Taughast,Tabghac,指中国中原地区)和莫克利(Moukri,指高丽),最后又征服了Og觝r人(指回纥人);由于这后一个民族人数众多和善于征战,所以就名居最强大的民族之列;他们居住在更靠东部一些的地方。提尔河(Til)就流经那里,突厥人一直称此河为黑水,该民族中最为古老的首领名叫瓦尔(Ouar)和库尼(Khounni);那些叫作瓦尔和库尼的民族即由此而来
。最后,西莫加特于598年收到了突厥可汗的一封信,可汗在信中介绍了他个人及其先任者们的胜利。西莫加特针对此而写道:“可汗开始了另外一项事业(首先战胜了阿拔人,即柔然人),柔然人逃向了桃花石人(Taughast,Tabghac,指中国中原地区)和莫克利(Moukri,指高丽),最后又征服了Og觝r人(指回纥人);由于这后一个民族人数众多和善于征战,所以就名居最强大的民族之列;他们居住在更靠东部一些的地方。提尔河(Til)就流经那里,突厥人一直称此河为黑水,该民族中最为古老的首领名叫瓦尔(Ouar)和库尼(Khounni);那些叫作瓦尔和库尼的民族即由此而来 。
。
——从这些文献中就可以看到,一方面,Ughru、Ogohr和Un-Ighur等形式均系指同一个民族。另外,这个人数众多的民族居住在更靠近东部的地方,其中有一部分居住在高加索以北。
四
十姓回鹘人可能是于7世纪初在亚速海沿岸创建的大不里阿耳国的主要成员 。在7世纪中叶,当这一地区被可萨突厥人征服之后,十姓回鹘人的一部分伙同一部分不里阿耳人逃向了西方,这两个民族在那里联合起来而形成了多瑙河流域的不里阿耳人
。在7世纪中叶,当这一地区被可萨突厥人征服之后,十姓回鹘人的一部分伙同一部分不里阿耳人逃向了西方,这两个民族在那里联合起来而形成了多瑙河流域的不里阿耳人 。其他的十姓回鹘人肯定继续留在了亚速海附近的可萨突厥人地区,那里同样也有一些不里阿耳人,因为8世纪时的一部宗教性著作提到了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个十姓回鹘人的主教管辖区
。其他的十姓回鹘人肯定继续留在了亚速海附近的可萨突厥人地区,那里同样也有一些不里阿耳人,因为8世纪时的一部宗教性著作提到了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个十姓回鹘人的主教管辖区 。停留在黑海以北的十姓回鹘人可能后来成了组成匈牙利民族的一种因素,匈牙利民族是从9世纪开始在这一地区出现的。匈牙利民族的现代名称Hongrois也就是由Ugri或Ungar演变而来的;欧洲人最早接触他们时称之为马扎尔人(Magyars),原来也是由十姓回鹘人(On-Orur)发展而来的
。停留在黑海以北的十姓回鹘人可能后来成了组成匈牙利民族的一种因素,匈牙利民族是从9世纪开始在这一地区出现的。匈牙利民族的现代名称Hongrois也就是由Ugri或Ungar演变而来的;欧洲人最早接触他们时称之为马扎尔人(Magyars),原来也是由十姓回鹘人(On-Orur)发展而来的 。无论如何,据拜占庭史料记载,在8世纪初叶之后,十姓回鹘人就不再见诸史料记载了
。无论如何,据拜占庭史料记载,在8世纪初叶之后,十姓回鹘人就不再见诸史料记载了 。
。
为了探讨拜占庭史料中的Ughur/Oghnr/Uighur/Ighur这些书写形式,究竟代表着哪一个民族。直到现在为止,这一问题主要是由芬兰—乌戈尔学家及其研究匈牙利民族起源的人们所推动。事实上,从19世纪起,人们就试图利用十姓回鹘来解释匈牙利人的名称。顺便提一下,其词源始终不太清楚;时至今日,有关Oghur的起源问题,以及人们所推测的他们与匈牙利先祖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各种猜测輪輯。所以,学者们从一开始就一致承认Oghur是Oghuz的一种颤音化的形式,后者当然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名称,基本上是指古突厥人 。这种颤音化的做法,即由-z而变成-r的过程,可能为古突厥语中的一种习惯;如同近代楚瓦什语(ˇcuva
。这种颤音化的做法,即由-z而变成-r的过程,可能为古突厥语中的一种习惯;如同近代楚瓦什语(ˇcuva )中那种越出常规的形式一样,它是伏尔加河上游(那里的纬度与莫斯科差不多)地区的一种小小的突厥方言。人们在引用颤音化方言的例证时,往往要提到楚瓦什人的祖先,尤其是古老的不里阿耳人和可萨突厥人。操这种语言的突厥人在7世纪左右,与十姓回鹘人有着一定程度的结盟关系,他们居住在黑海和高加索以北地区
)中那种越出常规的形式一样,它是伏尔加河上游(那里的纬度与莫斯科差不多)地区的一种小小的突厥方言。人们在引用颤音化方言的例证时,往往要提到楚瓦什人的祖先,尤其是古老的不里阿耳人和可萨突厥人。操这种语言的突厥人在7世纪左右,与十姓回鹘人有着一定程度的结盟关系,他们居住在黑海和高加索以北地区 。有关颤音化的突厥语文献,至今只残留下了一些8世纪末和9世纪初的墓志铭,它们恰恰是来自伏尔加河上游的楚瓦什人中
。有关颤音化的突厥语文献,至今只残留下了一些8世纪末和9世纪初的墓志铭,它们恰恰是来自伏尔加河上游的楚瓦什人中 。更何况,除了拜占庭史料中所出现的例证之外,人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未曾发现过Oghuz的变形字Oghur。所以,如果把拜占庭史料中出现的Ughur/ Oghur/Uighur/Ighur这一系列形式,考证为所谓的Oghuz的另一种变体字Oghur,归根结蒂,其根据也仅仅是这些形式与Oghuz之间的部分相似而已。只要我们尚没有找到5世纪左右Oghuz在口语中具有颤音化特点的可靠标志,那就不应该过分重视这种猜测。
。更何况,除了拜占庭史料中所出现的例证之外,人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未曾发现过Oghuz的变形字Oghur。所以,如果把拜占庭史料中出现的Ughur/ Oghur/Uighur/Ighur这一系列形式,考证为所谓的Oghuz的另一种变体字Oghur,归根结蒂,其根据也仅仅是这些形式与Oghuz之间的部分相似而已。只要我们尚没有找到5世纪左右Oghuz在口语中具有颤音化特点的可靠标志,那就不应该过分重视这种猜测。
然而,还有另外一个民族名称更会使人联想到上述十姓回鹘人,此字就是(On)Ughyur。从1891年起,拉德洛夫在浏览有关回鹘人的各种古代史料(包括拜占庭史料)时,就毫不犹豫地作了如此之考证。这一论点就作为导论而写在其《福乐智慧》(Kudatku Bilik)译注本的开头部分了(第1卷,转写文卷72—76)。1898年,马夸特也按照拉德洛夫的思路进行考证,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 。同样,沙畹在《西突厥史料》第247和251页中也同意这种观点。1900年,李默德(Grenard)曾经指出:“拜占庭的作家们在5世纪(普利斯古斯,Priscus)和6世纪时(梅南特,Ménander)就已经知道了On Ouigour(十姓回鹘,回纥人的两大部分之一,另一部分为九姓回鹘,即Tokouz Ouigour)、Utiger[据拉施特(Réch
。同样,沙畹在《西突厥史料》第247和251页中也同意这种观点。1900年,李默德(Grenard)曾经指出:“拜占庭的作家们在5世纪(普利斯古斯,Priscus)和6世纪时(梅南特,Ménander)就已经知道了On Ouigour(十姓回鹘,回纥人的两大部分之一,另一部分为九姓回鹘,即Tokouz Ouigour)、Utiger[据拉施特(Réch d-oud-din)的看法,这是十姓回鹘之一]和撒里黑回鹘(Sarygh Ouigour,稍后不久,人们曾在库库诺尔湖以西发现过他们的一些部落)……”
d-oud-din)的看法,这是十姓回鹘之一]和撒里黑回鹘(Sarygh Ouigour,稍后不久,人们曾在库库诺尔湖以西发现过他们的一些部落)……”
有关这些词的对音问题,在梅南特罗斯(Menandros)的两卷手抄稿中,确实是曾出现过Uighur和Uighor这两种形式。然而,如果这两种写法是由于抄写员的疏忽而造成的,即其原形本来应该是Unighur和Unighor的话 ,为了解释拜占庭人用(On-)Ughur/Oghur/Ighur来标注(On-)-Uyghur这一音组,那还必须提及另一事实,即在拜占庭时代的希腊语中,尚没有uy这一音素。由此看来,拜占庭人在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翻译十姓回鹘或回鹘人的时候,可能有时就使用u/o,而有时又使用i,以用来代表突厥语中的二合元音uy,而且他们的耳朵也非常不习惯听这种发音。
,为了解释拜占庭人用(On-)Ughur/Oghur/Ighur来标注(On-)-Uyghur这一音组,那还必须提及另一事实,即在拜占庭时代的希腊语中,尚没有uy这一音素。由此看来,拜占庭人在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翻译十姓回鹘或回鹘人的时候,可能有时就使用u/o,而有时又使用i,以用来代表突厥语中的二合元音uy,而且他们的耳朵也非常不习惯听这种发音。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份量的补充原因,可以推动我们解决On-Uyghur的问题:虽然On-Oghur=On-Oghuz仅仅属于一种猜测,但十姓回鹘确实是存在的,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在古代史料中,十姓回鹘人这一名称确实是出现过,尤其是在下面一些史料中更为明显:
1.在“西耐乌苏碑”的开头部分,就写有十姓回鹘人。西耐乌苏碑也是至今人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回鹘可汗碑。这通用鲁尼文撰写的古突厥碑铭,是由兰司铁于1909年在西耐乌苏的一个小湖旁边发现的。那里位于鄂尔浑河与色楞格河之间,碑文刻写的时间大概是760年左右,其内容是为了纪念回鹘汗国的一位重要可汗执政年间的事迹,这就是登里逻没密施颉翳德密施毗伽(T ηrid
ηrid Bolmi
Bolmi El Etmi
El Etmi Bilg
Bilg ,747—759年)。在论述该可汗的生平之前(该可汗的政治生涯是于730—740年左右开始的),碑文在最前几行中追述了回鹘民族最古老的历史。尤其是在北侧第3行中是这样记载的:suβght(?)nda q(a)Lm(i)
,747—759年)。在论述该可汗的生平之前(该可汗的政治生涯是于730—740年左右开始的),碑文在最前几行中追述了回鹘民族最古老的历史。尤其是在北侧第3行中是这样记载的:suβght(?)nda q(a)Lm(i) ibod(u)n onuyghur toq(u)züz
ibod(u)n onuyghur toq(u)züz yüz yil ol(u)rup……解读出来便是:“十姓回鹘人,(包括)……民族,他们居住在(色楞格)河地区(?),曾在100年前统治了九姓部族,而且……”
yüz yil ol(u)rup……解读出来便是:“十姓回鹘人,(包括)……民族,他们居住在(色楞格)河地区(?),曾在100年前统治了九姓部族,而且……” 因而,在760年左右撰写此碑的时候,十姓回鹘联盟已经有百年之余的历史了,此文献起码可以证明十姓回鹘人至少在7世纪中叶就已经存在了。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来假设,碑文中所暗示的十姓回鹘人统治的百年历史可能是从7世纪中叶开始的。总而言之(最后几年除外),这是回鹘人崛起和突厥人衰落的时代。事实上,十姓回鹘人对九姓部族的统治权建立之后,紧接着便是铁勒部族政治联盟的形成,该联盟是于公元600年左右开始的,当时这些部落正在纷纷揭竿而起地反叛突厥人。另外,由此文献来看,这里所指的十姓回鹘人仅仅是指那些停居在色楞格河(或者是该地区的另一条河)一带的部落,而该民族的另一部分可能已经离开了该地区。这里是否在暗示460年前后十姓回鹘人(On-Oghur=On-uyghur)向西部的迁徙呢?
因而,在760年左右撰写此碑的时候,十姓回鹘联盟已经有百年之余的历史了,此文献起码可以证明十姓回鹘人至少在7世纪中叶就已经存在了。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来假设,碑文中所暗示的十姓回鹘人统治的百年历史可能是从7世纪中叶开始的。总而言之(最后几年除外),这是回鹘人崛起和突厥人衰落的时代。事实上,十姓回鹘人对九姓部族的统治权建立之后,紧接着便是铁勒部族政治联盟的形成,该联盟是于公元600年左右开始的,当时这些部落正在纷纷揭竿而起地反叛突厥人。另外,由此文献来看,这里所指的十姓回鹘人仅仅是指那些停居在色楞格河(或者是该地区的另一条河)一带的部落,而该民族的另一部分可能已经离开了该地区。这里是否在暗示460年前后十姓回鹘人(On-Oghur=On-uyghur)向西部的迁徙呢?
2.在高昌(Qoˇco)发现的一卷摩尼教经文残卷中,也出现过十姓回鹘这一名词 ,高昌从8世纪末年起就是回鹘人的一个聚落中心。提到该民族的那一残叶文书可能是从摩尼教经书中脱落下来的,其时间很可能是9世纪或10世纪,其中还特别包括有一段用回鹘—龟兹两种语言所写的文献。该经文在跋尾中有一行文字阐述了施主在令人抄写经文时所积累的宗教功德:……ta
,高昌从8世纪末年起就是回鹘人的一个聚落中心。提到该民族的那一残叶文书可能是从摩尼教经书中脱落下来的,其时间很可能是9世纪或10世纪,其中还特别包括有一段用回鹘—龟兹两种语言所写的文献。该经文在跋尾中有一行文字阐述了施主在令人抄写经文时所积累的宗教功德:……ta ddin singar alqatmi
ddin singar alqatmi idduq on uy ur elint
idduq on uy ur elint ,解读出来便是:“在外部(指世俗者,与教徒是相对立的,而教徒一般都指“内部”),在十姓回鹘人这一光荣的和神圣的汗国之内……”。这篇文献证明,对于回鹘人来说,无论是7—8世纪鄂尔浑河流域的回鹘人,还是9—10世纪的高昌回鹘人,其名字的全称应该是“十姓回鹘人”,尤其是在强调其政治面貌的时候更为如此。
,解读出来便是:“在外部(指世俗者,与教徒是相对立的,而教徒一般都指“内部”),在十姓回鹘人这一光荣的和神圣的汗国之内……”。这篇文献证明,对于回鹘人来说,无论是7—8世纪鄂尔浑河流域的回鹘人,还是9—10世纪的高昌回鹘人,其名字的全称应该是“十姓回鹘人”,尤其是在强调其政治面貌的时候更为如此。
3.在公元1300年左右,拉施特也曾有一次提到过十姓回鹘人,作者根据回鹘人自己的史料而概述了他们的古代史 。作者写道,在作为回鹘人发祥之地的蒙古高原,一侧有10条河流,另一侧则有9条,住在10条河附近的回鹘人就叫作十姓回鹘;而住在9条河畔的回鹘人则称为九姓回鹘人(Toquz-Uyghuz)。拉施特再没有提到过九姓回鹘人,其原因很可能是他误将此写作Toquz-ōghuz(即九姓乌古斯)了。在阿拉伯文中,这两个名称特别容易混淆
。作者写道,在作为回鹘人发祥之地的蒙古高原,一侧有10条河流,另一侧则有9条,住在10条河附近的回鹘人就叫作十姓回鹘;而住在9条河畔的回鹘人则称为九姓回鹘人(Toquz-Uyghuz)。拉施特再没有提到过九姓回鹘人,其原因很可能是他误将此写作Toquz-ōghuz(即九姓乌古斯)了。在阿拉伯文中,这两个名称特别容易混淆 。拉施特还具体解释说,这十条河又叫作On-Orqun(即“十鄂尔浑河”),其名称分别为:I
。拉施特还具体解释说,这十条河又叫作On-Orqun(即“十鄂尔浑河”),其名称分别为:I g(i)l、ūtig(
g(i)l、ūtig( )r、Bōqr/Tōqír、ōrq(u)nd(u)r、Tūlār/Tülü、Bādār/Tārdār、Adr/Awr、ūˇc-Tābin/Bāyin、Q(a)mlān u和ōtitān。我们从该文献的下文可以看出,I
)r、Bōqr/Tōqír、ōrq(u)nd(u)r、Tūlār/Tülü、Bādār/Tārdār、Adr/Awr、ūˇc-Tābin/Bāyin、Q(a)mlān u和ōtitān。我们从该文献的下文可以看出,I gil和ōrqundur同时又是部族的名称,这一名单中的大部分名称也都如此,只有Qamlān u(忽木阑术)和ōtikan(=ōtük
gil和ōrqundur同时又是部族的名称,这一名单中的大部分名称也都如此,只有Qamlān u(忽木阑术)和ōtikan(=ōtük n,即于都斤山)例外,那里分别由王族(ōng)人和Q·h·n-Ati人居住。大部分部族原来只服从于他们的小首领,直到他们感到必须有和谐的配合为止。在思结(ì
n,即于都斤山)例外,那里分别由王族(ōng)人和Q·h·n-Ati人居住。大部分部族原来只服从于他们的小首领,直到他们感到必须有和谐的配合为止。在思结(ì gil)部落内部,他们选择了一位最高首领,名叫M
gil)部落内部,他们选择了一位最高首领,名叫M ngüBay,意为“永远富裕者”,其称号为ēLēlt·rir/Elb·t·r(肯定应该为El-t
ngüBay,意为“永远富裕者”,其称号为ēLēlt·rir/Elb·t·r(肯定应该为El-t bir,即俟利发)。在ōrqundur部族中,有一位副首领叫作k
bir,即俟利发)。在ōrqundur部族中,有一位副首领叫作k l irkin(屈俟斤)
l irkin(屈俟斤) 。他们的统治持续了100多年。还必须指出,这种选择两位首领俟利发和俟斤的做法又非常明显地使人回忆起了铁勒部族在7世纪初建立俟利发俟斤(Elt
。他们的统治持续了100多年。还必须指出,这种选择两位首领俟利发和俟斤的做法又非常明显地使人回忆起了铁勒部族在7世纪初建立俟利发俟斤(Elt bir irkin)作为大可汗,又推举俟斤的一位儿子作为小可汗的做法。他们执政百年之事,又使人想起了十姓回鹘人对九姓部族百年统治,在西耐乌苏碑中就曾强调过这一点。
bir irkin)作为大可汗,又推举俟斤的一位儿子作为小可汗的做法。他们执政百年之事,又使人想起了十姓回鹘人对九姓部族百年统治,在西耐乌苏碑中就曾强调过这一点。
另外,拉施特曾三次提到过Uyghur(回鹘)一名的词源,这种词源字的价值肯定比至今人们所普遍认为的那样还要宝贵。实际上,如果Uyghur明显是由后缀-ghur(-gh°r/q°r)和动词uy-派生而来的话,那么古代肯定用该后缀来组成不定过去时分词 ,但现在已经无法知道uy-这一动词的古突厥语形式了
,但现在已经无法知道uy-这一动词的古突厥语形式了 。因此,近代突厥学术界尚没有解释清楚Uy-ghur一名。然而,拉施特的解释如下:(一)Uyghur在突厥语中则具有“behempeyvesten ve meded kerden”的意思,即“互相汇合在一起和互相帮助”;(二)Uyghur是一个突厥词,在波斯语中的意思是“bemāpeyvest ve meded ve mu'āvenet kerd”,即“他们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并且帮助和支援我们”
。因此,近代突厥学术界尚没有解释清楚Uy-ghur一名。然而,拉施特的解释如下:(一)Uyghur在突厥语中则具有“behempeyvesten ve meded kerden”的意思,即“互相汇合在一起和互相帮助”;(二)Uyghur是一个突厥词,在波斯语中的意思是“bemāpeyvest ve meded ve mu'āvenet kerd”,即“他们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并且帮助和支援我们” 。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一个动词的意思是“跟在……的后面,按照……行动”。在拉施特时代的西部方言中,越来越倾向于读作uy-,而在古突厥语中都是ud-,这一点是毫无怀疑的
。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一个动词的意思是“跟在……的后面,按照……行动”。在拉施特时代的西部方言中,越来越倾向于读作uy-,而在古突厥语中都是ud-,这一点是毫无怀疑的 。然而,ud-一词并不完全符合拉施特所下的定义,因为它主要是具有“按照”和“符合”的意思,而“互相会合在一起和互相帮助”则更可能是指“结盟”。但是,古突厥语中的uya一词确实是具有“亲属”、“盟友”的意义,它很可能是动词uy-(与……结盟)再加上-a派生而来的
。然而,ud-一词并不完全符合拉施特所下的定义,因为它主要是具有“按照”和“符合”的意思,而“互相会合在一起和互相帮助”则更可能是指“结盟”。但是,古突厥语中的uya一词确实是具有“亲属”、“盟友”的意义,它很可能是动词uy-(与……结盟)再加上-a派生而来的 。在古突厥语中还有另外一个词uyur/uy(a)r,既是形容词,又是名词。它似乎也代表着一个所谓动词uy-的过去分词(联盟、联合、附属),尽管没有任何人认为这是动词u-的过去分词,u-的意思是“可以、能够、有能力”等等。事实上,我们很难决定最终应该采取哪一种解释为最佳:结盟/附属、能力影响、权势者/贵族等,因为根据唯一一次出现过uyur/uy(a)r
。在古突厥语中还有另外一个词uyur/uy(a)r,既是形容词,又是名词。它似乎也代表着一个所谓动词uy-的过去分词(联盟、联合、附属),尽管没有任何人认为这是动词u-的过去分词,u-的意思是“可以、能够、有能力”等等。事实上,我们很难决定最终应该采取哪一种解释为最佳:结盟/附属、能力影响、权势者/贵族等,因为根据唯一一次出现过uyur/uy(a)r 的前后文是很难决定如何取舍的。无论如何,假设在古突厥语中,除动词ud(按照、追随)之外,还有一个动词uy-(被联合)的话,那就很容易理解第一个动词uy-在古突厥语中与ud-/uy-相混淆的原因了。由此来看,根据拉施特的解释(当然,我个人还有保留意见),我就建议作如下解释:Uyghur一词是由动词uy-(被联合)+-ghur(过去分词后缀)而组成的,原来的意思是“盟友”,所以,On-Uyghur的本意仅仅是“十盟友”。
的前后文是很难决定如何取舍的。无论如何,假设在古突厥语中,除动词ud(按照、追随)之外,还有一个动词uy-(被联合)的话,那就很容易理解第一个动词uy-在古突厥语中与ud-/uy-相混淆的原因了。由此来看,根据拉施特的解释(当然,我个人还有保留意见),我就建议作如下解释:Uyghur一词是由动词uy-(被联合)+-ghur(过去分词后缀)而组成的,原来的意思是“盟友”,所以,On-Uyghur的本意仅仅是“十盟友”。
现在我们再来列举一下十姓回鹘(十盟友)各个氏族或部族的名单,如同九姓乌古斯情况一样,这一部落联盟的具体组成在其历史上可能有所变化。《旧唐书》卷195第2页中所记载的唐代(7—10世纪)9个氏族的名单,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些标志,尽管其中的某些名词是很难考证清楚的 。
。
1.药罗葛(Yaghlaqar/Yaghlaqir):这是一个传统的可汗氏族。在8—10世纪的多种汉文、突厥文与和阗文文献中,确实出现过这一名称。此名似乎是由-qar/-qir派生而来的,它是动词yaghla-(涂油)过去分词的古老形式,可能是意指“涂油的人,用油的人”。事实上,在突厥—蒙古游牧部族中,人们都把油当作是富贵的标志 。
。
2.胡咄葛(Uturqar)。此名与由拉施特用来分别指十姓回鹘的十条河流名表中的第二位ūtig( )ūtik(
)ūtik( )r很相似。非常明显,这就是拜占庭史料中所提到的ūturghur/ūtrighur/ūtighur/ūtigher人,他们在6世纪时与十姓回鹘人一起生活在高加索和北海以北地区。至于此名称的第一个意义,它好像又一次系指以-qar/-qur~-ghar/-ghur为结尾的一种过去分词,肯定也是由动词ut-(获胜、战胜)派生而来的,其中常有-r-的施动词,如utur-、utr-[utru(反对、对立)即由此而来]可能具有加强语义的作用
)r很相似。非常明显,这就是拜占庭史料中所提到的ūturghur/ūtrighur/ūtighur/ūtigher人,他们在6世纪时与十姓回鹘人一起生活在高加索和北海以北地区。至于此名称的第一个意义,它好像又一次系指以-qar/-qur~-ghar/-ghur为结尾的一种过去分词,肯定也是由动词ut-(获胜、战胜)派生而来的,其中常有-r-的施动词,如utur-、utr-[utru(反对、对立)即由此而来]可能具有加强语义的作用 ,其意思为“获胜的人、胜利者”。动词ut-变成了üt-,尤其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突厥方言中,如在奥斯曼语中,ütm
,其意思为“获胜的人、胜利者”。动词ut-变成了üt-,尤其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突厥方言中,如在奥斯曼语中,ütm k和utmaq就是同时存在的(见德尼:《突厥语语法》,第108页),这样一来就完全可以解释清楚拉施特著作中为什么将ütik·r这种书写形式读作ütig
k和utmaq就是同时存在的(见德尼:《突厥语语法》,第108页),这样一来就完全可以解释清楚拉施特著作中为什么将ütik·r这种书写形式读作ütig r的原因了。
r的原因了。
但是,如果拜占庭史料中的Uturghur(并且还认为它与On-Oghur结盟)确实相当于Uturgar,即汉文史料中的“胡咄葛”(同时也还认为这是回鹘部族之一),那么,On-Oghur当然就相当于On-Uyghur了,即均指十姓回鹘。另外,我们还可以认为,如果乌图尔古尔确实是回鹘的十个部族之一,那么它的兄弟部族库图尔古尔明显是动词qutur-以-ghur结尾的过去分词。qutur-的本义是“超越”、“溢出”、“暴怒”等等,这里是暗示“失去正常理智的人,发狂的人”。
3.啒(掘)罗勿,同样也写作俱罗勃,相当于鲁尼突厥文中的Kür bir/Kür
bir/Kür βir,在10世纪的和阗文中则是Kür
βir,在10世纪的和阗文中则是Kür bira
bira 。Kür
。Kür bir/Kür
bir/Kür βir/Kür
βir/Kür mür/Kür
mür/Kür bür可能由动词kür
bür可能由动词kür -(逃走)派生而来,后一个动词是由喀什噶里辞典中所提供的。
-(逃走)派生而来,后一个动词是由喀什噶里辞典中所提供的。
4.貊歌息讫。可能为Baqasir的对音,但现在尚未考证清楚。
5.阿勿嘀。可能为 Büˇc
Büˇc 或魨βüˇc
或魨βüˇc k的对音,现在尚无法考证清楚。
k的对音,现在尚无法考证清楚。
6.曷萨(Qazar/Qasar)。在十姓回鹘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名称,从而更加强了我们对于On-oghur=On-Uyghur的猜想。这一名称就相当于6—7世纪北加高索的Khazar人。在汉文史料中,对这一名称的对音共有三种形式,有两种带有-z-,而一种则是带有-s-。(a)葛萨,为Qazar的对音,为一回鹘部族;(b)曷萨,为Xazar的对音,指高加索以北的哈扎尔人或可萨突厥人,这同样也是824—832年的一位回鹘可汗的名字,即曷萨特勤。他在《摩尼教赞美诗》(第9页,第20~21行)的摩尼教经文中则相当于Xasār tegīn ;(c)可萨,可能相当于Qasar的对音,这是《唐书》中所记载的伏尔加河流域“曷萨”部族的译音字
;(c)可萨,可能相当于Qasar的对音,这是《唐书》中所记载的伏尔加河流域“曷萨”部族的译音字 。另外,除了上文所提到的摩尼教经文中的例证之外,带有-s-的形式还曾出现在6世纪一部古叙利亚文无名氏著作中,可能也曾出现在西耐乌苏的回鹘碑铭中
。另外,除了上文所提到的摩尼教经文中的例证之外,带有-s-的形式还曾出现在6世纪一部古叙利亚文无名氏著作中,可能也曾出现在西耐乌苏的回鹘碑铭中 。在其他各种典籍中,无论是在拜占庭希腊文、阿拉伯文、俄文、匈牙利文还是在亚美尼亚文中,我们唯有发现过带有-z-的形式。只有蒙古文除外,它没有-z-。然而,在古突厥文中,我们没有发现过qas-这样的动词。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此名词的第一种形式是Qazar,那些带有-s-的例证只可以通过以下原因得到解释:在某几种突厥语中,当时已经出现了z清化的现象
。在其他各种典籍中,无论是在拜占庭希腊文、阿拉伯文、俄文、匈牙利文还是在亚美尼亚文中,我们唯有发现过带有-z-的形式。只有蒙古文除外,它没有-z-。然而,在古突厥文中,我们没有发现过qas-这样的动词。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此名词的第一种形式是Qazar,那些带有-s-的例证只可以通过以下原因得到解释:在某几种突厥语中,当时已经出现了z清化的现象 。我始终坚持Qazar/Qazir是动词qaz-/ qazi-的过去分词这一看法,动词qaz-/qazi-是“挖掘”、“刮擦”的意思,其特殊意义是“后退的烈马用前脚踢土”(见喀什噶里大辞典,第2卷,第10页)。因此,Qazar/Qazir可能为“爱踢蹬的部族”的名称,即“暴烈的和毫无节制的”部族。qazaq意为“冒险者”,同样也是部族的名词,它也是同一动词qaz-的另一派生词[参阅葛玛丽(Annemarie·V·Gabain):《可萨民族社会—语言学研究》,载《匈牙利东方学报》,1960年,第11卷,第161~ 167页]。
。我始终坚持Qazar/Qazir是动词qaz-/ qazi-的过去分词这一看法,动词qaz-/qazi-是“挖掘”、“刮擦”的意思,其特殊意义是“后退的烈马用前脚踢土”(见喀什噶里大辞典,第2卷,第10页)。因此,Qazar/Qazir可能为“爱踢蹬的部族”的名称,即“暴烈的和毫无节制的”部族。qazaq意为“冒险者”,同样也是部族的名词,它也是同一动词qaz-的另一派生词[参阅葛玛丽(Annemarie·V·Gabain):《可萨民族社会—语言学研究》,载《匈牙利东方学报》,1960年,第11卷,第161~ 167页]。
7.斛嗢素。不可稽考,可能为Xughuzu的对音。
8.药勿葛。可能就相当于925年钢和泰藏卷中和阗文部落名称表中的Yagmurqar、Yabūtt kar
kar 的对音(参阅《大亚细亚杂志》,第2卷,第1期,第20页)。在Yaghmurqar(可能由yaghmur,即“雨”派生而来)、Yaghmutqar或Yabutqar中,再次出现了一个后缀-qar(-gh°r/-q°r),它既可以加入名词之中(见德尼:《突厥语语法》,第931页),也可以加入动词之中。
的对音(参阅《大亚细亚杂志》,第2卷,第1期,第20页)。在Yaghmurqar(可能由yaghmur,即“雨”派生而来)、Yaghmutqar或Yabutqar中,再次出现了一个后缀-qar(-gh°r/-q°r),它既可以加入名词之中(见德尼:《突厥语语法》,第931页),也可以加入动词之中。
9.奚耶勿。其他地方也写作“爱耶勿”,在9—10世纪的于阗文中写作Ayavìr /Ayabīr
/Ayabīr
 ,我还坚信应该把此名考证成Aymur,即喀什噶里辞典中所列举的乌古斯人21个部族中的第11位,也就是拉施特著作中乌古斯部落名称内的lmūr,5个部族中的第2个部落,也可能应读作Aymūr
,我还坚信应该把此名考证成Aymur,即喀什噶里辞典中所列举的乌古斯人21个部族中的第11位,也就是拉施特著作中乌古斯部落名称内的lmūr,5个部族中的第2个部落,也可能应读作Aymūr 。事实上,大家知道Ayamur的古代形式在11—13世纪缩减成了Aymur/Aymūr,Ayabir/Ayaβir/Ayamur,以及上文所提到的由Kür
。事实上,大家知道Ayamur的古代形式在11—13世纪缩减成了Aymur/Aymūr,Ayabir/Ayaβir/Ayamur,以及上文所提到的由Kür bir/Kür
bir/Kür βir/Kür
βir/Kür mür明显是借助于-b°r/-β°r/-m°r而形成的,可以将之与葛玛丽的《突厥语语法》123[yaghmur(雨),由ya-(下雨)派生而来;almir(贪婪),由al(拿)派生而来]中所描述的后缀-m°r进行比较;德尼的《突厥语语法》第583页中也对此有分析(c^oqmar、c^omur、qu
mür明显是借助于-b°r/-β°r/-m°r而形成的,可以将之与葛玛丽的《突厥语语法》123[yaghmur(雨),由ya-(下雨)派生而来;almir(贪婪),由al(拿)派生而来]中所描述的后缀-m°r进行比较;德尼的《突厥语语法》第583页中也对此有分析(c^oqmar、c^omur、qu -mar、qatmer)。至于该名词的第一种意义,伯希和在《金帐汗国史札记》第197页中,为了说明他不想注重此义,曾引证了拉施特的解释:“他无限善良和强大。”可是,那些“无限善良和强大”的人是一定会“受人尊重”的,而动词aya-确实是具有“尊重”的意思,它似乎是由Ayamur/Ayabir/Ayaβir派生而来的。后缀-m°r/-β°r/-b°r的作用尚待进行考证,但我们可以认为它的作用是加强语气和表示反复动作:经常要大量下雨(ya-mur);那些希望多拿东西的人的特点就是贪婪(al-mir)。因此,Ayabir/ Ayamur的意义可能有“举止稳重,非常受人尊重的人”(也可能是说“非常受人崇拜”),而Kür
-mar、qatmer)。至于该名词的第一种意义,伯希和在《金帐汗国史札记》第197页中,为了说明他不想注重此义,曾引证了拉施特的解释:“他无限善良和强大。”可是,那些“无限善良和强大”的人是一定会“受人尊重”的,而动词aya-确实是具有“尊重”的意思,它似乎是由Ayamur/Ayabir/Ayaβir派生而来的。后缀-m°r/-β°r/-b°r的作用尚待进行考证,但我们可以认为它的作用是加强语气和表示反复动作:经常要大量下雨(ya-mur);那些希望多拿东西的人的特点就是贪婪(al-mir)。因此,Ayabir/ Ayamur的意义可能有“举止稳重,非常受人尊重的人”(也可能是说“非常受人崇拜”),而Kür bir/Kür
bir/Kür mür却意指“随时都想逃走的人”。
mür却意指“随时都想逃走的人”。
因此,关于两唐书中所记载的9种转写形式,以下6个回鹘部族的名称已经考证清楚:Ya laqar/Ya laqir(药罗葛)、Uturqar/ Uturqur/ütig r(胡咄葛)、Kür
r(胡咄葛)、Kür mür/Kürt
mür/Kürt bir[啒(掘)罗勿]、Qazar/Qasar(葛萨、曷萨、可萨)、Yaghmurqar/Yabutqar(药勿葛)和Ayamur/Ayabir(奚耶勿)。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谈拉施特所赋予十姓回鹘的十条河流(十鄂尔浑河)的名称,这些形式多少有些讹变:
bir[啒(掘)罗勿]、Qazar/Qasar(葛萨、曷萨、可萨)、Yaghmurqar/Yabutqar(药勿葛)和Ayamur/Ayabir(奚耶勿)。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谈拉施特所赋予十姓回鹘的十条河流(十鄂尔浑河)的名称,这些形式多少有些讹变:
1.第一个名称也是为十姓回鹘人提供第一位君主的部族,这就是I g(i)l人,虽然人们经常见到的则是药罗葛人。í
g(i)l人,虽然人们经常见到的则是药罗葛人。í g(i)l肯定就相当于Izg(i)l,东突厥的阙特勤(K
g(i)l肯定就相当于Izg(i)l,东突厥的阙特勤(K l-tegin)曾于715年左右对该部族发动过袭击
l-tegin)曾于715年左右对该部族发动过袭击 ,即使说它不是一个回鹘部族,至少也可以说是九姓部族之一。浦立本(Pulleyblank)在《有关Toquzoghuz问题的简释》第41页注中曾将Izgil与汉语对音字“奚结”进行过比较,它也是铁勒部族之一,汉文史料也将之归于九姓部之列。此外,还必须说明,《旧唐书》在卷195第1页中提到这些部族创建各州的时候,没有写作《唐书》卷217上第1页中的“奚结”,而是写作“跌结”,很可能为“结”(Izgil)之误
,即使说它不是一个回鹘部族,至少也可以说是九姓部族之一。浦立本(Pulleyblank)在《有关Toquzoghuz问题的简释》第41页注中曾将Izgil与汉语对音字“奚结”进行过比较,它也是铁勒部族之一,汉文史料也将之归于九姓部之列。此外,还必须说明,《旧唐书》在卷195第1页中提到这些部族创建各州的时候,没有写作《唐书》卷217上第1页中的“奚结”,而是写作“跌结”,很可能为“结”(Izgil)之误 。另外,据伊斯兰史料记载,I
。另外,据伊斯兰史料记载,I gil/Isgil在10世纪左右,是伏尔加河流域不里阿耳人的三部族之一。
gil/Isgil在10世纪左右,是伏尔加河流域不里阿耳人的三部族之一。
2.ütig( )r相当于《唐书》中回鹘部族的第二位“胡咄葛”(Uturqar),也相当于拜占庭史料中的乌都尔胡尔(Uturghur/ Utigher)。
)r相当于《唐书》中回鹘部族的第二位“胡咄葛”(Uturqar),也相当于拜占庭史料中的乌都尔胡尔(Uturghur/ Utigher)。
3.Bōqr/Bōqir很可能是阿拉伯文Bōqū的误写。然而,“仆固”即钢和泰于阗文藏卷中的Bāku的对音[参阅亨宁(Henning)于《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报》第9卷,第555页的解释],这也是九姓部中一个重要的部族,即《唐会要》(卷98,第2页)中所列举的九姓部族的内继回鹘之后的第二个部落。在866年左右,中国突厥斯坦有一回鹘大首领也叫作仆固(见笔者旧作:《五代回鹘史》,第13—15页)。
4.ōrq(u)nd(u)r一名又不禁使人联想到了拜占庭史料中的(On-)Oghundur。Onoghundur应为On(+)-Oghundur。在7世纪时,他们与不里阿耳人密切结盟,居住在高加索和北海以北地区。他们在那里与库图尔胡尔人以及十姓回鹘人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国家,即大不里阿耳国 。On-Oghundur肯定就是Wn·ud·r或WI·un·r,也有可能是Ol·bd·r,据伊斯兰和其他各种史料记载,在10世纪左右,这个民族居住在黑海以西
。On-Oghundur肯定就是Wn·ud·r或WI·un·r,也有可能是Ol·bd·r,据伊斯兰和其他各种史料记载,在10世纪左右,这个民族居住在黑海以西 。Oghundur一词可能是由Oghu-(其意可能为“生育”)派生而来的,如同Oghul和
。Oghundur一词可能是由Oghu-(其意可能为“生育”)派生而来的,如同Oghul和
 一样,表面上看起来也似乎是以-nd°r结尾的一种形式,一种为了表示自反动作的形式。这一点与其他许多突厥古部族的名称一样,如Bayundur/βayindir是由bayu-(变成富翁)派生而来,
一样,表面上看起来也似乎是以-nd°r结尾的一种形式,一种为了表示自反动作的形式。这一点与其他许多突厥古部族的名称一样,如Bayundur/βayindir是由bayu-(变成富翁)派生而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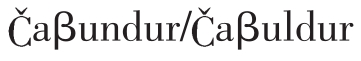 是由
是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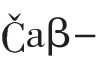 (受到赞美)派生而来,Zaβen der系由
(受到赞美)派生而来,Zaβen der系由 (感到自豪)或
(感到自豪)或 (驱逐、狩猎)派生而来
(驱逐、狩猎)派生而来 。拉施特著作中的ōrq(u)nd(u)r这种写法可能为
。拉施特著作中的ōrq(u)nd(u)r这种写法可能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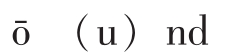 (u)r之误,也可能是由于On-Orqun(十鄂尔浑河)这一术语的讹变而引起的。所以,十姓回鹘这一部族的名称应该再次考订为与On-Oghur相同的一个部族名称。
(u)r之误,也可能是由于On-Orqun(十鄂尔浑河)这一术语的讹变而引起的。所以,十姓回鹘这一部族的名称应该再次考订为与On-Oghur相同的一个部族名称。
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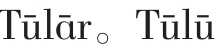 和
和 肯定是
肯定是 或
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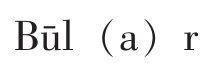 之异体,也就是不里阿耳人的一种无喉音的形式,这种用法在拉施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广为流传。请参阅伯希和在《金帐汗国史札记》第124~139、224~230页,尤其是225页中对“不里阿耳”一名的考证:“多松和白罗舍都认为在拉施特的著作中读到了Polo或Polar一名,并将之解释为波兰人,而事实上应该是Bular,指不里阿耳人。”据伯希和的分析,Bulghar可能是动词bul-带有后缀-ar(找到)的一种形式,Bular是一种缩写形式,完全如同Yazir和Salur分别是Yazghir和Salghur的缩体字一样。还需要提醒大家注意,无论如何,后缀-gh°r~-q°r可能是“过去分词的原始形式,它与持续现在量的混淆仅仅是语音发展中的一种次要现象”(同上引书,第229页)。拉施特似乎想列入十姓回鹘的不里阿耳人实际上是一个突厥民族,从5世纪起就在历史上出现了,居住于伏尔加河下游和多瑙河之间的地区;在5—8世纪的拜占庭史料中,他们与十姓回鹘人,特别是与上文所提到的On-Oghundur人具有结盟关系。
之异体,也就是不里阿耳人的一种无喉音的形式,这种用法在拉施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广为流传。请参阅伯希和在《金帐汗国史札记》第124~139、224~230页,尤其是225页中对“不里阿耳”一名的考证:“多松和白罗舍都认为在拉施特的著作中读到了Polo或Polar一名,并将之解释为波兰人,而事实上应该是Bular,指不里阿耳人。”据伯希和的分析,Bulghar可能是动词bul-带有后缀-ar(找到)的一种形式,Bular是一种缩写形式,完全如同Yazir和Salur分别是Yazghir和Salghur的缩体字一样。还需要提醒大家注意,无论如何,后缀-gh°r~-q°r可能是“过去分词的原始形式,它与持续现在量的混淆仅仅是语音发展中的一种次要现象”(同上引书,第229页)。拉施特似乎想列入十姓回鹘的不里阿耳人实际上是一个突厥民族,从5世纪起就在历史上出现了,居住于伏尔加河下游和多瑙河之间的地区;在5—8世纪的拜占庭史料中,他们与十姓回鹘人,特别是与上文所提到的On-Oghundur人具有结盟关系。
6. ,应该相当于
,应该相当于 (葛萨)人,汉文史料也将它们列入了回鹘部族之中。在拜占庭史料中,高加索和黑海以北的可萨—曷萨人在6—7世纪时,却是与十姓回鹘部、不里阿耳等部相结盟的。
(葛萨)人,汉文史料也将它们列入了回鹘部族之中。在拜占庭史料中,高加索和黑海以北的可萨—曷萨人在6—7世纪时,却是与十姓回鹘部、不里阿耳等部相结盟的。
7.Ad·r。很容易看出,这里就是指 (阿跌)人,它是九姓部一个重要部落。795—805年的回鹘大可汗就属于这个部落,他的继任者们的情况也可能基本如此
(阿跌)人,它是九姓部一个重要部落。795—805年的回鹘大可汗就属于这个部落,他的继任者们的情况也可能基本如此 。然而,有一卷写本中的写法略有小异
。然而,有一卷写本中的写法略有小异 ,写本中可能应读作Aw(a)r=Aβar,至少它并不是指Ad·r<Ad·z的一种变形写法。在阿跌和阿拨之间同样也发生了混乱。我们确实发现在唐代的某些文献中写作“阿跋”,而不是“阿跌”,后者为
,写本中可能应读作Aw(a)r=Aβar,至少它并不是指Ad·r<Ad·z的一种变形写法。在阿跌和阿拨之间同样也发生了混乱。我们确实发现在唐代的某些文献中写作“阿跋”,而不是“阿跌”,后者为 diz的对音;这就使人联想到,典籍编纂者们都把“阿跌”中的“跌”改为“跋”,以图更为接近“阿拔”一名,完全可能是Aβar的对音,即阿瓦尔族(Avar)的名称,没有任何理由把它看作是阿跌族的误写,因为第一种形式曾在比第二种形式更古老的史料中出现过,而且“拔”与“跌”这两个字还没有相似到足以使人互相混淆的程度
diz的对音;这就使人联想到,典籍编纂者们都把“阿跌”中的“跌”改为“跋”,以图更为接近“阿拔”一名,完全可能是Aβar的对音,即阿瓦尔族(Avar)的名称,没有任何理由把它看作是阿跌族的误写,因为第一种形式曾在比第二种形式更古老的史料中出现过,而且“拔”与“跌”这两个字还没有相似到足以使人互相混淆的程度 。据《隋书》(卷84,第3页;卷54,第4页)和《北史》(卷99,第10页)记载,阿拔人地区的部族在585年左右曾与突厥人发生过冲突,史料中在记载603年反对突厥人的斗争时,阿拔族也是铁勒联盟中的一员。因此,在未获得相反的证据之前,我可以认为阿拔族就是Aβar的对音,他们与回鹘人属于同一个部落联盟,至少在600年左右的情况是这样的。
。据《隋书》(卷84,第3页;卷54,第4页)和《北史》(卷99,第10页)记载,阿拔人地区的部族在585年左右曾与突厥人发生过冲突,史料中在记载603年反对突厥人的斗争时,阿拔族也是铁勒联盟中的一员。因此,在未获得相反的证据之前,我可以认为阿拔族就是Aβar的对音,他们与回鹘人属于同一个部落联盟,至少在600年左右的情况是这样的。
8 或
或 ,这个部落的名称尚未考证清楚。它可能是一个名词(河名?),前面加了一个ü(三)。如ü-Ba的意思就是“三泉河”。
,这个部落的名称尚未考证清楚。它可能是一个名词(河名?),前面加了一个ü(三)。如ü-Ba的意思就是“三泉河”。
9. 同样也在喀什噶里的辞典(卷3,第242页)中出现过,并且是作为“靠近伊基·俄古兹附近的一个山城的名字”而出现的,位于伊犁河畔,在巴尔喀什湖和伊塞克湖之间的地方(《世界境域志》第276~277页)
同样也在喀什噶里的辞典(卷3,第242页)中出现过,并且是作为“靠近伊基·俄古兹附近的一个山城的名字”而出现的,位于伊犁河畔,在巴尔喀什湖和伊塞克湖之间的地方(《世界境域志》第276~277页) 。在第9条河畔,居住有一个
。在第9条河畔,居住有一个 族,在突厥—蒙古语中,此名就相当于汉语中的“王”字。
族,在突厥—蒙古语中,此名就相当于汉语中的“王”字。
10.簟tikan当然是指 tük
tük n,即于都斤山林,又叫乌德健山,那里是杭爱山区突厥—蒙古汗国传统的中心。Q·h·n·Ati(肯定读作Qaghan Ati,即阿提可汗)的部落就居住在那里。可是,由于at的意思是“姓名、官职、阶位”,所以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以可汗名字命名的部落”,也就是指可汗的部落
n,即于都斤山林,又叫乌德健山,那里是杭爱山区突厥—蒙古汗国传统的中心。Q·h·n·Ati(肯定读作Qaghan Ati,即阿提可汗)的部落就居住在那里。可是,由于at的意思是“姓名、官职、阶位”,所以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以可汗名字命名的部落”,也就是指可汗的部落 。事实上,回鹘可汗在840年之前一直居住在于都斤山林。
。事实上,回鹘可汗在840年之前一直居住在于都斤山林。
这样看来,拉施特把On-Orqun(十鄂尔浑河)的名表同On-Uyghur(十姓回鹘人)考证为一体了,我们由此就会发现前7个名字似乎就相当于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知道的一些部落名称:1. I gil(奚结)=I
gil(奚结)=I gil/l
gil/l gil=lzgil;2.ütig
gil=lzgil;2.ütig r(胡咄葛)=Utigher/Utirghur=Uturqar;3.Boqu(仆固);4.Orqundur=Oundur;5.Bular=Bulghar(不里阿耳);6.Qazar(曷萨);7.Adiz或Aβar(阿跌)。其中仆固人与阿跌人都属于九姓部,他们肯定与回纥人(Uyghur)最为接近,在10世纪时可能也加入了十姓部族。对于其中第8个部落,我暂时不予考证,因为对它的来龙去脉,我一无所知。对于第9个部落,即王族部落,它可能是忽木阑术(Qamlan u,位于伊犁河附近,伊塞克湖的东北)。最后,第10个部落,即以可汗命名的部落居住在都于斤山林,可能相当于药罗葛部落,这是传统的可汗部族。虽然795年的一位阿跌人继位了,但药罗葛人在甘州回鹘人中一直统治到10—11世纪。
r(胡咄葛)=Utigher/Utirghur=Uturqar;3.Boqu(仆固);4.Orqundur=Oundur;5.Bular=Bulghar(不里阿耳);6.Qazar(曷萨);7.Adiz或Aβar(阿跌)。其中仆固人与阿跌人都属于九姓部,他们肯定与回纥人(Uyghur)最为接近,在10世纪时可能也加入了十姓部族。对于其中第8个部落,我暂时不予考证,因为对它的来龙去脉,我一无所知。对于第9个部落,即王族部落,它可能是忽木阑术(Qamlan u,位于伊犁河附近,伊塞克湖的东北)。最后,第10个部落,即以可汗命名的部落居住在都于斤山林,可能相当于药罗葛部落,这是传统的可汗部族。虽然795年的一位阿跌人继位了,但药罗葛人在甘州回鹘人中一直统治到10—11世纪。
回鹘部族,即十姓回鹘部落的简称,一方面是按照远东史料(汉文、突厥文与和阗方)而对音的;另一方面是根据拉施特的办法对音的。另外,在5—8世纪的基督教史料(拜占庭文、叙利亚文和拉丁文史料)也证明,这些部族位于高加索、黑海和里海以北;在许多情况下,9—11世纪的伊斯兰史料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所以,5—8世纪基督教史料中所提及的里海西部的On-Oghur/Uighur的主要部族事实上就相当于回鹘部族,即远东和拉施特史料中所提到的On-Uyghur。只有由伊兰起源的萨毗人和奄蔡人(Alan)除外,在6世纪时,他们也可能属于铁勒部,所以当然是突厥人了。我认为,所有这一切均可以证明,On-Oghur与On-Uyghur是一致的,即“十姓回鹘人”。
总而言之,大家从这篇论文中可以看出,最早不超过公元400年左右,铁勒部族以十姓回鹘(很可能是指“十姓联盟”)的名义而形成了。在5世纪时,由于西域的政治冲突和动乱,十姓回鹘部中的一部分离开了他们的故乡,即蒙古高原,开始西迁,最后在咸海以西的草原地区,尤其是在高加索以北的草原定居。这次民族大迁移可能是由十姓回鹘的各部落相继进行的,其中就包括白哈兹尔人(Aq-Qazir)、葛萨人(Xazar)、撒里黑人(Sarigh)、回鹘人(Uyghur)、不里阿耳人(Bulghar)、乌图尔古尔人(Uturghur)、胡图尔古尔人(Quturghur)、(Kuturghur)、十姓乌隆都尔人[(On-)Oghundur]、阿拔人[Aβar(?)]和奚结人(I gil/Isgil/Izgil)从7—8世纪开始,西部的回鹘部族开始在新的迁徙和与异族接触中发生变化和分化,这次特别是向欧洲方向迁徙,以至于最后丧失了他们的回鹘人的地位与东突厥人的特征。
gil/Isgil/Izgil)从7—8世纪开始,西部的回鹘部族开始在新的迁徙和与异族接触中发生变化和分化,这次特别是向欧洲方向迁徙,以至于最后丧失了他们的回鹘人的地位与东突厥人的特征。
就九姓部的考证而言,其情况也基本如此,但时代已经相当晚了。事实上,九姓乌古斯(Toquz-Oghuz<Toquz-Oghu )联盟是由蒙古高原和中国突厥斯坦的铁勒部族所组成的,其时间可能为7世纪初年。在8世纪末和9世纪初,当他们的汗国在回鹘人的领导下大举扩张的时候,九姓部的一部分一直越出了其西部边界,最后在咸海一带的草原地区定居下来了。该部族与他们的发祥地断绝了关系,在以后几个世纪中又被伊斯兰化,所以被人们称为乌古斯、古斯(Ghuzz)或乌斯(Uz)的部族逐渐与他们的东部同宗兄弟们不同了,但西方史料还一直称他们为九姓乌古斯,在后期对其统治部族主要是称之为回鹘。这一变化主要是同其他民族接触,尤其是同很久以来就居住在西部地区的突厥民族进行接触的结果。他们最后又与新的政治集团融合在一起,由于后来向欧洲和小亚细亚的迁徙才散开了。
)联盟是由蒙古高原和中国突厥斯坦的铁勒部族所组成的,其时间可能为7世纪初年。在8世纪末和9世纪初,当他们的汗国在回鹘人的领导下大举扩张的时候,九姓部的一部分一直越出了其西部边界,最后在咸海一带的草原地区定居下来了。该部族与他们的发祥地断绝了关系,在以后几个世纪中又被伊斯兰化,所以被人们称为乌古斯、古斯(Ghuzz)或乌斯(Uz)的部族逐渐与他们的东部同宗兄弟们不同了,但西方史料还一直称他们为九姓乌古斯,在后期对其统治部族主要是称之为回鹘。这一变化主要是同其他民族接触,尤其是同很久以来就居住在西部地区的突厥民族进行接触的结果。他们最后又与新的政治集团融合在一起,由于后来向欧洲和小亚细亚的迁徙才散开了。
注释:
①见拉德洛夫(W.Radloff):《福乐智慧》译注本,第1卷,1891年圣彼得堡版,作者用转写文和翻译文发表了现在所知道的有关乌古斯可汗传说的3种主要文本:(1)拉施特于14世纪初的文本,见其《史集》第14—24页;(2)阿布尔—哈吉(Abü-'I-Ghāzi)于17世纪时的文本,见其著第28—38页;(3)国立图书馆所藏薛爱华(Schefer)回鹘文写本中的文本,见第1—13页,232—244页。伯希和于1930年在《通报》第27卷,第247—358页发表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一篇论文。他指出,这是一篇晚期的回鹘文文献,很可能是15世纪时的。利扎·努尔(Riza Nour)于1928年在亚历山大城以《乌古斯传奇—突厥史诗》为题而发表,伯希和于1930年又作了校对。该文献的回鹘文本又由班格(Bang)和拉赫马蒂(Rachmati)以《有关乌古斯汗的传说》为题于1932年在《柏林德国科学论丛》第25卷中发表,A·W·切尔巴克 于1959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乌古斯纪事》中再次发表。
于1959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乌古斯纪事》中再次发表。
②参阅马夸特:《论库曼人的民族特征》,第35—37、201页;《匈牙利年鉴》,1929年,第9卷,第90页。事实上,uz从未曾具有过“人”的意思,但却具有“灵巧”的意思。在由马夸特所参阅的一段文字中,勒柯克于《在高昌发现的突厥文摩尼经残卷》第1卷,第16页中把uzlar译成了“能干的人”,uzlar是形容词uz的复数形式,这里当作名词使用。
③这种不同意见是由班克同拉赫玛蒂提出来的,见《有关乌古斯汗的传说》,第3页注。
④见:《论九姓回鹘与ToquzOruz的关系》,这是作者于1919年发表的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羽田亨先生雄辩地证明,在8世纪突厥碑铭中出现的Toquz-Oruz同以“九姓”著称的铁勒部落联盟是完全一致的。他所得出的结论又由西方作家们进行了总结,如浦立本先生在1956年发表的精辟论著《有关Toquzoghuz问题的简释》中,又为羽田亨先生的论点作出了非常有份量的新贡献。
⑤见该书铁勒传中间的部分,《通典》是于801年成书的。
⑥t gr
gr g(或者为t
g(或者为t gr
gr k?)是一个名词,意为“箍、圆套”。该词在喀什噶里的辞典和察合台语中都曾出现过(见拉德洛夫所著的《辞典》第3卷,第1038页),由该名词又派生出了一个动词:t
k?)是一个名词,意为“箍、圆套”。该词在喀什噶里的辞典和察合台语中都曾出现过(见拉德洛夫所著的《辞典》第3卷,第1038页),由该名词又派生出了一个动词:t grigl
grigl -(t
-(t grikl
grikl -?),意为“环绕,成圆形”,这后一个动词原来出现在一些用回鹘文所写的佛经文中(参阅《回鹘资料汇编》第3卷;《吐鲁番突厥文献集》第10卷)。如同t
-?),意为“环绕,成圆形”,这后一个动词原来出现在一些用回鹘文所写的佛经文中(参阅《回鹘资料汇编》第3卷;《吐鲁番突厥文献集》第10卷)。如同t gr
gr (环绕着……)和t
(环绕着……)和t girm
girm n(磨)一样,t
n(磨)一样,t gr
gr g也是由动词t
g也是由动词t gir-(使达到,使接触)派生而来的。除了作为汉语的对音字之外,T
gir-(使达到,使接触)派生而来的。除了作为汉语的对音字之外,T gr
gr g似乎没有作为专用名词出现过。
g似乎没有作为专用名词出现过。
卜弼德(P.A.Boodberg)曾正确地提出了一种古老的考证法:即把T li
li 考证为铁勒,把薛延陀考订为Sir-Tardu
考证为铁勒,把薛延陀考订为Sir-Tardu 。他的这种作法可能并不符合事实,我在《五代回鹘史》中也接受了这种考证。然而,对于第一个名词的对音问题,我不同意他的考证,他宁肯将此名考订为“铁勒”,而不是“特勒”,并且同蒙古文术语telegen、terge、tergen等进行了比较,这些词的意思是“车”。参阅卜弼德:《有关突厥的3条注释》,载《闪族和东方研究》,1951年伯利克版,第5—7页。
。他的这种作法可能并不符合事实,我在《五代回鹘史》中也接受了这种考证。然而,对于第一个名词的对音问题,我不同意他的考证,他宁肯将此名考订为“铁勒”,而不是“特勒”,并且同蒙古文术语telegen、terge、tergen等进行了比较,这些词的意思是“车”。参阅卜弼德:《有关突厥的3条注释》,载《闪族和东方研究》,1951年伯利克版,第5—7页。
⑦在位于阿尔泰山高山上的巴祖利克(Pazyryk)的5号墓中,发现了一辆完整的四轮车,可能为2000年之前的遗物。车轮上有许多精细的幅条,直径为2.15米。车轮的内圆是用两个弯曲的桦树轮 作成的,用一些木夹子和皮条而将两端连结起来。参阅陆登科(S.L.Rudenko):《山地阿尔泰居民的文化》,1953年莫斯科版,第232—233页,图146;利斯(T.T.Rice):《粟特考》,1958年巴黎版,第119页,图30。这辆车现藏列宁格勒博物馆。
作成的,用一些木夹子和皮条而将两端连结起来。参阅陆登科(S.L.Rudenko):《山地阿尔泰居民的文化》,1953年莫斯科版,第232—233页,图146;利斯(T.T.Rice):《粟特考》,1958年巴黎版,第119页,图30。这辆车现藏列宁格勒博物馆。
⑧引自《魏略》,成书于205年左右,原文载《三国志》中《魏志》第30卷末,由沙畹于1905年在《通报》第6卷,第558—561页翻译发表;马恩森—赫尔芬(Otto Maenchen-Helfen):《丁零考》,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39年,第4卷,第786页。马恩森—赫尔芬先生已经建议在丁零和敕勒/铁勒或高车之间作以比较。我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韩百诗(Louis Hambis)于1957年在《亚细亚学报》第245卷,第33页所表达的观点很相似,作者在注中还提出了有关这一问题的许多参考资料。另外,有关高车和铁勒的全部问题,请参阅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之研究》,1955年京都版。
⑨《隋书》和《北史》(卷99,第8页)基本是于同时代成书的,大约为630年左右。这两部史籍中都包括着铁勒传。801年成书的《通典》中的铁勒传(卷199)和在980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中的铁勒传(卷198,第1页)的记载基本都大同小异。
⑩“俟斤”应该是突厥文Irkin的对音,明显是没有把其中的-r-译出来(伯希和:《有关中亚的9条注释》,第229页)。在西突厥人中,右部的5个部族或箭的首领们同样也享有俟斤这一头衔,换句话说,“十箭”(Onoq)部落联盟西半部的5位大首领都享有这一尊号(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8页,见索引中“俟斤”一条目)。因此,只有某些大部落的大首领们才享有这种尊号,尤其是突厥最西部的5个部族,以及这里所指的铁勒最东部的5个部族的大首领们更为如此。
“俟斤”这一职称也出现在鲁尼文的突厥碑铭中,在8—9世纪的藏文中则为hir-kin(参阅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3号,第64—65行,由巴科发表在《亚细亚学报》第244卷,第137—153页)。在阿拉伯文中也是这样写的。另外,据喀什噶里辞典第1卷,第108页的分析,irkin(由动词irk-加上形容词词尾-n派生而来,动词的原义为“积合……”)适用于所有的“积合物”,如一片水塘中所积合的水。葛罗禄人所赋予他们的首领的那种屈俟斤(k l Irkin)职官尊号的意思是:“知识的积累就犹如池塘里所积蓄的水一样”。喀什噶里著作中的这段文献,可以使我们附带地将经常出现的突厥职称Kül改为k
l Irkin)职官尊号的意思是:“知识的积累就犹如池塘里所积蓄的水一样”。喀什噶里著作中的这段文献,可以使我们附带地将经常出现的突厥职称Kül改为k l,因为在鲁尼突厥文、回鹘文、阿拉伯文中,
l,因为在鲁尼突厥文、回鹘文、阿拉伯文中, 和ü的区别发音是不大清楚的。如K
和ü的区别发音是不大清楚的。如K l tegin(阙特勒)、Kǒl-Bilga(阙毗伽)和Kǒl or(阙嗫)等,人们一般都读作kül,这肯定是由于同Kü(名望)作比较而造成的结果。k
l tegin(阙特勒)、Kǒl-Bilga(阙毗伽)和Kǒl or(阙嗫)等,人们一般都读作kül,这肯定是由于同Kü(名望)作比较而造成的结果。k l的原意是“湖”。作为职称使用,它完全如同阿尔泰语传统中的ingiz(<t
l的原意是“湖”。作为职称使用,它完全如同阿尔泰语传统中的ingiz(<t ngiz,意为“海洋”)Khan(成吉思汗)和达赖(Dalai,在蒙古语中也具有“海洋”之意)喇嘛(参阅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考释》,第301页)。
ngiz,意为“海洋”)Khan(成吉思汗)和达赖(Dalai,在蒙古语中也具有“海洋”之意)喇嘛(参阅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考释》,第301页)。
 见《元和郡县图志》(卷9,第10页,伊吾县条)。该书指出,天山也被称为白山,或者是折罗漫。请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37页。
见《元和郡县图志》(卷9,第10页,伊吾县条)。该书指出,天山也被称为白山,或者是折罗漫。请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37页。
 从各种迹象来看,“契弊”一方面可能为“解批”,这是拓跋魏时代“高车”部的一个部落(《魏书》,卷103,第9页);另外也可能系指“契苾”或“契苾羽”,这是唐代铁勒部的部落之一。据《唐书》卷217下,第6页记载,该部位于焉耆西北的海都河上游(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8和87页)。
从各种迹象来看,“契弊”一方面可能为“解批”,这是拓跋魏时代“高车”部的一个部落(《魏书》,卷103,第9页);另外也可能系指“契苾”或“契苾羽”,这是唐代铁勒部的部落之一。据《唐书》卷217下,第6页记载,该部位于焉耆西北的海都河上游(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8和87页)。
 在同一传记下文不远的地方,该部落的名称也作为“小可汗”部落的名称,而于605年出现。我倾向于认为,“也咥”也代表着唐代史料中的“阿跌”或“
在同一传记下文不远的地方,该部落的名称也作为“小可汗”部落的名称,而于605年出现。我倾向于认为,“也咥”也代表着唐代史料中的“阿跌”或“ 跌”这同一个部族的名称,在鲁尼文的古突厥碑铭中,九姓部中的这一部族名称写作(
跌”这同一个部族的名称,在鲁尼文的古突厥碑铭中,九姓部中的这一部族名称写作( )d(i)z(参阅奥尔昆:《古代突厥碑铭集》,第4卷,第156页),即
)d(i)z(参阅奥尔昆:《古代突厥碑铭集》,第4卷,第156页),即 diz。然而,
diz。然而, diz的意思是“高、加高”,还有另外一种半园音的变形字yitiz(请参阅:《古突厥语语法》中idiz一条目中的解释;《吐鲁番突厥文献》第10卷,第55页),同样,还有iraq/yiraq,ǔrǔn/ yǔrǔη、ln g
diz的意思是“高、加高”,还有另外一种半园音的变形字yitiz(请参阅:《古突厥语语法》中idiz一条目中的解释;《吐鲁番突厥文献》第10卷,第55页),同样,还有iraq/yiraq,ǔrǔn/ yǔrǔη、ln g /yin g
/yin g 等词。因此,“也咥”是Y
等词。因此,“也咥”是Y diz的对音,即名词diz的半元音化形式。
diz的对音,即名词diz的半元音化形式。
 据我所知,阿得河至今尚未考证。由于人们把这一地区确定在了唐居以北,所以它很可能就是指《世界境域志》中的ātil河。这条河原则上是指伏尔加河,人们一般都认为它是沿着基麦克人(Kim
据我所知,阿得河至今尚未考证。由于人们把这一地区确定在了唐居以北,所以它很可能就是指《世界境域志》中的ātil河。这条河原则上是指伏尔加河,人们一般都认为它是沿着基麦克人(Kim k)和古斯人之间的边界,从额尔齐斯河由东至西地流淌,一直流到里海。额尔齐斯河就是这条河的支流,沿途流经康居和咸海以北的领土。参阅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第75、99、216和305页。另外,虽然尾音不同,但“阿得”与ātil很相似。(https://www.xing528.com)
k)和古斯人之间的边界,从额尔齐斯河由东至西地流淌,一直流到里海。额尔齐斯河就是这条河的支流,沿途流经康居和咸海以北的领土。参阅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第75、99、216和305页。另外,虽然尾音不同,但“阿得”与ātil很相似。(https://www.xing528.com)
 据《通典》(卷199)记载,“诃咥”是隋代(581—617年)对“阿跋”和“阿跌”人的称呼,“跋”是“跌”的另一种误写。《唐书》(卷217下,第6页)也把诃咥考证为阿跌,这也可能是以《通典》为依据而进行考证的。然而,我非常怀疑这种考证是否是以其他史料为基础的。唐代的典籍编纂家们,偶然发现了这两个转写名词之间的相似性。他们企图在较为古老的汉籍中寻找“阿跌”人的踪迹,尤其是在隋代的铁勒部族中寻求,完全如同《唐会要》的编纂者们在《隋书》中寻找有关黠戛斯人的踪迹一样。然而,我刚才已经讲到,阿跌人明显是在今中国新疆以北的部落中就已经提到的一个部族。另外,在7—8世纪的史料中,阿跌又似乎是西域东部地区的一个部族。7世纪的这部文献,又把诃咥人确定在西域的西部,康居以北和阿得河附近。阿得河似乎就相当于《世界境域志》中的Atil河,即伏尔加河(其上游一直延向西方,但这一问题至今仍处于设想阶段)。然而,“诃咥”这一转写词也与(即使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
据《通典》(卷199)记载,“诃咥”是隋代(581—617年)对“阿跋”和“阿跌”人的称呼,“跋”是“跌”的另一种误写。《唐书》(卷217下,第6页)也把诃咥考证为阿跌,这也可能是以《通典》为依据而进行考证的。然而,我非常怀疑这种考证是否是以其他史料为基础的。唐代的典籍编纂家们,偶然发现了这两个转写名词之间的相似性。他们企图在较为古老的汉籍中寻找“阿跌”人的踪迹,尤其是在隋代的铁勒部族中寻求,完全如同《唐会要》的编纂者们在《隋书》中寻找有关黠戛斯人的踪迹一样。然而,我刚才已经讲到,阿跌人明显是在今中国新疆以北的部落中就已经提到的一个部族。另外,在7—8世纪的史料中,阿跌又似乎是西域东部地区的一个部族。7世纪的这部文献,又把诃咥人确定在西域的西部,康居以北和阿得河附近。阿得河似乎就相当于《世界境域志》中的Atil河,即伏尔加河(其上游一直延向西方,但这一问题至今仍处于设想阶段)。然而,“诃咥”这一转写词也与(即使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 dil相当近似,这种形式与Atil/Itil/Idil/Etil一起作为伏尔加河的古名而出现过(见《金帐汗国史扎记》,第129页),另外,“曷截”这两个方块字也很像是Xazir的对音,这是曷萨人(或可萨人,即Khazar)的另一种写法。我认为完全应该转写成Xazir,即“伏尔加河流域的曷萨人”,这些部落也是众所周知的。据中世纪的某些地理学家们记载,曷(可)萨突厥人的都城就叫作ātil(或Adil,见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第161和452页)。
dil相当近似,这种形式与Atil/Itil/Idil/Etil一起作为伏尔加河的古名而出现过(见《金帐汗国史扎记》,第129页),另外,“曷截”这两个方块字也很像是Xazir的对音,这是曷萨人(或可萨人,即Khazar)的另一种写法。我认为完全应该转写成Xazir,即“伏尔加河流域的曷萨人”,这些部落也是众所周知的。据中世纪的某些地理学家们记载,曷(可)萨突厥人的都城就叫作ātil(或Adil,见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第161和452页)。
 苏拔又似乎是Suβar的对音。然而,在阿拉伯文中,Suwār也与Suβar很相似,在10世纪左右,这既是一个突厥部落的名称(伊斯兰作家们把他们与不里阿耳人和乌古斯人结合在一起了),同时又是可萨突厥人和不里阿耳人的一座城市名字,位于不里阿耳(Bolghary)东南30多俄里的地方,靠伏尔加河中游以东。请参阅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扎记》,第168—169,230—231页。
苏拔又似乎是Suβar的对音。然而,在阿拉伯文中,Suwār也与Suβar很相似,在10世纪左右,这既是一个突厥部落的名称(伊斯兰作家们把他们与不里阿耳人和乌古斯人结合在一起了),同时又是可萨突厥人和不里阿耳人的一座城市名字,位于不里阿耳(Bolghary)东南30多俄里的地方,靠伏尔加河中游以东。请参阅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扎记》,第168—169,230—231页。
 沙畹于《西突厥史料》第123页中建议将此考证为《唐书》(卷111,第2页)中的“三姓因麺”,即把得嶷海考证为贝加尔湖。然而,在康居以北和拜占庭以东的辽阔地域内,我们发现史籍中记载最多的还是里海与咸海。得嶷海肯定为突厥文t
沙畹于《西突厥史料》第123页中建议将此考证为《唐书》(卷111,第2页)中的“三姓因麺”,即把得嶷海考证为贝加尔湖。然而,在康居以北和拜占庭以东的辽阔地域内,我们发现史籍中记载最多的还是里海与咸海。得嶷海肯定为突厥文t ηiz的对音,意为“海”,这一点正如日本学者安部健夫于《西回鹘国史之研究》的导论第8页中所指出的那样。
ηiz的对音,意为“海”,这一点正如日本学者安部健夫于《西回鹘国史之研究》的导论第8页中所指出的那样。
 “都波”一名曾出现在一卷摩尼教经文写本中,很可能为9世纪时的作品(参阅F.W.K.米勒于《一页摩尼教赞美诗残卷》第11—70页、32页)。在今天,贝加尔湖西南的土瓦族即此民族的代表。
“都波”一名曾出现在一卷摩尼教经文写本中,很可能为9世纪时的作品(参阅F.W.K.米勒于《一页摩尼教赞美诗残卷》第11—70页、32页)。在今天,贝加尔湖西南的土瓦族即此民族的代表。
 浑(Xun/Qun)可能与欧洲人所说的Huns人以及远东人所说的匈奴人是相一致的。在4世纪初叶,粟特语中就把匈奴人写作Xwn,参阅W.B.享宁:《论古粟特文字的时间》,载《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报》,第12卷,第515页。
浑(Xun/Qun)可能与欧洲人所说的Huns人以及远东人所说的匈奴人是相一致的。在4世纪初叶,粟特语中就把匈奴人写作Xwn,参阅W.B.享宁:《论古粟特文字的时间》,载《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报》,第12卷,第515页。
 思结(Siqir/Siqar)在于阗文中肯定为Sika'r
思结(Siqir/Siqar)在于阗文中肯定为Sika'r 和Saikaira的对音,而在回鹘文中则为Siqir。参阅贝利(H.W.Bailey)于《大亚细亚杂志》第2卷,第1期,第19页的解释。另外,Saqar又是突厥蛮(土库曼)的一个部落名称(参阅《金帐汗国史扎记》第205页),因此,该部落也是起源于回鹘民族的,可能同样也与Siqar相接近。尽管人们可以把Siqar看作是动词siq-(压紧)的过去分词,但我更为倾向于认为这是以-qar/-air结尾的派生词,与药罗葛(Yarlaqar/Yarlaqir)、胡咄葛(Uturqar/Uturrur)和药勿葛(Yarmurqar/Yabūtt
和Saikaira的对音,而在回鹘文中则为Siqir。参阅贝利(H.W.Bailey)于《大亚细亚杂志》第2卷,第1期,第19页的解释。另外,Saqar又是突厥蛮(土库曼)的一个部落名称(参阅《金帐汗国史扎记》第205页),因此,该部落也是起源于回鹘民族的,可能同样也与Siqar相接近。尽管人们可以把Siqar看作是动词siq-(压紧)的过去分词,但我更为倾向于认为这是以-qar/-air结尾的派生词,与药罗葛(Yarlaqar/Yarlaqir)、胡咄葛(Uturqar/Uturrur)和药勿葛(Yarmurqar/Yabūtt kar
kar )等词的情况相似。参阅有关动词si-[粉碎,击败(军事力量)]的后缀形式-q°r/-°r等等,这样组成的新词的词义就是“击溃敌方力量者,打碎东西的人”。浦立本曾系统地把“思结”转写为Sik
)等词的情况相似。参阅有关动词si-[粉碎,击败(军事力量)]的后缀形式-q°r/-°r等等,这样组成的新词的词义就是“击溃敌方力量者,打碎东西的人”。浦立本曾系统地把“思结”转写为Sik r。但据我所知,这样的名词从未出现过(见浦立本于1952年在《通报》第41卷,第334页注释中的解释;《地理文献》,载人文科学研究所创建25周年纪念专刊号,1954年,第306页;《有关Toquzoghuz问题的简释》,第39页;《安禄山叛乱的历史背景》第168页)。事实上,我认为像sik
r。但据我所知,这样的名词从未出现过(见浦立本于1952年在《通报》第41卷,第334页注释中的解释;《地理文献》,载人文科学研究所创建25周年纪念专刊号,1954年,第306页;《有关Toquzoghuz问题的简释》,第39页;《安禄山叛乱的历史背景》第168页)。事实上,我认为像sik r这样的名词是不大可能存在的,因此此字只能是动词sik-的过去分词,其意义始终为“男性的性行为”,sik悉指男性生殖器。
r这样的名词是不大可能存在的,因此此字只能是动词sik-的过去分词,其意义始终为“男性的性行为”,sik悉指男性生殖器。
 参阅浦立本:《有关Toquzoghuz问题的简释》,第42页;有关九姓部的组成问题,见该文第39页。
参阅浦立本:《有关Toquzoghuz问题的简释》,第42页;有关九姓部的组成问题,见该文第39页。
 见《旧唐书》(卷67,第5页)和《唐书》(卷93,第4页)的李勣传;也请参阅《资治通鉴》(卷193,第9页)。
见《旧唐书》(卷67,第5页)和《唐书》(卷93,第4页)的李勣传;也请参阅《资治通鉴》(卷193,第9页)。
 事实上,毫无疑问,“俟利发”、“颉利发”、“吐利发”(只在《旧唐书》卷195,第2页出现过一次)和“希利发”(似乎还有许多其他同族复合词)都是古突厥文中的职称elt
事实上,毫无疑问,“俟利发”、“颉利发”、“吐利发”(只在《旧唐书》卷195,第2页出现过一次)和“希利发”(似乎还有许多其他同族复合词)都是古突厥文中的职称elt b?r/elt
b?r/elt β
β r的对音,尽管这种对音并不是完全和谐的(参阅伯希和:《有关西域的9条注释》,第225—229页)。在突厥统治时代,回鹘首领也享有这一尊号,组成突厥汗国其他部族的首领们也荣幸地冠戴这样的桂冠。此职官尊号在鲁尼文中写作(e)lt(
r的对音,尽管这种对音并不是完全和谐的(参阅伯希和:《有关西域的9条注释》,第225—229页)。在突厥统治时代,回鹘首领也享有这一尊号,组成突厥汗国其他部族的首领们也荣幸地冠戴这样的桂冠。此职官尊号在鲁尼文中写作(e)lt( )b(
)b( )r或(e)lt(
)r或(e)lt( )β(
)β( )r,而在回鹘文中则写作elt(
)r,而在回鹘文中则写作elt( )b
)b r,它很可能是一个复合词,由el(归附的民族、国家)+tabar/taβar(有、占有)而组成的(参阅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第1卷,第519页),此复合词在el之后很可能被鄂音化而成为t
r,它很可能是一个复合词,由el(归附的民族、国家)+tabar/taβar(有、占有)而组成的(参阅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第1卷,第519页),此复合词在el之后很可能被鄂音化而成为t b
b r/t
r/t β
β r。Eltabar的意思是“占有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可能是指归附了汗国的各民族的首领。Tabar/taβar确实是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其词义为“财产,各个人所拥有的东西”。动词tab-taβ的意思是“拥有、占有”,借助于施动后缀-ra就形成了Tabra/Taβra(拓跋),这就是征服中国北部的那个民族,本意是“主人,占有者”(参阅L·巴赞于《通报》第39卷,第294页的解释)。
r。Eltabar的意思是“占有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可能是指归附了汗国的各民族的首领。Tabar/taβar确实是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其词义为“财产,各个人所拥有的东西”。动词tab-taβ的意思是“拥有、占有”,借助于施动后缀-ra就形成了Tabra/Taβra(拓跋),这就是征服中国北部的那个民族,本意是“主人,占有者”(参阅L·巴赞于《通报》第39卷,第294页的解释)。
 “歌楞”可能是qaliη(陪嫁资产、嫁妆)的对音。它在9世纪的鲁尼文苏吉碑中就已经出现了(见兰司铁:《北蒙古发现的两块鲁尼文碑铭》第5页),在喀什噶里的辞典和其他地方也曾出现过。在一卷回鹘文文书中就出现过一个人名Qaliη,该文献已由拉德洛夫和马洛夫在《回鹘碑铭集》中发表,见第206—248页。
“歌楞”可能是qaliη(陪嫁资产、嫁妆)的对音。它在9世纪的鲁尼文苏吉碑中就已经出现了(见兰司铁:《北蒙古发现的两块鲁尼文碑铭》第5页),在喀什噶里的辞典和其他地方也曾出现过。在一卷回鹘文文书中就出现过一个人名Qaliη,该文献已由拉德洛夫和马洛夫在《回鹘碑铭集》中发表,见第206—248页。
 “莫何”是Bara的对音,这也是一种古突厥人的职称,明显是代表粟特文中的βr-(神),βr'是一个呼唤语。
“莫何”是Bara的对音,这也是一种古突厥人的职称,明显是代表粟特文中的βr-(神),βr'是一个呼唤语。
 据554年成书的《魏书》(卷101,第8页)高昌传记载,贪汗山位于赤石以北70里的地方,而赤石又位于高昌以北。一个世纪之后,《北史》(卷97,第4页)和《隋书》(卷83,第3页)又转抄了《魏书》的高昌传。即使在仲夏,贪汗山四周也遍布皑皑白雪。在此山之北,便是铁勒部的疆圉了。因此,今吐鲁番以北的博格达山就是5—10世纪时的贪汗山(Tamr an)。也请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第95、363页;《旧唐书》卷199下,第1页。然而,正如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64页中所指出的那样,10世纪的地理书《世界境域志》(见米诺尔斯基文第62、94、195页)所描述的Tafqān山即贪汗山之对音,我于1958年在《通报》第46卷,第144页未能考证出来。Tafqān似乎是Tanran的一种特殊发音,该词中中世纪的辅音已经清化(-mr->-fq-)。另外,在8世纪的鲁尼文古突厥碑铭中,我们又发现三位都叫作Tamran的人,有两位是Tamran达干(Taqan),一位是Tamran啜(
据554年成书的《魏书》(卷101,第8页)高昌传记载,贪汗山位于赤石以北70里的地方,而赤石又位于高昌以北。一个世纪之后,《北史》(卷97,第4页)和《隋书》(卷83,第3页)又转抄了《魏书》的高昌传。即使在仲夏,贪汗山四周也遍布皑皑白雪。在此山之北,便是铁勒部的疆圉了。因此,今吐鲁番以北的博格达山就是5—10世纪时的贪汗山(Tamr an)。也请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第95、363页;《旧唐书》卷199下,第1页。然而,正如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64页中所指出的那样,10世纪的地理书《世界境域志》(见米诺尔斯基文第62、94、195页)所描述的Tafqān山即贪汗山之对音,我于1958年在《通报》第46卷,第144页未能考证出来。Tafqān似乎是Tanran的一种特殊发音,该词中中世纪的辅音已经清化(-mr->-fq-)。另外,在8世纪的鲁尼文古突厥碑铭中,我们又发现三位都叫作Tamran的人,有两位是Tamran达干(Taqan),一位是Tamran啜( Cor)。参阅翁金(Qngin)碑第4行;伊赫阿塞特(Ihe-Ashete)碑第1行;《古突厥碑铭》,第1卷,第128页,第2卷,第122页。
Cor)。参阅翁金(Qngin)碑第4行;伊赫阿塞特(Ihe-Ashete)碑第1行;《古突厥碑铭》,第1卷,第128页,第2卷,第122页。
Tamran一词可能应归纳为以-xan/-qan/k n结尾的山和神的名字,这一后缀的意思可能为“汗”(Xan,执政者、王爷),请参阅班格于《匈牙利年鉴》第5卷,第248—251页的解释;葛玛丽:《古突厥语语法》第48页。例如,有一个词叫作burxan(布尔罕,佛陀),即突厥语中的bur(佛陀)+ xan而组成的;p
n结尾的山和神的名字,这一后缀的意思可能为“汗”(Xan,执政者、王爷),请参阅班格于《匈牙利年鉴》第5卷,第248—251页的解释;葛玛丽:《古突厥语语法》第48页。例如,有一个词叫作burxan(布尔罕,佛陀),即突厥语中的bur(佛陀)+ xan而组成的;p rik
rik n的意思是“仙女皇后”,即由p
n的意思是“仙女皇后”,即由p ri(仙女)+k
ri(仙女)+k n>xan而组成;Qad
n>xan而组成;Qad rqan是一座山的名字,即肯忒山,是由qad
rqan是一座山的名字,即肯忒山,是由qad r-(陡峭的)+qan/ xan而组成的;
r-(陡峭的)+qan/ xan而组成的; tük
tük n也是一个山名,即于都斤山(或乌德建山),它是由
n也是一个山名,即于都斤山(或乌德建山),它是由 tüg(祈祷)+kan<xan等组成的。对于Tamran一词,我们肯定应该作如下之剖析:tam(城墙、工事)+rana<xan,其意思就是“城堡里的王爷”。
tüg(祈祷)+kan<xan等组成的。对于Tamran一词,我们肯定应该作如下之剖析:tam(城墙、工事)+rana<xan,其意思就是“城堡里的王爷”。
 唯有《北史》中写作“子”,在其它所有的史料中都写作“字”,但在此处则令人莫名其妙。
唯有《北史》中写作“子”,在其它所有的史料中都写作“字”,但在此处则令人莫名其妙。
 有关这些事件,请参阅《旧唐书》卷199下,第1—3页,刘茂才在《关于东突厥史的汉文资料》第354—358页中对此有译文;《唐书》卷217下,第3页以下;《唐会要》卷96,第13—17页;《通典》卷199的薛延陀传。
有关这些事件,请参阅《旧唐书》卷199下,第1—3页,刘茂才在《关于东突厥史的汉文资料》第354—358页中对此有译文;《唐书》卷217下,第3页以下;《唐会要》卷96,第13—17页;《通典》卷199的薛延陀传。
 参阅米诺尔斯基:《塔明·伊本·巴赫尔在回鹘人地区的游记》,载《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报》,1948年,第12卷,第287和301页。
参阅米诺尔斯基:《塔明·伊本·巴赫尔在回鹘人地区的游记》,载《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报》,1948年,第12卷,第287和301页。
 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第311—312页。
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第311—312页。
 尤其请参阅F.夏德(Hirth):《暾欲谷碑跋》,1898年版,第43页;J.马夸特:《东欧东亚漫游记》,1903年版,第45页;羽田亨:《论九姓回鹘和Tonguz Qruz的关系》第347、372和385页;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之研究》,1955年版,导论第13页;克劳松(Gérard Clauson)于1957年在《亚细亚学报》第245卷,第21页的解释。
尤其请参阅F.夏德(Hirth):《暾欲谷碑跋》,1898年版,第43页;J.马夸特:《东欧东亚漫游记》,1903年版,第45页;羽田亨:《论九姓回鹘和Tonguz Qruz的关系》第347、372和385页;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之研究》,1955年版,导论第13页;克劳松(Gérard Clauson)于1957年在《亚细亚学报》第245卷,第21页的解释。
 “袁纥”肯定就是554年成书的《魏书》卷103,第9页高车传中的“敕勒”第2个部族在唐代的名称,尽管在《魏书》的现今版本中误写作“表纥”,在同一传记的下文(第10页)又提到高车部的一位首领名叫袁纥乌。然而,在766—801年编纂成书的《通典》(卷196)、1005—1013年成书的《册府元龟》(卷956,第33页)和1060年出版的《唐书》都写作“袁纥”,而这几部书的底本都是唐代版本的《魏书》。
“袁纥”肯定就是554年成书的《魏书》卷103,第9页高车传中的“敕勒”第2个部族在唐代的名称,尽管在《魏书》的现今版本中误写作“表纥”,在同一传记的下文(第10页)又提到高车部的一位首领名叫袁纥乌。然而,在766—801年编纂成书的《通典》(卷196)、1005—1013年成书的《册府元龟》(卷956,第33页)和1060年出版的《唐书》都写作“袁纥”,而这几部书的底本都是唐代版本的《魏书》。
然而,如果这里确实是指回纥人,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那么“袁纥”这种对音字则是很奇怪的。“袁”也很可能是与它很相似的另一个字“韦”之误,因为在隋代(581—617),“韦纥”是Uyrur所惯用的转写词。另外,我们可以假设最早曾有过一个“袁韦纥”的对音名称,而后来“韦”字脱落了。因为只有“袁韦纥”才能准确地对音为回鹘人自己所使用的名词On-Uyrur(十姓回鹘)。有关这些字的古代对音,还必须指出另一点,高本汉汉语拼音法中的j-很可能应该修订为rj-,在突厥语声的元音之前,rj-具体起一种分音的作用(见《五代回鹘史》第161—162页)。
 在7世纪时,乌桓的一些使节们曾抵达唐天朝宫庭(《旧唐书》卷199下,第7页;《唐书》卷219,第5页)在908年间,乌桓人受到了契丹人的攻击(《辽史》卷1,第2页)。请参阅米利耶(Jos.Mullié):《饶乐河考》,载《通报》第30卷,见第186页注2。然而,我还必须指出,克劳松(见1957年《亚细亚学报》第245卷,第21页)又认为乌古斯正是乌桓。他曾经写道(《突厥、蒙古、通古斯杂考》,载《大亚细亚杂志》第8卷,第1期,第117页):“仅次于匈奴而著名的突厥部落中不仅包括突厥人,而且还有Tav
在7世纪时,乌桓的一些使节们曾抵达唐天朝宫庭(《旧唐书》卷199下,第7页;《唐书》卷219,第5页)在908年间,乌桓人受到了契丹人的攻击(《辽史》卷1,第2页)。请参阅米利耶(Jos.Mullié):《饶乐河考》,载《通报》第30卷,见第186页注2。然而,我还必须指出,克劳松(见1957年《亚细亚学报》第245卷,第21页)又认为乌古斯正是乌桓。他曾经写道(《突厥、蒙古、通古斯杂考》,载《大亚细亚杂志》第8卷,第1期,第117页):“仅次于匈奴而著名的突厥部落中不仅包括突厥人,而且还有Tav ga
ga 人和乌古斯人;如果在早期的汉文文献中没有提到他们,那是非常奇怪的”。
人和乌古斯人;如果在早期的汉文文献中没有提到他们,那是非常奇怪的”。
 参阅《旧唐书》卷195,第1页,由沙畹翻译发表在《西突厥史料》第91页;《唐书》卷217上,第2页。
参阅《旧唐书》卷195,第1页,由沙畹翻译发表在《西突厥史料》第91页;《唐书》卷217上,第2页。
 有关orul这一古突厥职官尊号,请参阅羽田亨:《有关摩尼教祈祷文残卷的考证》,载《东洋文库研究部论丛》,1932年第6期,见第5页。有关Ulan的问题,请参阅A.莫克林斯基所编写的由突厥文派生而来的波兰文辞典,1858年圣彼得堡版,第139页。
有关orul这一古突厥职官尊号,请参阅羽田亨:《有关摩尼教祈祷文残卷的考证》,载《东洋文库研究部论丛》,1932年第6期,见第5页。有关Ulan的问题,请参阅A.莫克林斯基所编写的由突厥文派生而来的波兰文辞典,1858年圣彼得堡版,第139页。
 参阅阙特勒碑北侧第12行。有关这段碑文的释读,请参阅克列佳斯托尔尼:《阙特勒碑中的粟特文b
参阅阙特勒碑北侧第12行。有关这段碑文的释读,请参阅克列佳斯托尔尼:《阙特勒碑中的粟特文b r
r k
k r bugaraq释读》,载《中亚学报》,1958年,第3卷,第245—251页。
r bugaraq释读》,载《中亚学报》,1958年,第3卷,第245—251页。
 参阅内梅特:《匈牙利人和马扎尔人》,1930年布达佩斯版,第114页;羽田亨:《论九姓回鹘和Toquz oruz的关系》,第386页;克劳松于1957年在《亚细亚学报》第21页发表的文章和1960年在《大亚细亚杂志》第8卷,第117页的考释。也请参阅塞诺尔:《论5世纪左右的一次民族大迁移》,第11页,作者摒弃了内梅特的建议。
参阅内梅特:《匈牙利人和马扎尔人》,1930年布达佩斯版,第114页;羽田亨:《论九姓回鹘和Toquz oruz的关系》,第386页;克劳松于1957年在《亚细亚学报》第21页发表的文章和1960年在《大亚细亚杂志》第8卷,第117页的考释。也请参阅塞诺尔:《论5世纪左右的一次民族大迁移》,第11页,作者摒弃了内梅特的建议。
 见格罗特(De Groot):《公元前时期的匈奴人》,1921年柏林和来比锡版,第79页,作者在文中就已经提醒大家注意,“呼揭”完全相当于Uyur(回鹘)。
见格罗特(De Groot):《公元前时期的匈奴人》,1921年柏林和来比锡版,第79页,作者在文中就已经提醒大家注意,“呼揭”完全相当于Uyur(回鹘)。
 参阅高本汉:《汉语词族》,载《远东古迹博物馆学报》,1933年,第5卷,第18—38页;W.西蒙:《古汉字复原》,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通报》,第9卷,第270—276页。
参阅高本汉:《汉语词族》,载《远东古迹博物馆学报》,1933年,第5卷,第18—38页;W.西蒙:《古汉字复原》,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通报》,第9卷,第270—276页。
 《拜占庭突厥史料汇编》第2卷,第219和227页列举了这些名词的各种不同写法。
《拜占庭突厥史料汇编》第2卷,第219和227页列举了这些名词的各种不同写法。
 有关普利斯科斯的这篇文章,请参阅莫拉夫斯季科:《十姓回鹘人的历史》第60—61页;塞诺尔:《大迁徙》第1卷以下。
有关普利斯科斯的这篇文章,请参阅莫拉夫斯季科:《十姓回鹘人的历史》第60—61页;塞诺尔:《大迁徙》第1卷以下。
 有关萨拉回鹘人的问题,请参阅莫拉夫斯季科:《十姓回鹘人的历史》第60—61页;内梅特根据莫拉夫斯季科的考证,而将Saragur改作
有关萨拉回鹘人的问题,请参阅莫拉夫斯季科:《十姓回鹘人的历史》第60—61页;内梅特根据莫拉夫斯季科的考证,而将Saragur改作 ar(y)ogur(白回鹘人),因为他认为Saragur人操一种近代楚瓦什人那种类型的突厥方言。在该方言中,
ar(y)ogur(白回鹘人),因为他认为Saragur人操一种近代楚瓦什人那种类型的突厥方言。在该方言中, ura<Sarir的意思是“白色”。然而,在普通古突厥语中,Sarir似乎是指“黄白色”,yürη系指“乳白色”,aq为“灰白色,白马马衣的颜色”;尤其是在近代土耳其语中,sararmak完全系指“变成白色”,sapsari则为“全白,苍白”。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引证楚瓦什语以进行解释。另外,可萨突厥人的Sarigh
ura<Sarir的意思是“白色”。然而,在普通古突厥语中,Sarir似乎是指“黄白色”,yürη系指“乳白色”,aq为“灰白色,白马马衣的颜色”;尤其是在近代土耳其语中,sararmak完全系指“变成白色”,sapsari则为“全白,苍白”。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引证楚瓦什语以进行解释。另外,可萨突厥人的Sarigh in城在阿拉伯语中就为“白色”的意思,他们在顿河流城建立的军事城堡Sarkel就被其他民族称之为“白帐”。在此问题上,请参阅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扎记》第214—215页。伯希和的作法正好相反,他正是引证了楚瓦什语来解释这些名词的。
in城在阿拉伯语中就为“白色”的意思,他们在顿河流城建立的军事城堡Sarkel就被其他民族称之为“白帐”。在此问题上,请参阅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扎记》第214—215页。伯希和的作法正好相反,他正是引证了楚瓦什语来解释这些名词的。
 参阅布勒士奈德(Bretschneider):《中世纪研究》,第1卷,第263页;拉德洛夫:《福乐智慧》第1卷,第72页。
参阅布勒士奈德(Bretschneider):《中世纪研究》,第1卷,第263页;拉德洛夫:《福乐智慧》第1卷,第72页。
 参阅莫拉夫斯季科:《十姓回鹘人的历史》第59页;塞诺尔:《论5世纪时的一次民族大迁移》,第15—34页。在塞诺尔的论著中,我没有发现任何有力的证据,能将460年前的萨毗人置于乌拉尔山以西的南俄罗斯。
参阅莫拉夫斯季科:《十姓回鹘人的历史》第59页;塞诺尔:《论5世纪时的一次民族大迁移》,第15—34页。在塞诺尔的论著中,我没有发现任何有力的证据,能将460年前的萨毗人置于乌拉尔山以西的南俄罗斯。
 参阅福兰阁(Q.Franke):《中华帝国史》第3卷,第283页以下。Aβar一词明显就相当于动词aβ-(意为“在周围集合了许多人”)的过去分词。喀什噶里大辞典在《索引》第50—51页中,又提到了一个派生词aβala-(指一群乱无秩序的人集合起来)。汉人可能受到了Aβar一词此义的影响,所以就用它来指蠕蠕人(意为像昆虫一样蠕动)。
参阅福兰阁(Q.Franke):《中华帝国史》第3卷,第283页以下。Aβar一词明显就相当于动词aβ-(意为“在周围集合了许多人”)的过去分词。喀什噶里大辞典在《索引》第50—51页中,又提到了一个派生词aβala-(指一群乱无秩序的人集合起来)。汉人可能受到了Aβar一词此义的影响,所以就用它来指蠕蠕人(意为像昆虫一样蠕动)。
 有关阿卡齐尔人的问题,请参阅《拜占庭突厥资料汇编》第2卷;马夸特:《东欧东亚漫游记》,第40—43页;塞诺尔:《论5世纪时的一次民族大迁移》,第1—4页。
有关阿卡齐尔人的问题,请参阅《拜占庭突厥资料汇编》第2卷;马夸特:《东欧东亚漫游记》,第40—43页;塞诺尔:《论5世纪时的一次民族大迁移》,第1—4页。
 豪沃思(Henry H.Howorth)于1879年,就已经认为阿卡齐尔人就相当于白可萨人(Aq-Xazar),他们与10世纪时代伊斯兰史料中的黑可萨人(Qara-Khazar)相对称(参阅马夸特:《欧东亚漫游记》第41页注)。我们确实知道,突厥—蒙古人部落的名称前面常常带有一个形容颜色的词,如上文所提到的黄回鹘人(Sarigh-Uyghur)和黑可萨人(Qara-Khazar),波斯的白羊王朝(Aq-Qoyunlu)和黑羊王朝(Qara-Qoyunlu),蓝突厥人(K
豪沃思(Henry H.Howorth)于1879年,就已经认为阿卡齐尔人就相当于白可萨人(Aq-Xazar),他们与10世纪时代伊斯兰史料中的黑可萨人(Qara-Khazar)相对称(参阅马夸特:《欧东亚漫游记》第41页注)。我们确实知道,突厥—蒙古人部落的名称前面常常带有一个形容颜色的词,如上文所提到的黄回鹘人(Sarigh-Uyghur)和黑可萨人(Qara-Khazar),波斯的白羊王朝(Aq-Qoyunlu)和黑羊王朝(Qara-Qoyunlu),蓝突厥人(K k-Türk)和黑契丹人(Qara-khita)等等。在这方面,白匈奴人或厌口哒人(Hephthalites)的情况可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怀疑在Akatzir与Khazar人之间存在有一定的相似性。厌口哒人在拜占庭史料中又被称为“白匈奴人”,可萨人的两座主要城市也都带有“白色”的形容词(参阅马夸特于1898年在《维也纳东方学杂志》第12卷,第194—200页发表的文章:《东欧东亚漫游记》第1页以下)。我们很可能应该到汉人宇宙观中有关颜色象征的看法方面,去寻找带颜色的部落名称之原因。汉人一般都认为白色指西方,黑色指北方,青蓝色象征着东方,红色表示南方,而黄色则代表着中央,即中国中原地区。我们早已经知道了们的宇宙观中有许多成份,尤其是那些与日历有关的思想,而在阿尔泰民族中,在很早以前也就采取了这些观点。
k-Türk)和黑契丹人(Qara-khita)等等。在这方面,白匈奴人或厌口哒人(Hephthalites)的情况可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怀疑在Akatzir与Khazar人之间存在有一定的相似性。厌口哒人在拜占庭史料中又被称为“白匈奴人”,可萨人的两座主要城市也都带有“白色”的形容词(参阅马夸特于1898年在《维也纳东方学杂志》第12卷,第194—200页发表的文章:《东欧东亚漫游记》第1页以下)。我们很可能应该到汉人宇宙观中有关颜色象征的看法方面,去寻找带颜色的部落名称之原因。汉人一般都认为白色指西方,黑色指北方,青蓝色象征着东方,红色表示南方,而黄色则代表着中央,即中国中原地区。我们早已经知道了们的宇宙观中有许多成份,尤其是那些与日历有关的思想,而在阿尔泰民族中,在很早以前也就采取了这些观点。
然而,阿卡齐尔人更可能是以哈兹尔人(Qazir,甚至是Aq-Xazir中的Xazir)为前提的,还有以-ir结尾的另一种写法Qazar/Xazar,而在亚美尼亚文中确实曾出现过Xazirk一词(见《东欧东亚漫游记》第1页注),它可能就是汉语中“曷截”的对音。另外,在过去分词后缀-°r中,a/i经常交替使用,这在古突厥语中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在此情况下,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伯希和在《金帐汗国史扎记》第210—214页中,也轻易地对拉德洛夫(《福乐智慧》第1卷,第73页)、胡茨玛(Houtsma:《突厥语—阿拉伯语词汇集》第23—24页)、马夸特(《东欧东亚漫游记》第41页)和其他人(参阅《论5世纪时的一次民族大迁移》第2—4页)在Akatzir和Agha-eri之间进行的比较,我认为这种考订是非常令人质疑的。Agha-eri是一个奇怪的名词,一般都认为系指“林中百姓”,无论是在由胡特茨玛部分发表的1245年的阿拉伯—突厥和波斯—蒙古辞汇集中,还是在部落名单中,都曾经出现过这个字。据拉施特认为,这些部落最终都起源于乌古斯汗。事实上,在Akatzir和Agha-eri之间,从语音角度来讲,并不十分相似(其中有两个a与一个r相同);以- ri(人)结尾的这种形式作为部落名称,则是无先例可循的,至少在古代是这样的;agha的意思是“树棵”,而不是“森林”,据我所知,此字只是从13世纪起才出现。在古突厥语中,“森林”是i,而“树棵”则是igha。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唯一提到这个奇特的突厥词Agha
ri(人)结尾的这种形式作为部落名称,则是无先例可循的,至少在古代是这样的;agha的意思是“树棵”,而不是“森林”,据我所知,此字只是从13世纪起才出现。在古突厥语中,“森林”是i,而“树棵”则是igha。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唯一提到这个奇特的突厥词Agha c-eri的两部文献,恰巧是13世纪蒙古人统治波斯时代的作品,那也并非偶然。如果此词在以上两部著作中均被确定为“林中百姓”,那么,其意实际上可能是指“树丛中的人”。这也可能是由于模仿外来语(蒙古语或波斯语)而造成的结果,在蒙古统治时代,这也是波斯颇为时髦的一种习惯,完全如同1245年的辞汇集中所列举的由-
c-eri的两部文献,恰巧是13世纪蒙古人统治波斯时代的作品,那也并非偶然。如果此词在以上两部著作中均被确定为“林中百姓”,那么,其意实际上可能是指“树丛中的人”。这也可能是由于模仿外来语(蒙古语或波斯语)而造成的结果,在蒙古统治时代,这也是波斯颇为时髦的一种习惯,完全如同1245年的辞汇集中所列举的由- ri组成的复合词一览表所指出的那样:Qum-
ri组成的复合词一览表所指出的那样:Qum- ri(沙漠人)、Türük-
ri(沙漠人)、Türük- ri(突厥人)、Rūm-
ri(突厥人)、Rūm- ri(拂林人)
ri(拂林人) arq-
arq- ri(东方人)、ū
ri(东方人)、ū j-ri(边界人)。
j-ri(边界人)。
 参阅莫拉夫斯季科:《十姓回鹘人的历史》第62页。
参阅莫拉夫斯季科:《十姓回鹘人的历史》第62页。
 参阅马夸特:《东欧东亚漫游记》,第356页;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50页;莫拉夫斯季科,同上引书,61页。
参阅马夸特:《东欧东亚漫游记》,第356页;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50页;莫拉夫斯季科,同上引书,61页。
 这是梅南特洛斯的看法。参阅莫拉夫斯季科:同上引书,第63页;《拜占庭突厥资料汇编》第1卷,第70和424页。
这是梅南特洛斯的看法。参阅莫拉夫斯季科:同上引书,第63页;《拜占庭突厥资料汇编》第1卷,第70和424页。
 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30页;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3卷,第288页。
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30页;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3卷,第288页。
 莫拉夫斯季科:《拜占庭突厥资料汇编》第1卷,第546页;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30、231、247页;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3卷,第285—286页;塞诺尔:《论5世纪时的一次民族大迁移》,第34—35页。
莫拉夫斯季科:《拜占庭突厥资料汇编》第1卷,第546页;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30、231、247页;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3卷,第285—286页;塞诺尔:《论5世纪时的一次民族大迁移》,第34—35页。
 详见梅南特洛斯的考证。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38页;莫拉夫斯季科:《拜占庭史料汇编》,第1卷,第424页。
详见梅南特洛斯的考证。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38页;莫拉夫斯季科:《拜占庭史料汇编》,第1卷,第424页。
 梅南特洛斯的考证。参阅《拜占庭突厥资料汇编》,第1卷,第65和424页。
梅南特洛斯的考证。参阅《拜占庭突厥资料汇编》,第1卷,第65和424页。
 引自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47页。
引自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47页。
 见莫拉夫斯季科:《十姓回鹘人的历史》第64、71—74页;《拜占庭突厥资料汇编》,第1卷,第65—66页。十分遗憾,根据作者的假设,十姓回鹘人可能在大不里阿耳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这一假设却几乎完全是以一种相当不可靠的考证为基础的,即假设On-Oghundur与On-oghur是一致的,均指十姓回鹘人。因为在大不里阿耳国的问题上,史料中所讲的并不是On-Oghur人,而是Onoghur人。
见莫拉夫斯季科:《十姓回鹘人的历史》第64、71—74页;《拜占庭突厥资料汇编》,第1卷,第65—66页。十分遗憾,根据作者的假设,十姓回鹘人可能在大不里阿耳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这一假设却几乎完全是以一种相当不可靠的考证为基础的,即假设On-Oghundur与On-oghur是一致的,均指十姓回鹘人。因为在大不里阿耳国的问题上,史料中所讲的并不是On-Oghur人,而是Onoghur人。
 参阅《十姓回鹘人的历史》第67—68页;《拜占庭突厥资料汇编》第1卷,第66页。
参阅《十姓回鹘人的历史》第67—68页;《拜占庭突厥资料汇编》第1卷,第66页。
 参阅《拜占庭突厥资料汇编》第1卷,第463—465页。
参阅《拜占庭突厥资料汇编》第1卷,第463—465页。
 在拜占庭史料中,从837年起才首次提到了十姓回鹘人,参阅莫拉夫斯季科:《十姓回鹘人的历史》第80页。有关匈牙利人的名字是从十姓回鹘人的名称派生而来的问题,请参阅蒙卡西(Munkacsi):《回人的起源问题》,载《匈牙利人种学报》第5卷,1896年版,第7—10页,89—92页;G·内梅特:《十姓回鹘》第148页以下;莫拉夫斯季科:《十姓回鹘人的历史》第81—82页。
在拜占庭史料中,从837年起才首次提到了十姓回鹘人,参阅莫拉夫斯季科:《十姓回鹘人的历史》第80页。有关匈牙利人的名字是从十姓回鹘人的名称派生而来的问题,请参阅蒙卡西(Munkacsi):《回人的起源问题》,载《匈牙利人种学报》第5卷,1896年版,第7—10页,89—92页;G·内梅特:《十姓回鹘》第148页以下;莫拉夫斯季科:《十姓回鹘人的历史》第81—82页。
 最后一次提供带有时间记载的人可能为阿加东(Agathon),他是在读到712—713年Unnoghur-Bulghar人的入侵时才提到的。参阅《拜占庭突厥资料汇编》第1卷,第217页。
最后一次提供带有时间记载的人可能为阿加东(Agathon),他是在读到712—713年Unnoghur-Bulghar人的入侵时才提到的。参阅《拜占庭突厥资料汇编》第1卷,第217页。
 请参阅莫拉夫斯季科所列举的有关回鹘人和匈牙利人种起源的参考书目,见《拜占庭突厥资料汇编》第1卷,第67、134—145页。
请参阅莫拉夫斯季科所列举的有关回鹘人和匈牙利人种起源的参考书目,见《拜占庭突厥资料汇编》第1卷,第67、134—145页。
 尤其请参阅蒙卡西:同上引书,第90页。作者在这部1896年的著作中,特别参阅了许多更为古老的那些将Oghur考订为Oghuz的名著。另外,一旦当他接受了古突厥语中颤音化的原则之后,便认为理所当然地应将6世纪时代的突厥部落Uturghur考订为Otur-Oghur(Otuz-Oghugh,即三十姓乌古斯),而Kuturghur就完全应该是由于Tokurghur的字母易位造成的,也就是说Tokur-oghur=Toguz-Oghuz,即人所共知的“九姓部”。参阅内梅特:《十姓回鹘》第151页。
尤其请参阅蒙卡西:同上引书,第90页。作者在这部1896年的著作中,特别参阅了许多更为古老的那些将Oghur考订为Oghuz的名著。另外,一旦当他接受了古突厥语中颤音化的原则之后,便认为理所当然地应将6世纪时代的突厥部落Uturghur考订为Otur-Oghur(Otuz-Oghugh,即三十姓乌古斯),而Kuturghur就完全应该是由于Tokurghur的字母易位造成的,也就是说Tokur-oghur=Toguz-Oghuz,即人所共知的“九姓部”。参阅内梅特:《十姓回鹘》第151页。
 有关某几种古突厥语中所谓颤音化的问题,请参阅蒙卡西:同上引文;马夸特:《论库曼人的民族特征》,第200—201页;《匈牙利年鉴》,1929年,第9卷,第88页以下;贡博茨(Gombocz):《不里阿耳—突厥文词汇》,载《芬兰—乌戈尔语学会论丛》,1912年,第30卷,第196页以下;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扎记》第209页;塞诺尔:《论5世纪时的一次民族大迁移》第5—6页;J.本辛(J.Benzing):《土耳其基础语言学》,1959年威士巴登版,第697页;巴托尔德于《伊斯兰百科全书》第805页在Bulghār(不里阿耳)一条目下所作的注释;G.克劳松:《突厥、蒙古、通古斯考》,载1960年《大亚细亚杂志》第8卷,第117页。
有关某几种古突厥语中所谓颤音化的问题,请参阅蒙卡西:同上引文;马夸特:《论库曼人的民族特征》,第200—201页;《匈牙利年鉴》,1929年,第9卷,第88页以下;贡博茨(Gombocz):《不里阿耳—突厥文词汇》,载《芬兰—乌戈尔语学会论丛》,1912年,第30卷,第196页以下;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扎记》第209页;塞诺尔:《论5世纪时的一次民族大迁移》第5—6页;J.本辛(J.Benzing):《土耳其基础语言学》,1959年威士巴登版,第697页;巴托尔德于《伊斯兰百科全书》第805页在Bulghār(不里阿耳)一条目下所作的注释;G.克劳松:《突厥、蒙古、通古斯考》,载1960年《大亚细亚杂志》第8卷,第117页。
 有关这些碑铭,请参阅J.本辛:《土耳其基础语言学》,第692—693和697页;贡博茨:《不里阿耳—突厥文词汇》第202页以下;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第430页和图12.
有关这些碑铭,请参阅J.本辛:《土耳其基础语言学》,第692—693和697页;贡博茨:《不里阿耳—突厥文词汇》第202页以下;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第430页和图12.
 见马夸特于《维也纳东方学报》第12卷,1898年,第193页的解释;《论古突厥碑铭的时间》,1898年版,第81页注(作者在文中认为Uighur是此名最正确的音标)和第95页。1903年在《东欧东亚漫游记》第45页中,作者又放弃了他原来将此名考证为Uyghur的作法,最后终于同意了那种认为此字是Oghuz颤音化结果的论点;参阅《论库蛮人的特征》第200页;《匈牙利年鉴》,1929年,第89页。
见马夸特于《维也纳东方学报》第12卷,1898年,第193页的解释;《论古突厥碑铭的时间》,1898年版,第81页注(作者在文中认为Uighur是此名最正确的音标)和第95页。1903年在《东欧东亚漫游记》第45页中,作者又放弃了他原来将此名考证为Uyghur的作法,最后终于同意了那种认为此字是Oghuz颤音化结果的论点;参阅《论库蛮人的特征》第200页;《匈牙利年鉴》,1929年,第89页。
 参阅李默德(M.F.Grenard):《有关萨土克·布格拉汗的传说》,载1900年的《亚细亚学报》,见第17页注。
参阅李默德(M.F.Grenard):《有关萨土克·布格拉汗的传说》,载1900年的《亚细亚学报》,见第17页注。
 莫拉夫斯季科在《拜占庭突厥资料汇编》第2卷,第219页中把Uighur和Uighor都列在了Onoghur一栏中了。另外,还有人把Uighur看作是Utighur之误。参阅莫拉夫斯季科:同上引书;马夸特:《论古突厥碑铭的时间》第81页注。
莫拉夫斯季科在《拜占庭突厥资料汇编》第2卷,第219页中把Uighur和Uighor都列在了Onoghur一栏中了。另外,还有人把Uighur看作是Utighur之误。参阅莫拉夫斯季科:同上引书;马夸特:《论古突厥碑铭的时间》第81页注。
 有关西耐—乌苏碑,请参阅G.J.兰司铁:《在北蒙古发现的两块鲁尼文碑》,第12、13和44页,作者是这样来理解这句话的:“停留在(大河地区)的民族统治了十姓回鹘和九姓部族达100年……”。相反,根据L·巴赞教授的指点,我却把On-Uyghur作为了全句的主语,而qaImi
有关西耐—乌苏碑,请参阅G.J.兰司铁:《在北蒙古发现的两块鲁尼文碑》,第12、13和44页,作者是这样来理解这句话的:“停留在(大河地区)的民族统治了十姓回鹘和九姓部族达100年……”。相反,根据L·巴赞教授的指点,我却把On-Uyghur作为了全句的主语,而qaImi i bodun为“(包括)那些……留下来的民族”,它仅仅是作为修饰词而使用的。我们可以对兰司铁的解释提出异议,人们实际上根本不可能会发现一个“民族”(bodun,盟bod的集合名词,指一个小部落)会“统治”(üz
i bodun为“(包括)那些……留下来的民族”,它仅仅是作为修饰词而使用的。我们可以对兰司铁的解释提出异议,人们实际上根本不可能会发现一个“民族”(bodun,盟bod的集合名词,指一个小部落)会“统治”(üz olur-)两个部落联盟,或者是一个有限的政治联盟可以居于另一个范围更大的联盟之上。
olur-)两个部落联盟,或者是一个有限的政治联盟可以居于另一个范围更大的联盟之上。
 见葛玛丽和温特(W.Winter):《吐鲁番突厥文献集》第9卷,第18页。
见葛玛丽和温特(W.Winter):《吐鲁番突厥文献集》第9卷,第18页。
 我主要是根据贝尔津(Berezin)的版本而引证拉施特的著作的。有时也根据拉德洛夫的版本而引证:《福乐智慧》第1卷,第25—26页,作者发表了德译文。
我主要是根据贝尔津(Berezin)的版本而引证拉施特的著作的。有时也根据拉德洛夫的版本而引证:《福乐智慧》第1卷,第25—26页,作者发表了德译文。
 我觉得,浦立本(《有关Toquzoghuz问题的简释》第41页)中,对塔明·伊本·巴赫尔的一篇文献所作的非常高明的解释足可以证明,在9世纪初叶,蒙古高原地区肯定存在有一个十姓回鹘和九姓部族的政治联盟。
我觉得,浦立本(《有关Toquzoghuz问题的简释》第41页)中,对塔明·伊本·巴赫尔的一篇文献所作的非常高明的解释足可以证明,在9世纪初叶,蒙古高原地区肯定存在有一个十姓回鹘和九姓部族的政治联盟。
 有关俟利发(El-t
有关俟利发(El-t bir)这一职称:见上文注;有关屈俟斤(K
bir)这一职称:见上文注;有关屈俟斤(K l irkin)这一职称,见上文注⑩。
l irkin)这一职称,见上文注⑩。
 见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扎记》第229页;德尼:《突厥语语法》第931页。同一个后缀肯定是以清喉音的形式为代表的:-qur/-qar/-qir和-kür/-kar/-kir。有关古突厥语中清浊喉音和后缀声韵之间的变化问题,见葛玛丽:《古突厥语语法》§37。
见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扎记》第229页;德尼:《突厥语语法》第931页。同一个后缀肯定是以清喉音的形式为代表的:-qur/-qar/-qir和-kür/-kar/-kir。有关古突厥语中清浊喉音和后缀声韵之间的变化问题,见葛玛丽:《古突厥语语法》§37。
 当然,我们可以非常严格地理解动词Oy-(挖、压),其中的一种派生形式。oyghur可能是通过同化作用而变成了uyghur。
当然,我们可以非常严格地理解动词Oy-(挖、压),其中的一种派生形式。oyghur可能是通过同化作用而变成了uyghur。
 据贝尔津版本的该文献所分析,第一种定义有所重复。在拉德洛夫版本(同上,第1卷,第18、19、24页),又把第1种定义译作“联系和提供帮助”,他把第2种定义写作Muvàfaqat,即不是“符合、一致”,而是“帮助”:“他和我们有联系,并且提供帮助和支持”。
据贝尔津版本的该文献所分析,第一种定义有所重复。在拉德洛夫版本(同上,第1卷,第18、19、24页),又把第1种定义译作“联系和提供帮助”,他把第2种定义写作Muvàfaqat,即不是“符合、一致”,而是“帮助”:“他和我们有联系,并且提供帮助和支持”。
 参阅拉德洛夫:《福乐智慧》,第1卷,第2—9页,作者概述了一下先前有关这一问题的著作;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扎记》第229页。
参阅拉德洛夫:《福乐智慧》,第1卷,第2—9页,作者概述了一下先前有关这一问题的著作;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扎记》第229页。
 uya一词也出现在鲁尼文的3块古突厥碑中,其中有两块碑是在叶尼塞河地区发现的,另一块碑出土于突厥斯坦古城怛罗斯(Talas,参阅《古代突厥碑铭》第2卷,第134页,第5行;第3卷,第101页,第3和118行)。据喀什噶里辞典(第1卷,第85页;第3卷,第146页)解释,uya的意思是“亲属”。拉德洛夫的辞典(第1卷,第1628页)又认为uya的意思是“关节”、“世代”。请参阅葛玛丽:《古突厥语语法》,§106。
uya一词也出现在鲁尼文的3块古突厥碑中,其中有两块碑是在叶尼塞河地区发现的,另一块碑出土于突厥斯坦古城怛罗斯(Talas,参阅《古代突厥碑铭》第2卷,第134页,第5行;第3卷,第101页,第3和118行)。据喀什噶里辞典(第1卷,第85页;第3卷,第146页)解释,uya的意思是“亲属”。拉德洛夫的辞典(第1卷,第1628页)又认为uya的意思是“关节”、“世代”。请参阅葛玛丽:《古突厥语语法》,§106。
 uy(a)r一词曾在古突厥的5通鲁尼文墓志铭中出现过7次,其中有4通碑都是在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另一块是在鄂尔浑河流域发现的(《古代突厥碑铭》,第2卷,第122页;第3卷,第96、102、119和180页),从该词出现的前后文来看,大致可以分为3大类:(a)
uy(a)r一词曾在古突厥的5通鲁尼文墓志铭中出现过7次,其中有4通碑都是在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另一块是在鄂尔浑河流域发现的(《古代突厥碑铭》,第2卷,第122页;第3卷,第96、102、119和180页),从该词出现的前后文来看,大致可以分为3大类:(a) lüg uyarlir
lüg uyarlir rmi
rmi :“死者拥有uyar”;(b)inim
:“死者拥有uyar”;(b)inim im(~kada
im(~kada im)uyarinüün:“由于我的弟兄(~同事们)的uyar”,(人们而竖起了这一墓碑);(c)uyar qadinimüüm:“为了我岳父uyar”;uyar
im)uyarinüün:“由于我的弟兄(~同事们)的uyar”,(人们而竖起了这一墓碑);(c)uyar qadinimüüm:“为了我岳父uyar”;uyar simsizim
simsizim ~uyar b
~uyar b gimk
gimk ~uyar qada
~uyar qada imqa adiriltim,“我离开了你们,我的妻子uyar~、我的王爷uyar~、我的同事们uyar”。我还必须指出卡库尔(akul)的5号碑[属于(C)一类]中的uyar与3号碑中的uya的背景完全相同:elig uyamgha adirildim:“我与我的50多位亲属分开了”。
imqa adiriltim,“我离开了你们,我的妻子uyar~、我的王爷uyar~、我的同事们uyar”。我还必须指出卡库尔(akul)的5号碑[属于(C)一类]中的uyar与3号碑中的uya的背景完全相同:elig uyamgha adirildim:“我与我的50多位亲属分开了”。
另外,uyur一词也曾出现在《占卜书》(Irq Bitig)中,这是9—10世纪的一部用突厥鲁尼文所写的小作品,后于敦煌发现。其中的前后文是这样的:“可汗登基之后,便修造了都城。他的国家维持下来了。四方的好人和uyurs,在那里集合起来以娱乐消遣和修饰打扮”。参阅汤姆森(V.Thomsen)于1912年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201和213页的解释;《古代突厥碑铭》第2卷,第80页。
有关uyur/uyar(oyar?)的问题,也请参阅拉德洛夫:《蒙古古突厥碑铭》第256页;W.班格和葛玛丽于《匈牙利年鉴》第8卷,第250页和254页注释中的解释。他们二人所研究过的摩尼教经文残卷中的(uy)urlarnng一例的读法并不太可靠,因为在影印件中,在一个洞的上面有一点,而洞正好打在他们所假设的uy的位置上,这里就使人怀疑原文是否是一个r或q。
 这一名单同样也是由《唐书》(卷217上,第2页)所提供的,有关其中的具体情况,见浦立本:《有关Toquzoghuz问题的简释》,第38—41页;沙畹:《西突厥史料》第93—94页;本人旧作:《五代回鹘史》第3—4页。这一名单中仅有19个氏族,正如浦立本教授在上引著作中所解释的那样,《旧唐书》的编纂者可能把“九姓乌古斯”(Toquz-oghuz,以回鹘人为首的部落联盟)同真正的回鹘人,即十姓回鹘人相混淆了,因为后者实际上是十个部族。
这一名单同样也是由《唐书》(卷217上,第2页)所提供的,有关其中的具体情况,见浦立本:《有关Toquzoghuz问题的简释》,第38—41页;沙畹:《西突厥史料》第93—94页;本人旧作:《五代回鹘史》第3—4页。这一名单中仅有19个氏族,正如浦立本教授在上引著作中所解释的那样,《旧唐书》的编纂者可能把“九姓乌古斯”(Toquz-oghuz,以回鹘人为首的部落联盟)同真正的回鹘人,即十姓回鹘人相混淆了,因为后者实际上是十个部族。
 参阅古罗(RenéGiraud):《巴颜楚克图碑文考释》,1961年巴黎版,第65页,作者解释了暾欲谷(Tonyuquq,Toniyuquq)这一名字,他认为此名是由toni+yuquq组成的,其意思是“衣服沾满污垢的人”。相反,如果应该为药罗葛部的名字(Yaghlaqar)寻找另一辞源,那就可以联想到动词yaghila,由yayi(敌人)派生而来,其意思为“进行敌对活动,打击敌人”。
参阅古罗(RenéGiraud):《巴颜楚克图碑文考释》,1961年巴黎版,第65页,作者解释了暾欲谷(Tonyuquq,Toniyuquq)这一名字,他认为此名是由toni+yuquq组成的,其意思是“衣服沾满污垢的人”。相反,如果应该为药罗葛部的名字(Yaghlaqar)寻找另一辞源,那就可以联想到动词yaghila,由yayi(敌人)派生而来,其意思为“进行敌对活动,打击敌人”。
 参阅葛玛丽:《古突厥语语法》,§161。
参阅葛玛丽:《古突厥语语法》,§161。
 参阅W.B.亨宁于《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报》第9卷,第555页的解释;H.W贝利于《大亚细亚杂志》第2卷,第1期,第19页的解释;浦立本在《有关Toquzoghuz问题的简释》第40页中的解释。
参阅W.B.亨宁于《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报》第9卷,第555页的解释;H.W贝利于《大亚细亚杂志》第2卷,第1期,第19页的解释;浦立本在《有关Toquzoghuz问题的简释》第40页中的解释。
 请参阅F.W.K.米勒:《摩尼教赞美诗一残页》(Mahrn
请参阅F.W.K.米勒:《摩尼教赞美诗一残页》(Mahrn amag),第9、20—21页。有关该可汗的名称,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54页,《唐书》卷221下,第2页。也请大家参阅《唐会要》卷98,第9页;《册府元龟》卷967,第14页;《唐书》卷217下,第1页;《五代回鹘史》第141页。另外,在我上文所研究过的600年左右的铁勒诸部的名单中,曷截(Xazir)也可能是Khazar一名的不规则对音。
amag),第9、20—21页。有关该可汗的名称,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54页,《唐书》卷221下,第2页。也请大家参阅《唐会要》卷98,第9页;《册府元龟》卷967,第14页;《唐书》卷217下,第1页;《五代回鹘史》第141页。另外,在我上文所研究过的600年左右的铁勒诸部的名单中,曷截(Xazir)也可能是Khazar一名的不规则对音。
 有关可萨突厥人的最后一种对音形式,请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56页;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扎记》第207—208页。伯希和长篇大论地研究了Khazar一名,并在其名作第208页注中写道:“唯有一次出现过‘曷萨’,我怀疑那可能是‘葛萨’之讹误。然而,‘曷萨’这种形式还曾在一位回鹘可汗的名字中出现过,伯希和在其文第209页中的解释就不屑一顾了。据他认为:“唐代汉语中的这两个对音字是以Qasar,而不是根据Qazar为基础的”。另外,在研究Khazar这一名词的时候,伯希和曾特别卖力地企图抛开-z-这一音节,因为对于那些坚持认为古突厥语中颤音化理论的人来说,这一音节特别碍事。按照这些人的理论来分析,可萨突厥人即古代的不里阿耳人。当然on-oghur在普遍突厥语中就是以r代替了z。然而,我对于伯希和的作法却持怀疑态度。他企图由qa
有关可萨突厥人的最后一种对音形式,请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56页;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扎记》第207—208页。伯希和长篇大论地研究了Khazar一名,并在其名作第208页注中写道:“唯有一次出现过‘曷萨’,我怀疑那可能是‘葛萨’之讹误。然而,‘曷萨’这种形式还曾在一位回鹘可汗的名字中出现过,伯希和在其文第209页中的解释就不屑一顾了。据他认为:“唐代汉语中的这两个对音字是以Qasar,而不是根据Qazar为基础的”。另外,在研究Khazar这一名词的时候,伯希和曾特别卖力地企图抛开-z-这一音节,因为对于那些坚持认为古突厥语中颤音化理论的人来说,这一音节特别碍事。按照这些人的理论来分析,可萨突厥人即古代的不里阿耳人。当然on-oghur在普遍突厥语中就是以r代替了z。然而,我对于伯希和的作法却持怀疑态度。他企图由qa c-(逃走)演变出Qazar和Qazaq来,其办法是通过一种令人质疑的古老方言qas-,它可能没有qaz-那样重要。
c-(逃走)演变出Qazar和Qazaq来,其办法是通过一种令人质疑的古老方言qas-,它可能没有qaz-那样重要。
 参阅兰司铁:《在北蒙古发现的两块回鹘鲁尼文碑》,第23和53页。
参阅兰司铁:《在北蒙古发现的两块回鹘鲁尼文碑》,第23和53页。
 参阅葛玛丽:《古突厥语语法》§5、35。
参阅葛玛丽:《古突厥语语法》§5、35。
 参阅《五代回鹘史》第4页。
参阅《五代回鹘史》第4页。
 有关这些名称,见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扎记》,第195—197页。然而,伯希和却对此作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
有关这些名称,见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扎记》,第195—197页。然而,伯希和却对此作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
 参阅阙特勤碑,北侧第3行,汤姆森在《鄂尔浑河流域碑铭解读》注释52中就已经指出了I譓gil与Izgil之间的相似性。
参阅阙特勤碑,北侧第3行,汤姆森在《鄂尔浑河流域碑铭解读》注释52中就已经指出了I譓gil与Izgil之间的相似性。
 《旧唐书》中的这段文献已由沙畹翻译发表在《西突厥史料》第91页中,他认为《唐书》中“
《旧唐书》中的这段文献已由沙畹翻译发表在《西突厥史料》第91页中,他认为《唐书》中“ 结”的写法比“跌结”要更为妥善一些。我们通过用“
结”的写法比“跌结”要更为妥善一些。我们通过用“ 跌”来转写I缔造/Ädiz的作法而看到“
跌”来转写I缔造/Ädiz的作法而看到“ 结”是izgil的最佳对音。
结”是izgil的最佳对音。
 参阅马夸特:《东欧东亚漫游记》,第162和515页以下;米诺尔斯基:《世界疆域志》,第162、320和461页。
参阅马夸特:《东欧东亚漫游记》,第162和515页以下;米诺尔斯基:《世界疆域志》,第162、320和461页。
 莫拉夫斯季科:《十姓回鹘人的历史》,第67—74页;《拜占庭突厥资料汇编》,第2卷,Onoghundur一条目。
莫拉夫斯季科:《十姓回鹘人的历史》,第67—74页;《拜占庭突厥资料汇编》,第2卷,Onoghundur一条目。
 参阅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第162和465—471页。有关这些明显已被讹传的字,我不知道是否应考虑为On-oghundur的缩写形式-Onundur,或者又可能是ōghundur或On-Oghundur的一种误写。
参阅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第162和465—471页。有关这些明显已被讹传的字,我不知道是否应考虑为On-oghundur的缩写形式-Onundur,或者又可能是ōghundur或On-Oghundur的一种误写。
 有关Bayundur和Cavuldur的问题,请参阅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扎记》第194—197页;有关Zaβender,请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48页。
有关Bayundur和Cavuldur的问题,请参阅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扎记》第194—197页;有关Zaβender,请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48页。
 有关从795年的可汗时代起,在回鹘人中建立阿跌小王朝的问题,请参阅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之研究》,第170、194—199、266页以下。
有关从795年的可汗时代起,在回鹘人中建立阿跌小王朝的问题,请参阅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之研究》,第170、194—199、266页以下。
 参阅贝尔津:同上引书,第7卷,第161页注释。
参阅贝尔津:同上引书,第7卷,第161页注释。
 有关在
有关在 diz和Aβar诸名之间转写词的混淆问题,请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第88页注释,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3卷,第291—292页;刘茂才:《关于东突厥史的汉文资料》,第2卷,第527页。
diz和Aβar诸名之间转写词的混淆问题,请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第88页注释,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3卷,第291—292页;刘茂才:《关于东突厥史的汉文资料》,第2卷,第527页。
 志费尼(Juwaini)自称其原始史料是蒙古人时代对在鄂尔浑河流域回鹘古都发现的一块碑(可能系指喀喇巴勒哈逊碑)的解读,而且还认为Q(a)mlan
志费尼(Juwaini)自称其原始史料是蒙古人时代对在鄂尔浑河流域回鹘古都发现的一块碑(可能系指喀喇巴勒哈逊碑)的解读,而且还认为Q(a)mlan u是一个地名,位于独乐永与色楞格河的汇合处(?),回鹘人传奇中的仆固汗(Buqukhan)就是于那里在一团树根中诞生的。参阅:《论库蛮人的民族特征》,第59—60页;波依勒(John AndrewBoyle):《论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第55页。
u是一个地名,位于独乐永与色楞格河的汇合处(?),回鹘人传奇中的仆固汗(Buqukhan)就是于那里在一团树根中诞生的。参阅:《论库蛮人的民族特征》,第59—60页;波依勒(John AndrewBoyle):《论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第55页。
 有关这一名称,也请参阅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之研究》,第195页,作者建议重新转写阿跌可汗的名称,因为从795年起,阿跌可汗就位居回鹘人之首了。
有关这一名称,也请参阅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之研究》,第195页,作者建议重新转写阿跌可汗的名称,因为从795年起,阿跌可汗就位居回鹘人之首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